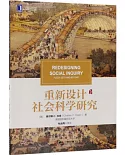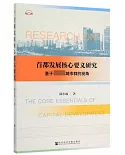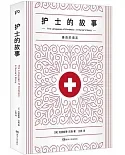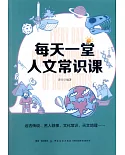考據學進入20世紀,隨著社會風潮的動盪經歷了幾度沉浮,也發生了重大的革新。最顯著的,就是二重證據法和三重證據法的實踐。
王國維的研究,是考據學發生歷史性進步的標志。他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就是以地下實物資料和歷史文獻資料互相印證的方法,對近代學術的進步有重要的影響。本書收錄孫機教授、楊泓教授等先生的文章就是運用這樣的研究方法推進考據學發展的實例。有了「二重證據法」,又有學者提出了「三重證據法」。葉舒憲和他的學術同志蕭兵教授被收入本書的文章,就是這種「三重證據法」研究的收獲。
本書同時還選編其他眾多著名學者考據學成就的文章,選擇一些生活史和文化史題材之外的考據經典,重在發掘和體味考據過程眾多興趣,還有他們關於生態史研究,性別史研究等方面的心得。
目錄
神桑:生命樹與哭喪棒
桃和鬼
三足烏
女兒國的來歷
西王母和東王公的類似故事
”公”概念的祭典起源
跳出《周易》看〈周易〉
《周易》中的古歌
迷幻藥與生命樹
古代房中術的用藥
吐沫
減食致壽
”三十六”與”七十二”的由來
說早期地圖的方向
惜字律二種
南人與北人
釋奴才
”有朋自遠方來”解讀
語錄考
吹牛考
秦漢人的罵詈語言
屁與詩文
屁與石子文
桃和鬼
三足烏
女兒國的來歷
西王母和東王公的類似故事
”公”概念的祭典起源
跳出《周易》看〈周易〉
《周易》中的古歌
迷幻藥與生命樹
古代房中術的用藥
吐沫
減食致壽
”三十六”與”七十二”的由來
說早期地圖的方向
惜字律二種
南人與北人
釋奴才
”有朋自遠方來”解讀
語錄考
吹牛考
秦漢人的罵詈語言
屁與詩文
屁與石子文
序
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趣味考據》面世以後,受到一些讀者的歡迎。趙世瑜先生著文《趣味與考據及圖與文》(《博覽群書》2004年4期),予以鼓勵。趙文還寫道:
「期待王子今教授再續編一本《趣味考據》,選擇一些生活史和文化史題材以外的考據經典,重在發掘和體味考據過程中的興趣,其實也是蠻不錯的。」趙世瑜先生對我們提出的要求比較高,現在擺在朋友們面前的這本書,就是「續編」的《趣味考據》,不過沒有完全實現趙世瑜先生的期望。
考據學進入20世紀,隨著社會風潮的動盪經歷了幾度沉浮,也發生了重大的革新。最顯著的,就是二重證據法和三重證據法的實踐。
王國維的研究,是考據學發生歷史性進步的標志。他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就是以地下實物資料和歷史文獻資料互相印證的方法,對近代學術的進步有重要的影響。
1925年,王國維在清華國學研究院設《古史新證》演講課。在《古史新證》講義第一章《總論》中,王國維提出了著名的古史研究「二重證據法」。他說:「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王國維:《古史新證》,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王國維運用「地下之新材料」與古文獻記載相印證, 以探索古代歷史文化的真實面貌,形成了一種公認科學可靠的學術正流。直到今天,沒有什麽人能夠否定這種研究方法的科學性。王國維的學術榜樣,對於此後的史學研究產生了極重要的影響。1934年,陳寅恪曾經概括王國維等人所倡起的新的學術風格的特征:「一日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日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日取外來之觀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他認為,這一進步,「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頁)。「地下之實物」、「異族之故書」以及「外來之觀念」得到重視並加以利用,體現出20世紀的中國學術對於18世紀、19世紀的歷史性超越。陳氏「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的說法,是對於包括考據學在內的歷史文化研究利用考古學資料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的總結與肯定。
本書所收錄孫機教授、楊泓教授等先生的文章,就是運用這樣的研究方法推進考據學發展的實例。
有了「二重證據法」,又有學者提出「三重證據法」。對於所謂「三重證據法」,有兩種不同的說法。李學勤在一次關於「走出疑古時代」的發言中,談到「兩種考古證據」。他說: 「王靜安先生是講『二重證據法』 ,最近聽說香港饒宗頤先生寫了文章,提出『三重證據法』 ,把考古材料又分為兩部分。這第三重證據就是考古發現的古文字資料。如果說一般的考古資料和古文字資料可以分開,那麽後者就是第三重證據。像楚簡就是第三類。考古學的發現基本上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有字的,一種是沒字的。有字的這一類,它所負載的信息當然就更豐富。有字的東西和挖出來的一般東西不大相同, 當然也可以作為另外的一類。」考古發現的沒有字的東西,對於精神文化的某一方面,甚至於對古書的研究也很有用。 「當然,今天更重要的東西還是帶文字的東西。帶文字的發現,即第三重證據,是更重要的,它的影響當然特別大。王靜安先生講近代以來有幾次大的發現,都是帶文字的材料。」 「王靜安先生說, 中國歷代發現的新學問都是由於有新的發現。他舉的例子很多,最重要的是漢代的孔壁中經和西晉的汲冢竹書,都是地地道道的古書。這些古書發現之後,對於中國文化和學術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這種作用到今天還能看到。」(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修訂本),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頁)
有的學者提出過另一種「三重證據法」,即在運用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同時,再加上「文化人類學」的資料與方法的運用。葉舒憲最早較為明確地提出了這一觀點。他還指出, 「超越二重證據的研究實踐在建國以前的學術界已經積累了一大筆豐碩成果。」一些歷史文獻研究學者的學術成就實際上在這一方向已經踏出了新路。葉舒憲說,「假如把王氏的《觀堂集林》同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稍加對照,從『二重』到『三重』的演進軌跡也就一目了然了。」郭沫若在這部書的《序錄》中所列出的14種主要參考書中,「除前9種為甲金文專著外,後5種卻都是域外著作,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葉列妙士的《古代東方精神文化綱要》、威德訥爾的《巴比倫天文學概覽》第1卷等。這些外文文獻說明郭沫若已在嘗試某種跨文化的人類學研究思路,而他所倚重的恩格斯的著作本身就是人類學史的經典文獻。可以說從『二重證據』到『三重證據』的演進在某種程度上正是考據學、甲骨學同人類學相溝通、相結合的結果。」其他在這一研究方向上成就突出的名家名作,葉舒憲又舉出聞一多的《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等。「從神話學出發研究古史,有衛聚賢《古文研究》(1936)、李玄伯《中國古代社會新研》(1939)、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1943)等著作問世,從神話學出發研究文學則以聞一多的《神話與詩》和鄭振鐸《湯禱篇》最為突出。所有這些嘗試,就其方法論意義而言,就在於將民俗和神話材料提高到足以同經史文獻和地下材料並重的高度,獲得三重論證的考據學新格局。」魯迅1926年在中山大學講中國文學史的講義中的一段話「在昔原始之民,其居群中,蓋惟以姿態聲音, 自達其情意而已。聲音繁變,浸成言辭,言辭諧美,乃兆歌詠。時屬草昧,庶民淳朴,心志郁於內,則任情而歌呼,天地變於外,、則祗畏以頌祝,踴躍吟嘆, 時越儕輩,為眾所賞,默識不忘, 口耳相傳,或逮後世。復有巫覡,職在通神,盛為歌舞,以祈靈貺,而贊頌之在人群,其用乃愈益廣大。試察今之蠻民。雖狀極狂榛,未有衣服宮室文字,而頌神抒情之什,降靈召鬼之人,大抵有焉。呂不韋雲,『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鄭玄則謂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 (《詩譜序》)。雖荒古無文,並難征信,而證以今日之野人,揆之人間之心理,固當以呂氏所言,為較近於事理矣。」(魯迅:《漢文學史綱要》,《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年版,第9卷第343頁)葉舒憲亦解釋為「運用了關於原始社會方面的第三重證據去分析和解決古書上聚訟不清的問題——詩之起源」,「魯迅的這一辨析雖嫌簡略了一些,但他的論證方式卻已超出了考據學的封閉視野,多少具有了人類學的性質,其意義和影響均不容低估。」在魯迅發表這一看法16年之後,朱光潛又提出了融貫中西的詩歌發生論,他批評了「以為在最古的書籍里尋出幾首詩歌,就算尋出詩的起源了」的思路,指出,荷馬史詩是希臘最早記錄下的詩,其原始程度卻不如非洲土著的歌謠,「所以我們研究詩的起源,與其拿荷馬史詩或《商頌》《周頌》作根據,倒不如拿現代未開化民族┅┅的歌謠作根據」(朱光潛:《詩論》,重慶國民圖書出版社1942年版,三聯書店 1984年版,第2—4頁)。葉舒憲提出,國學的進步,應當「借鑒我們自己傳統中缺如的世界性通觀視野和人類學方法」。他確信,「把本國本民族的東西放置在人類文化的總格局中加以探討,這將是順應時代發展趨勢的一種融通中西學術的有效途徑。」(葉舒憲:《人類學「三重證據法」與考據學的更新》,錄自《詩經的文化闡釋》,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頁)考據學的新成就,也體現於在這一學術路徑上的進步。
葉舒憲和他的學術同志蕭兵教授被收入本書的文章,就是這種「三重證據法」研究的收獲。
本書選編的文章,與前一本比較,收納的范圍可能更寬一些。學者有關生態史研究、性別史研究的心得也有采擷,是考慮到運用傳統的考據學方法,從新的學術視角進行的探索,或許會給讀者以有益的啟示。趙世瑜先生建議續編《趣味考據》收入「顧頡剛對大禹原型的考據」, 「陳垣對多種宗教的考據、後代學者對雍正即位問題的考據、對『玄武門之變』的考據、對沈萬三史事的考據等等」,因為各種原因,也沒有實現。也許還有機會,我們今後會和朋友們一起,重溫顧頡剛、陳垣等前輩學者的考據學成就。
考據學進入20世紀,隨著社會風潮的動盪經歷了幾度沉浮,也發生了重大的革新。最顯著的,就是二重證據法和三重證據法的實踐。
王國維的研究,是考據學發生歷史性進步的標志。他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就是以地下實物資料和歷史文獻資料互相印證的方法,對近代學術的進步有重要的影響。
1925年,王國維在清華國學研究院設《古史新證》演講課。在《古史新證》講義第一章《總論》中,王國維提出了著名的古史研究「二重證據法」。他說:「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王國維:《古史新證》,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王國維運用「地下之新材料」與古文獻記載相印證, 以探索古代歷史文化的真實面貌,形成了一種公認科學可靠的學術正流。直到今天,沒有什麽人能夠否定這種研究方法的科學性。王國維的學術榜樣,對於此後的史學研究產生了極重要的影響。1934年,陳寅恪曾經概括王國維等人所倡起的新的學術風格的特征:「一日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日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日取外來之觀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他認為,這一進步,「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頁)。「地下之實物」、「異族之故書」以及「外來之觀念」得到重視並加以利用,體現出20世紀的中國學術對於18世紀、19世紀的歷史性超越。陳氏「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的說法,是對於包括考據學在內的歷史文化研究利用考古學資料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的總結與肯定。
本書所收錄孫機教授、楊泓教授等先生的文章,就是運用這樣的研究方法推進考據學發展的實例。
有了「二重證據法」,又有學者提出「三重證據法」。對於所謂「三重證據法」,有兩種不同的說法。李學勤在一次關於「走出疑古時代」的發言中,談到「兩種考古證據」。他說: 「王靜安先生是講『二重證據法』 ,最近聽說香港饒宗頤先生寫了文章,提出『三重證據法』 ,把考古材料又分為兩部分。這第三重證據就是考古發現的古文字資料。如果說一般的考古資料和古文字資料可以分開,那麽後者就是第三重證據。像楚簡就是第三類。考古學的發現基本上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有字的,一種是沒字的。有字的這一類,它所負載的信息當然就更豐富。有字的東西和挖出來的一般東西不大相同, 當然也可以作為另外的一類。」考古發現的沒有字的東西,對於精神文化的某一方面,甚至於對古書的研究也很有用。 「當然,今天更重要的東西還是帶文字的東西。帶文字的發現,即第三重證據,是更重要的,它的影響當然特別大。王靜安先生講近代以來有幾次大的發現,都是帶文字的材料。」 「王靜安先生說, 中國歷代發現的新學問都是由於有新的發現。他舉的例子很多,最重要的是漢代的孔壁中經和西晉的汲冢竹書,都是地地道道的古書。這些古書發現之後,對於中國文化和學術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這種作用到今天還能看到。」(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修訂本),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頁)
有的學者提出過另一種「三重證據法」,即在運用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同時,再加上「文化人類學」的資料與方法的運用。葉舒憲最早較為明確地提出了這一觀點。他還指出, 「超越二重證據的研究實踐在建國以前的學術界已經積累了一大筆豐碩成果。」一些歷史文獻研究學者的學術成就實際上在這一方向已經踏出了新路。葉舒憲說,「假如把王氏的《觀堂集林》同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稍加對照,從『二重』到『三重』的演進軌跡也就一目了然了。」郭沫若在這部書的《序錄》中所列出的14種主要參考書中,「除前9種為甲金文專著外,後5種卻都是域外著作,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葉列妙士的《古代東方精神文化綱要》、威德訥爾的《巴比倫天文學概覽》第1卷等。這些外文文獻說明郭沫若已在嘗試某種跨文化的人類學研究思路,而他所倚重的恩格斯的著作本身就是人類學史的經典文獻。可以說從『二重證據』到『三重證據』的演進在某種程度上正是考據學、甲骨學同人類學相溝通、相結合的結果。」其他在這一研究方向上成就突出的名家名作,葉舒憲又舉出聞一多的《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等。「從神話學出發研究古史,有衛聚賢《古文研究》(1936)、李玄伯《中國古代社會新研》(1939)、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1943)等著作問世,從神話學出發研究文學則以聞一多的《神話與詩》和鄭振鐸《湯禱篇》最為突出。所有這些嘗試,就其方法論意義而言,就在於將民俗和神話材料提高到足以同經史文獻和地下材料並重的高度,獲得三重論證的考據學新格局。」魯迅1926年在中山大學講中國文學史的講義中的一段話「在昔原始之民,其居群中,蓋惟以姿態聲音, 自達其情意而已。聲音繁變,浸成言辭,言辭諧美,乃兆歌詠。時屬草昧,庶民淳朴,心志郁於內,則任情而歌呼,天地變於外,、則祗畏以頌祝,踴躍吟嘆, 時越儕輩,為眾所賞,默識不忘, 口耳相傳,或逮後世。復有巫覡,職在通神,盛為歌舞,以祈靈貺,而贊頌之在人群,其用乃愈益廣大。試察今之蠻民。雖狀極狂榛,未有衣服宮室文字,而頌神抒情之什,降靈召鬼之人,大抵有焉。呂不韋雲,『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鄭玄則謂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 (《詩譜序》)。雖荒古無文,並難征信,而證以今日之野人,揆之人間之心理,固當以呂氏所言,為較近於事理矣。」(魯迅:《漢文學史綱要》,《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年版,第9卷第343頁)葉舒憲亦解釋為「運用了關於原始社會方面的第三重證據去分析和解決古書上聚訟不清的問題——詩之起源」,「魯迅的這一辨析雖嫌簡略了一些,但他的論證方式卻已超出了考據學的封閉視野,多少具有了人類學的性質,其意義和影響均不容低估。」在魯迅發表這一看法16年之後,朱光潛又提出了融貫中西的詩歌發生論,他批評了「以為在最古的書籍里尋出幾首詩歌,就算尋出詩的起源了」的思路,指出,荷馬史詩是希臘最早記錄下的詩,其原始程度卻不如非洲土著的歌謠,「所以我們研究詩的起源,與其拿荷馬史詩或《商頌》《周頌》作根據,倒不如拿現代未開化民族┅┅的歌謠作根據」(朱光潛:《詩論》,重慶國民圖書出版社1942年版,三聯書店 1984年版,第2—4頁)。葉舒憲提出,國學的進步,應當「借鑒我們自己傳統中缺如的世界性通觀視野和人類學方法」。他確信,「把本國本民族的東西放置在人類文化的總格局中加以探討,這將是順應時代發展趨勢的一種融通中西學術的有效途徑。」(葉舒憲:《人類學「三重證據法」與考據學的更新》,錄自《詩經的文化闡釋》,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頁)考據學的新成就,也體現於在這一學術路徑上的進步。
葉舒憲和他的學術同志蕭兵教授被收入本書的文章,就是這種「三重證據法」研究的收獲。
本書選編的文章,與前一本比較,收納的范圍可能更寬一些。學者有關生態史研究、性別史研究的心得也有采擷,是考慮到運用傳統的考據學方法,從新的學術視角進行的探索,或許會給讀者以有益的啟示。趙世瑜先生建議續編《趣味考據》收入「顧頡剛對大禹原型的考據」, 「陳垣對多種宗教的考據、後代學者對雍正即位問題的考據、對『玄武門之變』的考據、對沈萬三史事的考據等等」,因為各種原因,也沒有實現。也許還有機會,我們今後會和朋友們一起,重溫顧頡剛、陳垣等前輩學者的考據學成就。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7折$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