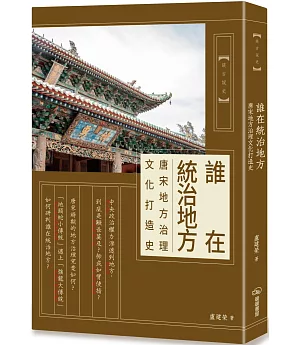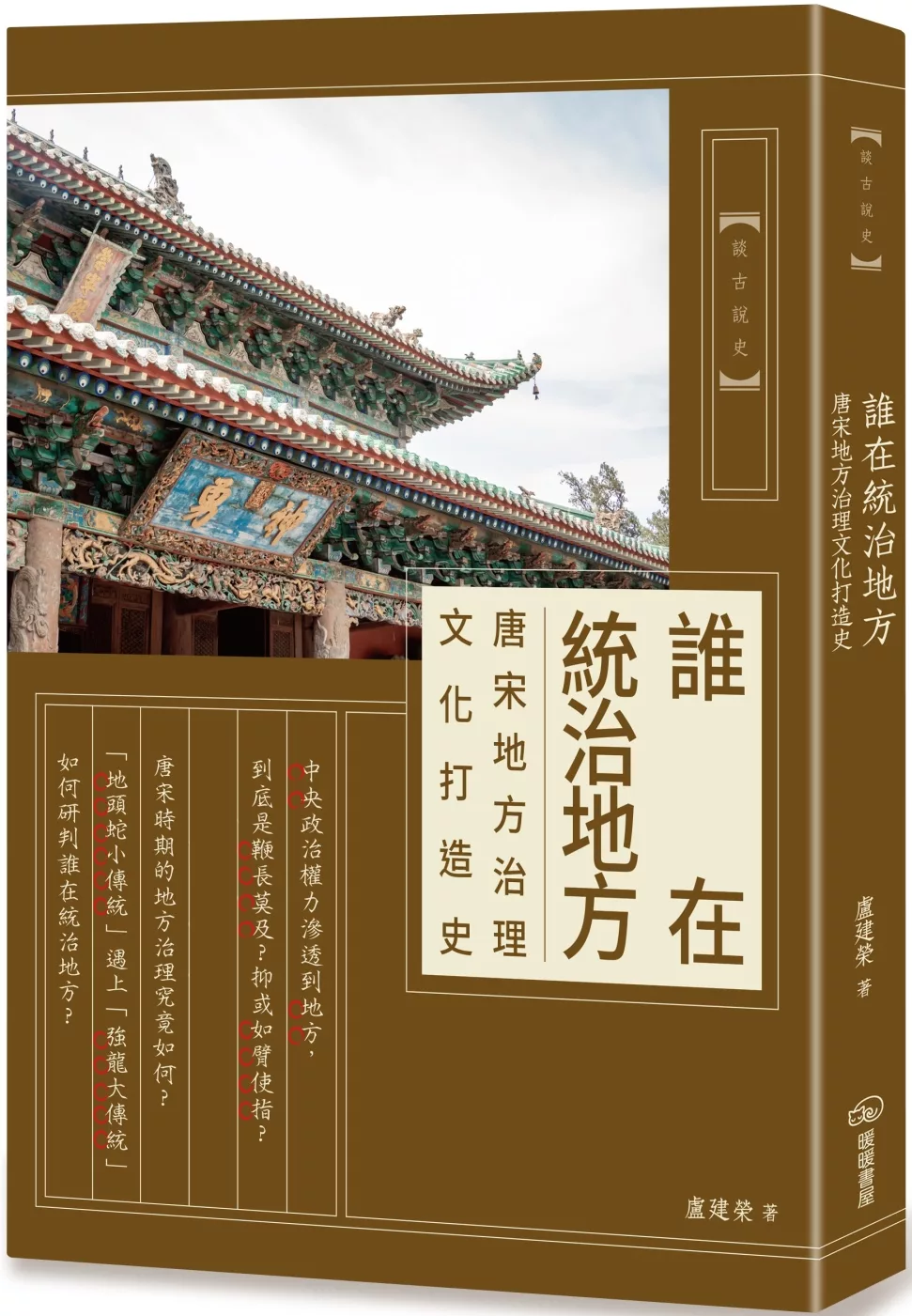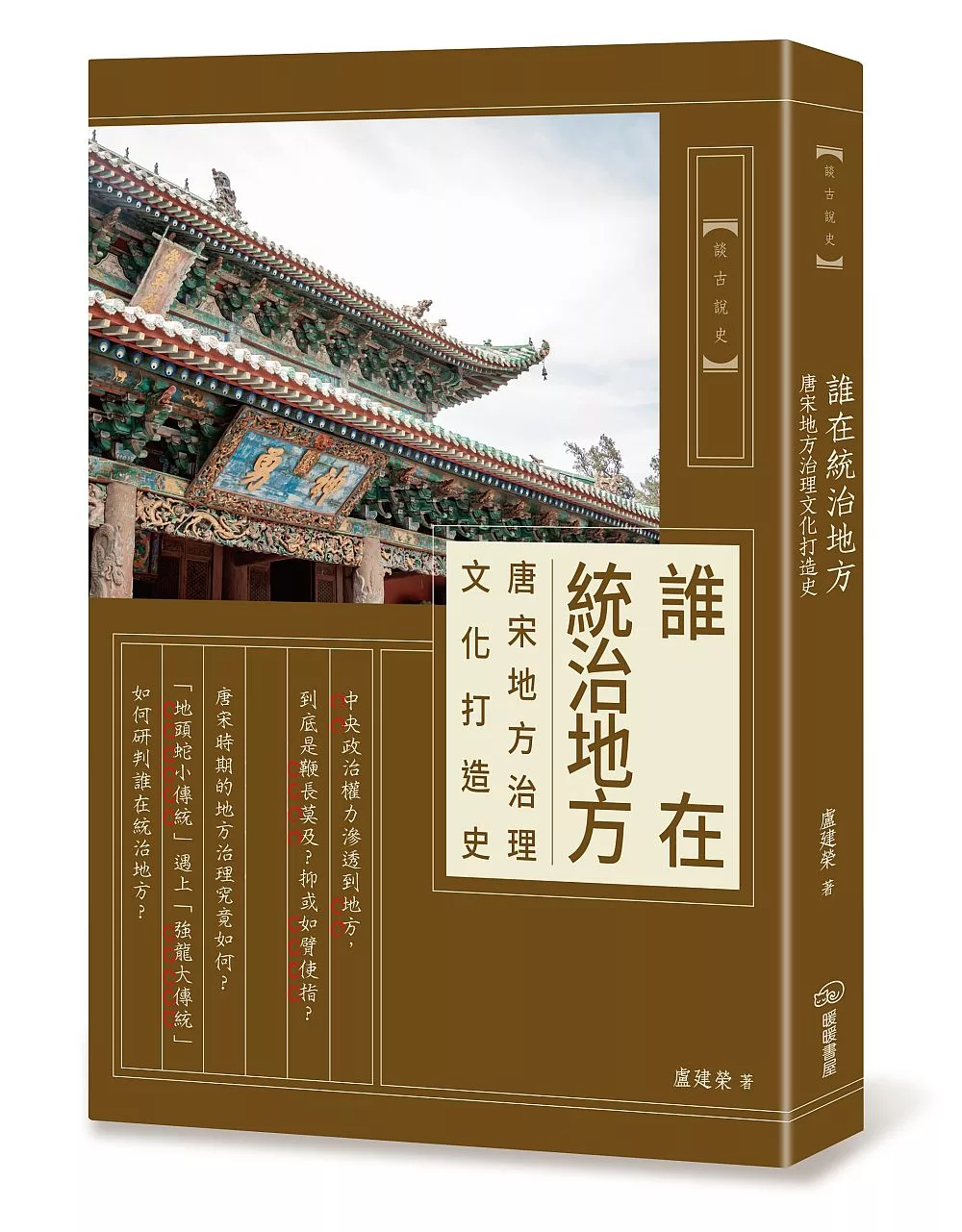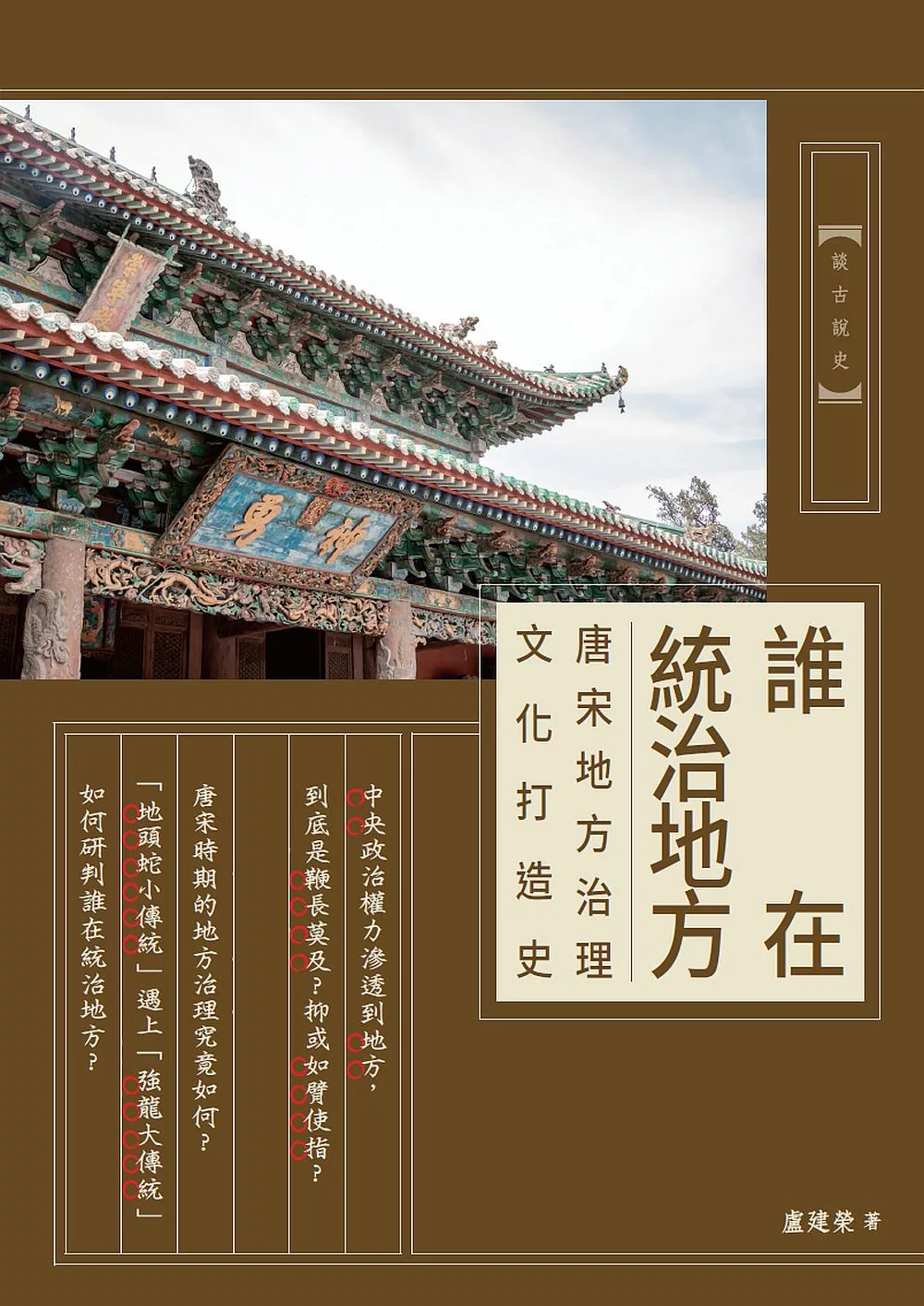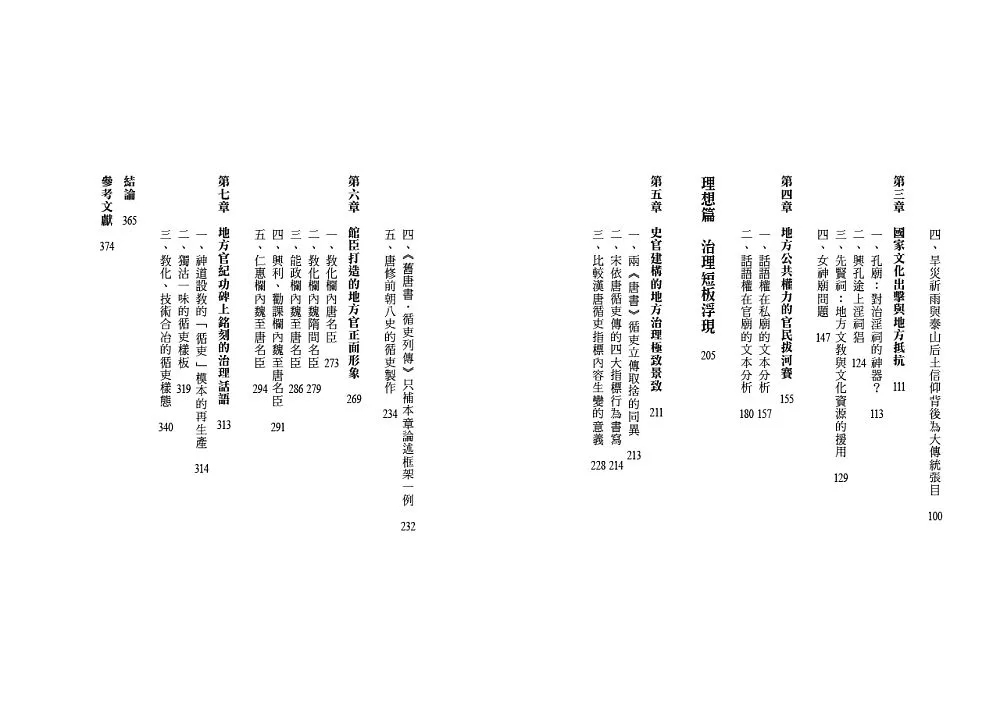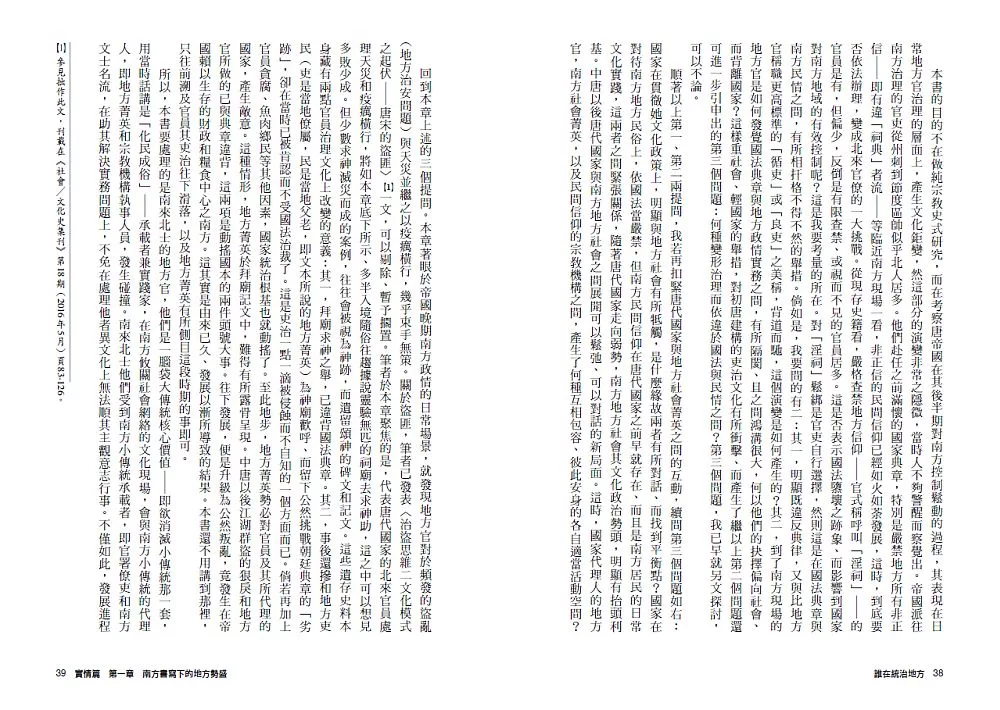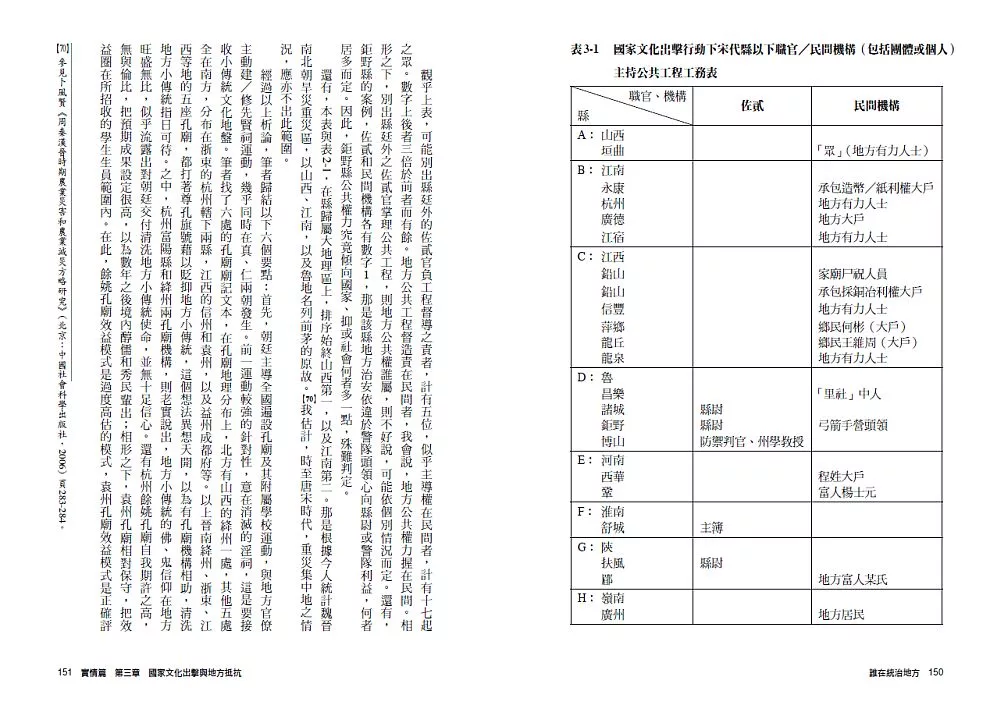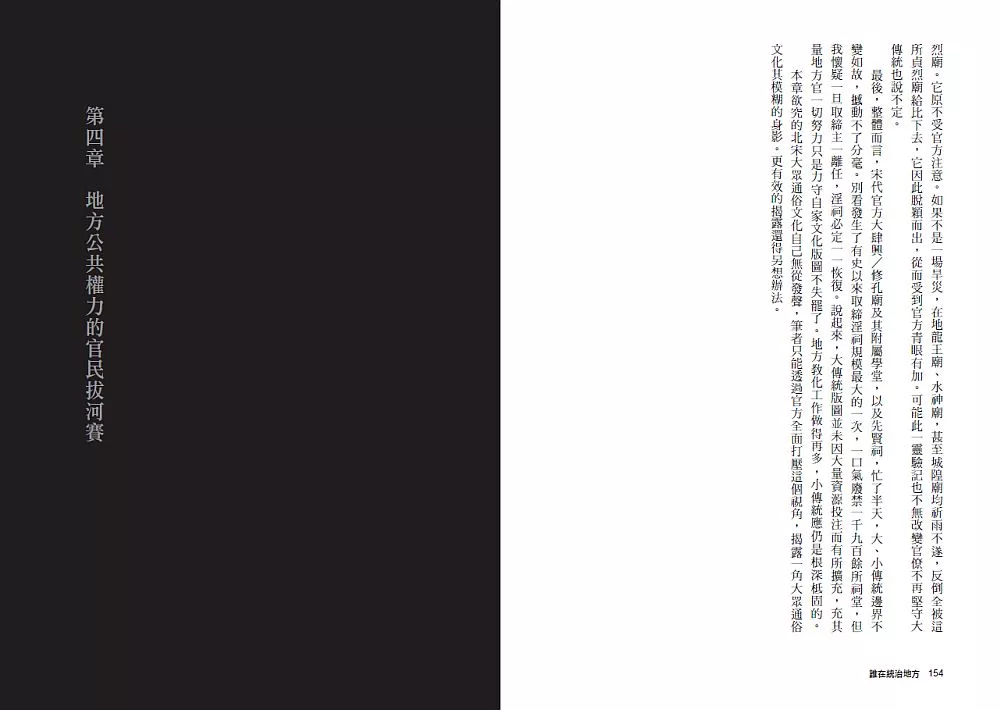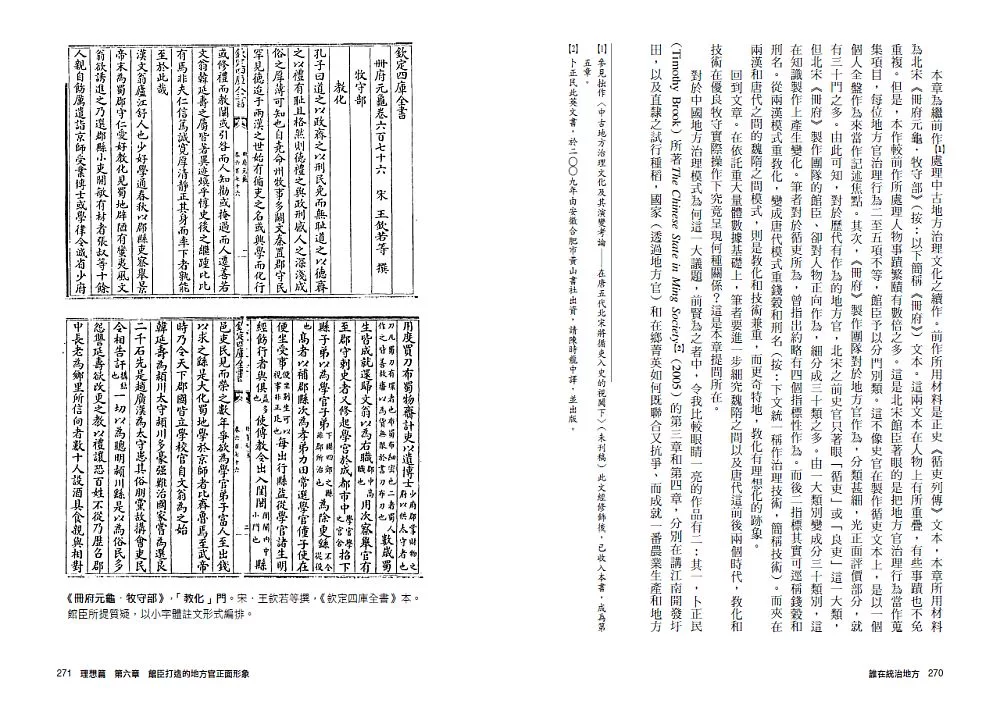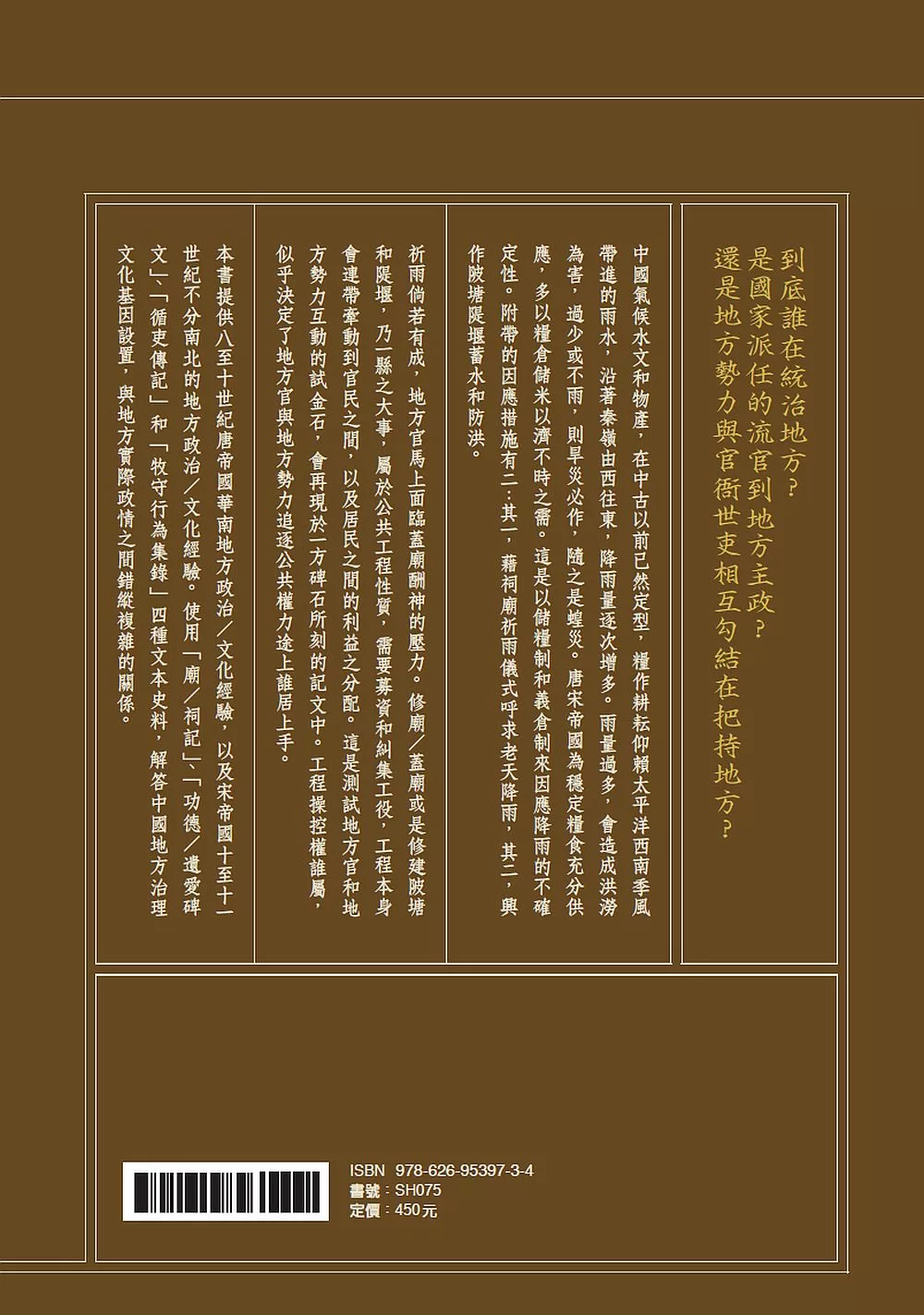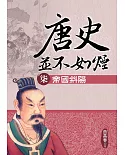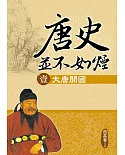代自序
托克維爾半路殺出
一
二十世紀六○至七○年代,美國漢學界在處理中國文化議題上,是聚焦在儒家上面,它有個前提假設:就是儒家即令不足代表中國文化全體,但起碼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先是在芮沃壽(Arthor
Wright)領軍下編出了好幾本論文集。這是以思想史思維在做中國上層文化史。同時,又有以社會史思維在做中國下層社會,或至少是地方菁英政治/文化史。這方面的成就代表有蕭公權和張仲禮師徒,分別推出了《中國鄉村》和《中國紳士》這兩本先驅之作。以上各書在台灣皆以盜版方式出現在書市,多少彌補了當時高教接軌國際的需求。
我在六○年代末和七○年代中,即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七年的大學本科生和碩士生階段,同時受這兩股學風之影響。當時因性近思想史關係,比較傾向芮沃壽及其繼任者主編儒家研究各集。彼時,我致力於魏晉和明清思想的探究。迨離開母校──台灣師範大學──我讀到低我五班的黃克武碩論,作的是清代經世思想的研究,這讓我對美國近二十年儒家研究業績,一種比較傾向教化倫理範疇的物事,有了強烈的對照。原來晚明和清中葉編輯的兩套《經世文編》,展示了儒家人物中有人警覺地把其短板的技術範疇物事,做了適時調整和強調。黃克武所為,與先前美國漢學界的儒家研究,有了強烈反差的對照。一九八一年我入職中研院史語所,研究重心從思想史調到社會史,我就把以上思想史界的兩派研究路徑予以擱置。沒想到這一耽擱一晃眼便三十多年!
二
二○一七年至二○一八年,我指導一位博士生作明代地方官的居官和宦遊生活這一議題。因為黃克武是主考官之一,我有幸與他共聚一堂討論明代地方政治。我因曾讀翁文灝先生著書談到中國古代衙署內部陳設,故爾特別指示博士生關注衙署圖材料。由圖樣知,衙署住宅內部結構中,主要有知縣、丞、主簿宅舍,還有雜吏如典史、胥吏等的房舍,這不稀奇,比較引我注意的,是知縣獨立書房的退思堂或思政堂這一建物。我因做宋.曾鞏從政、試圖走第三條路的研究
,知曉曾氏寫有〈退思堂記〉,從此由宋至明清,莫不有〈退思堂記〉這一文類(genre)大量存在。這一文類所蘊藏訊息,究與地方政情有何關涉?是我要博士生特別關注所在。我閱讀大量〈退思堂記〉文本後,比較傾向這些是官樣文章,講的是冠冕堂皇,但衡諸地方政治實情,恐怕猶有一間。博士答辯會場合中,連兩年我都與在座明清專家,包括黃克武在內,有所爭鋒相對。他們比較傾向〈退思堂記〉是明代地方政治的若干面向的反映。在兩次博士論文答辯會中,我的看法並未充分說明。畢竟學生和考官才是此會的主角,我身為指導教授只能多聆聽專家意見。儘管該博士生最後順利取得學位,但在我,這個中國地方政治/文化的問題,仍未結束,這引領我從此多關注這一議題。
三
事實上,這議題在二○一一年早就因故有所發酵,二○一二年我收到中國人民大學楊念群教授寄給我他所主編《新史學》第五卷(北京:中華,2011年11月),內有他及其學生胡垣所寫,關於清代地方治理問題兩文。楊寫的是乾隆與疆吏之間通訊搜討吏治之道。胡寫的是雍正時縣佐雜官別出縣廷,與知縣分轄地方,因而主張皇權下縣始於雍正,而非杜贊奇所說,要到清末新政始然。在此,胡強調了從中唐始設的巡檢司之功能。為此,我去信楊教授有所討論。我記得主要講兩點;其一,皇帝的諭旨和疆吏的奏書是規範性史料,不能據以充分體現地方實情,其二,巡檢司從設置以來,對治盜即不彰,在此,制度性史料及效益如何,理應予以檢核,不能說只要有所設置,便證明效益良好。
針對胡原文,我於二○一六年有所回應。我發表〈治盜思維二文化模式之起伏:唐宋的盜匪〉《社會/文化史集刊》第18期(2016年5月)頁83-126。在文中,我指出,由唐入宋,巡檢司其功能多不彰。亦即,我輩研究者不能只拘泥於單方面的制度面,要能一併反思制度的對治面,即盜匪,以及雙方互動這個面向來。針對楊念群研究依傍諭旨和奏書這種規範性史料,我還要多思索幾年,才提出對策。
四
針對楊念群文意見的更落實方案,我要到二○二○年七月想到,使用祠/廟記文、德政/遺愛碑文,以及史官《循吏列傳》,以及館臣大套書中的牧守正面行動書寫文等,來加以解答中國地方治理文化基因設置,與地方實際政情之間錯縱複雜的關係。
我從二○二○年七月,託請卜元鼎兄寄來黃永年寫唐.狄仁傑取締淫祠一文,等如正式進入詳細與楊念群教授對話的階段。這番對話基本上花費兩個夏天(即2020至2021),大體完成本書的寫作。比較兩個不同研究路徑,在我集中在唐宋地方治理所累積的文化資源,在楊念群、胡垣,以及黃克武等,他們是集中在清代的地方治理實務研究。幸而在學術資源上,我有黃宗智和杜贊奇兩教授清末民國的地方治理實務研究業績,可以當作參考座標。就這樣,我做的是唐宋中央集權制下的地方控制,所呈現的似乎只到縣這一層級,縣以下幾乎是地方勢力的天下。這一唐宋模式降及清季之前,理應不出此模式。相形之下,黃宗智和杜贊奇無獨有偶,均發現此一模式到清末新政(按:約從1907至1911年)才有了突破口,中央政治權力首度滲透到縣以下的鄉村社會。這就呼應了一九六○至一九七○年代蕭公權和張仲禮師徒所研究的鄉村社會實情了。然而,黃、杜的觀點,到了二○一一年十一月,遭到楊念群和胡垣師徒的修正,說皇權下到縣,早在雍正時期,即已開始。中國中央集權制與地方自治是以縣以下作為疆界線,究竟從何時起才開始被中央政府所突破?是由清季新政發韌、再降及北洋、國民政府呢?抑提前在雍正時從事吏治改革之時?目前遺下爭議,有待更多的地方治理史研究個案,才能更準確地說分明。
五
同時,漫長的從秦漢至清季(即西元前三世紀初至十九世紀結束),長達二千一百餘年,光只有盧建榮所究中唐至北宋末(從西元760-1200年)這四百四十年個案,仍是太單薄,還要更多人投入,才能更具體知曉這二千一百年皇權不下縣這一模式的實質。當然,地方治理文化基因早在西元一世紀班固所寫《漢書.循吏列傳》時,即已設定此文化程式,繼而五世紀范曄寫《後漢書.循吏列傳》更加碼予以鞏固。這部分,有余英時於一九八六年發表〈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一文於《聯合報.副刊》,有所疏解其中關於教化的文化意涵。這其實部分地與經世思想側重技術部位文化意涵,有所針鋒相對,可惜雙方並未形成文化交鋒。黃宗智和杜贊奇的地方治理研究,是孤立於這場學術語境之外,並未產生學術對話意義的自成體系的研究。有所針對黃杜的學術對話,要到二○一一年的楊念群及其學生胡垣出現,才有了有意義的結果。
六
二○二一年十月的此刻,我完成本書,在付梓前夕,回首前塵往事,從一位大學生,沾染儒家思想這一上層建築物,同時被澆灌以經世思想者與官僚另一下層建築物,在這上下震盪之下,思維獲得展開,但還談不上有自己想法。直到九○年代讀黃宗智和杜贊奇的書,內心經歷一場類如啟蒙運動式的文化風暴,這是大開眼界。再往下二○一二年讀到楊念群和胡垣針對黃杜的修正看法。我多年醞釀的想法,在二○一七─二○一八年上述兩場博士論文答辯會上,有了黃克武等明清史專家的刺激,以及此前二○一五年發表曾鞏政治生涯(老於擔任地方官),與二○一六年發表唐宋盜匪等兩文,整個想法愈發清晰。此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二○二○年至二○二一年,時值全世界肺炎病毒疫情肆虐期間,激發了我提筆寫本書的強烈慾望!
七
以上講來,本書是我職涯四、五十年期間,與我終極關懷關係密切,即民主盟友是地方自治,民主敵人是中央集體制,這一教示是托克維爾於其《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的精華所在,從一九八七年我閱讀該書以來拳拳服膺至今,不敢一日或忘。在我於台北大學歷史系兼課三年承乏「法國史」教席,以及文化大學專任十年擔任「法國史」課程,不斷向學生重複以上托克維爾關於民主政治的真諦。如今寫到唐宋地方自治的情形,正可以與托克維爾說法國地方自治的千年傳統相互對照,這個法國地方自治傳統因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以及大革命的持續摧折而告終,法國政治朝向中央集權制之途大邁其步,以至於遲滯法國現代民主到托克維爾死於十九世紀中葉,法國人仍得不到政治自由。實際上,法國民主政治受到一九八七年左派上台完成首度政黨輪替,才開新紀元。如此說來,從大革命發生,法國花費近二百年才走上民主政治的坦途。在此,欠缺地方自治的基礎文化工程下,民主政治的建立,何其比登天還難。
回到本書的唐宋時期,中央集權制是時興當紅的體制,即令它滲透不入縣以下,而縣以下實際是仕紳、世吏在共管,也與二十世紀法國民主式政治無關。迨一九一二年中國行共和,但彼時地方自治已被中央政治權力所消滅,倘若參照托克維爾的民主理論,這似乎解釋了清末新政既走不上君主立憲制,也使北洋和國民政府想走共和立憲制也潰不成軍!這段清末民國史(1907-1949)仍有待更精緻的研究,好為中國人解惑。但無論如何,托克維爾的民主政治說是可以據以加以檢測中國個案的。
是為序。
盧建榮寫於二○二一年十月二十日
台北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