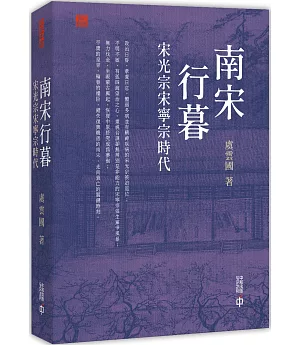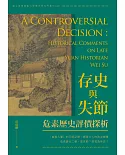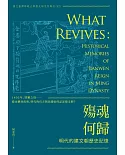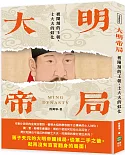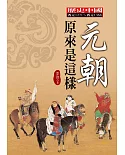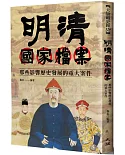兩個知名度不高的皇帝,在歷史的洪流中,卻是南宋走向衰亡的關鍵。
患有精神疾病的光宗,一邊緊握權力不放,一邊企圖不上朝以躲避直面眾臣的壓力;
治國之道侃侃而談,卻無力治國的寧宗,最後留下「不明不敏,有孤四海望治之心」的自我評價。
宋史專家虞雲國在大歷史背景下細看宋光宗宋寧宗的統治,外有大金南北對峙、蒙古鐵騎崛起,內有黨爭民怨四起,然而君主無能,權臣逐利,缺乏危機感的南宋,終在光寧二宗的治下,錯過了復興的機遇,走向不可逆轉的衰亡。
推廣重點
南宋關鍵
剖析南宋走向衰亡的關鍵時刻
興衰揭秘
細看宋光宗宋寧宗的統治
黨爭風暴
權臣逐利催生黨爭風暴
1.錯失復興機遇,南宋走向衰亡的關鍵時刻;
2.直把杭州當汴州。於蒙古興起逐鹿中原之際,偏安一隅的南宋朝野的奢靡生活;
3.政治日昏,孝養日怠。體弱多病並有精神疾病的宋光宗,如何被迫退位;
4.不明不敏,有孤四海望治之心。重視台諫卻無辨是非能力的宋寧宗,如何催生黨爭風暴;
5.平庸的皇帝,韓侂冑、史彌遠無縫接軌的輪替,終南宋一朝的權臣專政最佳展示。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虞雲國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宋史研究會理事。主要從事宋代歷史與文獻的研究。
撰有《宋代台諫制度研究》《細說宋朝》等專著;論文結集為《兩宋歷史文化叢稿》《學史帚稿》;編撰《程應鏐先生編年事輯》;主編《宋代文化史大辭典》《中國文化史年表》;整理標校《文獻通考‧四裔考》等宋元古籍十餘種;近年文史隨筆編為《敬畏歷史》《放言有忌》《從陳橋到厓山》《水滸亂彈》《書砦梁山泊》《三聲樓讀記》等。
虞雲國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宋史研究會理事。主要從事宋代歷史與文獻的研究。
撰有《宋代台諫制度研究》《細說宋朝》等專著;論文結集為《兩宋歷史文化叢稿》《學史帚稿》;編撰《程應鏐先生編年事輯》;主編《宋代文化史大辭典》《中國文化史年表》;整理標校《文獻通考‧四裔考》等宋元古籍十餘種;近年文史隨筆編為《敬畏歷史》《放言有忌》《從陳橋到厓山》《水滸亂彈》《書砦梁山泊》《三聲樓讀記》等。
目錄
新版自序 001
初版前言 019
第一章 兩朝內禪
一 淳熙內禪 024
二 紹熙初政 045
三 「政治日昏,孝養日怠」 076
四 又一幕內禪鬧劇 098
第二章 慶元黨禁
一 從風起青蘋到軒然大波 120
二 偽學逆黨之禁 150
三 韓侂胄專政 182
第三章 從開禧北伐到嘉定和議
一 以「恢復」的名義 200
二 開禧北伐 224
三 誅韓與議和 253
第四章 因循苟且的十七年
一 嘉定更化 278
二 在中原變局前束手無策 301
三 史彌遠專政下的嘉定政治 317
四 寧宗的晚年 340
附錄1 南宋光宗寧宗時代簡表 358
附錄2 徵引古籍版本 365
初版前言 019
第一章 兩朝內禪
一 淳熙內禪 024
二 紹熙初政 045
三 「政治日昏,孝養日怠」 076
四 又一幕內禪鬧劇 098
第二章 慶元黨禁
一 從風起青蘋到軒然大波 120
二 偽學逆黨之禁 150
三 韓侂胄專政 182
第三章 從開禧北伐到嘉定和議
一 以「恢復」的名義 200
二 開禧北伐 224
三 誅韓與議和 253
第四章 因循苟且的十七年
一 嘉定更化 278
二 在中原變局前束手無策 301
三 史彌遠專政下的嘉定政治 317
四 寧宗的晚年 340
附錄1 南宋光宗寧宗時代簡表 358
附錄2 徵引古籍版本 365
序
新版自序
古人有「三十年為一世」之說,原指代際相繼之意。北宋邵雍將其引入自家的宇宙歷史演化論,作為最小的時段概念,提出「三十年為一世,十二世為一運,三十運為一會,十二會為一元」。撇除其周而復始的神秘色彩,顯然也將三十年作為考察歷史的基本時段。
西方年鑑學派主張綜合長時段、中時段與短時段的多種方式,多層級地構成對總體歷史的全面研究。相對於以一個世紀乃至更久的長時段與以事件史為標誌的短時段,中時段的研究閾限「涉及十年、二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歷史態勢」,自有其特定價值。這種中時段,足以完整展現長時段歷史中某個變化週期,身處其中者往往到該週期結束才能察覺其終始之間發生了多大的時代差異與歷史變動。
《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寧宗時代》,雖是舊著《宋光宗 宋寧宗》的改訂新版,但當年撰著時因他們父子的個人史料存世有限,便立意「以帝王傳記的形式來表現光寧時代」,「力圖把光寧時代作為南宋歷史演進的不可或缺的一環」,有心寫一部時代史,這個初衷仍沒有變。宋光宗即位於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宋寧宗去世在嘉定十七年(1224)八月,兩位皇帝在位跨36個年頭,既符合「三十年為一世」的概念,也恰在中時段範圍(如果不考慮以帝王為坐標的話,這一時段不妨下延至史彌遠去世的1233年)。倘若將宋孝宗淳熙內禪時1189年與宋寧宗駕崩時1224年的政治、軍事、經濟與文化作一對比的話,就能發現:經過三十餘年緩慢頓漸的變化,南宋王朝已不可逆地從治世折入了衰世。這次改版儘可能地做了修訂,但總體結構未做改動,故擬就這一時段若干總體性問題略抒己見,以便加深對這段時代史的全局性把握。
一
既然說這一時段是南宋從治世折入衰世的關鍵時代,當然必須以其前與其後的時代作為比較的參照系。這裡,先說其前的宋孝宗時代。宋孝宗在位期間為1162年至1189年,共27年,大體也在中時段的閾限內。
紹興三十二年(1162)六月,借由「紹興內禪」甫登皇位的宋孝宗,雄心勃勃主動發起隆興北伐,試圖改變紹興和議定下的地緣政治格局。然而,受制於內部因素(太上皇宋高宗的掣肘與反對,主事者張浚「志大而量不弘,氣勝而用不密」,等等)與外部條件(金朝的實力),被迫與金朝再訂隆興和議,重歸宋高宗確立的「紹興體制」。其後,在內政上,宋孝宗也只能在奉行「紹興體制」的大前提下略做微調與騰挪。有鑑於秦檜擅權的前車之轍,他在位期間一方面頻繁易相,以便皇綱獨攬;一方面開放言路,以便「異論相攪」。隆興和議後,南北政權間長期維持着相對穩定的和平局面。作為南宋唯一欲有所為的君主,宋孝宗曾坦承短期內恢復中原已無可能,但仍寄望於君臣協力一改國弱民貧的局面。他尤其注重興修水利,推動農業生產;同時關注財政與經濟,制定鼓勵商業與對外貿易的政策,城市經濟與市民文化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惟其如此,南宋社會在乾道、淳熙間(1165—1189)也進入了繁盛期。
宋孝宗時代(1163—1189),一方面在專制政體上繼承了紹興體制的政治遺產,另一方面在對官僚士大夫的做法上則有明顯的調整,他還能容忍不同的政見與批評的聲音,政治生態與思想氛圍較之宋高宗秦檜專權時期大有改善。他對道學儘管不持好感,卻並未以一己好惡而推行整肅政策。在傳統中國的大多數時候,政治總是決定一切的,即便微調也效果明顯。由於宋孝宗的政治統治相對寬鬆,致使這一時代在思想文化上頗有亮色。
在《中國轉向內在》裡,劉子健認為,北宋學術「令人耳目一新,具有挑戰性和原創性」;相對說來,南宋學術「都難免相對狹隘、受制於正統、缺乏原創性的問題」。這一說法有其獨到之見,但也不盡然,南宋浙東學派諸家,就提供了某些北宋未有的學術成果與思想體系。這是由於浙東學派的學術建構,還有賴於北宋以來士大夫階層的事功實踐充實其思想資源,也與宋孝宗時代的環境改善有着內在關聯。也正是利用了乾道、淳熙年相對優容的政治環境,朱熹才有力推動了道學派的擴容,完成了理學集大成進程;張栻也自成一派,張大了湖湘之學。繼北宋中期以後,這一時段以朱熹為領袖的程朱理學,以陸九淵為開山的心學,與呂祖謙、陳亮、葉適領軍的浙東事功學派幾成鼎足之勢,湧現出自己時代的學術大師群體。無論思想上,還是人才上,正是宋孝宗時代,宋學進入了又一巔峰期。繼北宋中葉的文學鼎盛期之後,這一時段陸游、辛棄疾、范成大與楊萬里等各領風騷,宋代文學也形成了第二個高峰期(雖然比起歐陽修、蘇軾父子與王安石等領軍的北宋高峰來略見遜色),而代表人物都成長並活躍在這一時段。史學家李燾也在宋孝宗朝完成了當代史《續資治通鑑長編》的編纂,繼司馬光之後令宋賢史學再放異彩。
所有這些,都出現在宋孝宗時代,顯然絕非偶然現象。南宋曹彥約認為,南宋乾道、淳熙期間堪與北宋慶曆、元祐時期相媲美:
朝廷無事,四方寧謐;士渾厚而成風,民富饒而知義。負者歌,行者樂,熙熙侃侃,相期於咸平、慶曆、元祐之治。
本朝人讚美難免摻有水分,但明代史家柯維騏也有好評,說宋孝宗「有君人之度,其繫人心成乾(道)淳(熙)之治」。縱觀宋孝宗時代,顯然迥異於南宋理宗以降內有權臣疊相擅政、外有蒙元鐵騎壓境的高危期,確是政局相對穩定、政治相對清明、社會經濟相對繁榮的最好時段,堪稱南宋史上的鼎盛期。如此一對照,南宋光宗寧宗時代的全面逆轉就更顯得觸目驚心。
二
《朱熹的歷史世界》堪稱研究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巔峰之作,但著者認為,淳熙內禪前後,宋孝宗有一個扭轉其晚年因循政策的重大構想,一是親自選定「周必大、留正、趙汝愚三相」,「有意建立一個以理學型士大夫為主體的執政團體」;二是刻意部署「理學集團的許多重要成員進入了權力核心」,試圖以如此的執政團隊與理學集團相結合,支持理學家在「外王」領域革新政治,恢復北方。對宋孝宗是否確有這種構想與部署,學界頗有不同意見:「他的證據很有意思,但卻不很充分,因此遠不具有決定性。」我只對其部署執政集團與理學集團之說,略說管見。
依據慶元黨籍的後出名單,斷言宋孝宗晚年部署的三相都「深得理學家集團的信任」,是值得斟酌的。首先,那張名單只是韓侂胄及其追隨者出於打擊政敵的需要編派的(據學界研究甚至還有後黨禁時代道學傳人追加的痕跡),列名者並非都與理學(或道學)有關。以留正而論,有研究表明,他雖未與道學派公開為敵,但在反道學派的前任左相王淮與傾向道學的前任右相周必大之黨爭中明顯左袒,而王淮在內禪前一年罷相,便由「留正接過了反道學派之大旗,開始了新一輪反擊鬥爭」。在攻去周必大後,留正雖也起用了一些道學人士,但應是其獨相秉政後出於協調各方政治勢力的需要,道學家對他未見得有多大信任。
周必大自淳熙七年(1180)起即進入宰執圈而深受信用,作為守成輔政的宰相人選,宋孝宗命其輔佐新君藉以遙控朝政,自在情理之中;但其任左相僅五個月,即遭御史中丞何澹攻擊而不得不去位。其中留正與其「議論素不相合」而窺伺帝意大有作用,而宋光宗之授意默許,顯然出於不願受太上皇掣肘等微妙考量(由於周必大「密奏」,望眼欲穿的內禪繼位至少推遲一年,無疑讓新君大感不爽),而對周必大罷相與其後留正獨相,也未見宋孝宗有進一步干預與部署,足見不宜過分誇大他作為太上皇對朝政控制的力度與效果。
趙汝愚遲至紹熙四年(1193)才以同知樞密院事初入宰執圈,宗室出任宰執有違於祖制,在這點上宋孝宗確實力挺過,但其時宋光宗精神病頻頻發作,一再鬧出過宮鬧劇,宋孝宗支持其執政,也未見有部署趙汝愚推行革新的史證,恐怕更多指望他能調護兩宮父子、渡過朝局危機而已。
總之,將周必大、留正與趙汝愚這樣頗有差異的三位宰相(何況趙汝愚任相更在宋孝宗已死的紹熙內禪後)拉在一起,推論宋孝宗晚年刻意部署執政集團,以實行「規模頗大的長期性的革新構想」,顯然缺乏堅強有效的證據鏈,以致「只好用心理史學來填補這個缺陷」,但心理史學猶如理校法,「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陳垣語)。
至於說淳熙內禪前宋孝宗「所親自擢用的六人都出於理學集團」,以及淳熙內禪後理學之士「進入中樞的便有十一人」,余英時認為,這是宋孝宗晚年刻意擢拔理學集團的另一部署。從這些客觀現象倒推式論證宋孝宗曾有那種主觀部署,依然存在着證據鏈脫節的困惑。我認為,首先,如前所述,宋孝宗的政治生態相對寬鬆,儘管他本人不好道學,但用人政策上卻從未排斥具有道學傾向的士大夫官僚。其次,下文即將論及,正是有賴於這種相對寬容的政治文化生態,朱學、陸學與浙學三派經過授徒講學,擴大了新儒學的影響,推動了新儒家的擴容,他們補充官僚隊伍的比重自然大為提高,進入中樞也是理所當然的。余英時指出的現象,乃是宋孝宗朝寬鬆政策與新儒學自身發展勢運相輔相成的結果,並非基於所謂革新構想而刻意為之的精心部署。實際上,包括留正獨相以後轉而啟用道學人士,趙汝愚在宋寧宗初年拜相之後一度汲引「眾賢盈庭」,試圖重溫「小元祐」之夢,都應作如此平實之觀,而不宜過度詮釋。
古人有「三十年為一世」之說,原指代際相繼之意。北宋邵雍將其引入自家的宇宙歷史演化論,作為最小的時段概念,提出「三十年為一世,十二世為一運,三十運為一會,十二會為一元」。撇除其周而復始的神秘色彩,顯然也將三十年作為考察歷史的基本時段。
西方年鑑學派主張綜合長時段、中時段與短時段的多種方式,多層級地構成對總體歷史的全面研究。相對於以一個世紀乃至更久的長時段與以事件史為標誌的短時段,中時段的研究閾限「涉及十年、二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歷史態勢」,自有其特定價值。這種中時段,足以完整展現長時段歷史中某個變化週期,身處其中者往往到該週期結束才能察覺其終始之間發生了多大的時代差異與歷史變動。
《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寧宗時代》,雖是舊著《宋光宗 宋寧宗》的改訂新版,但當年撰著時因他們父子的個人史料存世有限,便立意「以帝王傳記的形式來表現光寧時代」,「力圖把光寧時代作為南宋歷史演進的不可或缺的一環」,有心寫一部時代史,這個初衷仍沒有變。宋光宗即位於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宋寧宗去世在嘉定十七年(1224)八月,兩位皇帝在位跨36個年頭,既符合「三十年為一世」的概念,也恰在中時段範圍(如果不考慮以帝王為坐標的話,這一時段不妨下延至史彌遠去世的1233年)。倘若將宋孝宗淳熙內禪時1189年與宋寧宗駕崩時1224年的政治、軍事、經濟與文化作一對比的話,就能發現:經過三十餘年緩慢頓漸的變化,南宋王朝已不可逆地從治世折入了衰世。這次改版儘可能地做了修訂,但總體結構未做改動,故擬就這一時段若干總體性問題略抒己見,以便加深對這段時代史的全局性把握。
一
既然說這一時段是南宋從治世折入衰世的關鍵時代,當然必須以其前與其後的時代作為比較的參照系。這裡,先說其前的宋孝宗時代。宋孝宗在位期間為1162年至1189年,共27年,大體也在中時段的閾限內。
紹興三十二年(1162)六月,借由「紹興內禪」甫登皇位的宋孝宗,雄心勃勃主動發起隆興北伐,試圖改變紹興和議定下的地緣政治格局。然而,受制於內部因素(太上皇宋高宗的掣肘與反對,主事者張浚「志大而量不弘,氣勝而用不密」,等等)與外部條件(金朝的實力),被迫與金朝再訂隆興和議,重歸宋高宗確立的「紹興體制」。其後,在內政上,宋孝宗也只能在奉行「紹興體制」的大前提下略做微調與騰挪。有鑑於秦檜擅權的前車之轍,他在位期間一方面頻繁易相,以便皇綱獨攬;一方面開放言路,以便「異論相攪」。隆興和議後,南北政權間長期維持着相對穩定的和平局面。作為南宋唯一欲有所為的君主,宋孝宗曾坦承短期內恢復中原已無可能,但仍寄望於君臣協力一改國弱民貧的局面。他尤其注重興修水利,推動農業生產;同時關注財政與經濟,制定鼓勵商業與對外貿易的政策,城市經濟與市民文化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惟其如此,南宋社會在乾道、淳熙間(1165—1189)也進入了繁盛期。
宋孝宗時代(1163—1189),一方面在專制政體上繼承了紹興體制的政治遺產,另一方面在對官僚士大夫的做法上則有明顯的調整,他還能容忍不同的政見與批評的聲音,政治生態與思想氛圍較之宋高宗秦檜專權時期大有改善。他對道學儘管不持好感,卻並未以一己好惡而推行整肅政策。在傳統中國的大多數時候,政治總是決定一切的,即便微調也效果明顯。由於宋孝宗的政治統治相對寬鬆,致使這一時代在思想文化上頗有亮色。
在《中國轉向內在》裡,劉子健認為,北宋學術「令人耳目一新,具有挑戰性和原創性」;相對說來,南宋學術「都難免相對狹隘、受制於正統、缺乏原創性的問題」。這一說法有其獨到之見,但也不盡然,南宋浙東學派諸家,就提供了某些北宋未有的學術成果與思想體系。這是由於浙東學派的學術建構,還有賴於北宋以來士大夫階層的事功實踐充實其思想資源,也與宋孝宗時代的環境改善有着內在關聯。也正是利用了乾道、淳熙年相對優容的政治環境,朱熹才有力推動了道學派的擴容,完成了理學集大成進程;張栻也自成一派,張大了湖湘之學。繼北宋中期以後,這一時段以朱熹為領袖的程朱理學,以陸九淵為開山的心學,與呂祖謙、陳亮、葉適領軍的浙東事功學派幾成鼎足之勢,湧現出自己時代的學術大師群體。無論思想上,還是人才上,正是宋孝宗時代,宋學進入了又一巔峰期。繼北宋中葉的文學鼎盛期之後,這一時段陸游、辛棄疾、范成大與楊萬里等各領風騷,宋代文學也形成了第二個高峰期(雖然比起歐陽修、蘇軾父子與王安石等領軍的北宋高峰來略見遜色),而代表人物都成長並活躍在這一時段。史學家李燾也在宋孝宗朝完成了當代史《續資治通鑑長編》的編纂,繼司馬光之後令宋賢史學再放異彩。
所有這些,都出現在宋孝宗時代,顯然絕非偶然現象。南宋曹彥約認為,南宋乾道、淳熙期間堪與北宋慶曆、元祐時期相媲美:
朝廷無事,四方寧謐;士渾厚而成風,民富饒而知義。負者歌,行者樂,熙熙侃侃,相期於咸平、慶曆、元祐之治。
本朝人讚美難免摻有水分,但明代史家柯維騏也有好評,說宋孝宗「有君人之度,其繫人心成乾(道)淳(熙)之治」。縱觀宋孝宗時代,顯然迥異於南宋理宗以降內有權臣疊相擅政、外有蒙元鐵騎壓境的高危期,確是政局相對穩定、政治相對清明、社會經濟相對繁榮的最好時段,堪稱南宋史上的鼎盛期。如此一對照,南宋光宗寧宗時代的全面逆轉就更顯得觸目驚心。
二
《朱熹的歷史世界》堪稱研究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巔峰之作,但著者認為,淳熙內禪前後,宋孝宗有一個扭轉其晚年因循政策的重大構想,一是親自選定「周必大、留正、趙汝愚三相」,「有意建立一個以理學型士大夫為主體的執政團體」;二是刻意部署「理學集團的許多重要成員進入了權力核心」,試圖以如此的執政團隊與理學集團相結合,支持理學家在「外王」領域革新政治,恢復北方。對宋孝宗是否確有這種構想與部署,學界頗有不同意見:「他的證據很有意思,但卻不很充分,因此遠不具有決定性。」我只對其部署執政集團與理學集團之說,略說管見。
依據慶元黨籍的後出名單,斷言宋孝宗晚年部署的三相都「深得理學家集團的信任」,是值得斟酌的。首先,那張名單只是韓侂胄及其追隨者出於打擊政敵的需要編派的(據學界研究甚至還有後黨禁時代道學傳人追加的痕跡),列名者並非都與理學(或道學)有關。以留正而論,有研究表明,他雖未與道學派公開為敵,但在反道學派的前任左相王淮與傾向道學的前任右相周必大之黨爭中明顯左袒,而王淮在內禪前一年罷相,便由「留正接過了反道學派之大旗,開始了新一輪反擊鬥爭」。在攻去周必大後,留正雖也起用了一些道學人士,但應是其獨相秉政後出於協調各方政治勢力的需要,道學家對他未見得有多大信任。
周必大自淳熙七年(1180)起即進入宰執圈而深受信用,作為守成輔政的宰相人選,宋孝宗命其輔佐新君藉以遙控朝政,自在情理之中;但其任左相僅五個月,即遭御史中丞何澹攻擊而不得不去位。其中留正與其「議論素不相合」而窺伺帝意大有作用,而宋光宗之授意默許,顯然出於不願受太上皇掣肘等微妙考量(由於周必大「密奏」,望眼欲穿的內禪繼位至少推遲一年,無疑讓新君大感不爽),而對周必大罷相與其後留正獨相,也未見宋孝宗有進一步干預與部署,足見不宜過分誇大他作為太上皇對朝政控制的力度與效果。
趙汝愚遲至紹熙四年(1193)才以同知樞密院事初入宰執圈,宗室出任宰執有違於祖制,在這點上宋孝宗確實力挺過,但其時宋光宗精神病頻頻發作,一再鬧出過宮鬧劇,宋孝宗支持其執政,也未見有部署趙汝愚推行革新的史證,恐怕更多指望他能調護兩宮父子、渡過朝局危機而已。
總之,將周必大、留正與趙汝愚這樣頗有差異的三位宰相(何況趙汝愚任相更在宋孝宗已死的紹熙內禪後)拉在一起,推論宋孝宗晚年刻意部署執政集團,以實行「規模頗大的長期性的革新構想」,顯然缺乏堅強有效的證據鏈,以致「只好用心理史學來填補這個缺陷」,但心理史學猶如理校法,「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陳垣語)。
至於說淳熙內禪前宋孝宗「所親自擢用的六人都出於理學集團」,以及淳熙內禪後理學之士「進入中樞的便有十一人」,余英時認為,這是宋孝宗晚年刻意擢拔理學集團的另一部署。從這些客觀現象倒推式論證宋孝宗曾有那種主觀部署,依然存在着證據鏈脫節的困惑。我認為,首先,如前所述,宋孝宗的政治生態相對寬鬆,儘管他本人不好道學,但用人政策上卻從未排斥具有道學傾向的士大夫官僚。其次,下文即將論及,正是有賴於這種相對寬容的政治文化生態,朱學、陸學與浙學三派經過授徒講學,擴大了新儒學的影響,推動了新儒家的擴容,他們補充官僚隊伍的比重自然大為提高,進入中樞也是理所當然的。余英時指出的現象,乃是宋孝宗朝寬鬆政策與新儒學自身發展勢運相輔相成的結果,並非基於所謂革新構想而刻意為之的精心部署。實際上,包括留正獨相以後轉而啟用道學人士,趙汝愚在宋寧宗初年拜相之後一度汲引「眾賢盈庭」,試圖重溫「小元祐」之夢,都應作如此平實之觀,而不宜過度詮釋。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79折$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