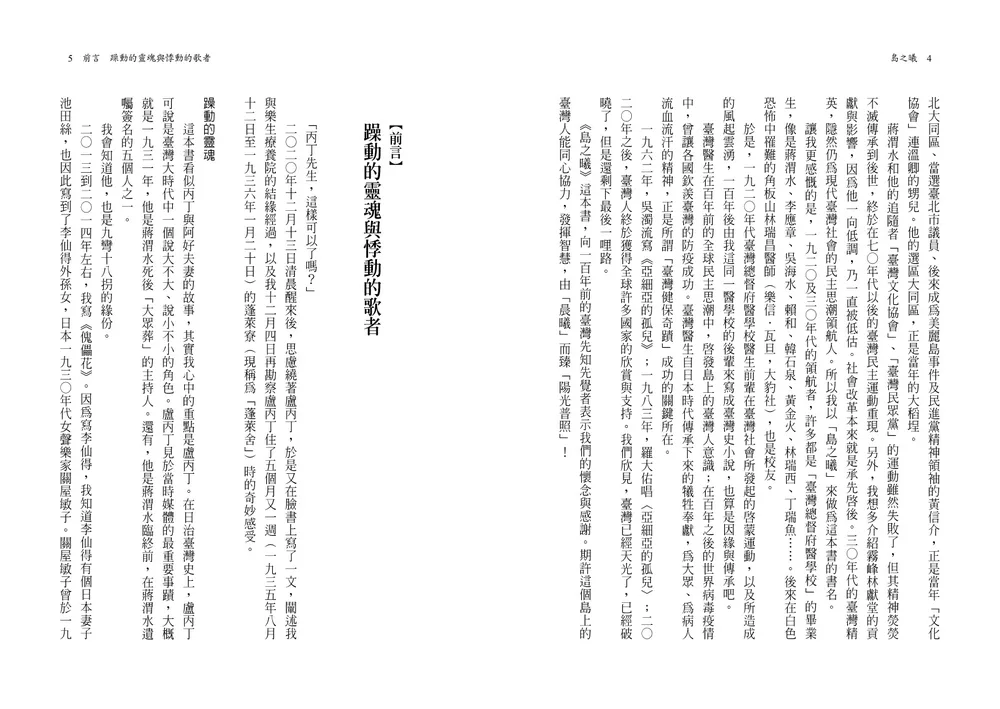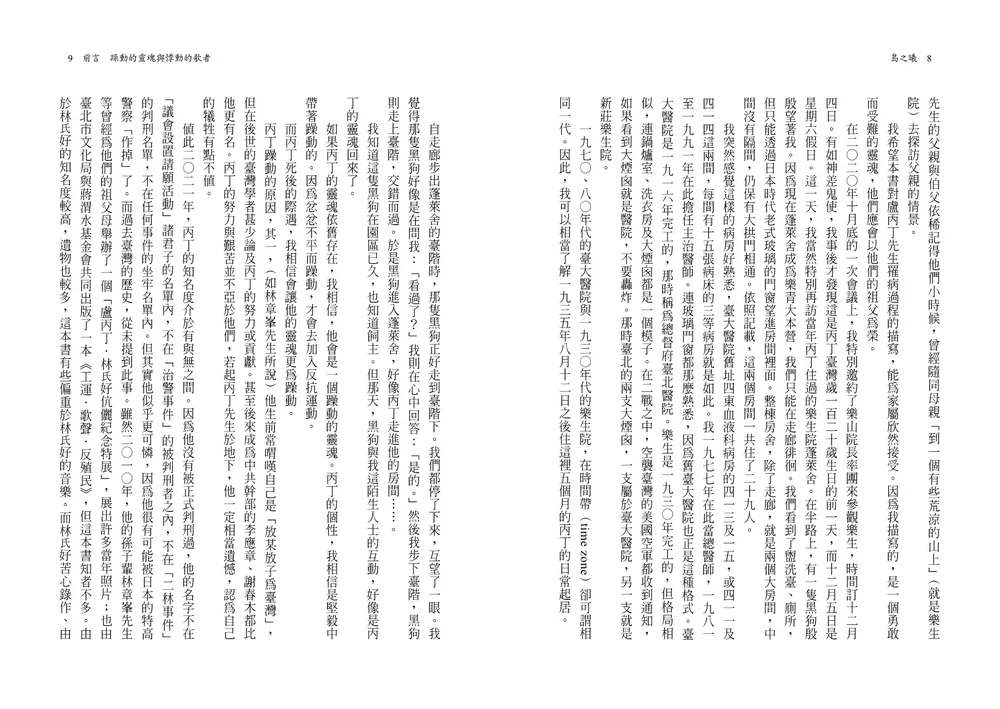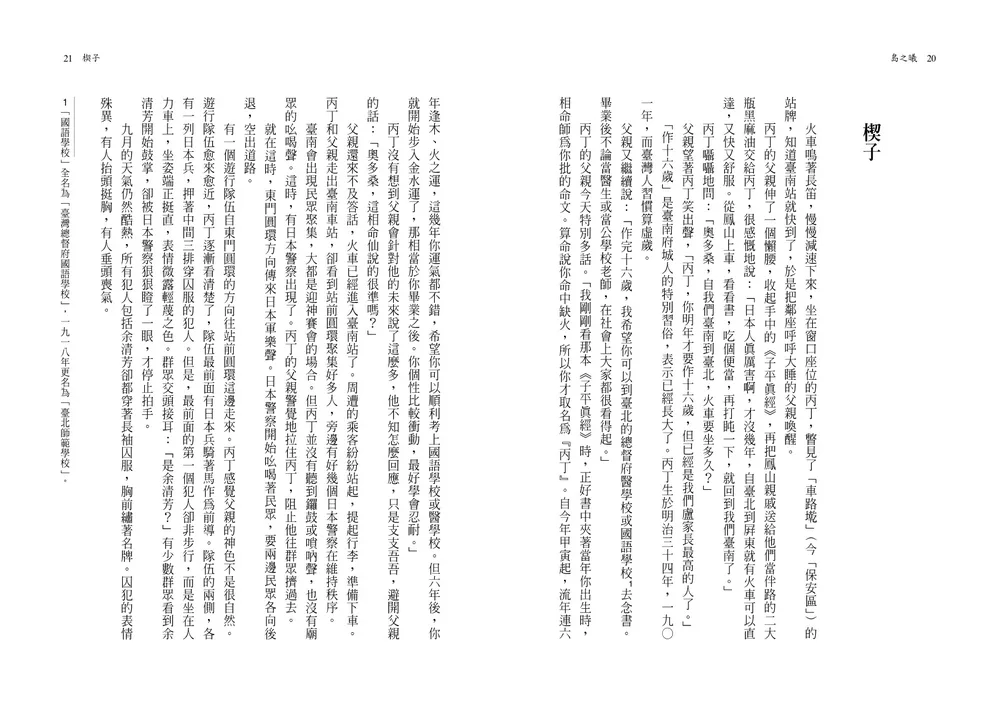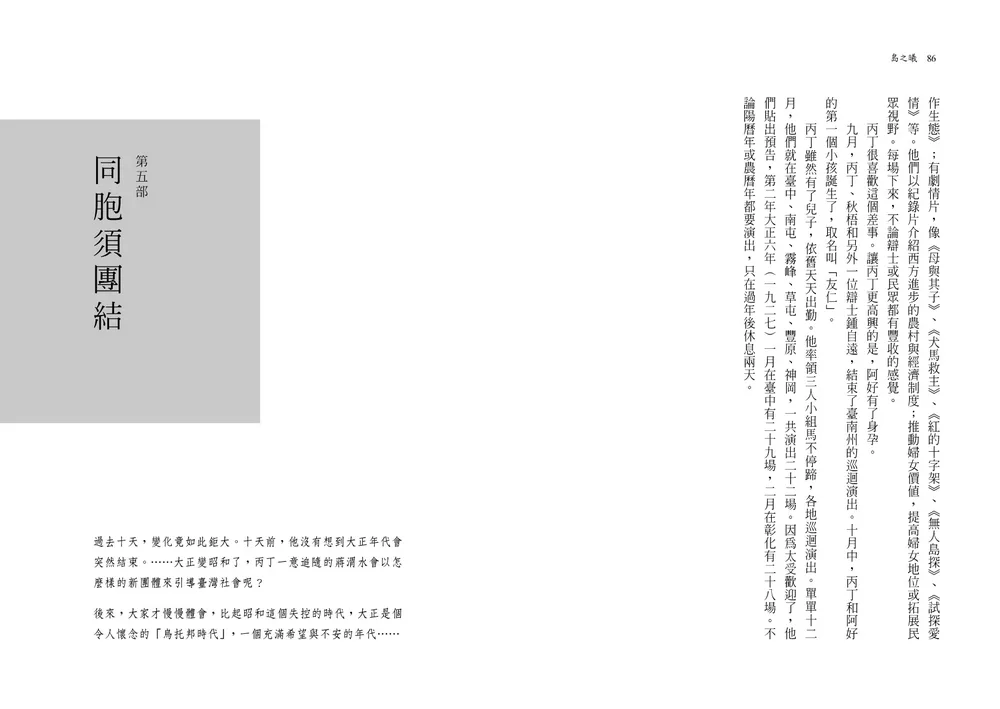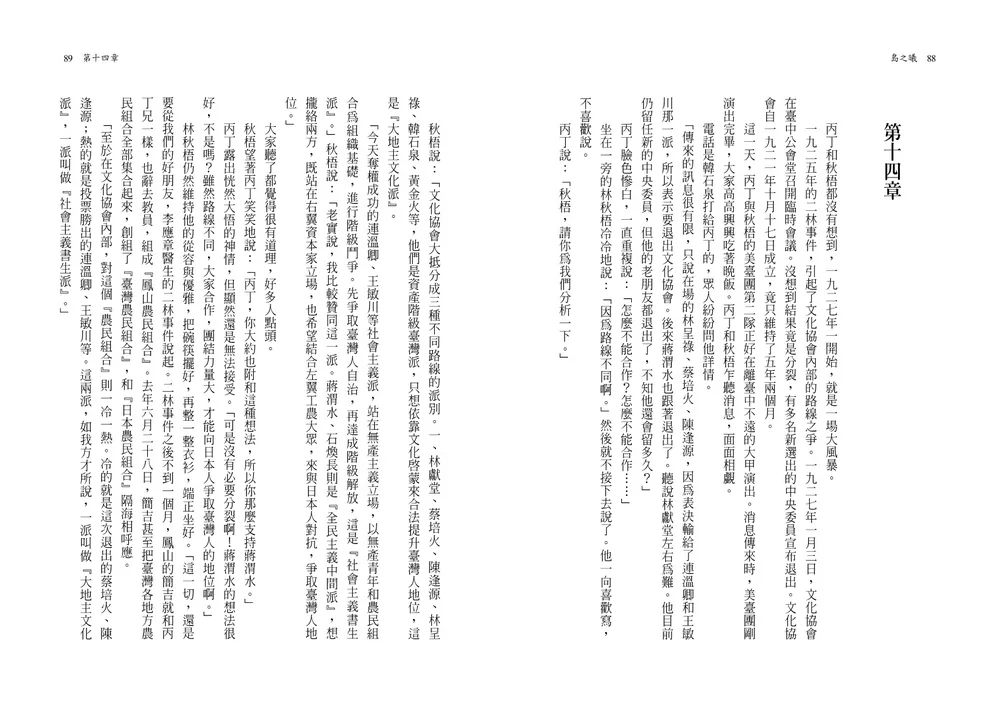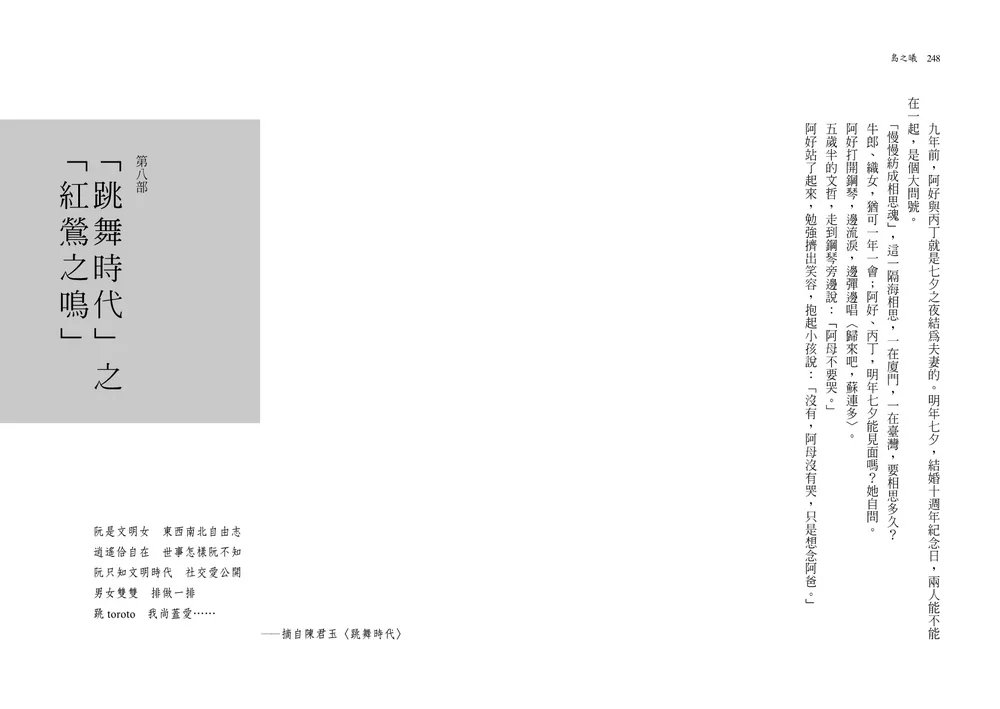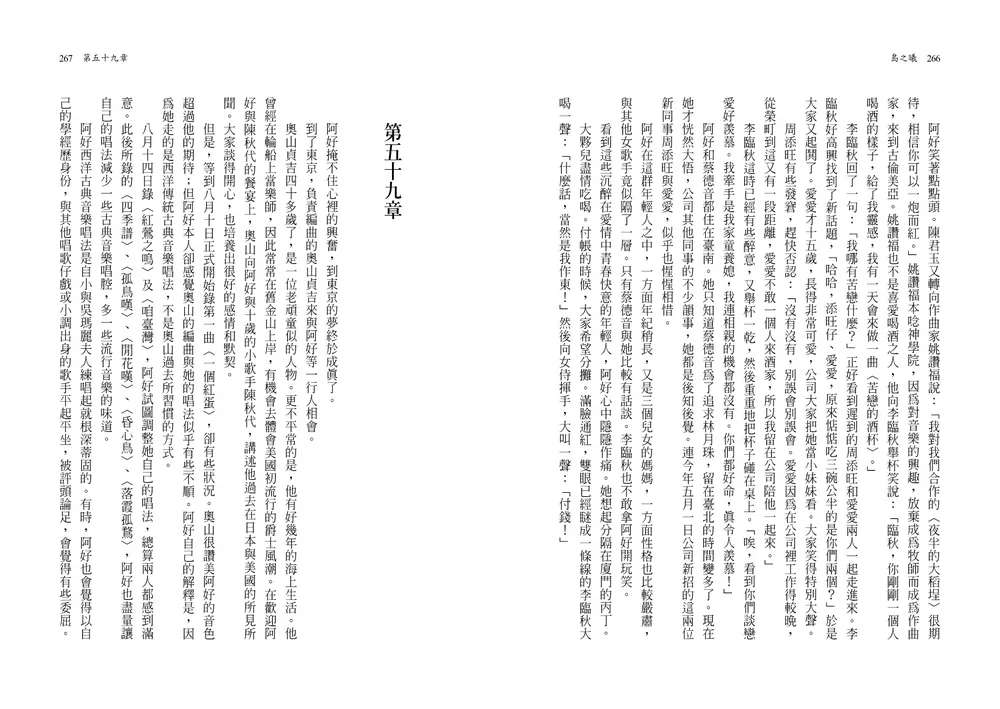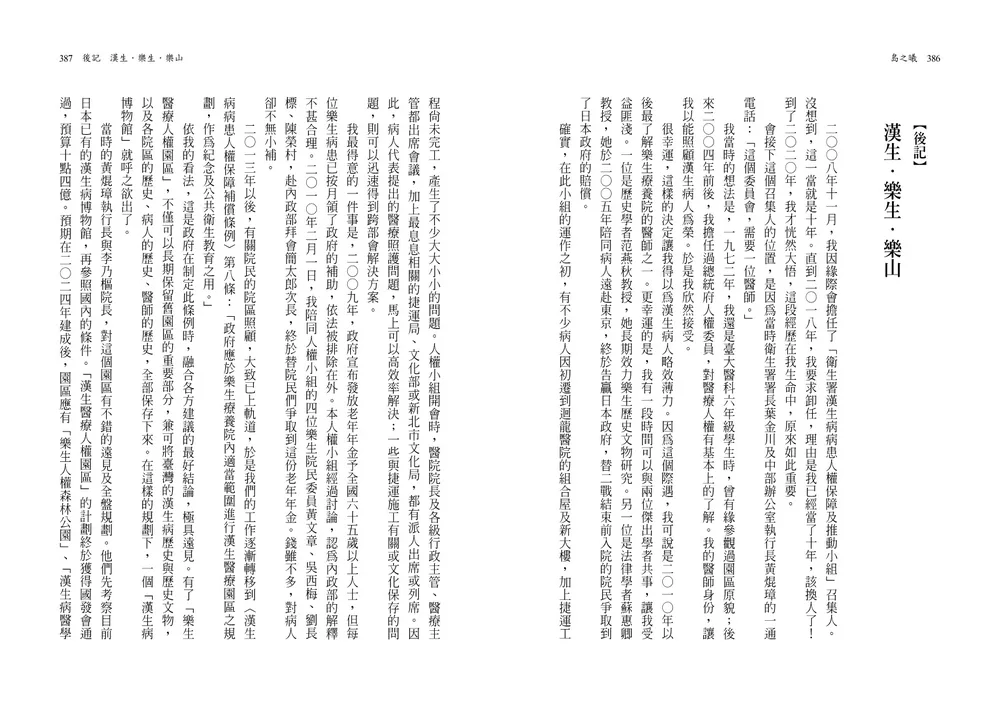導讀
島之曦:福爾摩沙臺灣的重生
二○二○年三月以前,我一直認為我不太可能去寫日本時代的小說,因為我不懂日文。
沒想到,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起,我開始振筆直書,寫盧丙丁、林氏好這對夫妻的故事,以十一個月的時間完成這本書。
我寫盧丙丁及林氏好這對夫妻,寫當時引領臺灣文化啟蒙運動的「臺灣文化協會」及政治上第一個政黨「臺灣民眾黨」。我以丙丁串出那一代掀起「臺灣人意識」的各行各路知識份子,期 能寫出一九二○至一九三五年那個臺灣社會運動最蓬勃的年代;我藉林氏好帶出一九三○年代臺灣的流行音樂。我希望本書能生動刻劃出那個臺灣最活潑的年代。
蔣渭水、林獻堂及那個時代知識份子的臺灣人意識反抗運動,先是受挫於日本政府在一九三六年以後的嚴厲壓制,以及其後的皇民化運動;一九四五年之後更受到「祖國」的暴虐摧殘;國民政府遷臺之前有二二八大屠殺,遷臺之後有白色恐怖,更有種種臺灣意識、語言、文化的「清洗」。於是這些曾經輝煌於二○年代及三○年代的臺灣歷史人物,有些不幸死難,大多被臺灣人所淡忘;少數則成為中國共產黨高幹。於今回顧,令人不勝唏噓。
然而,就像臺灣俗語所說的「番薯不驚落土爛」,到了一九六一年,「黨外」乍起,風靡臺北大同區、當選臺北市議員、後來成為美麗島事件及民進黨精神領袖的黃信介,正是當年「文化協會」連溫卿的甥兒。他的選區大同區,正是當年的大稻埕。
蔣渭水和他的追隨者「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的運動雖然失敗了,但其精神熒熒不滅傳承到後世,終於在七○年代以後的臺灣民主運動重現。另外,我想多介紹霧峰林獻堂的貢獻與影響,因為他一向低調,乃一直被低估。社會改革本來就是承先啟後。三○年代的臺灣精英,隱然仍為現代臺灣社會的民主思潮領航人。所以我以「島之曦」來做為這本書的書名。
讓我更感慨的是,一九二○及三○年代的領航者,許多都是「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的畢業生,像是蔣渭水、李應章、吳海水、賴和、韓石泉、黃金火、林瑞西、丁瑞魚……。後來在白色恐怖中罹難的角板山林瑞昌醫師(樂信.瓦旦,大豹社),也是校友。
於是,一九二○年代臺灣總督府醫學校醫生前輩在臺灣社會所發起的啟蒙運動,以及所造成的風起雲湧,一百年後由我這同一醫學校的後輩來寫成臺灣史小說,也算是因緣與傳承吧。
臺灣醫生在百年前的全球民主思潮中,啟發島上的臺灣人意識;在百年之後的世界病毒疫情中,曾讓各國欽羨臺灣的防疫成功。臺灣醫生自日本時代傳承下來的犧牲奉獻,為大眾、為病人流血流汗的精神,正是所謂「臺灣健保奇蹟」成功的關鍵所在。
一九六二年,吳濁流寫《亞細亞的孤兒》;一九八三年,羅大佑唱〈亞細亞的孤兒〉;二○二○年之後,臺灣人終於獲得全球許多國家的欣賞與支持。我們欣見,臺灣已經天光了,已經破曉了,但是還剩下最後一哩路。
《島之曦》這本書,向一百年前的臺灣先知先覺者表示我們的懷念與感謝。期許這個島上的臺灣人能同心協力,發揮智慧,由「晨曦」而臻「陽光普照」!
專文推薦一
當第一道曙光鑿穿了鴻濛
There is a crack,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Leonard Cohen, Anthem.
島之曦──臺灣島的第一道曙光。對於我而言,本書的一切謎團,均始於此。
小說家陳耀昌書寫臺灣,始於十七世紀,也就是大航海後期進入世界史的臺灣,《島之曦》已經是第五本。但是,他為何並不認為一六六二年(鄭氏)、一六八三年(清朝)甚或一九四五年(蔣氏)是臺灣的晨曦?他為何認定一九二○年代(從「大正民主」到昭和初期的日治),是臺灣的黎明期?
第一種可能性,奠基於歷史學。
凡是研究臺灣史、乃至於世界史的學徒學究,都可以旁徵博引、宅氣橫溢地告訴我們:單就殖民地而論,一九二○年代所顯示的獨特性有多麼明顯。如以臺灣為例,則晨曦正是啟蒙主義與現代性的暗喻。在現代性的驕陽照耀之下,無論前近代的明鄭、滿清,同時代的、乃至於近未來的(受困於帝制與納粹/史達林小學兩極夾縫的)國共,率皆猶疑黯淡,恍如非理性、反文明的蠻族。相較之下,陳耀昌以臺灣議會運動、治警事件為序幕,帶出一系列臺灣民族、階級運動的英雄人物,「啓蒙曙光」的象徵性可謂十足。
當治警事件發生之際,臺灣社會已初步具備了一個「公民社會」的諸般條件。以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所謂的「市民的公共性的概念」看來,其時在臺灣出現的媒體(如《臺灣青年》、《臺灣民報》)或結社(如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都是以近代立憲主義(明治憲法)為基礎,有組織地挑戰總督的委任立法權。這些媒體或結社的中心人物,也和前近代的「讀書人」、「士大夫」全然不同,而是若林正丈所言的「新興知識人」。這些新興知識人接受現代教育、具備啟蒙主義的文化教養、受過醫學(科學)/法律(權利意識),甚至神學等專業訓練,並且能說一口流利的(而且是都會知識份子的)日語,擁有或至少追求全球視野與國際連帶。
與武裝抗日的前輩們不同,他們放棄武裝抗日,嘗試以思想或「合法的」言論與行動,進行公民不服從的抵抗。臺灣總督府固然視其為背中芒刺,卻不能不承認這群臺灣人對於現代性的認識,並不在日本人之下。所以治警事件這般大規模羅織的政治審判,卻只能以取締「微罪」的治安警察法起訴,而且第一審法官,居然判決被告們全體無罪。在往後將近一百年裡的臺灣──或許直到太陽花運動──此等「奇蹟」可從未再現。假如發生在日本,這麼精采的事件、出現這麼一大群英雄被告、反派統治者以及跨海馳援的日本/沖繩律師,不知道已經被松本清張、司馬遼太郎及其徒子徒孫寫了多少本書,拍成多少部電影或大河劇了。
第二種可能性,來自於文學史的詮釋。
宋澤萊在《台灣文學三百年》的自序裡曾經談到,加拿大文學批評家弗萊(Northrop
Frye)以春夏秋冬的四季循環,分別套用在「原始社會的神話」與「文明社會的文學」裡,「使我茅塞頓開,解答了我三十幾年裡所想的問題」。春夏秋冬套用於文學的具體結果是什麼呢?「文明社會的春天階段會出現傳奇(浪漫)文類;夏天階段會出現田園、喜劇、抒情文類;秋天階段會出現悲劇文類,冬天階段會出現諷刺文類……四季循環完畢,還會復活過來,又出現下一個四季的循環」。
宋澤萊便是以此為基礎,對三百年來的臺灣文學進行分析。雖然他的重點是「春夏秋冬的四個階段不必有一定時間的限制/文學不是悲觀的,任何文明、文學都可以再生,死而復活」,但是這和陳耀昌的《島之曦》──以及其餘的歷史小說書寫──有什麼相關呢?因為宋澤萊在二○二一年初某個(由我擔任引言人的)演講中,提到這個理論,並且明確地指出:「包括在場的新生代小說家陳耀昌醫師在內的、近年來開始流行的臺灣歷史小說書寫潮,正顯示了臺灣文學春天的到來」。而臺灣文學的春天,顯然與臺灣政治與社會的春天重疊,也就是進入了最有活力與希望的時代。既然如此,則陳耀昌的歷史小說,正是應運而生的傳奇浪漫文類,那麼無論錫名晨曦或春暉,其差別也就無關宏旨矣。
然而,仔細閱讀本書之後,我發現陳耀昌似乎並不是一個浪漫的傳奇文學小說家。他也不是「國族無極願無窮」的深心悲願、巴不得人家不知道的臺灣國族主義者。他甚至不是一個天真的啟蒙主義者。
否則,他又何必選擇盧丙丁做為主角?
在人才輩出的一九二○至三○年代的臺灣,盧丙丁縱然被總督府視為蔣渭水的左右手,他仍然是一個不甚為後世所熟知、記憶的人物。當然啦,從創作的角度觀之,如此選擇,未嘗不是書寫歷史小說的「樂趣」所在──惟其事蹟湮沒不彰,才給予小說家更多的想像空間,更多的筆底迴旋。
不過,在本書中,對於任憑想像揮灑的「樂趣」,陳耀昌顯然極其自制,自制到了幾乎讓讀者懷疑他是刻意避免「傳奇/浪漫」的「春天」效果。他做足了歷史學究般考證、還原的笨功夫,幾乎到了「附魔」的程度。他對於歷史細節的推敲提問,以及因而發掘出的歷史真相,不知道讓多少學院派的專業史家受窘。相反的,在史料不足處──也就是縱然恣意騁其想像,也絕不會有人抱怨的時候,陳耀昌卻擱筆了。環繞盧丙丁而出場的歷史人物,佔了那麼多篇幅,卻個個淡淡進場、淡淡退場,彷彿在較量誰的發言最為雋永簡潔,如《世說新語》。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作者如神探一般,終於查明了盧丙丁空前絕後的「進出」樂生院,以及隨後不可思議的「被出國/被旅行」,從此人間蒸發的原因,都與統治者的變質墮落(從大正到昭和)與殖民地官僚(公衛菁英與特高警察)間的矛盾密切相關。在推理完成(好吧,雖然大部分是狀況證據),犯人呼之欲出,正值得小說家盡顯本領、大書特書之際,陳耀昌竟然還是讓盧丙丁淡淡地「不知所終」,「後遂無問津者」!
這也未免太不「春天」了。
雖說寫歷史小說講究虛實相間,只不過「實」的功能並不只為「虛」架設背景,還得破除不實之實;而「虛」的目的也不只在於為「實」增添娛樂效果,更負責提出解釋。就本書而言,就是要為亡者發聲,為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平反。縱然無需使源義經變作成吉思汗、無需讓胡太明化身胡志明,但處處皆實,那還寫歷史小說?這是我初次閱讀本書的過程中,最無法理解,也最為古人忿忿不平的一刻。
這時候,我剛看完了本書第七十四章,而且以為下一頁就是「劇終」。
沒想到,之後還有足足六章,交代盧夫人林氏阿好。我這才開始逐漸意識到,陳耀昌如此自制的目的。
儘管篇幅似乎分散而不平均,但他仍以盧丙丁夫婦的青壯人生做為全書的兩條主線,讓讀者看到:殖民地的政治啟蒙與文化啟蒙,兩者對殖民宗主國(戰前的日本──以及更重要、更畫龍點睛的──戰後的中國)而言,感受到的危險程度落差甚大。而這不但預示了夫婦未來走向,行將趨於崎嶇或平順,更無言地嘲諷了前後兩個殖民政權本質的差異。
一方面,政治丙丁愈受到總督府的迫害,就愈發顯露我島之曦,即彼島之暮(進入昭和時代的日本)。而藝術阿好在政治丙丁的末路晚年,不但得到殖民者(西歐現代性的亞洲代理人)青睞,居然還能短暫征服/討好下一波殖民者(啟蒙文化上的鄉巴佬),使阿好能夠保全盧氏家族性命,於下一波亂世與黑夜。
我並不是想證明文化藝術的政治騎牆性,或者音符、線條、色彩、影像的艱澀文法,較能掩飾政治不正確。我的意思是,無論政治丙丁或藝術阿好,一旦啟蒙了,就再也回不去奴隸狀態。因此盧丙丁夫婦(與當代臺灣人未來)的命運,無論再如何顛沛坎坷,都已不再是毫無自覺與自決權的原始奴隸狀態了。這就是康德(Immanuel Kant)所謂的不恃外力的精神上成年,也就是啟蒙,也就是第一道曙光。
至於天亮(啟蒙)之後,是風和日麗,還是颳風下雨,並不相干。至少,戰前的我島之曦或彼島之暮,戰後的我島之暮與彼島之曦,無論如何輪迴流轉,直至今日,西側始終是黑暗大陸。
既然《影武者德川家康》裡的德川家康,一開場就被暗殺;《三劍客》裡的主角,其實是第四個劍客,那麼《島之曦》為什麼不能陰暗絕望如暮色?光明來了,黑暗還會遠嗎?何況,如果文學四季之說屬實,即使(像我這種)仍然滿腦子諷刺文類的冬日犬儒,也不妨豁達的效法 Leonard Cohen,躲在地下室,當個自以為在寫聖經的小猶太人。
對我而言,書名之謎到此算是解開了,但只解開了三分之二。還差一個碎片,最重要的碎片。因為第一道曙光,同樣照耀在本書的變奏曲,也就是「痲瘋/癩病」──漢生病的情節上。
近代以前,「痲瘋/癩病」是「天譴」(死亡政治,至死方休),近代之後是「國恥」(生命政治,無所遁逃)。所以盧丙丁沒有被殖民者打敗,卻因罹患此病,而第一次在小說家筆下意志消沉,生無可戀。他這個體驗,是其他民族/階級運動的大小英雄們所共同欠缺的。因為這個體驗,不但如亞當、夏娃被逐出完美的伊甸樂園,還更進一步,被逐出任何不完美的人類所建構的不完美社會。罹病猶如死亡般終極平等,不分民族、階級,完全「內地延長」,毋須「一國兩制」。入樂生院者,從此人鬼殊途,只能相濡以沫,與世再無干涉。
然後,奇峰突起。盧丙丁居然空前絕後的「進出」樂生院,獲得了弔詭之至的「社會死」的瀕死體驗。這讓他在樂生院離別宴上的演講虎虎生風。他大聲疾呼,直指不同情憐惜患者的院外人「卑鄙無聊」,並呼籲病友們應團結抵抗,促使歧視者悔悟的講詞,實在遠遠超越了戰前所有殖民地抵抗運動的類型與派別、經驗與想像。
讀到這一段貨真價實、又幾乎無人得知的歷史,使我無法不聯想到2004年因捷運而被迫遷,並因而展開抗爭的樂生院民自救會的長輩們。我還記得當年院民陳再添阿伯告訴我,支持他在如此逆境中長期抗爭的原動力,是因為他「發現」自己也是人,也有人權。
第一道啟蒙曙光確然存在。儘管曾經被極力忽略掩蓋,小說家陳耀昌,仍然奮力揭開了一絲縫隙。
吳豪人(臺灣人權促進會前會長、輔仁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專文推薦二
他們的臺灣之愛與大眾之愛
長期以來,我已經非常熟悉陳耀昌的歷史小說。從最早的《福爾摩沙三族記》與《島嶼DNA》,一直到《傀儡花》、《苦楝花》、《獅頭花》,小說故事不一定相同,都大部份是以原住民為敘事主體,以及他們與外來殖民者的戰鬥與抵抗。他的筆尖所到之處,往往可以帶出讀者的燃燒魂魄。縱然故事議題有異,卻都同樣指向臺灣歷史的多元與繁複。他是一位醫生,卻擁有豐富的臺灣歷史知識,更擁有一個博大的心,容許不同的階級、族群、性別都同時登上歷史舞臺。
這種書寫策略,從文學研究的觀點來看,就是一種新歷史主義(new historicism)。所謂新歷史主義,便是以多元而複數的觀點,看待過去曾經發生的故事。從前的中國歷史書寫,如果不是以漢人為中心,就是以男性為中心,或是以異性戀為中心。這樣那樣的中心論,等於貶抑不同族群、不同性別、不同階級的生命存在。
陳耀昌歷史小說的特點,長久以來便是嘗試突破單一價值的中心論。那種片面的、獨斷的、霸權的敘述方式,曾經主宰許多帝國的歷史書寫。身為醫師的陳耀昌,顯然並不受到那種霸權式的思維方式所影響,總是以一種開放的、開闊的、開展的視野,觀察歷史舞臺上曾經演出過的種種人物。他的筆觸,不容許使用聚光燈投射在特定的族群身上,而是把整個舞臺的燈光都全部打亮。讓舞臺上出現過的演員都不會被觀眾錯過,容許所有演員公平地接受觀眾的喝彩與歡呼。
《島之曦》這部小說,是發生在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時期。曾經被稱為瘴癘之地的臺灣,必須要到一八九五年日本軍隊進駐海島之後,殖民者才開始注意到疫病的存在。所謂瘴癘,指的是霍亂、痢疾、傷寒、天花等各種流行病。漢人先民抵達臺灣時,毫無差別地遭到島上疾病的侵襲。經過長達二十五年的時間,也就是一九二○年左右流行病才慢慢地消失。日本殖民者用盡全力來對付島上疫病,並非是為了臺灣住民著想,而是為日本資本家來臺投資所考慮。不過為了長久之計,殖民者在一八九九年就設立了臺灣總督府醫學校。這部小說並非是疾病史,而是一部臺灣音樂史,也是一部臺灣工運史。
一九二○年代,是臺灣知識份子反殖民運動的黃金時期。那段期間,也是左派右派不斷結合、不斷分裂的時期。所謂右派,大約是以林獻堂為中心的知識份子團體;所謂左派,則是以臺灣農民運動、臺灣共產黨為主幹。那是一個風起雲湧的時代,無論左派右派都是受到日本現代教育的啓蒙。他們卻因為世界觀與社會觀的認識差異,而開始展開一系列的團結與分裂。這部小說的精彩之處,並非在強調抗日團體之間的矛盾與衝突,而是藉由主角盧丙丁偶然患了癩病,從此拉出一條抗日運動史,也拉出一條疾病抵抗史。
《島之曦》不同於過去的歷史小說,並非只是依照年代先後展開敘述,而是藉由疾病的惡化,來描述殖民地知識份子的兩種抵抗。一方面要對付具體可見的殖民統治,一方面也要對付看不見的疾病侵蝕。盧丙丁參與社會改革的同時,又同時要與體內的癩病對抗。整部小說最精彩之處,便是臺灣抗日團體內部發生了左右兩派的分裂。一九二七年,中國知識份子發生國共分裂,同一年日本左翼團體也發生分裂。作為政治運動下游的臺灣文化協會,也開始出現左右兩派的對峙。在臺北領導抗日運動的蔣渭水,離開他當初所組織的文化協會,另外設立臺灣民眾黨,並且也把他所發行的《臺灣民報》帶走。盧丙丁是一位真正的行動者,凡是能夠對抗日本統治者的方式,他都樂於去參與或領導。
客觀形勢的變化,往往超過殖民地知識份子的預測。不僅是殖民統治加緊對臺灣的控制,甚至疾病也開始侵襲。當時的臺灣知識份子,小說中的主角盧丙丁,在無意間染上了痲瘋病,整個故事從此便以雙軌敘述的方式,拉出殖民地知識份子的兩種困境。參與政治運動的臺灣人,眼見自己陣營的夥伴陷入疾病的痛苦,似乎也無法伸出援手。陳耀昌在描述整個故事的過程中,有意點出當時知識份子是如何展開兩面作戰。一方面是政治壓迫者,一方面是疾病侵襲者;前者屬於公領域,後者屬於私領域。盧丙丁在小說中就被置放在進退兩難的困境,既要參加反殖民的抗日運動,而自身又要進行疾病的治療。
這部小說精妙之處,便是在抗日與抗病之間,拉出一條愛情故事。小說中的女主角林氏好,是臺灣殖民史上的一位歌手。她顛覆了傳統女性的固有形象,在一九三○年代是一位相當知名的流行音樂歌手。她是當時古倫美亞(Columbia)唱片公司的專屬歌手,幾乎可以視為開時代風氣的旗手。這樣前進的一位女性,又與臺灣政治運動的主幹盧丙丁結盟,更使他們的愛情故事成為傳說。他們兩位夫妻一起走在時代的最前端,抗日運動並非只是反抗而已,他們也同時開創了社會風氣。陳耀昌在描述他們的愛情故事時,其實也融入他們的臺灣之愛與大眾之愛。他使用雙軌敘述的說法,一方面彰顯臺灣政治運動的開展,一方面也揭露私領域的愛情故事。
如果把他們的愛情故事置放在一九二○年代,就可以窺見當時政治人物的起伏升降。從意識形態的光譜來看,臺灣社會存在著從極右派到極左派的政治團體。還未分裂之前的臺灣文化協會,基本上都是由右派知識份子所領導。文協在一九二七年分裂成左右兩派,使得抗日運動的力量分散了。尤其在一九二八年臺灣共產黨成立時,極左的勢力儼然成形。中間偏左是臺灣民眾黨,蔣渭水離開了臺灣文化協會,而盧丙丁也跟著蔣渭水。面對如此強烈的形勢,熱心參與政治運動的盧丙丁不免感到失望,他的夫人阿好也感到非常失望。在整個政治形勢惡化時,盧丙丁的病情也跟著惡化。
這是陳耀昌的春秋之筆,他把殖民統治與疾病傳播拿來相提並論。盧丙丁的癩病愈來愈明顯,就像臺灣的政治運動也愈來愈惡化。從殖民地的歷史來看,一九二○年代所有的政治團體都一一遭到解散。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軍隊已經開始準備要侵略中國。整個臺灣的政治團體,如果不是被解散,就是重要成員遭到逮捕。當政治人物的活動空間被壓縮之際,也正是殖民地作家、美術家、音樂家開始尋找伸展的空間。只有文學與藝術的靜態發表,再也沒有政治言論的發抒。這樣的變化,正好緊緊扣合盧丙丁癩病的惡化。臺灣政治運動的黃金時期終於到達盡頭,殖民地知識份子不得不改變抵抗的方式,開始以文學、藝術手法來強調臺灣主體性的存在。
這部小說是陳耀昌的一次重要突破,他同時整理兩條歷史主軸,一是臺灣政治運動史,一是臺灣疾病傳播史。但更重要的是,小說加入林氏好的藝術追逐過程,正好點出臺灣文化主體性的發展。盧丙丁罹患癩病是生命中的一個悲劇,卻可以反襯殖民地知識份子的抵抗精神。他們夫妻分別投入政治運動與藝術運動,非常清楚拉出了兩條時間的演變。這可能是陳耀昌小說藝術的重要挑戰,當他投入殖民地歷史的重新建構,一方面重建臺灣命運共同體的意義,也一方面理出臺灣疾病史的脈絡,足以讓二十一世紀的讀者重新認識已經消失的文化記憶。
在某些時刻,小說並非是虛構,反而可以協助後人重新認識殖民地社會的發展過程。陳耀昌把疾病當作一種政治來看待,那是一種翻轉的書寫策略。這部小說提供了一個讓我們重新省思的管道,使我們的歷史視野更加開闊。
陳芳明(政治大學臺文所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