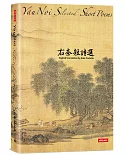編者序
百年紀念/百年永恆
「天以百凶成就一詞人」(王國維)。純粹詩人周夢蝶,因詩憔悴,劌目鉥心、憂樂生死於其中;選擇例外,「如人嘔盡一生心血只有一句詩為後世所傳誦」(〈我選擇〉)。詩人不憂歲華搖落:
瘦與孤清,乃至
輾轉反側。只恨無新句
如新葉,抱寒破空而出
趁他人未說我先說(〈花心動〉)
在詩心觀照下,生命磨難化成澄澈透亮的光與熱。周夢蝶以生命為詩,盡情的燃燒生命,面對懸臨之死,慢條斯理地說:「我喜歡慢。我要張著眼睛,看它一分一寸一點一滴地逼近我,將我淹沒……。」把與死亡的邂逅視為走赴一個秘約,一個淒絕美絕的假期,相遇相喣而又相忘。死亡並不可怕,怕的是在墓穴裡「無詩可讀」;反之,只要有詩,就沒什麼好遺憾好抱怨的。
周夢蝶有顏回情操、淵明境界,洵為當代最具思想性的傳奇詩人。武昌街書攤擺了二十一年又二十五天,愚人始,愚人終;詩創作自冥想出發,歷經雪火的往復取鑄,仍歸止於冥想,唯詩意詩境已從垂釣靜寂轉向世間人情、人性的溫馨溫慰。詩集五種,加上《風耳樓逸稿》,總數近四百首。整體詩風轉折,耙梳各詩集主題詩略可窺見端倪。〈孤獨國〉咀嚼時間,沉思「現在」,凝駐剎那照見永恆。〈還魂草〉在生與死、紅與黑、塵裡塵外矛盾掙扎;擺盪於聖與凡、形而上與形而下之間,追尋並等待「自孤峰頂上坐起」。〈十三朵白菊花〉從世界邊緣走入「裡面」,趺坐斷崖上、落照邊,默識佛咒梵音,枕流洗耳,抵拒十方三世的情、慾襲擊。〈約會〉與有情有覺的橋墩促膝密談,話尾話頭靈犀交會;高山流水印成知己,庶幾忘憂思遺形骸。〈有一種鳥或人〉自嘲為人形之鳩,鳩既得其性,詩人亦安之若素,兼得達者智者的通透灑脫。要言之,孤獨國王汲取傳統情采,溝通現代精神,兼涉東西方宗教;由苦心雕琢而至清水出芙蓉,從造境寫境而臻禪境化境。詩壇孤峰別流,一代風騷典律已然形成。
周夢蝶獨鍾花草蟲鳥等弱小微物,每每賦詩頌詠。首先,自比如蝸牛,「祇揚起沉默忐忑的觸角/一分一寸忍耐的向前挪走」(〈蝸牛〉);讚蝸牛匍匐而上椰樹頂梢,怯生生的雙角撐起錦江春色,仁、智、勇媲美諸葛武侯(〈蝸牛與武侯椰〉);稱蝸牛與先知穆罕默德站在同樣高度,同一鼻孔出氣,一起宣示真理:走總有到的時候(〈走總有到的時候〉)。其次,高度肯定螢火自覺「獨醒」的存在姿態:我是思想的燈,我是螢火,我就是我。「一隻螢火蟲,將世界/從黑海裡撈起——//只要眼前有螢火蟲半隻,你我/就沒有痛哭和自縊的權利」(〈四句偈〉),上半意如「一滴之濕,可解/百千億劫之苦之熱。」(〈急雨即事〉),一蕊微光足以劃破萬古長夜,帶來無窮的希望。至於作為個人象徵的小蝴蝶,莊嚴宣示:「世界老時/我最後老/世界小時/我最先小」;憑藉著翅膀,夢想有一天能成為天空。詩人斬釘截鐵地說:「能!當然——當然你能/只要你想,你就能!」(〈藍蝴蝶〉),因為天空是你想出來的,飛也是。如同「每一棵樹都深知,且堅信自己/會飛」,「每一棵樹皆我,我皆會飛,想飛」(〈想飛的樹〉),我和樹沒有翅膀也會飛,一直飛到自己看不到自己。
周夢蝶自謙沒有重量,不佔面積,「希望自己縮小再縮小,退後再退後,一直縮到退到小得不能再小,後得不能再後的所在——」;瑟縮在寧靜角落,瞑默思索獨身、兼身,荒涼、溫馨,自由、不自由,與何處是家、何處非家?「異鄕人的孤寂──/冷,早已成爲我的盾/我的韻腳。我的/不知肉味的/韶。」(〈不怕冷的冷〉)被迫離家超過一甲子,肉體靈魂雙重漂泊,欲溯洄來時路,倒退著回家,卻往往「鄉心纔動,已雲山千疊!」(〈七十五歲生日一輯‧不信〉)久而久之,回去或不回去?似乎也不再那麼的糾結。加斯東・巴舍拉《空間詩學》裡提及曾在某書中讀到:蝸牛造了一戶自己背著走的家屋,「不管旅行到哪鄉哪村,牠們永遠都在自己家中。」周夢蝶好似蝸牛負裹一襲沉重的城堡,跋涉於艱難人間。反正人在那裏家就在那裏,所有的流浪,不曾離家。
「詩與宗教,有其先天性之差異。宗教是素的,詩是葷的。宗教再華麗也是素;詩再沖淡,再質樸也是葷。」周公主張「生活」之外無宗教無藝術,詩是生活的證據,其本色多於情為實,而於事於理為虛。認為創作貴能「以寫實寫非寫實,以非寫實寫寫實。」明知其難,猶自拳拳期許。《約會》富有日常性、生活化特色,多借景寓情、托物寄興,而以濃稠哲思作結。如〈淡水河側的落日〉:落日同時是朝陽,昇落總在圓軌環繞;豌豆圓,菱角彎,一切所以為一切。於領受落日面面俱到的說法後,油然產生「悟識」欣喜:
如是如是。曾經在這兒坐過的
這兒便成為永遠──
淡水河永遠
淡水河側的落日永遠
觀音山永遠
永遠永遠
娑婆世界,皆是因緣聚合。具「植物性格」的周公,只一次便生生世世,成為永遠。誠然浪漫得可以。
周公凝視下的世界,生命無高下崇卑、美醜老少之別。每天,當九宮鳥一叫,灰鴿子、小蝴蝶、小花貓,及「那位小姑娘,大約十五六七歲/(略)/毫無忌憚的/把雪頸皓腕與蔥指/裸給少年的早晨看」,於是,「世界就全在這裏了」(〈九宮鳥的早晨〉);公車上,遇「老婦人,年約七十六七歲,姿容恬靜,……料峭曉氣中,特具豔姿。」於是,「春色無所不在/車遂如天上坐了」(〈老婦人與早梅〉)。小姑娘抑或老婦人,靈動雀躍和孤山之喜,詩人神思飛動,一般美好。新世紀以降,耄耋周公雲淡風清,似古剎老僧,又如返老還童,詩越寫越淺,但是詩性密度、濃度,及詩藝、詩境造極登峰。
周公自陳不懂、不會寫散文。然而,遍讀《全集》收錄的小品、札記和尺牘,文字洗鍊純淨,情感質樸真誠,兼有詩的冷靜與清醒,發人深思,意味悠長。寢饋百二十回《石頭記》數十年,心得筆記成《不負如來不負卿》。獨於「紅學」考證、索隱之外闢蹊徑、開生面。雖說效蜻蜓點水,避重就輕、淺嚐輒止,實則扼要勾稽玄旨,而有淪肌浹髓般深刻。關於《石頭記》,亦多以詩「互文」,如《風耳樓逸稿》中的〈無題〉:「我們在一冊石頭裡相顧錯愕/一如但丁與琵特麗絲的初識。」《還魂草》輯四「焚麝十九首」,典出《紅樓夢》第廿一回;〈二月〉,詠嘆神瑛侍者、絳珠仙草澆灌之恩和流淚以自懺的循環宿緣。《十三朵白菊花‧紅蜻蜓》,吃臙脂長大的紅蜻蜓,「臙脂的滋味由甜/而淡,而酸,而苦,而苦苦/而苦成一襲袈裟/苦成一闋寄生草,乃至/苦成一部淚盡而繼之以血的/石頭記。」,蜻蜓、臙脂之「紅」,皆示情根塵緣,並連結《紅樓夢》。對於寶玉口中的「絕色」——尤三姐,一詠再詠:「自石頭記第六十六回逸出/驚定痛定之後/屬於尤三姐的/夢與醒。」(〈癸酉冬續二帖〉)、「夢中之夢中夢,莫非/石頭記第六十六回之又一回?」(〈詠野薑花〉)
人道周公似寶玉轉世、曼殊再來,敏感溫柔、細膩多情而善聽,贏得眾多蘭心蕙質女子之迎擁。史安妮、洛冰、姚安莉、鄭至慧、王海若、顧蓮喜、陳媛、葛萱萱、薛幼春、嚴嬋娟……,孤獨國裡,奇女子何止十二!數十年魚雁往返,冰火交會、精神密約,風絲雨片繽紛飄落,輯作《風耳樓墜簡》。周公常說自己是罪人、無能的人,既不成人子,又慚為人夫人父。然而,能夠做到不負如來不負卿,俯仰無愧無怍者,周公之外,不知有誰!
上一世紀九零年代初識周公,開啟長達二十二年的談詩「聽說」。我們坐熟了明星、百福、老樹、逛街、紫藤廬……,「誰說雨不識字,/未解說法?」(〈急雨即事〉),縱然我是鈍之又鈍,而且懶慢。尤其每週三晚「百福」散會,挽著周公穿過入夜的臺北街道,去塔城街等公車,或開車載他返回五峰山下小屋,那段美好時光,持續將近十年。踏下的腳印,無論輕重深淺,迴響不已。
二零二一年周公百歲冥誕,《周夢蝶全集》付梓面世,藉誌紀念,亦所以饗海內外讀者。《全集》都五卷,包括詩三卷、尺牘一卷、札記一卷。邀請荷蘭漢樂逸、法國胡安嵐和美國陳耀成撰序。異國視角竟一致標舉周公詩「內傾」及符合「人性」真實的普世情感,揭示出隱匿於文字內的無言之言,頗有撫慰、淨化及提升的力量。感謝陳義芝、翁文嫻、奚密、羅智成、傅月庵、楊澤引言。諸人與周公皆有某種「近過遠過翱翔過而終歸於參差的因緣」,也都解會周公「不足為外人道」的幽微。此外,幸得掃葉工房玉成美事。作為一位出版人、愛書人,傅兄的耿介與澹泊,儼然是光。
曾進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