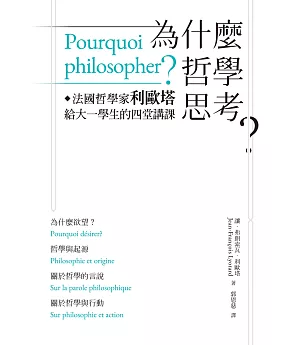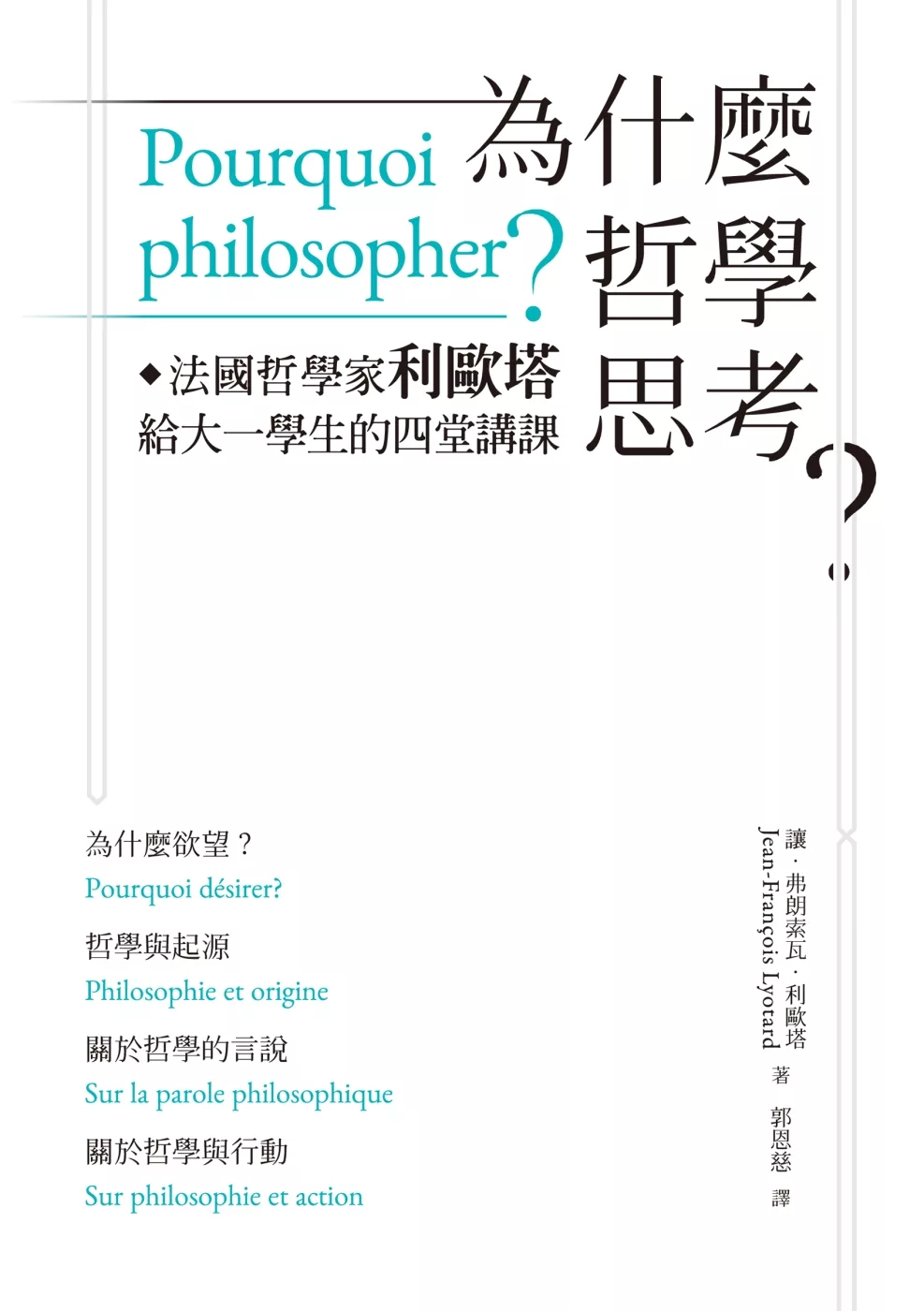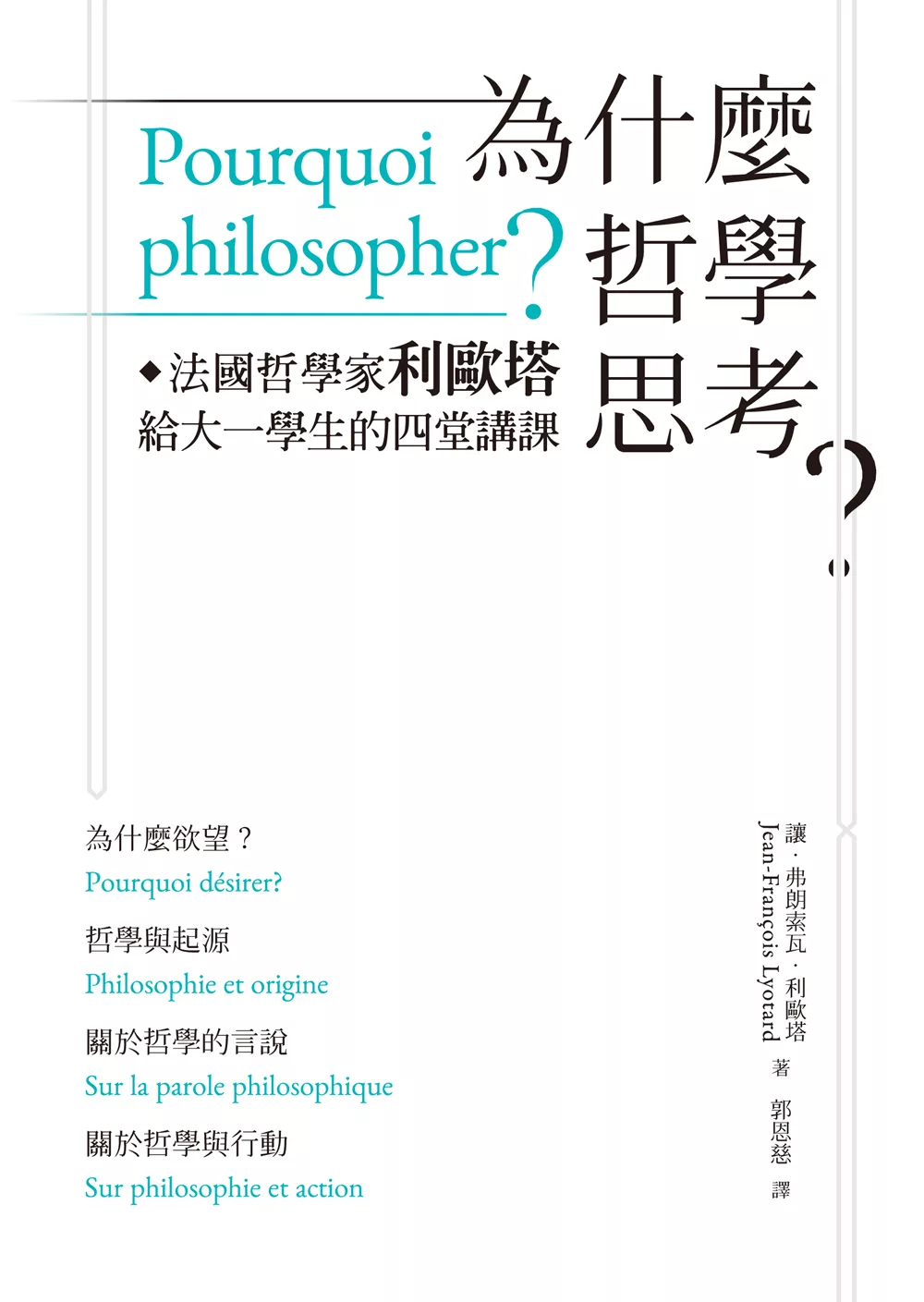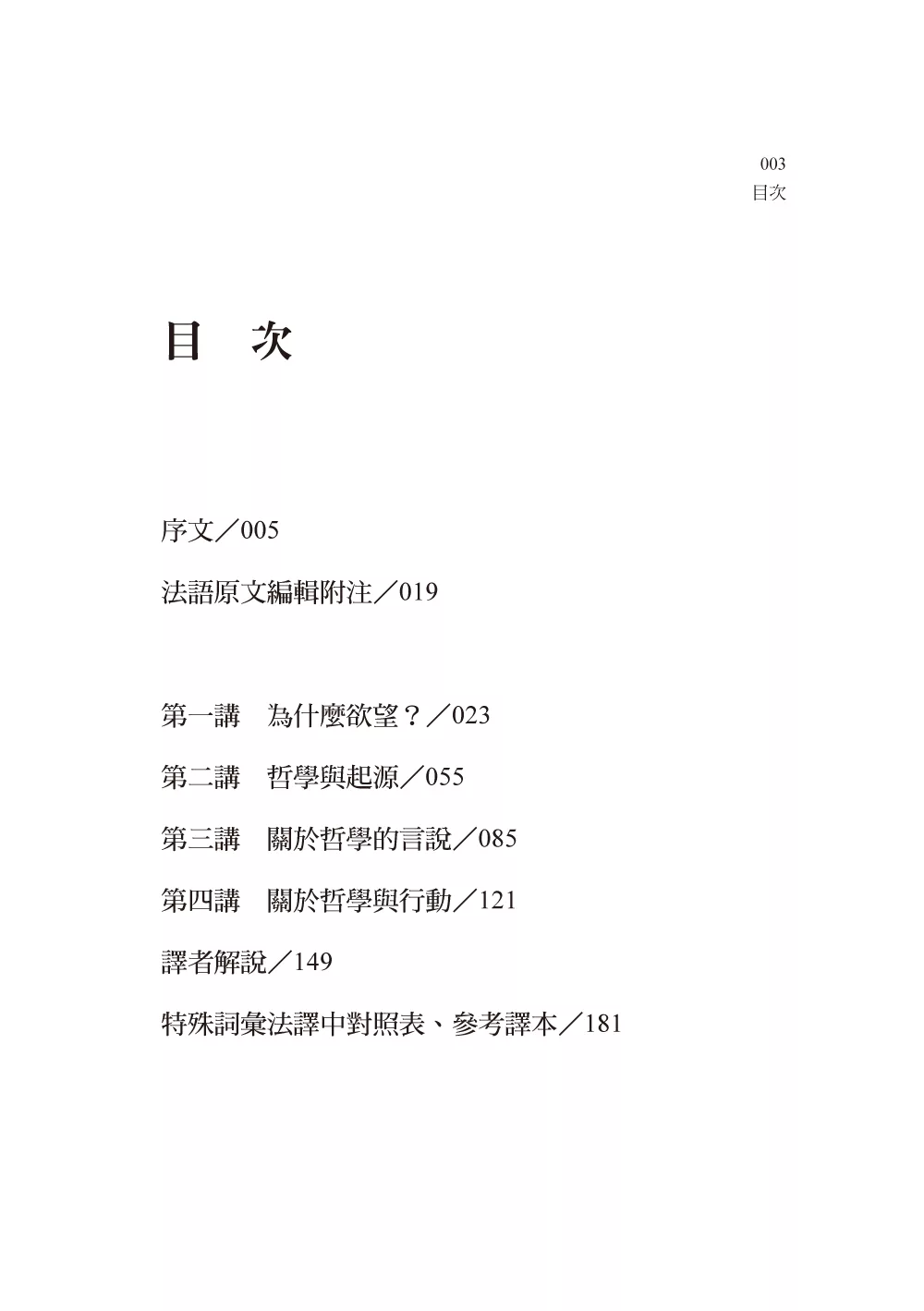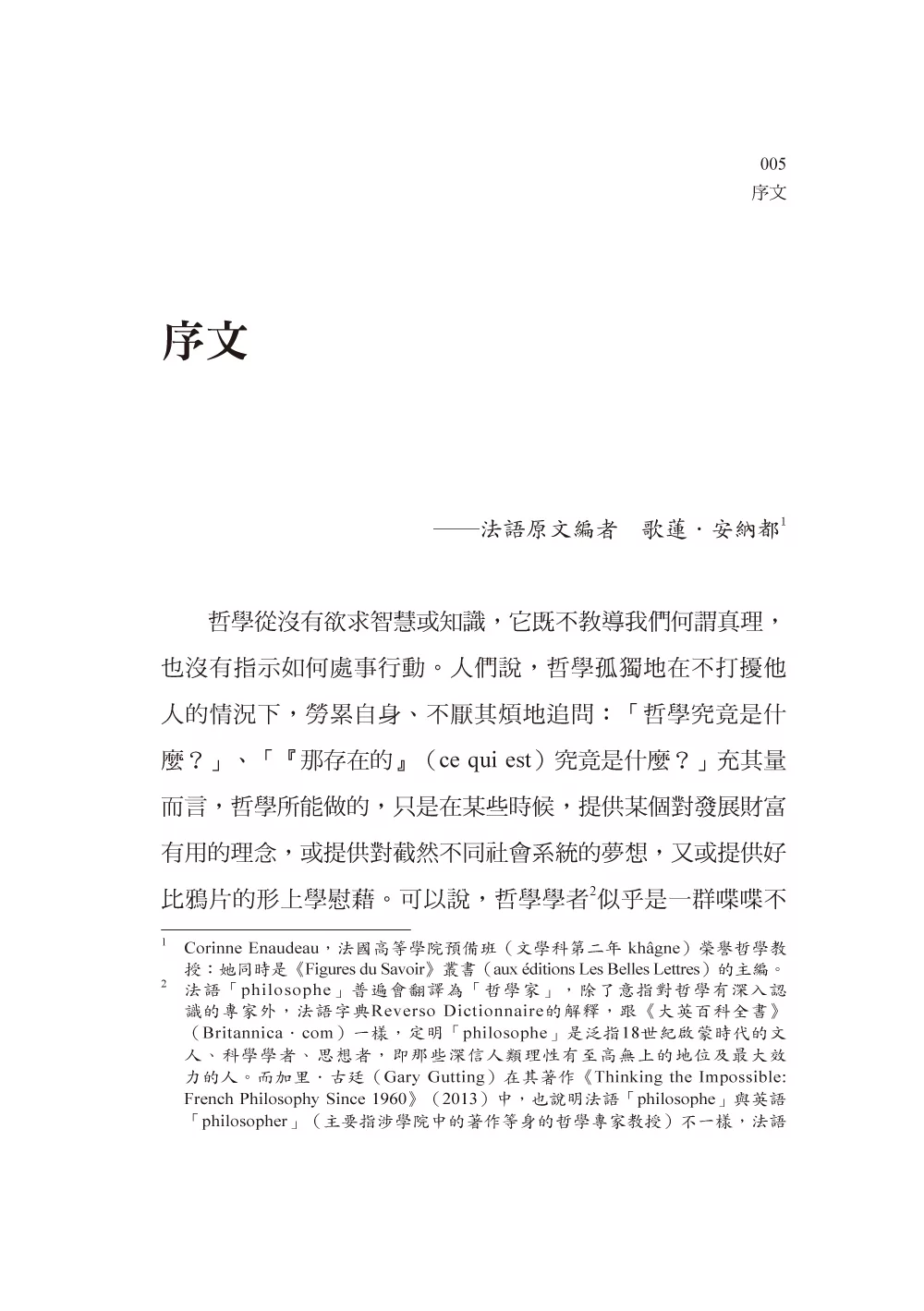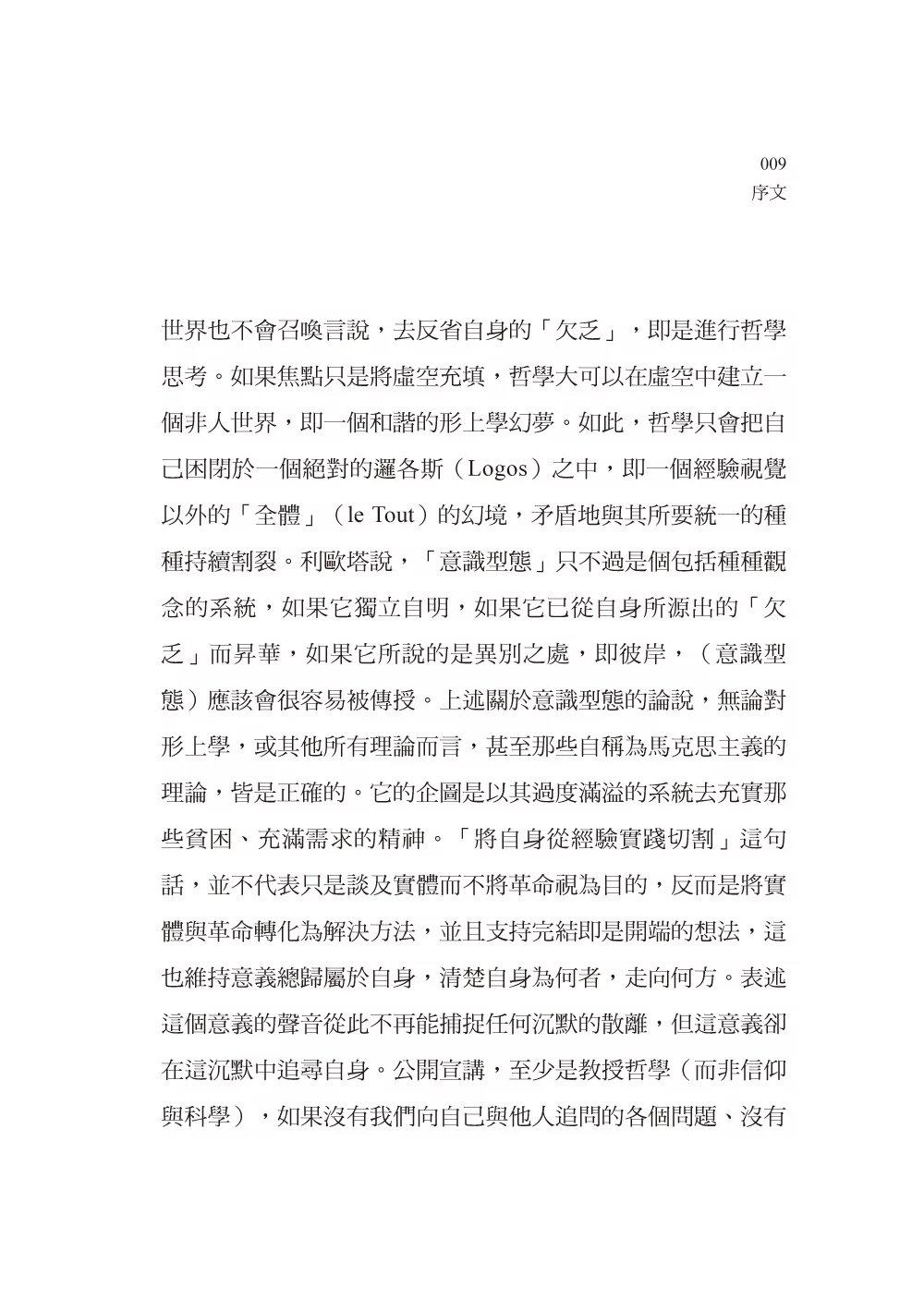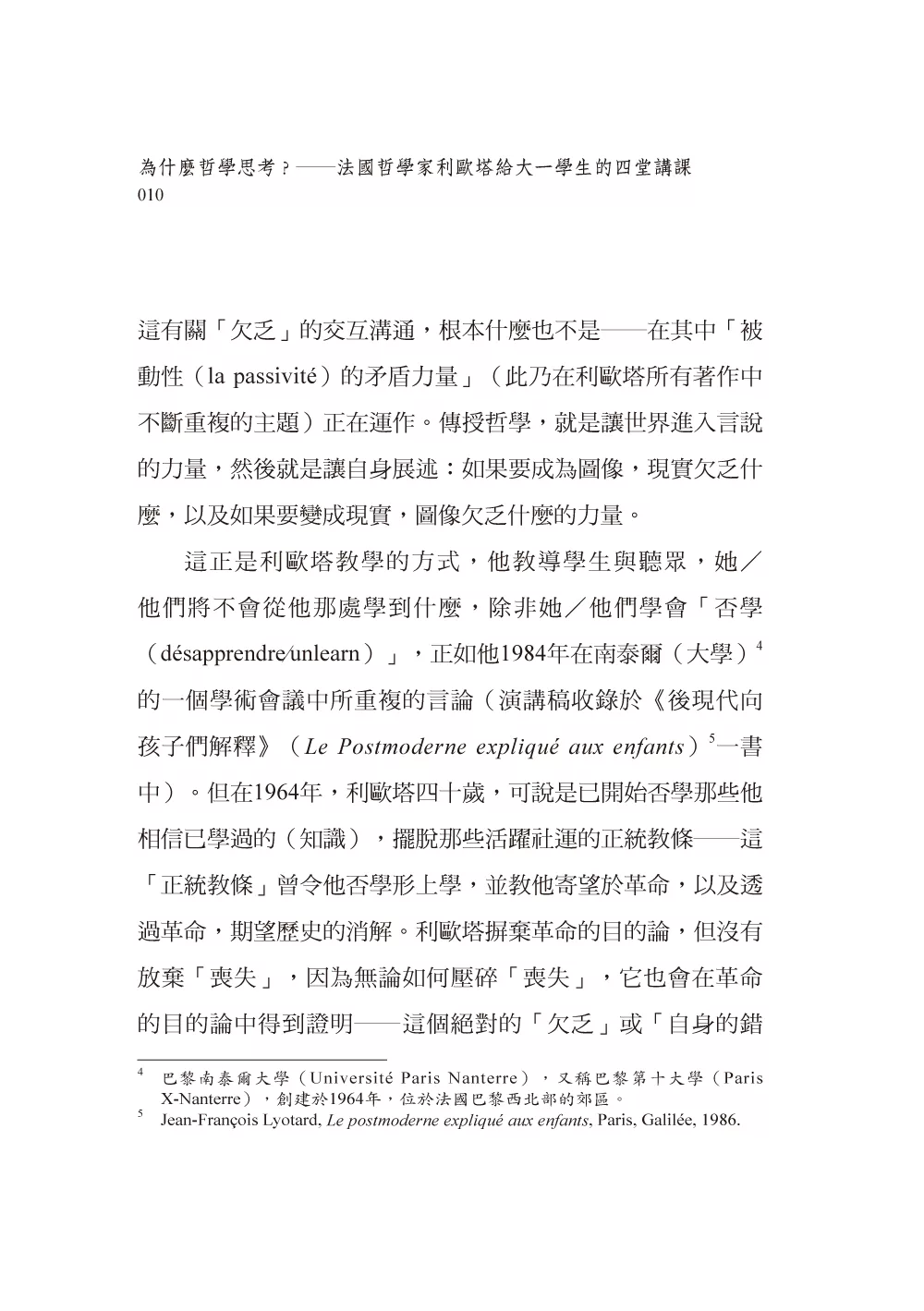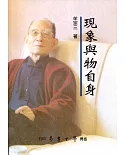序文
哲學從沒有欲求智慧或知識,它既不教導我們何謂真理,也沒有指示如何處事行動。人們說,哲學孤獨地在不打擾他人的情況下,勞累自身、不厭其煩地追問:「哲學究竟是什麼?」、「『那存在的』(ce qui
est)究竟是什麼?」充其量而言,哲學所能做的,只是在某些時候,提供某個對發展財富有用的理念,或提供對截然不同社會系統的夢想,又或提供好比鴉片的形上學慰藉。可以說,哲學學者似乎是一群喋喋不休的瘋子,人類歷史的長河乘載她/他們滾滾而流,她/他們沒有提供什麼利益,但也沒釀成什麼大的失誤。她/他們的確能夠解釋世界,但卻停在世界的大門外且從未能改變它。哲學學者的論述可以停頓,可以回歸沉默,世界的面貌卻不會有什麼改變。總而言之,哲學學者的論述,於最終極情況,總顯示一條線索:哲學與「喪失」(la
perte)總有一絲奇怪的牽絆,其欲望就是,不肯失去這侵蝕所有人類活動,並使其與自身分離的「喪失」,亦不願放棄那將死亡之釘釘入生命的「貧乏」(la
pénurie)。因此,在2012年的今日,我們仍可如1964年的讓-弗朗索瓦-利歐塔那樣追問:為什麼要進行哲學思考?人們曾經有過什麼動機,以致到在今時今日,還要去哲學思考?還有什麼理由,以那可能會被評斷為幼稚的天真,一再重新墮入意義的深淵?換個角度,這問題可以從修辭學理解:它是自我指涉的,因為它的表述其實已為發表了的問題提供答案,當我們不厭其煩地考慮是否值得重複追問這問題時,我們已經開始哲學思考了。而這也是語言自身的命運:它因為憂慮自身的中斷而必須持續發聲;這同時也是意識清醒與生命的命運―兩者不斷探究,卻又必須活生生地(in
vivo)否定抗拒的,正是沉睡與死亡。當我們在那「喪失」的威脅下說話、行動與生活時,我們就不可能從「不在」(l’absence)自顯為「現前」(la
présence),以及「現前」不斷被「不在」挖空這循環中脫離。利歐塔告訴我們,我們很難像一隻笨拙的野獸,也無法令到自己暈眩懵懂,在被給予(的環境中)不再說甚麼,在完全地完備的狀態中感到無欠乏、在夜晚無夢睡到天明。所以,我們乃是以這不可避免的唯一動機投入哲學思考:「以我們的言說(la parole)驗證了欠乏(le manque)的現前/呈現(la Présence)。」
利歐塔在1998年逝世,遺下未完成的著作《奧古斯丁的懺悔》(la Confession d’Augustin)。他當時可能只專注於這種意義還不完整的建構,這既是思想的刀又是它的傷口,是思想被灼傷的傷口,又是其不可或缺的支撐。利歐塔的一本著作《論述、形象》(Discours, figure)(1971)宣稱拒絕成立任何結論,而另一著作《歧論》(Le
Différend)(1983)則以突發的某些歷史項目,打斷了段落之間的連續性。利歐塔的每本著作,都將某種拒斥分割(la
disjunction)插進其研究對象、他的每個寫作之內,以及他的不同著作之間隔中。早在1964年他就確信,哲學的種子如能自某人心內播種生長,這人就必須容許「不在」滲入自身思維,同時帶著詭辯式的能量,將這種子散播予其他人,這好比告訴其他人有《債權法》存在,但又有些債卻是永遠不能還清的。利歐塔的整體著作使這種子得以散播與成長,對利歐塔而言,哲學寫作出現在他對教學與政治行動的熱情參與之前及期中。這種追問、教學與(社會政治)行動的生活,與其哲學工作是不可分割的。對「斷裂」(la
faille)、對於實體性的缺乏的留意,正如對意義運作的缺乏的留意一樣,已經假設了這正是「其他人」而甚於事物,將言說鑿穿孔漏;也正是「其他人」令到社會全體缺乏統一性,透過她/他們,矛盾對立將意義的統一性分裂開來。如果沒有「其他人」混淆爭論、阻撓行動、辜負滿腔熱情,「欠乏」就永遠不會走近真實(le
réel),並將之轉化為人間世界,這個世界也不會召喚言說,去反省自身的「欠乏」,即是進行哲學思考。如果焦點只是將虛空充填,哲學大可以在虛空中建立一個非人世界,即一個和諧的形上學幻夢。如此,哲學只會把自己困閉於一個絕對的邏各斯(Logos)之中,即一個經驗視覺以外的「全體」(le
Tout)的幻境,矛盾地與其所要統一的種種持續割裂。利歐塔說,「意識型態」只不過是個包括種種觀念的系統,如果它獨立自明,如果它已從自身所源出的「欠乏」而昇華,如果它所說的是異別之處,即彼岸,(意識型態)應該會很容易被傳授。上述關於意識型態的論說,無論對形上學,或其他所有理論而言,甚至那些自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皆是正確的。它的企圖是以其過度滿溢的系統去充實那些貧困、充滿需求的精神。「將自身從經驗實踐切割」這句話,並不代表只是談及實體而不將革命視為目的,反而是將實體與革命轉化為解決方法,並且支持完結即是開端的想法,這也維持意義總歸屬於自身,清楚自身為何者,走向何方。表述這個意義的聲音從此不再能捕捉任何沉默的散離,但這意義卻在這沉默中追尋自身。公開宣講,至少是教授哲學(而非信仰與科學),如果沒有我們向自己與他人追問的各個問題、沒有這有關「欠乏」的交互溝通,根本什麼也不是―在其中「被動性(la
passivité)的矛盾力量」(此乃在利歐塔所有著作中不斷重複的主題)正在運作。傳授哲學,就是讓世界進入言說的力量,然後就是讓自身展述:如果要成為圖像,現實欠乏什麼,以及如果要變成現實,圖像欠乏什麼的力量。
這正是利歐塔教學的方式,他教導學生與聽眾,她/他們將不會從他那處學到什麼,除非她/他們學會「否學(désapprendre∕unlearn)」,正如他1984年在南泰爾(大學)的一個學術會議中所重複的言論(演講稿收錄於《後現代向孩子們解釋》(Le Postmoderne expliqué aux
enfants)一書中)。但在1964年,利歐塔四十歲,可說是已開始否學那些他相信已學過的(知識),擺脫那些活躍社運的正統教條―這「正統教條」曾令他否學形上學,並教他寄望於革命,以及透過革命,期望歷史的消解。利歐塔摒棄革命的目的論,但沒有放棄「喪失」,因為無論如何壓碎「喪失」,它也會在革命的目的論中得到證明―這個絕對的「欠乏」或「自身的錯誤」,就即是剝削―這意味著利歐塔理解到,他需要說那同時說著對於「是」及「否」、「現前」及「不在」充滿模稜兩可、歧異的言說。換句話說,利歐塔以佛洛依德修正馬克思主義、以性衝動力的多義性(l’ambivalence
pulsionnelle)糾正歷史唯物論、以欲望的不確定性修正社會性的和解。簡單地說,他需要令到馬克思的聲音恢復那被黑格爾式整體化思想剝奪了的力量:這力量清楚述說割離(La
séparation)。社會與它自身的割離,世界與心靈的割離,現實與意義的割離。同時,在佛洛依德觀點而言,割離體現為:愛情與對象、男女性之間、童年時光與語言的割離。這連串的分離,利歐塔在1964年將它們稱為「對立」(les oppositions):在《論述、形象》中,它們被轉稱為「差異」(la différence),隨後更激進化為不可化約的「歧論」(le
différend):這歧論持續出現在資本家與受雇者之間,以及―儘管以相當不同的方式--出現在猶太教義與基督教義之間。對利歐塔而言,「童年時光」(Enfance)是他反覆思考超過三十年的「名號」,這題目是有關那激烈情緒:即暴露在不斷傷害語言又同時需求語言的情緒中。
於1964年,利歐塔正處於就算未知道如何開始,也需要重新思考「童年時光」的狀況。因為於人(l’homme)之內在,對人而言童年時光乃是「偏離了的軌道,充滿可能性及威脅的偏流」(根據利歐塔1984年的措詞)。於此,利歐塔「從馬克思及佛洛依德開始了他的偏流」,在這階段中,他正在道途之中、在哲學之途中:他在索邦大學教授哲學課程的期間,也於同時(短時間地)活躍於「社會主義或野蠻」(Socialisme
ou Barbarie)與後來的「工人權力」(Pouvoir ouvrier)等組織,他於1954年出版《現象學的介紹》(la Phénoménologie)(收錄於《我知為何?Que
sais-je?》文庫),當時他更在拉岡的課堂上研讀佛洛依德,庫里奧利的課程則為他扎了語言學知識的根。在上列種種狀況交雜構成的環境下,利歐塔努力讓學生聽聞「統一性」的喪失,並在他自身與學生的思維中,掏空那基於對「完全完備」的死亡的哀悼,並且於此,他錨繫上哲學的責任。
哲學論述乃是被一種充滿矛盾的熱情所激活。它的欲求是在絕對孤獨的狀態下追求自我歸屬,而這欲求卻又同時重疊著否定/拒絕歸屬於自身的願望;再者,哲學又欲求作為一種深入世界,依從於自身缺陷的言說。教授哲學,即是此矛盾歧異的體現,但這教學操作卻又包含令人走向幻滅的境界―因為教導而幻滅―如果哲學是一項「課程」,它是一個從「半站中途」啟動的課程,課程中所有徒生都背負著自身經歷與種種疑問而來參與上課。因此,哲學是一門既定學制之外的課程,如要備課就要偏離所有可參考的預設系譜,因其內容既非關乎世界之內(因哲學的追問使其與世界分隔),也並非世界之外(因其表述乃沿用在別處已說過的言說),哲學乃是指向世界(au
monde)的。如利歐塔所說,在某種距離下,我們容許事物滲入自身,但同時又與事物保持距離,好讓我們可以評斷它們。如果沒有這種「指向世界」的「受動可能性(la
passibilité)」(利歐塔1987年的用詞)―意即指向人間世界,指向人間世界那頑固地存現的「欠乏」,傳授哲學不過像是展示閃閃發亮的金銀器,無疑會令人稱羨但卻毫無核心焦點。這問題焦點假設了欲望與責任間的張力,「哲學沒有特定的欲望,[……]而是欲望擁有哲學,即如它以同樣的方式擁有任何人」。利歐塔於此補充,哲學會回頭向著這掌握著它的衝動力量,也向著哲學自身以及所有人類活動。但如果哲學自身僅滿足於這種對欲望的反思,思想仍會不能歸還它所負的債。
對1964年的利歐塔而言,哲學是一項實踐,如同精神分析對佛洛依德來說是一項醫學臨床實踐。重要之處,乃是社會生活所欠乏的,不是為了使社會與自身和解,而是為了使社會確認自身的正當性。馬克思從那「絕對的欠乏」釐清一個架構―他稱之為「無產階級」,這個架構雖然是無法容忍的,但它沒有指出「社會的真實欲望為何」,這與正統馬克思主義所宣稱的互相違背。因此我們必須確認這欲望的不透明性,與它的沉默溝通共處,並冒險去試著解釋,那在人與人之間的種種關係中瀰漫流連、早已存在但隱而不宣的意義。利歐塔將這四次講課中最後一講的範圍集中在「哲學與行動」,這是因為哲學面對那「欠乏」的責任,正與政治的債欠面對著世界是不可分割的:責任與「債欠」,共同維持將沉默轉化成言說、被動轉化為行動的賭注。
於此,我們可見到兩種同時並行的信念。首先,透過梅洛龐蒂而承傳自胡塞爾,哲學家正是將沉默的經驗,提升到正確意義的表達之層面。另一項信念繼承自馬克思,即哲學家解釋世界只是為了協助它的變革。這兩項信念將分別於討論「言說」的第三講,以及關於「行動」的第四講深入討論。第一講致力於討論欲望。透過拉岡,上承自佛洛依德,提及任何因「現前」衍生的關係,皆是基於「不在」的背景而成立的。第二講論及欲望如何與語言及行動扣繫連結,哲學不斷重複的努力,細緻地討論,在其歷史發展中,那統一性的喪失,以及這喪失的保存。如果依照正確順序,「為什麼哲學思考?」這問題的處理會如此展開:投入哲學思考的理由是我們欲望,而欲望同時重疊了它對自身運動的追問。促動這反思的理由是統一性已經自行喪失:並非由於這(統一性之)喪失隱沒於根本性的消失,而致令我們忘記直至統一性本身,這(喪失)其實是發生在歷史的開展中,即發生在真實與意義之間的配接總是漏失不能掌握,而兩者的配接一而再、再而三地嘗試實現,卻總又趨歸喪失(在那段歷史中)。實則而言,在以下情形,我們不會進行哲學思考:(一)如果我們不說話,又或如果我們不能說任何話,我們就停止說話了;(二)如果世界的靜寂詛咒論述,而將之化為漫無目的之絮語;(三)如果有一邏各斯與世界並存共生,已將一切都說了出來,並令到文字注定除了一再重複這邏各斯,別無其他可能。這正是「世界透過童年時光抓緊著我們」,被世界抓緊的傷口令到哲學學者開口說話,並給予她/他這「被動的能力」,以證明那已存在的意義,即那使其論述總是未能完整的裂碎的意義,然而卻因此而真確。因為世界侵蝕我們,言說可以透過表達世界而(倒過來)侵蝕世界,而行動則可變革它。我們投入哲學思考,正是因為我們被展示在世界中,同時我們有「命名那應當被說出的、與被作業的(事物)之責任」。
如果哲學思考意味著容許我們被「欠乏」掌控,而我們只是佐證這欠乏,但沒有補足填滿它,如果從事教學,就是去釐清我們不了解自身的部分,那麼於此,利歐塔的課程可以是說教式/依書直說的,幾乎可說是被悖論所操縱:即在不同生命層面之間,就像不同學科界域的邊界之間,依照特定方法交錯逾越,由此將欲望、時間、言說與行動,圍繞著(作為主軸的)「現前」與「不在」之間所形成隱形邊界,而綑織結連。如果有某人記得利歐塔繼本書之後,七年後寫成的著作《論述、形象》(Discours,
Figure)中,致力於以「爆裂」作為討論的主題,相比之下,對這某人來說,利歐塔是次的四講課程也許過於依書直說了:利歐塔在1964年所構思的講述,可說是令到欲望過於快樂、言說太過貼近肉體性(trop
charnelle)、時間太過統一且行動過於激昂。死亡,陰魂不散地籠罩生命,很快就不再能讓自身適應於「欠乏」之中,或在信仰中自我抑制,作為潛藏意義;在結構被散碎的「形象性」(figural)中,或在那令人窒息的叫聲之中密封了的「歧論」(Le
Différend)、死亡使自身更清澈銳利。無論(不同時代的)哲學思想如何一代又一代地曾經多少次重複修正,它們皆事先自身驗證為正當,因為直到目前,「在歷史長河中,並不止一位哲學家―首先是柏拉圖,或者康德、胡塞爾―各人皆在生命歷程中,實踐過同樣的批判,自身回歸到種種曾反覆思考的,將其拆解,並又再重新思考,各哲學家因此證明,她/他們的著作的真正統一性,乃基於統一性的喪失而產生的欲望上,而非基於對完整建構的系統、重新掌握統一性的自滿」。所謂「重新開始」並非從零開始,恰恰相反,這種素樸單純是個過分誇大的願望:有關此點,利歐塔將會在本書較後章節闡述革命概念時也會一併展示。利歐塔與歷史學家的辯論,正如他對「時間」的多重分析一樣,有關歷史的敘述(無論所指的歷史為何),我們都好像持續卡陷在一個旋轉輪,在其中如不是從脅迫著的枷鎖掙脫,就是被壓制的枷鎖所拘繫。毋庸置疑地,哲學於此找到拷問自身語言、追尋自身規律(之途徑),以及--如利歐塔在這本書說的--「惹惱所有人」的理由。
法語原文編者 歌蓮.安納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