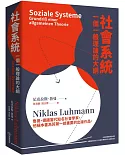序言
「蝠」蝶效應
如今,這顆《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口中「刺刺的病毒小球」遍布了整個世界。一月下旬,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埃克特(Alissa Eckert)及她的同事希金斯(Dan
Higgins)受命繪製二○一九冠狀病毒的樣貌。埃克特後來向《紐約時報》解釋,為了要「吸引公眾注意」,他們畫出一個銀色的球體圖像,上面有明亮的大紅色突起物。這張圖果然引起軒然大波和眾人的不安,很快便隨處可見,出現在報紙、雜誌和電視新聞上。如果現在要在腦中想像冠狀病毒的樣子,八成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埃克特及希金斯繪製的版本或其衍生的圖片。專業醫學繪圖家的品味都很有趣,比如這張圖是採所謂的「特寫鏡頭」(beauty
shot),近距離描繪了單株病毒株的模樣,所以看起來既危險又巨大。但實際上,二○一九冠狀病毒的大小只有這個句子結尾的句號的萬分之一。
人們常說我們要從大處著眼,但也許現在我們需要開始思考細節。無論軍事攻擊、入侵這類典型的巨大威脅有多罕見,我們都很善於想像它們的樣貌,也善於制定大規模計畫去回應。各國政府花費上兆美元建立龐大的軍隊,追蹤全球軍隊的動向,並針對潛在敵人進行軍事演習。光是美國自己每年的國防預算就高達約七千五百億美元。但面對小小的病毒,我們卻沒有事先做任何防備。結果,這樣一顆小小的病毒將為人類帶來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傷害。
這本書不是在寫二○一九冠狀病毒的疫情,而是關於疫情大流行之後的世界將變成什麼模樣,以及更重要的,我們該如何因應後疫情時代的生活。每次巨大衝擊的後果,都會根據當時世界的狀態,根據人類的反應是恐懼、拒絕承認還是適應,而有所不同。在如今這個大家脣齒相依的世界中,二○一九冠狀病毒肆虐帶來的影響,也不同於以往。大多數國家都無法及時回應這場疫情,甚至連最富有國家在內的許多地區,後來都紛紛封鎖了邊界和經濟活動,這在人類史上幾乎不曾見過。
這本書寫的是「後疫情時代的世界」,之所以寫這個主題,不是因為我們擺脫了二○一九冠狀病毒,而是因為我們跨過了一道很關鍵的坎。在這之前,幾乎所有還活著的人都從未經歷過大瘟疫,但二○一九冠狀病毒讓我們知道了疫情大流行是什麼樣子。我們都看到了疫情帶來的挑戰,以及為此付出的代價。這場疫情很可能會持續下去,但即使我們消滅了這個疾病,未來肯定還會爆發其他傳染病。這次疫情獲得的知識和經驗,讓我們走入了後疫情的全新時代。
二○一九冠狀病毒疫情究竟造成了哪些後果?有人認為,這場瘟疫將會被視為現代歷史的關鍵時刻,將永遠改變世界的走向。另外有些人認為,疫苗問世之後,世界很快就會恢復成以往的樣子。還有一些人認為,與其說這場疫情改變了歷史,不如說是在加速歷史的進展。目前看起來,最後一種猜測最可能為真。列寧曾說過:「有時可能幾十年都沒有大事發生,但有時也可能在短時間內一口氣發生幾十年才出現一次的巨變。」後疫情時代的世界就是如此,未來的世界在很多方面都會比不久之前變化得更快速。但當生活快速變遷,許多事情的發展就會開始逸出常軌,很可能引起混亂,甚至致命。一九三○年代,許多發展中國家正以穩定的步伐走向現代,人們漸漸棄農從工。蘇聯卻決定粗暴的加速進展,推行了農業集體化,最後導致饑荒、數百萬農民遭到「肅清」(liquidation),更加鞏固獨裁統治,讓整個蘇聯社會慘不忍睹。如今,若我們以飲鴆止渴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未來可能也會發生意料之外的悲劇。
對國家、公司,特別是個人來說,疫情後的生活將大不相同。即使經濟和政治恢復正常,人們也不會再以過去的方式生活。人們將經歷一場不尋常的艱難考驗,並且發現一個全新的難得機會。麥斯威爾(William Maxwell)一九三七年出版了一部小說《他們像燕子一樣襲來》(They Came Like Swallows),書中的一個角色從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中倖存了下來,一股「奇妙的感覺縈繞不去。無論是他還是別人,從來沒有人能知道他的人生會變成這樣」。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一九三九年的半自傳小說《蒼白的馬,蒼白的騎士》(Pale Horse, Pale Rider)也描述了西班牙流感結束後的經驗:當最糟的時刻過去,我們會突然「冷靜下來」。該書的最後一句就是:「現在所有事情都該重新開始。」
瘟疫的力量
照理來說它不該這麼陌生。那株冠狀病毒或許是新型的,但大瘟疫卻源遠流長。最早的西方文學開頭就是一場瘟疫。荷馬的《伊利亞德》(Iliad)的最初幾句,就是在描述希臘軍隊正遭受瘟疫的蹂躪,這是給他們自負、貪婪、好鬥的領導人阿伽門農國王的天譴。西方第一部嚴謹的歷史著作也是在一場瘟疫中展開,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記錄了當時兩大超級強國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長期衝突。修昔底德寫道,在戰爭開始之初,一場可怕的瘟疫席捲雅典,大批身強體壯的市民死於非命,就連城邦裡舉世無雙的領袖也命喪黃泉。雅典是民主社會,斯巴達則是以嚴格聞名的勇士社會,兩地的政治制度南轅北轍。歷史上贏的是斯巴達,不過要是沒有瘟疫的話,贏家就很可能變成雅典,那可能會讓西方歷史走向一條不同的路,讓一個充滿活力的民主國家成為成功的典範,而非一團一瞬即逝的火焰。瘟疫就是有這麼大的力量。
史上影響最慘烈的大瘟疫莫過於腺鼠疫(bubonic
plague),一三三○年代始於中亞,接下來十年傳播到歐洲。一位中世紀的編年史家認為蒙古人使用了歷史上第一種生化武器,將得瘟疫而死的屍體以投石機投入熱那亞(Genoese)城內,從而將疾病傳入歐洲大陸。但更可能的是,腺鼠疫是靠全球貿易傳播的,商隊和船隻將貨物從東方運送到西西里島的墨西拿(Messina)以及法國的馬賽這些主要港口,腺鼠疫就跟著貨物上路。這種傳染病又稱為黑死病(Black
Death),細菌寄生在老鼠背上的跳蚤上,會攻擊患者的淋巴系統,導致前所未見的苦難,不計其數的人死去,歐洲人口頓時少掉一半。這個疾病跟其他許多疾病一樣,目前從未完全根除,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報告,每年仍約有幾百個病例,幸好現在可以用抗生素治療。
腺鼠疫在當時的歐洲投下震撼彈。學者認為,這個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數過於龐大,把當時的經濟搞得天翻地覆。史丹福大學歷史系教授謝德爾(Walter
Scheidel)說,疫情造成勞動力稀缺,土地放著沒有人用,於是工資上漲、租金下降。勞工有更大的議價權,貴族則逐漸無權置喙。農奴制在西歐大部分地區逐漸消亡。當然,各國所受影響因經濟和政治結構而異。某些高壓統治的地區,腺鼠疫過後反而愈來愈不平等,例如:東歐的貴族地主利用苦難和混亂,首次收緊控制,實行了農奴制。這場大瘟疫除了上述物質方面的影響,還引發了一場思想革命。許多十四世紀的歐洲人開始問:「為什麼上帝會允許地獄降臨在人間?」並質疑原來根深柢固的階級制度,最後這些思想改變使歐洲脫離了中世紀的痼疾(medieval
malaise),掀起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在一片死亡和恐怖之中,科學、現代化和文明演進如焉誕生。幸好,二○一九冠狀病毒並不像過去的大瘟疫那樣造成屍橫遍野。但這場當代的大瘟疫是否會像過去一樣激發社會反省,讓我們不再驕矜自滿?
歷史學家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撰寫了一部影響深遠的著作《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他為了找出少數歐洲士兵能夠迅速征服並改變美洲數百萬人的原因,而對流行病學產生興趣。像是西班牙探險家柯爾特斯(Hernan Cortes)的遠征軍只有六百人,卻征服了幾百萬人口的阿茲特克帝國(Aztec
Empire)。麥克尼爾發現答案與瘟疫有關。西班牙人不僅帶來了先進的武器,還帶來了天花等疾病,他們自己對天花已經有了免疫力,但當地的原住民卻沒有。隨後爆發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數很驚人,一開始估計死了三○%的人,十六世紀估計六○%至九○%,總共大約數以千萬計的人死去。麥克尼爾想像,「當時原住民看到死亡的全是印地安人,西班牙人卻毫髮無傷,心裡應該受到了衝擊。」他推測當時的原住民認為,外國人之所以不怕瘟疫,是因為崇拜強大的神祇。許多原住民後來屈服於西班牙人的控制,並皈依基督教,可能也與此有關。
至今仍讓我們印象深刻的疫情大流行是西班牙流感,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重創了世界,殺死五千萬人,超過戰爭中死亡人數的兩倍。它之所以被稱為西班牙流感,並非因為它起源於西班牙,而是因為這個國家當時並未參戰,所以沒有審查新聞。當疫情爆發時,整個西班牙都大肆報導,後來新聞傳到了國外,讓許多人誤以為這場瘟疫源於西班牙。自二十世紀以來,科學進展突飛猛進。當時還沒有發明電子顯微鏡,也還沒有抗病毒藥物,沒有人見過病毒的本體,也不知道如何治療這種新興的感染。儘管如此,當時的衛生當局制定了三個最重要的方針:社交距離、口罩和洗手。在疫苗研發出來之前,這三項依然是今日用來減緩二○一九冠狀病毒傳播的重要機制。只不過當代還會再加上一項方針:定期檢驗。
近十年來,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MERS)、禽流感、豬流感和伊波拉病毒陸續爆發,每一次都傳播得又快又遠,讓許多專家紛紛警告,我們很快將面臨一場真正的全球疫情大流行。這也引起了公眾的關注。一九九四年,普雷斯頓(Richard Preston)的暢銷書《伊波拉浩劫》(The Hot
Zone)詳細介紹了伊波拉病毒的起源。二○一一年的電影《全境擴散》(Contagion)則根據二○○二年至二○○三年的SARS疫情和二○○九年的豬流感大流行,虛構了一種奪去全世界兩千六百萬人性命的病毒。二○一五年,蓋茲(Bill Gates)在TED演講中警告說:「未來幾十年內會殺死一千萬人的,很可能是高度傳染性的病毒。」二○一七年,他在慕尼黑安全會議(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上又更大聲疾呼,未來十至十五年,將可能爆發一場全球疫情大流行。
照理來說,當時的狀況應該很容易讓我們知道得投入更多時間、資源和精力去預防下一場疫情才對。但二○一七年六月,川普總統卻提議削減處理公共健康和疾病的關鍵機構預算。當時我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節目中引了一段話來談論這個話題:
美國最嚴重的威脅根本就不是什麼巨大的敵人,而是非常微小,小到得用顯微鏡才看得到,比針頭還要小幾千倍的東西。無論奪人性命的病原體是人造的還是天然的,都會引發全球健康危機,而美國目前卻完全沒有做好準備。……才不過一百年前,一九一八年的西班牙流感就造成全球約五千萬人殞命,而我們現在的世界在許多方面都比當時更加脆弱。密集的城市、戰爭、自然災害和國際航空旅行,讓致命病毒可以在非洲小村莊裡流傳之後的二十四小時內,傳播到包含美國的世界各地。……生物安全(Biosecurity)和全球大流行是無視國界的。在病原體、病毒和疾病面前,人人都無法倖免於難。當危機來臨時,我們會希望自己有更多的資金和更多的全球合作。但到那時候才這樣想就太遲了。
現在確實是太遲了。明明有夠多的資訊為我們敲響警鐘,我們卻沒有及時應對二○一九冠狀病毒。而且除了二○一九冠狀病毒疫情的具體危機,我們還得同時意識到既有的體系也可能會有所改變。
冷戰結束後,世界進入了新的國際體系,由三種力量鼎立:地緣政治力量、經濟力量和技術力量,換個方式說:美國強權、自由市場和資訊革命。所有人似乎都在為創造一個更加開放和繁榮的世界共同努力。但這個世界依然危機重重,其中有一些危機甚至會失控,比如之前的巴爾幹半島戰爭、亞洲金融崩潰、九一一恐怖攻擊、全球金融危機,再到現在的二○一九冠狀病毒。儘管這些危機的成因大不相同,但有一個關鍵共通點:他們都是不對稱的(asymmetric)衝擊,都是從很小的事情開始,最後影響波及整個世界。當年的九一一事件、二○○八年經濟海嘯,以及二○一九冠狀病毒,就是讓全世界都刻骨銘心的經典案例。
震驚全球的九一一恐怖攻擊,讓人們開始注意許多西方國家都經常忽略了世界上的某一種反彈力量。攻擊事件使眾人開始關注伊斯蘭激進派的憤怒、中東的緊張局勢,以及西方國家與這兩者之間的複雜關係。該事件還激起美國強烈反應,不僅擴大了龐大的國內安全機構、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發動戰爭,還對許多地方出手。據估計,美國在所謂的「反恐戰爭」(War on
Terror)上總共花費了五.四兆美元;並製造了流血衝突、革命、鎮壓和難民,它造成了數以百萬計的傷亡,直至今日,餘波仍未停止。
二○○八年金融海嘯則是另一種衝擊。經濟崩盤在歷史上很常見,景氣好的時候,資產價格水漲船高,同時也引發投機行為,進而讓市場泡沫化,最後無可避免的走向崩盤。這場危機始於美國,但很快就蔓延到全球,讓全世界陷入了自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後來實體經濟復甦緩慢,但市場迅速漲回,拉大了資本和勞工之間的差距。這場危機也為政治帶來複雜且負面的影響。金融海嘯的起源明明是私人公司的力量過於龐大,許多國家卻沒有因此提出更左派的經濟政策,反而文化思維慢慢趨於保守。經濟上的焦慮也讓人們產生文化焦慮,一邊對移民產生敵意,一邊渴望回到過去熟悉的生活。右翼民粹主義在西方的勢力愈來愈強。
現在我們又面臨了第三次衝擊,這場衝擊可能最為劇烈,也最為全球化。二○一九冠狀病毒一開始只是中國的衛生問題,卻很快蔓延到全球,引爆了一場大混亂。這場疫情危機導致全球所有商業活動停擺,經濟陷入大癱瘓。從某些層面來看,這場因流行病造成的經濟損失,已經可以與當年的經濟大蕭條相提並論。未來幾年,許多國家將各自出現不同的政治影響;而恐懼、孤立、人生失去方向等社會與心理衝擊則可能會持續更久。二○一九冠狀病毒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都畫下了又深又久的印記,而且我們現在甚至還不夠清楚究竟會有哪些印記。
這三次大規模的全球危機,都源自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九一一恐怖攻擊的源頭只是十九位年輕人,他們利用和四千年前青銅器時代沒兩樣的簡單粗糙小刀,使世界各地掀起了一股戰爭、間諜戰、反抗和鎮壓的浪潮。全球金融危機則源於總是游移在灰色地帶的「信用違約交換」(credit default swap,
CDS),它是一種針對抵押貸款的保單,銀行把CDS包裹再包裹,然後分割出去,出售再出售,最後滾出一個四十五兆美元的市場,價值高達美國經濟規模的三倍,全球經濟規模的四分之三。這個市場一崩潰,全世界的經濟便牽一髮而動全身,最後更掀起一波民粹主義浪潮。要是沒有信用違約交換,川普後來也不會選上總統。
這次的二○一九冠狀病毒則提醒我們,蝴蝶效應真的會在現實中發生。一隻蝴蝶拍個翅膀,可以影響地球另一邊的天氣;一撮微小的病毒粒子搭上中國湖北省的蝙蝠翅膀,可以讓整個世界陷入一團混亂。許多小小的改變都能造成巨大的影響。在電網及電腦網絡中,某些微小的元件故障,會使負載移轉到另一個元件上,造成那個元件負載過大而故障,接下來就引發連鎖反應,問題愈滾愈大,從原來的小漣漪變成滔天駭浪。這就是所謂的「連鎖事故反應」(cascading
failure),一個軟體故障或變壓器壞掉就能讓整個系統停擺。生物學也有類似的「缺血連鎖反應」(ischemic cascade),輕微的血液感染可能導致輕微的血栓,連鎖反應下去可能變成嚴重中風。
過去的人把流行病(epidemic)視為人類沒有能力解決或沒有責任解決的問題。流感的英文「influenza」源於義大利,古代的義大利人以為感冒與發燒是因為受到星星的影響(influence)。但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人們的觀念也開始轉變,開始歸納問題發生會出現哪些特徵,藉此找出預防與解決的方式。法國人開始將流感稱為「grippe」⸺⸺來自「seizure」(意思是發作)這個詞,可能是指喉嚨或胸腔感受到的緊繃感。自一九九○年以來,大約每十年就會因為連鎖反應而發生一次大問題(seizure),讓整個世界動彈不得(gripped)。二○一九冠狀病毒這種事件未來還會更多,它們既不是有人刻意為之,也不完全出於偶然,比較像是我們整個跨國體系之中內建的某種機制。我們需要做的事情是去了解這個體系,或者應該說,我們需要了解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才能夠理解後疫情時代究竟會變成什麼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