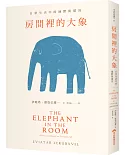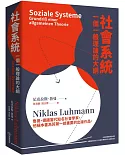內容簡介
本書透過「醫療史」觀察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變遷和政治轉變,角度新奇,不乏趣味性。內容涉及中國人在西醫治療下的身體感受、個體如何在新的社會空間裡得到安置,以及這些安排在相關治理體系的配合之下是如何被制度化的,最後則試圖辨析這種制度化設計在某一特定時刻如何轉換成了廣泛的政治動員。概而言之,全書主題可提煉出以下幾個關鍵詞:身體、空間、制度和社會動員。以此為線索,讀者可以尋覓出一條從醫療史角度觀察中國政治變遷的新路徑。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楊念群
中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史學理論研究所所長,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
主要著作有:《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三大知識群體互動的比較研究》(一九九七),《楊念群自選集》(二〇〇〇),《中層理論:東西方思想會通下的中國史研究》(二〇〇一),《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史》(合編,二〇〇三),《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主編,二〇〇四),《昨日之我與今日之我——當代史學的反思與闡釋》(二〇〇五),《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二〇〇六),《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二〇一〇),《五四的另一面:「社會」觀念的形成與新型組織的誕生》(二〇一九)等,主持《新史學》叢刊(中華書局版)及「新史學:多元對話」系列叢書。主要學術興趣是中國政治史、社會史研究,並長期致力於從跨學科、跨領域的角度探究中國史研究的新途徑。
楊念群
中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史學理論研究所所長,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
主要著作有:《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三大知識群體互動的比較研究》(一九九七),《楊念群自選集》(二〇〇〇),《中層理論:東西方思想會通下的中國史研究》(二〇〇一),《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史》(合編,二〇〇三),《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主編,二〇〇四),《昨日之我與今日之我——當代史學的反思與闡釋》(二〇〇五),《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二〇〇六),《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二〇一〇),《五四的另一面:「社會」觀念的形成與新型組織的誕生》(二〇一九)等,主持《新史學》叢刊(中華書局版)及「新史學:多元對話」系列叢書。主要學術興趣是中國政治史、社會史研究,並長期致力於從跨學科、跨領域的角度探究中國史研究的新途徑。
目錄
自序:當手術刀插入中國人身體的時候,到底發生了什麼? 001
「地方感」與西方醫療空間在中國的確立 005
「蘭安生(John B. Grant)模式」與民國初年北京生死控制空間的轉換 075
北京地區「四大門」信仰與「地方感覺」——兼論京郊「巫」與「醫」的近代角色之爭 113
附錄:如何從「醫療史」的視角理解現代政治? 207
作者簡介 231
著述年表 232
「地方感」與西方醫療空間在中國的確立 005
「蘭安生(John B. Grant)模式」與民國初年北京生死控制空間的轉換 075
北京地區「四大門」信仰與「地方感覺」——兼論京郊「巫」與「醫」的近代角色之爭 113
附錄:如何從「醫療史」的視角理解現代政治? 207
作者簡介 231
著述年表 232
序
總序
陳平原
老北大有門課程,專教「學術文」。在設計者心目中,同屬文章,可以是天馬行空的「文藝文」,也可以是步步為營的「學術文」,各有其規矩,也各有其韻味。所有的「滿腹經綸」,一旦落在紙上,就可能或已經是「另一種文章」了。記得章學誠說過:「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我略加發揮:不僅「良史」,所有治人文學的,大概都應該工於文。
我想像中的人文學,必須是學問中有「人」─喜怒哀樂,感慨情懷,以及特定時刻的個人心境等,都制約着我們對課題的選擇以及研究的推進;另外,學問中還要有「文」─起碼是努力超越世人所理解的「學問」與「文章」之間的巨大鴻溝。胡適曾提及清人崔述讀書從韓柳文入手,最後成為一代學者;而歷史學家錢穆,早年也花了很大功夫學習韓愈文章。有此「童子功」的學者,對歷史資料的解讀會別有會心,更不要說對自己文章的刻意經營了。當然,學問千差萬別,文章更是無一定之規,今人著述,盡可別立新宗,不見得非追韓摹柳不可。
錢穆曾提醒學生余英時:「鄙意論學文字極宜著意修飾。」我相信,此乃老一輩學者的共同追求。不僅思慮「說什麼」,還在斟酌「怎麼說」,故其著書立說,「學問」之外,還有「文章」。當然,這裡所說的「文章」,並非滿紙「落霞秋水」,而是追求佈局合理、筆墨簡潔,論證嚴密;行有餘力,方才不動聲色地來點「高難度動作表演」。
與當今中國學界之極力推崇「專著」不同,我欣賞精彩的單篇論文;就連自家買書,也都更看好篇幅不大的專題文集,而不是疊床架屋的高頭講章。前年撰一《懷念「小書」》的短文,提及「現在的學術書,之所以越寫越厚,有的是專業論述的需要,但很大一部分是因為缺乏必要的剪裁,以眾多陳陳相因的史料或套語來充數」。外行人以為,書寫得那麼厚,必定是下了很大功夫。其實,有時並非功夫深,而是不夠自信,不敢單刀赴會,什麼都來一點,以示全面;如此不分青紅皂白,眉毛鬍子一把抓,才把書弄得那麼臃腫。只是風氣已然形成,身為專家學者,沒有四五十萬字,似乎不好意思出手了。
類似的抱怨,我在好多場合及文章中提及,也招來一些掌聲或譏諷。那天港島聚會,跟香港三聯書店總編輯陳翠玲偶然談起,沒想到她當場拍板,要求我「坐而言,起而行」,替他們主編一套「小而可貴」的叢書。為何對方反應如此神速?原來香港三聯向有出版大師、名家「小作」的傳統,他們現正想為書店創立六十週年再籌畫一套此類叢書,而我竟自己撞到槍口上來了。
記得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九三二年出版,也就五萬字左右,錢鍾書對周書有所批評,但還是承認:「這是一本小而可貴的書,正如一切的好書一樣,它不僅給讀者以有系統的事實,而且能引起讀者許多反想。」稱周書「有系統」,實在有點勉強;但要說引起「許多反想」,那倒是真的──時至今日,此書還在被人閱讀、批評、引證。像這樣「小而可貴」、「能引起讀者許多反想」的書,現在越來越少。既然如此,何不嘗試一下?
早年醉心散文,後以民間文學研究著稱的鍾敬文,晚年有一妙語:「我從十二三歲起就亂寫文章,今年快百歲了,寫了一輩子,到現在你問我有幾篇可以算作論文,我看也就是有三五篇,可能就三篇吧。」如此自嘲,是在提醒那些在「量化指標」驅趕下拚命趕工的現代學者,悠着點,慢工方能出細活。我則從另一個角度解讀:或許,對於一個成熟的學者來說,三五篇代表性論文,確能體現其學術上的志趣與風貌;而對於讀者來說,經由十萬字左右的文章,進入某一專業課題,看高手如何「翻雲覆雨」,也是一種樂趣。
與其興師動眾,組一個龐大的編委會,經由一番認真的提名與票選,得到一張左右支絀的「英雄譜」,還不如老老實實承認,這既非學術史,也不是排行榜,只是一個興趣廣泛的讀書人,以他的眼光、趣味與人脈,勾勒出來的「當代中國人文學」的某一側影。若天遂人願,舊雨新知不斷加盟,衣食父母繼續捧場,叢書能延續較長一段時間,我相信,這一「圖景」會日漸完善的。
最後,有三點技術性的說明:第一,作者不限東西南北,只求以漢語寫作;第二,學科不論古今中外,目前僅限於人文學;第三,不敢有年齡歧視,但以中年為主──考慮到中國大陸的歷史原因,選擇改革開放後進入大學或研究院者。這三點,也是為了配合出版機構的宏願。
自序
當手術刀插入中國人身體的時候,到底發生了什麼?
一看標題可能有人覺得這個問題很奇怪,對一個病人而言,手術刀插入身體一般只有兩種結局:身體康復或者不治身亡,也許還有第三種可能:不死不活。總之,現在中國人對開刀這件事已經不會大驚小怪,因為大家都知道,看病除中醫之外,西醫是唯一的選項,誰不知道開刀排毒是西醫的拿手活,區別只不過是你願不願意躺在手術台上任人處置罷了。可是在一百多年前,刀割人體全然是大忌,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別說肉體受損,就是幾寸頭髮被剪掉都會鬧得刀光血影,屍橫遍地,不信你就看看清朝發佈剪辮令後江南士人的反應。
與剃髮相比,外科手術無疑是對身體的深度侵犯,不僅病人心理極易陷入恐懼,一旦進入手術階段,其周邊環境也會從熟悉變得陌生,比如中醫習慣的是家訪,哪怕是老大夫坐堂看診也給病人一種親密的居家感覺,並不覺得隔膜。西醫手術在空間上要求無菌狀態,會有意強化治病氛圍的陌生感,在病人眼裡,僅醫師穿著的白大褂就貌似葬禮喪服,很容易引起病人及家屬的生理不適。這些看似微妙的感覺差異實際上往往隱藏著病人擇醫心理背後的文化考量。
在我看來,手術刀插入中國人身體所引起的震動,絕不是一種簡單的「擇醫」過程,其背後應予關注的是中國人如何重新定義自己的身體,以及由此引發的心理變化問題。接受西醫對身體的改造意味著中國人對自己周邊世界的認知從此發生了劇變,手術刀既重塑了身體,也更新了觀念。舉個簡單的例子,當初中國人在鄉村中與熟人相處的方式是家長里短地打招呼串門,是不分彼此地相互幫助,直到某天,當一座形制特別的教堂在家族鄰里之間突然矗立起來,教堂裡面的人時常「詭異」地崇拜一具釘在十字架上的洋人屍體時,不引發群體恐慌那才是怪事。而西醫進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也與教堂的「詭秘」活動密切相關。
據西方醫療史考證,醫院幾乎就是教會慈善空間的自然延伸,中國的教堂與醫院大多為傳教士所建,在中國人的腦海裡,這兩種建築都屬神秘封閉的場所,崇拜耶穌屍體與切割人體器官幾乎可以同構到一個想像畫面之中,難以讓人接受。晚清發生的大量教案中,教堂與醫館常常一起被打砸焚燒即是個鮮明的例子。晚清以來的歷史證明,過激行為與文化誤解使中國人被迫戴上了「東亞病夫」的帽子,為了甩掉這頂帽子,反過來又進一步誘發了更為激烈的暴力反抗行動。與此同時,西醫對國人身體的改變乃是在昭示一種新的世界觀。這套世界觀描述的圖景在中國人的眼裡是如此陌生,以至於他們常常把教堂想像成邪教流毒的場所,把手術室當作了挖眼刨心的魔窟。
記得在耶魯神學院收集資料的時候,我曾偶然發現數十幅油畫,讓我感到震驚的是,這些油畫描繪的都是一些扭曲病態的中國人,畫面幾乎清一色表現的是身扛一顆或大或小瘤子的病人;另有一幅是瘤子切割前後的對比圖,左邊顯示病人肩上頂著一顆瘤子,右圖則是瘤子摘除後的圖像。我當時的第一反應是,這些洋人好生奇怪,怎麼放著耶穌貴族不描,拋開風花雪月不畫,卻專門幹起了這醜化中國人的勾當。可仔細觀瞧就能感覺到,這些畫裡一定暗藏玄機,其極力彰顯的隱喻主題是,通過摘除瘤子前後的畫面對比,說明西人已經把一個身陷痛苦的病態中國人徹底改造成了一個健康的新人。
從這幅畫中我還了解到,一把手術刀切入身體和一根灸針扎入人體的涵義其差別竟然如此巨大。它絕非僅僅表現出的是醫療史意義上的中西醫之爭,其背後隱藏著的是兩種觀念、兩種制度、兩種文化之間的反差與衝突。所以,手術刀與灸針之間的較量,也不應該僅僅屬醫史講述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還應該有傳教士、產婆、巫醫、草醫、赤腳醫的身影,也應該有軍人、政治家、警察、陰陽先生和普通百姓的活動畫面。他們共同編織了一幅中國近代歷史變遷的複雜絢爛圖景。一把手術刀切入人體的那一刻,就與身體感受、社會組織、城市改造、政治動員等等一系列的變化過程緊密糾纏在了一起,難以清楚地相互剝離。觀察這些歷史要素如何發生互動與交集才是最有趣的事情,而不是預先遵循西醫無敵與中醫沒落的二元對立公式,人為構造出一個中西醫衝突的現代化解釋模式,或據此展開一個單向性的演化線索。
需要說明的是,這本小冊子收錄的幾篇文章很容易被歸類進所謂「醫療史」研究,其實我一直在反覆澄清,本人對中醫西醫的相關知識幾乎為零,所以每當有人問我相關的醫療專業問題時我都會因為回答不上來深感汗顏。因此,這些文章尚無資格稱之為專門的「醫療史研究」。所謂關涉「醫療」的這部分內容只不過為我觀察中國近百年歷史變化提供了若干新視角,或者搭建了一個研究政治史的獨特平台。
與西方相比,中國人對各類政治活動的參與程度之高令人難以想像,不僅個人時常被強迫納入到各種政治運動中去,而且經常身不由己地成為社會組織規訓中無法逃避的一分子,不管其選擇方式是被動還是主動,如果不能理解中國人言行背後隱秘的政治邏輯,反而不斷陷入各種細碎專門的討論之中,就很難把握歷史變化的主脈和實質,因此,對中國政治狀況演進態勢的觀察應該是所有歷史研究的終極目標。這些文章涉及中國人在西醫治療下的身體感受,個體如何在新的社會空間裡得到安置,以及這些安排在相關治理體系的配合之下是如何被制度化的,最後則試圖辨析這種制度化設計在某一特定時刻如何轉換成了廣泛的政治動員。本書的主題可以提煉出以下幾個關鍵詞:身體、空間、制度和社會動員。按照這個線索,我希望讀者可以尋覓出一條從醫療史角度觀察中國政治變遷的新路徑。
陳平原
老北大有門課程,專教「學術文」。在設計者心目中,同屬文章,可以是天馬行空的「文藝文」,也可以是步步為營的「學術文」,各有其規矩,也各有其韻味。所有的「滿腹經綸」,一旦落在紙上,就可能或已經是「另一種文章」了。記得章學誠說過:「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我略加發揮:不僅「良史」,所有治人文學的,大概都應該工於文。
我想像中的人文學,必須是學問中有「人」─喜怒哀樂,感慨情懷,以及特定時刻的個人心境等,都制約着我們對課題的選擇以及研究的推進;另外,學問中還要有「文」─起碼是努力超越世人所理解的「學問」與「文章」之間的巨大鴻溝。胡適曾提及清人崔述讀書從韓柳文入手,最後成為一代學者;而歷史學家錢穆,早年也花了很大功夫學習韓愈文章。有此「童子功」的學者,對歷史資料的解讀會別有會心,更不要說對自己文章的刻意經營了。當然,學問千差萬別,文章更是無一定之規,今人著述,盡可別立新宗,不見得非追韓摹柳不可。
錢穆曾提醒學生余英時:「鄙意論學文字極宜著意修飾。」我相信,此乃老一輩學者的共同追求。不僅思慮「說什麼」,還在斟酌「怎麼說」,故其著書立說,「學問」之外,還有「文章」。當然,這裡所說的「文章」,並非滿紙「落霞秋水」,而是追求佈局合理、筆墨簡潔,論證嚴密;行有餘力,方才不動聲色地來點「高難度動作表演」。
與當今中國學界之極力推崇「專著」不同,我欣賞精彩的單篇論文;就連自家買書,也都更看好篇幅不大的專題文集,而不是疊床架屋的高頭講章。前年撰一《懷念「小書」》的短文,提及「現在的學術書,之所以越寫越厚,有的是專業論述的需要,但很大一部分是因為缺乏必要的剪裁,以眾多陳陳相因的史料或套語來充數」。外行人以為,書寫得那麼厚,必定是下了很大功夫。其實,有時並非功夫深,而是不夠自信,不敢單刀赴會,什麼都來一點,以示全面;如此不分青紅皂白,眉毛鬍子一把抓,才把書弄得那麼臃腫。只是風氣已然形成,身為專家學者,沒有四五十萬字,似乎不好意思出手了。
類似的抱怨,我在好多場合及文章中提及,也招來一些掌聲或譏諷。那天港島聚會,跟香港三聯書店總編輯陳翠玲偶然談起,沒想到她當場拍板,要求我「坐而言,起而行」,替他們主編一套「小而可貴」的叢書。為何對方反應如此神速?原來香港三聯向有出版大師、名家「小作」的傳統,他們現正想為書店創立六十週年再籌畫一套此類叢書,而我竟自己撞到槍口上來了。
記得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九三二年出版,也就五萬字左右,錢鍾書對周書有所批評,但還是承認:「這是一本小而可貴的書,正如一切的好書一樣,它不僅給讀者以有系統的事實,而且能引起讀者許多反想。」稱周書「有系統」,實在有點勉強;但要說引起「許多反想」,那倒是真的──時至今日,此書還在被人閱讀、批評、引證。像這樣「小而可貴」、「能引起讀者許多反想」的書,現在越來越少。既然如此,何不嘗試一下?
早年醉心散文,後以民間文學研究著稱的鍾敬文,晚年有一妙語:「我從十二三歲起就亂寫文章,今年快百歲了,寫了一輩子,到現在你問我有幾篇可以算作論文,我看也就是有三五篇,可能就三篇吧。」如此自嘲,是在提醒那些在「量化指標」驅趕下拚命趕工的現代學者,悠着點,慢工方能出細活。我則從另一個角度解讀:或許,對於一個成熟的學者來說,三五篇代表性論文,確能體現其學術上的志趣與風貌;而對於讀者來說,經由十萬字左右的文章,進入某一專業課題,看高手如何「翻雲覆雨」,也是一種樂趣。
與其興師動眾,組一個龐大的編委會,經由一番認真的提名與票選,得到一張左右支絀的「英雄譜」,還不如老老實實承認,這既非學術史,也不是排行榜,只是一個興趣廣泛的讀書人,以他的眼光、趣味與人脈,勾勒出來的「當代中國人文學」的某一側影。若天遂人願,舊雨新知不斷加盟,衣食父母繼續捧場,叢書能延續較長一段時間,我相信,這一「圖景」會日漸完善的。
最後,有三點技術性的說明:第一,作者不限東西南北,只求以漢語寫作;第二,學科不論古今中外,目前僅限於人文學;第三,不敢有年齡歧視,但以中年為主──考慮到中國大陸的歷史原因,選擇改革開放後進入大學或研究院者。這三點,也是為了配合出版機構的宏願。
二○○八年五月二日
於香港中文大學客舍
於香港中文大學客舍
自序
當手術刀插入中國人身體的時候,到底發生了什麼?
一看標題可能有人覺得這個問題很奇怪,對一個病人而言,手術刀插入身體一般只有兩種結局:身體康復或者不治身亡,也許還有第三種可能:不死不活。總之,現在中國人對開刀這件事已經不會大驚小怪,因為大家都知道,看病除中醫之外,西醫是唯一的選項,誰不知道開刀排毒是西醫的拿手活,區別只不過是你願不願意躺在手術台上任人處置罷了。可是在一百多年前,刀割人體全然是大忌,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別說肉體受損,就是幾寸頭髮被剪掉都會鬧得刀光血影,屍橫遍地,不信你就看看清朝發佈剪辮令後江南士人的反應。
與剃髮相比,外科手術無疑是對身體的深度侵犯,不僅病人心理極易陷入恐懼,一旦進入手術階段,其周邊環境也會從熟悉變得陌生,比如中醫習慣的是家訪,哪怕是老大夫坐堂看診也給病人一種親密的居家感覺,並不覺得隔膜。西醫手術在空間上要求無菌狀態,會有意強化治病氛圍的陌生感,在病人眼裡,僅醫師穿著的白大褂就貌似葬禮喪服,很容易引起病人及家屬的生理不適。這些看似微妙的感覺差異實際上往往隱藏著病人擇醫心理背後的文化考量。
在我看來,手術刀插入中國人身體所引起的震動,絕不是一種簡單的「擇醫」過程,其背後應予關注的是中國人如何重新定義自己的身體,以及由此引發的心理變化問題。接受西醫對身體的改造意味著中國人對自己周邊世界的認知從此發生了劇變,手術刀既重塑了身體,也更新了觀念。舉個簡單的例子,當初中國人在鄉村中與熟人相處的方式是家長里短地打招呼串門,是不分彼此地相互幫助,直到某天,當一座形制特別的教堂在家族鄰里之間突然矗立起來,教堂裡面的人時常「詭異」地崇拜一具釘在十字架上的洋人屍體時,不引發群體恐慌那才是怪事。而西醫進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也與教堂的「詭秘」活動密切相關。
據西方醫療史考證,醫院幾乎就是教會慈善空間的自然延伸,中國的教堂與醫院大多為傳教士所建,在中國人的腦海裡,這兩種建築都屬神秘封閉的場所,崇拜耶穌屍體與切割人體器官幾乎可以同構到一個想像畫面之中,難以讓人接受。晚清發生的大量教案中,教堂與醫館常常一起被打砸焚燒即是個鮮明的例子。晚清以來的歷史證明,過激行為與文化誤解使中國人被迫戴上了「東亞病夫」的帽子,為了甩掉這頂帽子,反過來又進一步誘發了更為激烈的暴力反抗行動。與此同時,西醫對國人身體的改變乃是在昭示一種新的世界觀。這套世界觀描述的圖景在中國人的眼裡是如此陌生,以至於他們常常把教堂想像成邪教流毒的場所,把手術室當作了挖眼刨心的魔窟。
記得在耶魯神學院收集資料的時候,我曾偶然發現數十幅油畫,讓我感到震驚的是,這些油畫描繪的都是一些扭曲病態的中國人,畫面幾乎清一色表現的是身扛一顆或大或小瘤子的病人;另有一幅是瘤子切割前後的對比圖,左邊顯示病人肩上頂著一顆瘤子,右圖則是瘤子摘除後的圖像。我當時的第一反應是,這些洋人好生奇怪,怎麼放著耶穌貴族不描,拋開風花雪月不畫,卻專門幹起了這醜化中國人的勾當。可仔細觀瞧就能感覺到,這些畫裡一定暗藏玄機,其極力彰顯的隱喻主題是,通過摘除瘤子前後的畫面對比,說明西人已經把一個身陷痛苦的病態中國人徹底改造成了一個健康的新人。
從這幅畫中我還了解到,一把手術刀切入身體和一根灸針扎入人體的涵義其差別竟然如此巨大。它絕非僅僅表現出的是醫療史意義上的中西醫之爭,其背後隱藏著的是兩種觀念、兩種制度、兩種文化之間的反差與衝突。所以,手術刀與灸針之間的較量,也不應該僅僅屬醫史講述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還應該有傳教士、產婆、巫醫、草醫、赤腳醫的身影,也應該有軍人、政治家、警察、陰陽先生和普通百姓的活動畫面。他們共同編織了一幅中國近代歷史變遷的複雜絢爛圖景。一把手術刀切入人體的那一刻,就與身體感受、社會組織、城市改造、政治動員等等一系列的變化過程緊密糾纏在了一起,難以清楚地相互剝離。觀察這些歷史要素如何發生互動與交集才是最有趣的事情,而不是預先遵循西醫無敵與中醫沒落的二元對立公式,人為構造出一個中西醫衝突的現代化解釋模式,或據此展開一個單向性的演化線索。
需要說明的是,這本小冊子收錄的幾篇文章很容易被歸類進所謂「醫療史」研究,其實我一直在反覆澄清,本人對中醫西醫的相關知識幾乎為零,所以每當有人問我相關的醫療專業問題時我都會因為回答不上來深感汗顏。因此,這些文章尚無資格稱之為專門的「醫療史研究」。所謂關涉「醫療」的這部分內容只不過為我觀察中國近百年歷史變化提供了若干新視角,或者搭建了一個研究政治史的獨特平台。
與西方相比,中國人對各類政治活動的參與程度之高令人難以想像,不僅個人時常被強迫納入到各種政治運動中去,而且經常身不由己地成為社會組織規訓中無法逃避的一分子,不管其選擇方式是被動還是主動,如果不能理解中國人言行背後隱秘的政治邏輯,反而不斷陷入各種細碎專門的討論之中,就很難把握歷史變化的主脈和實質,因此,對中國政治狀況演進態勢的觀察應該是所有歷史研究的終極目標。這些文章涉及中國人在西醫治療下的身體感受,個體如何在新的社會空間裡得到安置,以及這些安排在相關治理體系的配合之下是如何被制度化的,最後則試圖辨析這種制度化設計在某一特定時刻如何轉換成了廣泛的政治動員。本書的主題可以提煉出以下幾個關鍵詞:身體、空間、制度和社會動員。按照這個線索,我希望讀者可以尋覓出一條從醫療史角度觀察中國政治變遷的新路徑。
楊念群
二○二○年一月六日
二○二○年一月六日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79折$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