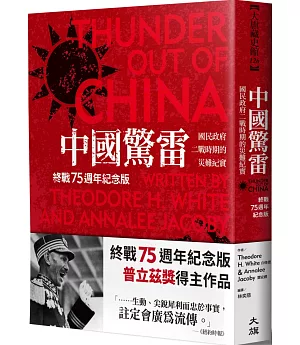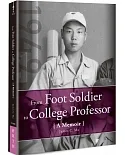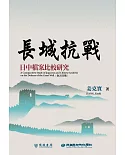序
時勢所造之英雄,終究是無可取代,一旦發生了,就會在某個主題上造就一段具有啟發性的史詩,並在那個分毫不差的當下引爆,成為社會關注的核心。
如此非凡的事件,指的就是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 的《中國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一書。今天全世界對白修德的認識勝過了一九四六年的時候,也就是他與賈安娜(Annalee Jacoby)
的早期成果問世之時。白修德從那個時候開始就已經寫過十幾本書,在每一本書裡,他追求真相的熱情都遭遇了重大的社會問題與政治問題,但卻沒有一本像《中國驚雷》這般舉足輕重。
美國在華利益,源遠流長,深深扎根於十九世紀時的美國貿易形式—飛剪式快速帆船,以及後來的傳福音行為,試圖把基督教和善功帶給被視為落後且無宗教信仰的中國人。
這樣資本主義和倫理的考量,在對於一個被視為陌生、神祕且難忘之國度的浪漫渴求下獲得了支持。
中國在這樣長達一世紀的吸引力下,將其自身更加鮮明地投射在美國的意識上,於是在某種程度上,美國開始透過所謂的「門戶開放」政策(現實中這只是美國政府堅持它在對華貿易上享有利益均霑的權力),以及伴隨大量美國傳教士的努力而出現的慈善事業,把自己視為中國的保護者和施惠者。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中國對日本侵略的抵抗被視為英勇的對抗,而為自己搏得了廣大的同情,美國的同情也完全傾向了中國,蔣介石與他美麗的妻子遂成為了美國人心中的英雄;與此同時,在愛德加.史諾(Edgar Snow)的《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e)與海倫.史諾(Helen Snow)的《紅色中國內幕》(Inside Red
China)二書的大力推波助瀾下,對於中國共產主義的運動也存在一股日漸廣泛的興趣。
白修德在《探尋歷史》(In Search of History)這本一九七八年出版的自傳體書中,說了他前往中國的故事,而且說得比任何人都好。當時已經有大量來自中國的美國報導,但是愛德加.史諾和他那時以尼姆.威爾斯(Nym Wales)為名寫作的結髮妻海倫所寫下關於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人的出色作品卻無可比擬。關於中國抵抗日本的逐日紀錄得以被許多一流的美國記者報導出來。
在這樣的情境下,出現了擁有特殊經歷的白修德。他在哈佛學過中文,也在無與倫比的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門下研究中國的歷史和政治。來自南達科他州的費正清,當時在哈佛學院是初出茅廬的二十九歲,曾到過中國,不僅結識了史諾夫婦,也深知中國的實際現況,而且他所傳達的那些勇氣、活力、熱忱和冒險精神,讓白修德有了一種感覺:沒什麼—真沒什麼—比中國更重要。
白修德於一九三九年四月十日抵達中國的戰時首都重慶,從那一刻起,他的人生即是中國。他幾乎直接成為《時代》(Time)雜誌的「地方」(非雇員)特派員,然後很快又成為專職特派員。他無處不到,而且對任何事都帶有狂熱的好奇心和回火鋼般的耐力,並以非凡的寫作能力跟對真相的著迷加以涉及。
在戰爭結束之前,無論是中國還是蔣介石和他卓越妻子的缺點,抑或是腐敗,以及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這些人和其他中國共產黨員的個人魅力及能力,白修徳幾乎無所不知。他認識非凡的「醋性子喬」(Vinegar Joe)將軍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和令人驚異的派屈克.赫爾利(Patrick Hurley)將軍,也認識一些老中國通(old China
hands),像是謝偉思(John Service)和小約翰.佩頓.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 Jr.),後來跟他的老闆亨利.魯斯(Henry Luce)非常熟識,亨利.魯斯本身是中國的「傳教士之子」,起初他是魯斯的紅人,後來成了魯斯無法寬容的競爭對手。
最重要的是,白修德開始了解中國,包括整個中國、國民黨員、共產黨員和傳統派,然後更逐漸了解了中國和美國之間微妙而且最終變得極為複雜的關係。如果他沒有完全掌握毛澤東和史達林之間錯綜複雜而且基本上屬於對立的關係,那也不能怪他。任何處於中國和蘇聯政治局最核心以外的人都無法理解這些細微差別,或者說是不被允許去了解。不過,白修德的分析卻緊緊抓住了這些本質。他理解中國共產主義不是蘇聯共產主義,延安不是莫斯科,而毛澤東也不是史達林的屬官。他正確察覺到中國共產黨員靠向美國的傾向,而且也完全明白,史達林從一九三○年代中期以來,就一直支持就一直支持蔣介石,而中國共產黨員在抗日戰爭中只能仰賴自己。正如白修德的觀察:「毛澤東試圖闡明他的信念,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員所依據的唯一架構必須是中國的現實,而非外來的政策。」
隨著日本投降,白修德明白中國的未來以及美中關係的未來將取決於國民黨員與共產黨員之間可能發生內戰的勢力平衡。美蘇干預的預期是確實的,而美國與蘇聯之間的戰爭態勢將凌駕於中國情勢之上的預期也是真切的。
《中國驚雷》是白修德讓美國人了解這個危險局勢所作出的英勇貢獻。他曾就蔣介石和毛澤東兩人所扮演的角色與意義跟亨利.魯斯及《時代》雜誌發生爭吵,並因此分道揚鑣。白修德以狂熱寫作,因為他感覺中國和美國正站在災難的邊緣,在局面變得無法挽回之前,他要不計代價地讓美國人掌握中國真實現況的事實。他出色地完成了他的目的,過去《中國驚雷》非常成功,現今讀起來仍然像當初寫下的時候一樣鮮明,其中的報導、判斷以及人物性格的描寫都經得住時間的考驗。在將近四十年後,《中國驚雷》的描寫,還是讓中國在大規模內戰以及革命前夜的寫照生動而適切地躍然於紙上。白修德所捕捉到的當下就宛如琥珀中的蒼蠅,讓我們可以在它的所有複雜光度中回首重視,他身為記者的本能並沒有將他帶往錯誤的方向。
確實,白修德對未來所提出的解決方法,就像他在一九四六年時寫下的,對於某些人而言可能理想到惱人的地步,但假如他的想法被採納了,中國和美國也許已經避免了流血、犧牲、受難和對抗的損失,那是龐大到無法估計的代價。中國將會也一定會發生革命,白修德此時的理解已是普遍的常識,他的明智之處是希望政府由國民黨人、共產黨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聯合參與,但中國政治的現實(殘酷)和美國政策的無能都讓白修德的希望成為難以企及的目標。
《中國驚雷》對於中美兩國來說都是有幫助的,它是一系列由美國記者持續寫下的非凡著作之一,這些作品用一種參與動亂之人無法複製,甚至無法試圖觸及、跟上的方式,捕捉到了一個國家處於動亂之中的當代史,因為這些人正身陷於事件的暴力迴旋當中。今日當我們在了解中國共產黨員是如何在最後的掙扎階段為自己帶來權力時,白修德的著作是不可或缺的,正如一九三○年代,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從延安展開,當我們要了解其運動本質時,史諾的著作同樣是必須的存在。《中國驚雷》正如當初完成時那樣,如今依然是一個注定要花一輩子探尋歷史的人(就像白修德自己後來所描述)的一場輝煌冒險。
哈里森.薩利斯伯里(Harrison Salisbu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