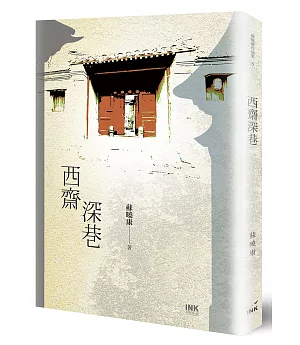小街、古都、天子腳下
紅樓、五四、反帝百年
流亡者蘇曉康回眸當年
崇禎上吊自盡御花園
青年毛澤東打工閱覽室
中共創始西齋廂房
文革狂飆沙灘大院
學生運動百年迴圈
我在那「五四紅樓」旁度過了整個少年時代,一直不知道它與我們「新中國一代」有何關係,直到八○年代我偶然走進那裡,才發現「歷史」整個兒是一個騙局。——蘇曉康
他的文字掃過景山東街,彷彿蔡元培、李大釗、胡適、魯迅、郭沫若、梁漱溟、錢穆的身影還在流動
再進紅樓大院,依稀仍有陸定一、周揚、江青、戚本禹等留下的蹤跡
新文化發源地曾是皇家馬廄
皇城根已是明清兩朝絢爛的屍骨
世界獨有八公里長古都中軸線隕落
古城牆改建為「北京的瓔珞」夢碎
林徽因吟唱古城樓在時間上漫不可信的變遷
「梁思成悲史」摹寫千年燕京淒涼的毀滅
這個最「文化」的地方恰是百年劇變漸成文化沙漠的策源地
「沙灘」上構建造反神話新人譜系「戀父」愛黨
「孑民堂」出產革命經典偷換大眾想像
「瘋婆婆」匿名攻擊「副統帥」
「閻王殿」終成屠場傾巢無完卵
好一個白茫茫大地
一把辛酸淚恰似《紅樓》
筆直的街道,蘇曉康執筆如火燭,帶著我們走入其中
本書特色
◎圍繞皇城根上的波濤,以數萬字推起漣漪。跨越漫長時間,流亡者夢回故鄉,窺看歷史的明滅。
◎蘇曉康距離五四整整一百年,以《西齋深巷》回應那已黯淡的知識分子投向黑暗的怒吼。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蘇曉康
一九四九年生於西子湖畔,少年長於京城景山腳下,青年流落中原;遂以〈洪荒啟示錄〉開篇,引領「問題性報告文學」浪潮,嘗試一度被稱做「蘇曉康體」的寫作文本,即「全景式」、「集合式」、「立體式」的「記者型報告文學」,且多為「硬碰硬」的重大題材,每每產生爆炸效應,為「新啟蒙運動」推波助瀾;繼而,領銜製作《河殤》,詰問華夏歷史,悲歎文明衰微。一九八九年流亡海外凡三十年,未止思索,筆耕不綴。著有《離魂歷劫自序》、《寂寞的德拉瓦灣》、《屠龍年代》、《鬼推磨--中國魔幻三十年1989-2019》等。
蘇曉康
一九四九年生於西子湖畔,少年長於京城景山腳下,青年流落中原;遂以〈洪荒啟示錄〉開篇,引領「問題性報告文學」浪潮,嘗試一度被稱做「蘇曉康體」的寫作文本,即「全景式」、「集合式」、「立體式」的「記者型報告文學」,且多為「硬碰硬」的重大題材,每每產生爆炸效應,為「新啟蒙運動」推波助瀾;繼而,領銜製作《河殤》,詰問華夏歷史,悲歎文明衰微。一九八九年流亡海外凡三十年,未止思索,筆耕不綴。著有《離魂歷劫自序》、《寂寞的德拉瓦灣》、《屠龍年代》、《鬼推磨--中國魔幻三十年1989-2019》等。
目錄
引子
上闋│皇城根上
「西齋夜雨聲」
歪脖老槐樹
萬春亭
中軸線
紫禁城
筒子河
雪池胡同
紅學家
文華殿曹雪芹展覽
「記住老師說的話」
孑民堂
楊家有女
中闋│景山東街
景山公園清道夫
明清猶在
三海
四十五號院
後海一水榭
「感情說」大將
銀錠橋
「北河沿的路燈」
東華門
隆福寺
下闋│紅樓大院
圖書館抄寫員
爬窗溜進審片室
白毛女
東方紅
忠叛之辯
刀筆吏
瘋姥姥
「閻王殿」
電影處長
劫餘
老夫子
筆墨之禍
煤山斜暉
上闋│皇城根上
「西齋夜雨聲」
歪脖老槐樹
萬春亭
中軸線
紫禁城
筒子河
雪池胡同
紅學家
文華殿曹雪芹展覽
「記住老師說的話」
孑民堂
楊家有女
中闋│景山東街
景山公園清道夫
明清猶在
三海
四十五號院
後海一水榭
「感情說」大將
銀錠橋
「北河沿的路燈」
東華門
隆福寺
下闋│紅樓大院
圖書館抄寫員
爬窗溜進審片室
白毛女
東方紅
忠叛之辯
刀筆吏
瘋姥姥
「閻王殿」
電影處長
劫餘
老夫子
筆墨之禍
煤山斜暉
序
引子
一個人的少年,常常到中年之後只剩下濕漉漉鵝卵石的雨夜迷濛,或者清晨瀰漫在胡同裡勾魂的炊煙,然而我的少年卻是另外一種,雖然也同一條小街藕斷絲連著,雖然那也是再平常不過的一條小街,沿街有副食店、理髮館、煤球場、小飯鋪等等,來來往往的也都是表面上只為柴米油鹽的升斗小民,但是那彷彿只是一個錯覺─這條街的西頭,緊靠明清兩朝的皇宮後苑,於是這尋常巷陌,沒有一絲過渡就銜接了「黃瓦紅牆」,一種優美的古典,而黎民晨起暮伏於其間,並未覺察城牆、樹木、街道的美妙襯托、銜接,別具一格。
我要到青年時代,才從一位建築師的描述中追憶這美妙:「北平四郊近二三百年間建築物極多,偶爾郊遊,觸目都是饒有趣味的古建築。天然的材料經人的聰明建造,再受時間的洗禮,成美術與歷史地理之和,使它不能不引起鑑賞者一種特殊的靈性的融合、神志的感觸。無論哪一個巍峨的古城樓,或一角傾廢的殿基的靈魂裡,無形中都在訴說乃至歌唱時間上漫不可信的變遷……。」這段文字取自梁思成一九三二年寫的《平郊建築雜錄》,據說這優美的文字其實出自他的妻子林徽因,極富盛名的民國才媛,新月派詩人,寫得一手極品散文。她那句「時間上的漫不可信」,恰好叫人遠溯到一千年前的另一句話:「很早以前,一個遙遠的國家曾有一座迷人的城市。那裡有金碧輝煌的宮殿,莊嚴的廟宇,華麗的牌樓,優美恬靜的園林以及由成千上萬座灰色瓦房組成的幽靜的四合院。」這是一個義大利人說的,他叫馬可.波羅。
少年從南方來北京,我還些許能感覺到一種古帝都的氣派,那黃瓦紅牆、嶙峋城樓、廟宇殿群,是隨時隨地觸目可見的;不過我後來從書上讀到的、當時梁思成對周恩來動情描述的「帝王廟牌樓在夕陽跌墜,漸落西山背景下的高度美的畫面」,則是壓根兒無緣見識了。這座古都最終沒有倖存下來,是我們追懷這些文字之際最為痛徹的。八○年代我在報告文學創作的初期,曾挖掘一部建築史與政治史交織在一起的「梁思成悲史」,四九年北平改名為北京,梁思成就建議中央行政區應在古城之外的西部地區建設,以避免毀掉古都,求得新舊兩全,但是遭到蘇聯專家的反對,他們主張將中央行政區放在古城中心區建設,毛澤東支持後者。接下來北京的城牆、城樓、牌樓等陸續被拆除。所以北京在五六○年代是有一種歷史性的擠壓發生了,讓你處處覺得有一個驕橫的粗人,肆無忌憚地躺在明清兩朝絢爛的屍骨上撒潑,你或許可以聽到那屍骨的呻吟。
這裡是所謂「天子腳下」的地方,古皇城的邊緣,至今留著一個地名叫「皇城根」,還分東西兩段。我剛來時很久都不懂這個「根」字是什麼意思,北京人喊它時又添了一個輕飄飄的「兒」的尾音,讓我覺得更怪。其實我從杭州來,杭州話本多「兒」音,只是那「兒」一下的位置,與北京話多不在同一處。哪裡還有什麼皇城?皇城該是個何等模樣?只聽老北京說,至少大清時的皇城範圍是沒有百姓居住的,以現代北京城從東四到西四這麼大一塊地方無人居住,那情形我是想像不出來的。六○年代初,也就是「文革」前的北京城,這一帶的氣象,是中央機關的衙門、宿舍糾纏在港汊般胡同裡的民居之間,設若一個做腳力的搬運夫,全家五六口住在胡同裡幾米見方的破屋裡,出門來拉著他的板車從這「皇城根」逶迤西去,途經紫禁城外的護城河時,就會穿過許多從前的王府大門,裡面如今都住上了坐紅旗轎車的元帥或副總理什麼的,搬運夫的兒子永遠不會同那深宅大院裡的某個公子哥兒,在路邊彈玻璃球或踢毽子,也絕不會一道去逛景山的;過了故宮再往西一兩里多,上得一座橋來,便有鐵欄杆和佩槍的士兵了,橋一側是悠悠的白塔,另一側便是中南海,猶如一口不斷釋放出風暴來的深潭,平日裡卻總是靜靜的……不過連販夫走卒都很清楚,有一個他們稱之為「救星」(不再叫「天子」)的人住在那裡面,他若起心動念或者脾氣不對勁,那可是不得了。有野史也稱,梁思成對中央機關設在中南海有意見,認為不應該在皇家花園這樣旅遊的地方辦公,建議到北京東南朝陽門外日壇一帶搞政府大院辦公,則北京市民不僅可以到北海划船,也可以划到中南海去,毛聞之不悅,說這不是要把我趕出去?
再回到那小街。上面我說了小街西頭連接的古代和古典,終於隕落了,然而小街的東頭,卻奇妙地連接著現代,因為那裡坐落著近百年中國人無法拒絕的兩棟建築物,一是舉世聞名的北大紅樓(即北洋時期的北京大學一院,也就是文學院),二是紅樓後面的大操場上四九年後蓋起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的辦公大樓,是淡紅色的。於是,這條小街的西頭,就怪誕地連接著相隔半個世紀的兩個風暴眼:「五四」和「文革」,而從這條街上走過的那些身影裡,必定會有蔡元培、李大釗、胡適、魯迅、郭沫若、梁漱溟、錢穆等,還有那個當年寒酸卻野心勃勃的毛澤東,以及六○年代初在文革舞臺上顯赫一時的諸多「文痞」..於是你可以發現,小街西頭古典的隕落,究其因果,多少又同小街的東頭有關。
這條小街叫景山東街。此地緊挨皇宮,從清朝中期以來都屬於一座公主府,晚清改為京師大學堂,那時仍沿用舊稱叫馬神廟,但廟址不存;張中行老先生對它的描繪最簡潔:「馬神廟是景山山頭直向東看的一條街」。到北洋時代學堂改為北大,街名亦更新為景山東街,直到上世紀六○年代我去那裡的時候還叫這個街名,現在好像改稱沙灘後街了,大概因為這一帶俗稱「沙灘」。少年時剛到那裡,我就很奇怪如此繁華的地方怎會叫「沙灘」這麼個荒涼的地名,有人解釋說北京在遠古不過是渤海灣淤沙堆積而成,所以留下這個稱呼。我慢慢長成大人的歲月裡,越是回味這個稱呼便越發覺得它再貼切不過:這個最「文化」的地方,可不就是中國經百年劇變漸成文化沙漠的一塊策源地嗎?曾經踏上這條小街連同掩隱在它後面的那種歷史,沒有半點值得誇耀之處,我只驚異自己居然那樣貼近過釀成這種「失去」的歷史源頭。
再交代幾句方位。這裡還借張中行先生,一位老北大也是老沙灘的文字,他寫在《負暄瑣話》裡的一句:「紅樓是多方面的中心。形勢四通八達:東接東四牌樓,西接西四牌樓;南行不遠是王府井大街、東安市場;北行不遠是地安門、鼓樓,風景也好,西行幾百步就是故宮、景山、三海。」紅樓是名副其實的紅色,四層磚木結構,坐北向南,到六○年代,已是北京鳳毛麟角的西洋化建築,樓前一條車水馬龍的通衢大道,貫通北京東西城的幾路電車均必經此站,站名在「文革」時改為「五四大街」,可人潮洶湧之中,會有幾人還知道「五四」聖殿就是這棟紅樓?
這「五四」紅樓,文革前幾年搬進去了國家文物局,我家則一直住在緊挨它的那棟沙灘大院「紅前樓」裡,到八○年代初才搬走。日後每每路經那個繁忙車站,我都忍不住要觀望那紅樓的門簾一眼,它旁邊那個郵局當年是「未名社」的遺址呢。接近八○年代尾聲,我製作那部流產的電視片《五四》之際,要說一說現代中國之開幕式的這場運動裡的一個小故事,又跟這紅樓有關,而「五四」歷史著作中很少提到它,記得我們還特意進國家文物局裡面,拍了一組鏡頭。故事要講的是,當年北大校長蔡元培就住在離這兒不遠的遂安伯胡同,他計畫一九一九年五月二日,要召集北大學生班長和代表,把巴黎和會的噩耗告訴大家,號召學生奮起救國,可是五月四日(「五四」)那天早上,他卻匆匆趕到馬神廟北大一院,即這棟「五四紅樓」,去勸阻學生上街遊行!他說示威遊行並不能扭轉時局,北大因提倡學術自由,已被視為異端,若再鬧出事來,恐怕首先遭難;他甚至說學生因救國而犧牲學業,其損失幾乎與喪失國土相等。然而蔡元培也難挽狂瀾於既倒,「五四」運動還是發生了。這個細節的歷史張力實在太大了,而「五四」公案,說它是「斬斷中國傳統」之大禍,拿它上比拳亂下附紅衛兵造反一鍋熬,指它抑啟蒙而揚救亡,至今眾說紛紜。
還要惋惜的是,我想拍的電視片《五四》,也因七十年後驟起於天安門廣場的另一場學生運動而夭折,其間我也曾去廣場紀念碑下勸說學生撤退,即五月十四日「十二名知識分子上廣場」,自然我們也不能「挽狂瀾於既倒」,畢竟模仿是笨拙的,儘管是模仿七十年前的蔡元培。那學運後來潰散於血泊之中,我也因此倉皇辭國,不覺已然三十年流逝,到此刻二○一九年我來寫「沙灘」,距離「五四」已整整一百年。
一個人的少年,常常到中年之後只剩下濕漉漉鵝卵石的雨夜迷濛,或者清晨瀰漫在胡同裡勾魂的炊煙,然而我的少年卻是另外一種,雖然也同一條小街藕斷絲連著,雖然那也是再平常不過的一條小街,沿街有副食店、理髮館、煤球場、小飯鋪等等,來來往往的也都是表面上只為柴米油鹽的升斗小民,但是那彷彿只是一個錯覺─這條街的西頭,緊靠明清兩朝的皇宮後苑,於是這尋常巷陌,沒有一絲過渡就銜接了「黃瓦紅牆」,一種優美的古典,而黎民晨起暮伏於其間,並未覺察城牆、樹木、街道的美妙襯托、銜接,別具一格。
我要到青年時代,才從一位建築師的描述中追憶這美妙:「北平四郊近二三百年間建築物極多,偶爾郊遊,觸目都是饒有趣味的古建築。天然的材料經人的聰明建造,再受時間的洗禮,成美術與歷史地理之和,使它不能不引起鑑賞者一種特殊的靈性的融合、神志的感觸。無論哪一個巍峨的古城樓,或一角傾廢的殿基的靈魂裡,無形中都在訴說乃至歌唱時間上漫不可信的變遷……。」這段文字取自梁思成一九三二年寫的《平郊建築雜錄》,據說這優美的文字其實出自他的妻子林徽因,極富盛名的民國才媛,新月派詩人,寫得一手極品散文。她那句「時間上的漫不可信」,恰好叫人遠溯到一千年前的另一句話:「很早以前,一個遙遠的國家曾有一座迷人的城市。那裡有金碧輝煌的宮殿,莊嚴的廟宇,華麗的牌樓,優美恬靜的園林以及由成千上萬座灰色瓦房組成的幽靜的四合院。」這是一個義大利人說的,他叫馬可.波羅。
少年從南方來北京,我還些許能感覺到一種古帝都的氣派,那黃瓦紅牆、嶙峋城樓、廟宇殿群,是隨時隨地觸目可見的;不過我後來從書上讀到的、當時梁思成對周恩來動情描述的「帝王廟牌樓在夕陽跌墜,漸落西山背景下的高度美的畫面」,則是壓根兒無緣見識了。這座古都最終沒有倖存下來,是我們追懷這些文字之際最為痛徹的。八○年代我在報告文學創作的初期,曾挖掘一部建築史與政治史交織在一起的「梁思成悲史」,四九年北平改名為北京,梁思成就建議中央行政區應在古城之外的西部地區建設,以避免毀掉古都,求得新舊兩全,但是遭到蘇聯專家的反對,他們主張將中央行政區放在古城中心區建設,毛澤東支持後者。接下來北京的城牆、城樓、牌樓等陸續被拆除。所以北京在五六○年代是有一種歷史性的擠壓發生了,讓你處處覺得有一個驕橫的粗人,肆無忌憚地躺在明清兩朝絢爛的屍骨上撒潑,你或許可以聽到那屍骨的呻吟。
這裡是所謂「天子腳下」的地方,古皇城的邊緣,至今留著一個地名叫「皇城根」,還分東西兩段。我剛來時很久都不懂這個「根」字是什麼意思,北京人喊它時又添了一個輕飄飄的「兒」的尾音,讓我覺得更怪。其實我從杭州來,杭州話本多「兒」音,只是那「兒」一下的位置,與北京話多不在同一處。哪裡還有什麼皇城?皇城該是個何等模樣?只聽老北京說,至少大清時的皇城範圍是沒有百姓居住的,以現代北京城從東四到西四這麼大一塊地方無人居住,那情形我是想像不出來的。六○年代初,也就是「文革」前的北京城,這一帶的氣象,是中央機關的衙門、宿舍糾纏在港汊般胡同裡的民居之間,設若一個做腳力的搬運夫,全家五六口住在胡同裡幾米見方的破屋裡,出門來拉著他的板車從這「皇城根」逶迤西去,途經紫禁城外的護城河時,就會穿過許多從前的王府大門,裡面如今都住上了坐紅旗轎車的元帥或副總理什麼的,搬運夫的兒子永遠不會同那深宅大院裡的某個公子哥兒,在路邊彈玻璃球或踢毽子,也絕不會一道去逛景山的;過了故宮再往西一兩里多,上得一座橋來,便有鐵欄杆和佩槍的士兵了,橋一側是悠悠的白塔,另一側便是中南海,猶如一口不斷釋放出風暴來的深潭,平日裡卻總是靜靜的……不過連販夫走卒都很清楚,有一個他們稱之為「救星」(不再叫「天子」)的人住在那裡面,他若起心動念或者脾氣不對勁,那可是不得了。有野史也稱,梁思成對中央機關設在中南海有意見,認為不應該在皇家花園這樣旅遊的地方辦公,建議到北京東南朝陽門外日壇一帶搞政府大院辦公,則北京市民不僅可以到北海划船,也可以划到中南海去,毛聞之不悅,說這不是要把我趕出去?
再回到那小街。上面我說了小街西頭連接的古代和古典,終於隕落了,然而小街的東頭,卻奇妙地連接著現代,因為那裡坐落著近百年中國人無法拒絕的兩棟建築物,一是舉世聞名的北大紅樓(即北洋時期的北京大學一院,也就是文學院),二是紅樓後面的大操場上四九年後蓋起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的辦公大樓,是淡紅色的。於是,這條小街的西頭,就怪誕地連接著相隔半個世紀的兩個風暴眼:「五四」和「文革」,而從這條街上走過的那些身影裡,必定會有蔡元培、李大釗、胡適、魯迅、郭沫若、梁漱溟、錢穆等,還有那個當年寒酸卻野心勃勃的毛澤東,以及六○年代初在文革舞臺上顯赫一時的諸多「文痞」..於是你可以發現,小街西頭古典的隕落,究其因果,多少又同小街的東頭有關。
這條小街叫景山東街。此地緊挨皇宮,從清朝中期以來都屬於一座公主府,晚清改為京師大學堂,那時仍沿用舊稱叫馬神廟,但廟址不存;張中行老先生對它的描繪最簡潔:「馬神廟是景山山頭直向東看的一條街」。到北洋時代學堂改為北大,街名亦更新為景山東街,直到上世紀六○年代我去那裡的時候還叫這個街名,現在好像改稱沙灘後街了,大概因為這一帶俗稱「沙灘」。少年時剛到那裡,我就很奇怪如此繁華的地方怎會叫「沙灘」這麼個荒涼的地名,有人解釋說北京在遠古不過是渤海灣淤沙堆積而成,所以留下這個稱呼。我慢慢長成大人的歲月裡,越是回味這個稱呼便越發覺得它再貼切不過:這個最「文化」的地方,可不就是中國經百年劇變漸成文化沙漠的一塊策源地嗎?曾經踏上這條小街連同掩隱在它後面的那種歷史,沒有半點值得誇耀之處,我只驚異自己居然那樣貼近過釀成這種「失去」的歷史源頭。
再交代幾句方位。這裡還借張中行先生,一位老北大也是老沙灘的文字,他寫在《負暄瑣話》裡的一句:「紅樓是多方面的中心。形勢四通八達:東接東四牌樓,西接西四牌樓;南行不遠是王府井大街、東安市場;北行不遠是地安門、鼓樓,風景也好,西行幾百步就是故宮、景山、三海。」紅樓是名副其實的紅色,四層磚木結構,坐北向南,到六○年代,已是北京鳳毛麟角的西洋化建築,樓前一條車水馬龍的通衢大道,貫通北京東西城的幾路電車均必經此站,站名在「文革」時改為「五四大街」,可人潮洶湧之中,會有幾人還知道「五四」聖殿就是這棟紅樓?
這「五四」紅樓,文革前幾年搬進去了國家文物局,我家則一直住在緊挨它的那棟沙灘大院「紅前樓」裡,到八○年代初才搬走。日後每每路經那個繁忙車站,我都忍不住要觀望那紅樓的門簾一眼,它旁邊那個郵局當年是「未名社」的遺址呢。接近八○年代尾聲,我製作那部流產的電視片《五四》之際,要說一說現代中國之開幕式的這場運動裡的一個小故事,又跟這紅樓有關,而「五四」歷史著作中很少提到它,記得我們還特意進國家文物局裡面,拍了一組鏡頭。故事要講的是,當年北大校長蔡元培就住在離這兒不遠的遂安伯胡同,他計畫一九一九年五月二日,要召集北大學生班長和代表,把巴黎和會的噩耗告訴大家,號召學生奮起救國,可是五月四日(「五四」)那天早上,他卻匆匆趕到馬神廟北大一院,即這棟「五四紅樓」,去勸阻學生上街遊行!他說示威遊行並不能扭轉時局,北大因提倡學術自由,已被視為異端,若再鬧出事來,恐怕首先遭難;他甚至說學生因救國而犧牲學業,其損失幾乎與喪失國土相等。然而蔡元培也難挽狂瀾於既倒,「五四」運動還是發生了。這個細節的歷史張力實在太大了,而「五四」公案,說它是「斬斷中國傳統」之大禍,拿它上比拳亂下附紅衛兵造反一鍋熬,指它抑啟蒙而揚救亡,至今眾說紛紜。
還要惋惜的是,我想拍的電視片《五四》,也因七十年後驟起於天安門廣場的另一場學生運動而夭折,其間我也曾去廣場紀念碑下勸說學生撤退,即五月十四日「十二名知識分子上廣場」,自然我們也不能「挽狂瀾於既倒」,畢竟模仿是笨拙的,儘管是模仿七十年前的蔡元培。那學運後來潰散於血泊之中,我也因此倉皇辭國,不覺已然三十年流逝,到此刻二○一九年我來寫「沙灘」,距離「五四」已整整一百年。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79折$205
-
新書79折$205
-
新書79折$205
-
新書79折$206
-
新書85折$221
-
新書9折$234
-
新書$264
-
新書$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