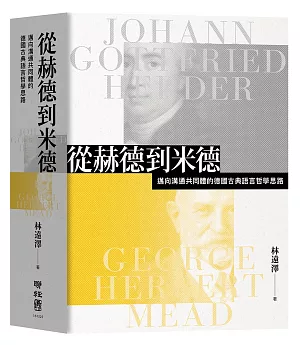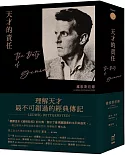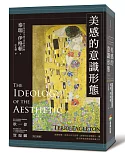序
哲學中「語言轉向」的別支
自從美國學者羅蒂提出哲學中有所謂的「語言轉向」後,哲學界便必須回答一個問題:語言的論述在哪一意義下可有助於哲學問題的懸解!就這一議題,學界一般認為「語言轉向」指的是英美分析哲學傳統對哲學語言的使用做出批判與重審的「治療模式」。但筆者向來認為,由於語言的關鍵作用,近世除了分析哲學以外,我們於許多其他哲學傳統中其實也可以找到「語言轉向」的另類模式:例如首先有現象學傳統藉意向性分析(胡塞爾)或身體理論(梅露龐蒂)而展開的「意義建構模式」;有德里達為首的,力求揭露哲學語言包含著各種帶壓抑意味的對立的「解構模式」;有伽達默爾為首的,強調不同界域與傳統之間的辯證調和的「詮釋學模式」;有以哈伯瑪斯為代表的,強調社會不同持份者之間的溝通行動的「超驗實用模式」;而在這些模式之外,我向來最重視和認為更根本的,其實還有由洪堡特締建,並特別重視人能仗語言之習得與積極操作以開顯一世界觀的「育成模式」。這多種模式對語言的理解及其各自強調的語言功能雖不盡相同,而且彼此間往往存在著爭議,但不約而同地都與當世過分偏重語言的客觀表達功能的英美傳統相抗衡。這些「另類」的語言轉向,其更重視的,是語言的文化功能,乃至其社會功能,換言之,對這些語言哲學的「別支」而言,語言的習得、運用與溝通,歸根結柢而言,是一些人文現象乃至是一些社群現象!
最近得觀林遠澤君新著《從赫德到米德》,展閱之餘,深慶上述這一意義的另類的語言轉向得到了更深入的闡述。林著展視了作者深邃的哲學史識:他首先是把分析哲學意義的「語言轉向」歸根於亞里士多德的語言工具觀的復熾與貫徹,並指出這根自亞氏對語言的工具理解,實乃後世乃至當今只知偏重自然科學與對象認知這一主流思想的觀念源頭;亞氏流風所及,當今哲學乃能振振有詞地對諸如、詰問、祈願、虛擬等人文訴求下的語言運用以其不涉認知為由而予以忽視。林著即據此以顯出,歐陸傳統語言哲學的一大特色,就是力求擺脫亞里士多德語言工具觀此一桎梏,而洪堡特認為語言並非單純的表達工具,而乃人類思想得以同步塑成的「器官」,和其認為應重視語言的活動多於重視其果實這些立場,實即此一另類傳統的鮮明旗幟。
洪堡特於學術思想上的地位是很多元的,撇開他於教育學、政治學、史學和美學方面的許多貢獻不表,他首先憑其豐富的語言知識(包括漢語和梵語)被譽為現代普通語言學之父,而在哲學領域中,他繼承了康德哲學的精神,也堪稱為德意志觀念論之殿軍!而他這兩方面的成就的有機整合,便釀成其楬櫫的既立足於經驗觀察,亦不失於觀念深度的語言「育成模式」,和使他所倡議的語言理論於處理經驗對象之餘,能更合理地安頓人類社會中極盡豐富的人文現象與意義世界。
整體而言,洪堡特語言哲學顯然是林著的一大理論樞紐。事實上,看林書的結構,洪堡特就正好像分水嶺一般把全書分為兩大部分:即可再分為「從赫德到洪堡特」,和「從馮特到米德」。其中前者乃循洪堡特回溯其理論之濫觴與訴求,而後者則順洪堡特以觀其理論的後續影響及發展。其間先後論及赫德的「語言起源論」、哈曼對康德及啟蒙理性的「語文學後設批判」、馮特的「語言身體姿態起源論」、卡西勒的「符號形式哲學」、米德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提出的「姿態會話」學說和「符號互動論」等。此外,於論述過程中,林著也吸納了不少近代和當代先輩學者的相關討論,較重要的有史坦塔爾、魏斯格爾博、布朗、博許、圖根哈特、哈伯瑪斯等,儼然擬出一有關語言理論的德國哲學系譜。正如前述,在林書的視野中,這個從18世紀末伸延至20世紀的語言理論浪潮的中心議題,並非主流哲學所強調的對象認知問題,而乃人文社會現象的問題,而其中最耀目的焦點,正是人際的有效溝通問題,而這正是全書副題「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之所指。至於附錄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的漢語研究〉一文,雖與本書的核心結構無直接關涉,但正是運用這另類的語言轉向以回饋於漢語漢字反思的重要文獻,讀者殊不應錯過。全書總體而言,可謂構成了德國近代哲學中的「語言論」的支脈;正如作者自詡,這一個脈絡的整理,即使放眼西方學界,亦屬新猷!
總而言之,林遠澤君新著涵蓋之豐富,可謂洋洋大觀。遠澤是我於東海大學任教最後一年時入學的學生,他當年由於是越級旁聽我的課,所以當初我對他並沒有留下印象。我真正認識遠澤,是許多年後的事。事緣十年前我應李瑞全兄之邀請,於中央大學作了一場與洪堡特語言理論有關的演講,其時遠澤剛於中央大學執教,作為聽眾之一的遠澤很快便和我建立起緊密的聯繫。我倆的學術興趣雖極為相近,但卻各有不同的重點,正好足以互補。坦白說,語言哲學之於英美傳統雖然盛行,但歐陸特別是德語傳統的語言哲學,放諸當世,卻只屬冷門。故當年得見遠澤這方面的關注和已具備的條件,真有點「吾道不孤」的喜悅!更難得的,是遠澤自此努力不懈,循洪堡特這基點上溯其源頭和下追其餘緒,能廣諏博採之餘又能深耕細作,終有今日這可觀成績,實極為難得。數月前遠澤求序於我,我毫不猶豫便答允了!唯月來諸事踵至,而自己赴德講學之期限又已逼近眉睫,本欲更詳細論列本書觀點之打算看來已難實行。賞識之餘,惟有爰書數語,以誌其新作之意義。是為序!
關子尹
序
本書以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傳統作為研究的對象,我所謂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涵蓋從18世紀末探討語言起源論的赫德(J. G. Herder)到20世紀初為社會心理學建立符號互動論基礎的米德(G. H. Mead)。這中間還包括主張語言上帝起源論以反對啟蒙的哈曼(J. G. Hamann)、創立普通語言學的洪堡特(W. von
Humboldt)、設立第一個心理實驗室且開創民族心理學研究的馮特(W. Wundt),與嘗試以文化哲學取代先驗觀念論的卡西勒(E.
Cassirer)。這些學者除了卡西勒被列入新康德主義馬堡學派陣營,還在哲學史占有一席之地外,其他學者幾乎在各種哲學史的教科書中,都不曾出現過。本書將這些乍看之下毫無關聯的思想家(米德甚至應是歸屬實用主義陣營的美國人),都包括到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的範圍內,實因他們的哲學研究,不僅在學術旨趣與立論出發點方面,都極為一致,他們相續提出的論點,更是環環相扣、相互發明,從而能在語言哲學中,形成一種首尾融貫、體系完整的理論典型。本書因而借鏡《從康德到黑格爾》的提法,闡釋《從赫德到米德》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如何相對於先驗觀念論的意識哲學進路,推動哲學轉向去思考在語言學模式中的溝通共同體理念。
相較於近代西方哲學,就其作為強調以意識哲學為基礎的主體性哲學而言,難免會有獨我論的傾向,其知識建構的觀點,也難免將使存有現象化,成為科學操控宰制的對象。德國古典語言學家則都非常有意識地,想透過批判亞里士多德以來的語言工具觀,闡釋語言的真正本性與作用。他們試圖透過論證世界或理性的語言性,以求最終能在溝通共同體的交互主體性構想中,說明為何吾人應在符號結構化的文化世界中,才能理解世界的真理性,並從而得以回答「人是什麼?」的哲學基本問題。「從赫德到米德」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其哲學研究的學術旨趣因而主要在於,嘗試使哲學能從康德建構先驗觀念論的「純粹理性批判」,轉向建立文化哲學基礎的「語言批判」理論。他們透過對語言之起源、範圍與界限的研究,來說明人類得以建構文化世界的基本法則,俾使哲學不再局限於為自然科學的世界觀奠基,而是轉向為人文科學奠基的哲學人類學研究。
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的重要性,當然不是本書所獨見。但在眾多意識到這些議題之重要性的當代哲學家中,能歷史通貫地把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剖析清楚的卻也尚未得見。卡西勒是當代第一個意識到德國古典哲學傳統之重要性的哲學家,他慨嘆當時學界竟然還沒有一部語言哲學史。他自己雖在《符號形式哲學》第一卷《論語言》中,嘗試勾畫語言哲學史的思路,但他對語言哲學史的研究,僅止於馮特的表達理論。對於他自己的「符號形式哲學」如何能從洪堡特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傳統中發展出來,仍未有清晰的理路論述。哈伯瑪斯同樣非常清楚,當代德國的詮釋學理論與他自己的普遍語用學理論(或者說溝通行動理論),都是從洪堡特所代表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傳統而來的,他自己並致力於研究洪堡特、卡西勒與米德的理論。而對於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的歷史發展,最有深入研究的則應首推阿佩爾。阿佩爾指出,在西方哲學的發展中,除了由經驗主義的名目論與理性主義的普遍記號學所形成的科學—經驗主義語言研究傳統外,還包括來自基督教傳統的邏各斯神祕主義、與來自希臘—羅馬之修辭學傳統的人文主義語言觀。後兩種語言觀點代表一種先驗詮釋學的語言觀,對此進行哲學的闡釋,乃始於赫德與哈曼,而最終綜合於洪堡特。阿佩爾雖然深入歷史文本,對於存在於修辭學與近代母語文學中的人文主義語言觀,做了詳細的研究,而寫了《從但丁到維柯之人文主義的語言理念》(Die
Idee der Sprache in der Tradition des Humanismus von Dante bis Vico)一書,但他並未接著「從但丁到維柯」而續寫「從赫德到洪堡特」。這個工作在泰勒那裡得到補充,泰勒以“HHH”的縮寫,論述了赫德、哈曼與洪堡特三人並列的語言哲學觀點。在2016年甫出版的《語言動物》(The language
Animal)中,他致力於說明這個傳統與由霍布斯、洛克與孔狄亞克(縮寫為“HLC”)代表的語言哲學傳統之間的不同,但他的討論也未能深入到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後續「從馮特到米德」的發展與完成。
我在這本書中,試圖完成西方學界這一段尚未完的工作。在本書劃分六章與一個附錄的架構中,我的研究工作主要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I)包含前三章,在這裡我要說明,在赫德與哈曼關於語言起源論的爭議中,一種不同於亞里士多德語言工具觀的語言哲學觀點如何產生出來。以及這種觀點如何影響了洪堡特,以至於他會主張作為建構思想的器官,語言不應是成品而是活動。洪堡特最後透過語言的交談結構,解釋在語言世界觀之意義多元主義下,吾人的世界理解如何具有客觀性,這開創了語用學之溝通向度的討論。包括第四至六章的第二部分(II),探討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在20世紀初期的發展過程。它始於馮特的研究,因為在青年語法學派將歷史比較語言學轉向語言心理學的研究之後,馮特首先針對語音之語意表達的普遍可理解性問題,深入研究了人類的語言如何能從動物的身體姿態表達,轉化成以表意符號進行溝通互動。而一旦人類的思想活動惟有透過語言符號才成為可能,那麼對於思想機能的心理學研究,就應進一步建立在形構語言之民族精神的交互主體性之上。馮特的這個觀點,一方面影響了卡西勒,他試圖在建構神話、語言與科學等文化系統的符號形式中,闡釋人類建構文化世界之精神形構力所依據的基本原則,以取代康德以先驗邏輯學為自然科學的知識基礎所做的哲學奠基;另一方面則影響了當時曾到德國留學的米德,他嘗試透過動物的姿態會話,追溯人類語言溝通的起源,從而說明人如何借由意義理解的規範建構活動,創建人類社會獨具的自由整合模式。米德並由此為當代以「我思」為基礎的反思性主體哲學,補充了前反思的身體性基礎與後反思的對話性向度。卡西勒的符號形式哲學與米德的符號互動論,可說是初步完成了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意圖轉化康德先驗統覺的主體主義以邁向溝通共同體的思路。
本書的附錄討論的則是漢字思維的問題,這個討論仍以附錄的形式呈現,係因這仍是一個尚未完成的研究議題。它雖未完成,但仍可作為對照而屬於本書論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的一部分。在當代研究深層語法的語言學、與研究邏輯語法學的語言哲學中,作為孤立語的漢語與作為音義同構的漢字,與印歐語的曲折語與拼音文字的結構差異並未得到重視。但在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傳統中,洪堡特卻因主張語言結構的差異即是世界觀差異,而特別針對漢語與漢字的世界觀,做出開創性的研究。馮特則在語言之身體姿態起源論的研究中,發現漢語的無文法性與漢字的獨立表意作用,與手勢等身體姿態語言最為接近。這些研究使我們能反省到,西方哲學傳統的世界觀,基本上是基於語音中心主義、邏各斯中心主義與主知主義而成立的,而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的語言觀,不僅能使西方哲學本身基於語音中心主義的局限性被意識到,也能使中國人的思維形態與世界觀重新得到重視。這部分雖需另撰專書處理,但在此先以附錄的形式,說明我當前粗略的想法,那麼或許能拋磚引玉,讓我得到更多讀者回應的啟發。
本書的論述風格顯然是歷史的。我沒有將赫德、哈曼、洪堡特、馮特、卡西勒與米德的語言哲學理論系統化,而是每章都獨立地研究他們各自的思想發展過程。這有三方面的考慮:一是,這些哲學家本身的理論都各自有他們獨立研究的意義,試圖把它們系統化到某一思潮範圍內,將會窄化他們思想的原創性。保持每位思想家思想的獨立發展,將使讀者即使不就本書的脈絡來看他們在語言哲學史中的意義,也能從各章去看語言起源論(赫德、哈曼)、普通語言學(洪堡特)、語言心理學與民族心理學(馮特)、文化哲學(卡西勒)與社會心理學(米德)等領域,在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醞釀與發展;二是,哲學史研究的意義在當代被不當地貶低,當前如果我們說一位學者的研究只是哲學史的研究,那通常就是說他沒辦法做開創性的理論研究,只能整理一下過去哲學家的見解。但其實這是非常危險的偏見,因為一種缺乏歷史反思的哲學研究,只會讓我們陷於積澱為「常識」之特定理論偏見的蒙蔽。當一個觀念愈能得到常識之明證性的支持,就愈可能會使我們自陷於某種權威論述之偏見的籠罩而不自知。在此惟有透過思想之歷史演進的自覺批判,才能使我們脫離各種主流思想之理所當然的假象。重新追尋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的思路,正可以有助於批判那些已經被當代語言哲學視為理所當然的前提;三是,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的發展,同時具有開創與過渡的性質,它將康德的先驗觀念論轉向當代的語用學、詮釋學、解構主義與溝通行動理論。讀者若能通貫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的發展,那麼對於當代語言哲學的來龍去脈,就自有理路可尋。本書因而無需選擇個別學派的語言哲學觀點,來為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做出系統的建構,反而更想致力於保留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未竟發展的思想潛能,以能為當前東、西方語言哲學之賡續發展,提供源泉不絕的思想來源。
寫作本書讓我在德國人的故紙堆裡翻滾很久,鎮日與被大家視為已經落伍而遺忘的理論為伍。今日若還有人會對哈曼的語言上帝起源論、馮特的民族心理學或米德的社會心理學有興趣,那麼他們大概都會被看成是不知學術發展現況,以至於會把敝帚當成珍寶的外行人。然而,豈容青史盡成灰,對於能從18、19世紀的歷史文獻中,發掘出人類思想的瑰寶,我是樂此而不疲的。本書的研究首先必須感謝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Dietrich
Böhler的啟發,他作為阿佩爾最早的學術助手與後來的理論共同創建者,始終致力於康德先驗哲學的語用學轉化,他的先驗語用學與洪堡特研究,引發我對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的研究興趣。其次,我必須感謝張旺山與楊儒賓教授,張旺山教授很早就意識到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的重要性,他在2003年召開《赫德逝世兩百週年紀念研討會》,並邀請我發表論文。我當時發表的會議論文:〈哲學的語言學轉向是否開始於赫德?試做赫德語言起源論的先驗詮釋學解讀〉,不僅是我進入學界發表的第一篇論文,也是我寫作現在這本書的開始。楊儒賓教授對於洪堡特、卡西勒與米德的跨領域研究興趣,則引導我循這個思路,走向漢字思維的研究,若沒有他以極其宏觀的學術視野舉辦各項活動,帶動我持續進行這方面的研究,這本書的完成鐵定還是遙遙無期。此外,我更要感謝關子尹教授,他是華人世界研究洪堡特語言哲學的開創者,他對卡西勒《人文科學的邏輯》一書所做的詳盡譯注,啟發了我對卡西勒的理解。若無他首開風氣,將洪堡特的語言哲學應用於漢語與漢字的研究,那麼促成本書研究的動機,也就無由存在了。而本書若有任何價值,那麼最後都請容許我感謝那些能寬縱地解免我在人生中應盡之義務的家人與朋友。
導論(節錄)
在影響近代人類思想發展甚鉅的德國古典哲學中,存在著兩條相當不同的思路。一條是「從康德到黑格爾」的觀念論思路,它從統覺的自我意識與自律的道德主體性出發,走向對於理念之客觀化體現達到全面自覺的絕對精神,與團結所有個體的總體性國家;另一條則是「從赫德到洪堡特」的語言哲學思路,他們透過世界理解與人類理性的語言性,開闢一條邁向溝通共同體的道路,以凸顯出人類文化生活與民主體制的核心價值所在。在前一條道路中,嚴格的理性自律與絕對精神的一體籠罩,遭到社會生活的矛盾鬥爭、潛意識的欲望衝動與個體權力意志的反叛。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觀念論,因而接著走上「從黑格爾到尼采」這一段顛簸崎嶇的道路;但從「赫德到洪堡特」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卻接著透過「從馮特到米德」的溝通共同體思路,承認在情緒衝動的姿態表達中,即存在有身體性的意義建構活動,主張惟有透過在社會互動中,角色扮演的相互承認,人類社會的團結整合才能賦予個人自由的實現。在哲學史的發展中重新發現「從赫德到米德」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使我們能將哲學從在意識領域中的先驗自我或絕對精神,轉移到以語言的溝通共同體作為哲學思考的基點。這不僅能建構出以人文社會科學為基礎的哲學思維模式,更能為人類提供自我理解的新圖像。
剛從我們身邊流逝的20世紀,已被公認是哲學語言學轉向後的世紀。語言哲學既已經是當代的顯學,我們何以還需回顧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的遺跡?這是歷史憑弔的興趣,還是只想在哲學史的神殿中,為赫德到米德這幾位哲學家,爭列作為當代語言哲學先祖的牌匾?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的思路,早已經是一條湮沒在歷史中的古道,我們並不知道,經由它究竟可以通向何方去尋幽訪勝。然而一旦這條道路能被清理出來,那麼我們將可發現,當代的語言哲學研究,也有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條是從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經過中世紀的共相之爭、到近代經由康德對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綜合,最終抵達邏輯實證論與語言分析哲學的道路。這條分析哲學的語言哲學道路,號稱它完成哲學語言學轉向的工作。但其實它並沒有使哲學轉向,它走的還是「思有一致性原則」的老路。他們之所以感到哲學有了轉向,係因為他們在亞里士多德以邏輯學建構存有論的哲學傳統中,擺脫探討主體機能的心理學與對象建構的存有論,而只專注於思想判斷的邏輯學,俾使語言哲學能為科學的理論建構提供具有真值涵蘊的邏輯語法。
然而語言是以詞構句的言說行動,在構詞學與文法學中,特別是在語言溝通的使用中,世界之意義建構與行動協調之規範建制的基礎,卻沒有在這條道路中得到專題化的討論。而由希臘化—羅馬時期的修辭學傳統與基督教的邏各斯神祕主義開始,經由文藝復興時期但丁(Dante)的人文主義與維柯(Vico)主張的新科學,直到最終綜合於從赫德到米德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這些問題才在語言起源論、歷史比較語言學與語言心理學的範圍內,得到詳細的討論。以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為代表的第二條思路,就其肇始於語言起源論的探討而言,一開始即帶領哲學走向探討「人是什麼?」的哲學人類學問題。人有語言,才與動物截然有別,人文世界與人的語言性密不可分。動物依本能而生活在它的環境之中,但人類卻能抽離他的環境而面對整個世界。世界這個概念,因而主要不是指在物理學意義下的自然環境,而是指人類透過語言所建構的意義視域。語言作為人類溝通互動的媒介,它所具有的普遍有效性只能透過交互主體性建構。這使得語言中介的文化創造,不同於科學僅借助理性的邏輯去進行獨白的沉思,而是必須在世界解釋的意義理解,與行動規範的溝通協調中,取得共識的普遍有效性。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因而在一開始就非常有意識地,要相對於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進行「語言的批判」。語言無法離開社群共同體的歷史發展,在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研究基礎上,德國古典語言哲學轉而關注語言之世界開顯性的作用。且當語言不再只被看成是透過約定而產生的現成工具,而是創造思想活動的器官,語言學的研究就更必須從研究經典文本的文獻學,轉向研究人之語言資能的語言心理學。這使得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得以說明,詞語的符號性意義與透過文法形塑的世界性結構,如何能從人類社會互動的身體姿態表現與民族共同體的共通感中產生出來。
從赫德到米德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研究,因而不是在做翻案文章,而是要凸顯出,語言哲學不應只是將語言當成是哲學研究的一個分支領域,而應是哲學研究的重新開始。正如海德格在講述赫德的語言起源論時所說的:「在發問語言起源的問題線索上,我們所思索的,首先並非意在語言科學及其基礎的問題。它並不是要處理哲學的一個分支領域(或關於它的學說),也不是要主張『語言的哲學』應成為哲學的基本學說。在這裡我們所思考的,既非語言科學,也非語言哲學;而是從詞語作為『存有之真理的本質』出發,對語言的起源(本質根據)所進行的思考。」在這個意義下,哲學之語言學轉向的時間點,即非如語言分析學者所追溯的,是始於19世紀末弗雷格(G.
Frege, 1848-1925)關於《數學基礎》(1884)的探討,而應是更早地始於18世紀赫德的《論語言的起源》(1776)。
面對語言哲學的這兩條思路,本書選擇以德國古典語言哲學作為哲學研究的新開始。為了闡述本書研究德國古典語言哲學之必要性、重要性與進路的合法性,我們在這個導論中,有必要先向讀者說明,為何本書不採取從亞里士多德邏輯學到當代語言分析哲學發展出來的語言哲學觀點,而主張哲學真正的語言學轉向,應當取道於從赫德到米德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為此之故,我在底下將先分析西方主流的語言哲學觀點,如何在亞里士多德邏輯學的影響下產生出來(一);其次,我將深入解析,在此種語言工具觀的影響下,當代語言分析哲學仍存在哪些語言哲學觀點的限制(二),以能進一步論述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如何借助「語言作為開顯世界的存有論詮釋學」,超越傳統語言哲學在語意學研究方面的窄化,以及如何借助「語言作為規範建制的溝通行動理論」,補充傳統語言哲學在語用學向度上的缺乏。以凸顯相對於「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古典哲學,「從赫德到米德」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如何透過溝通共同體的觀點,推動先驗哲學的語言學轉化,俾使哲學思維的先驗主體或絕對精神,能重新回到真實的生活世界。並從而使得哲學不再僅專注於為自然科學奠基,而是在重視以人文科學的知識建構活動作為哲學思考的典範時,能更好地給出人作為符號動物的哲學人類學圖像(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