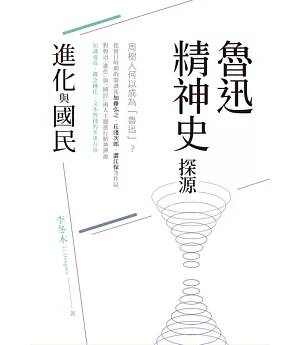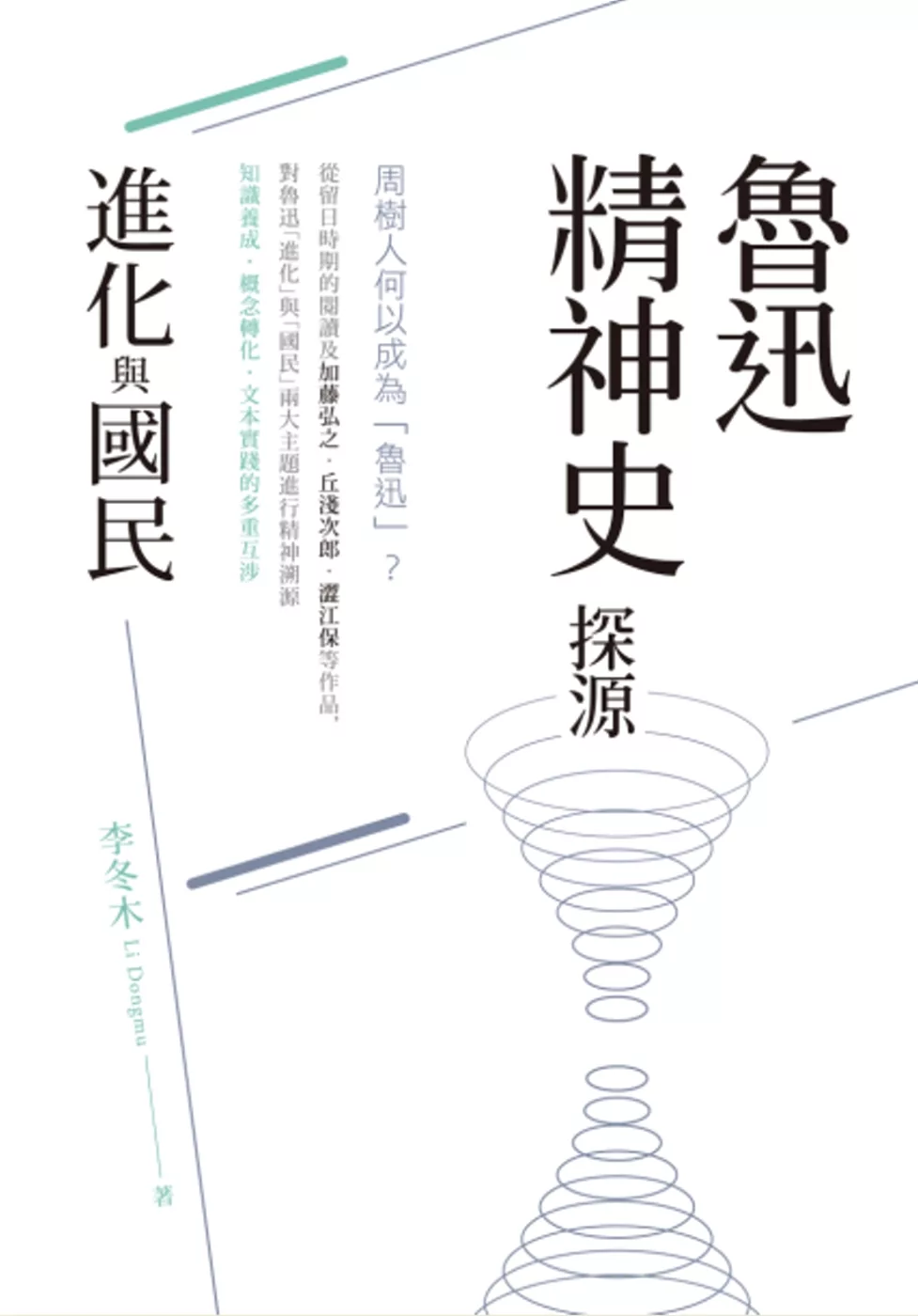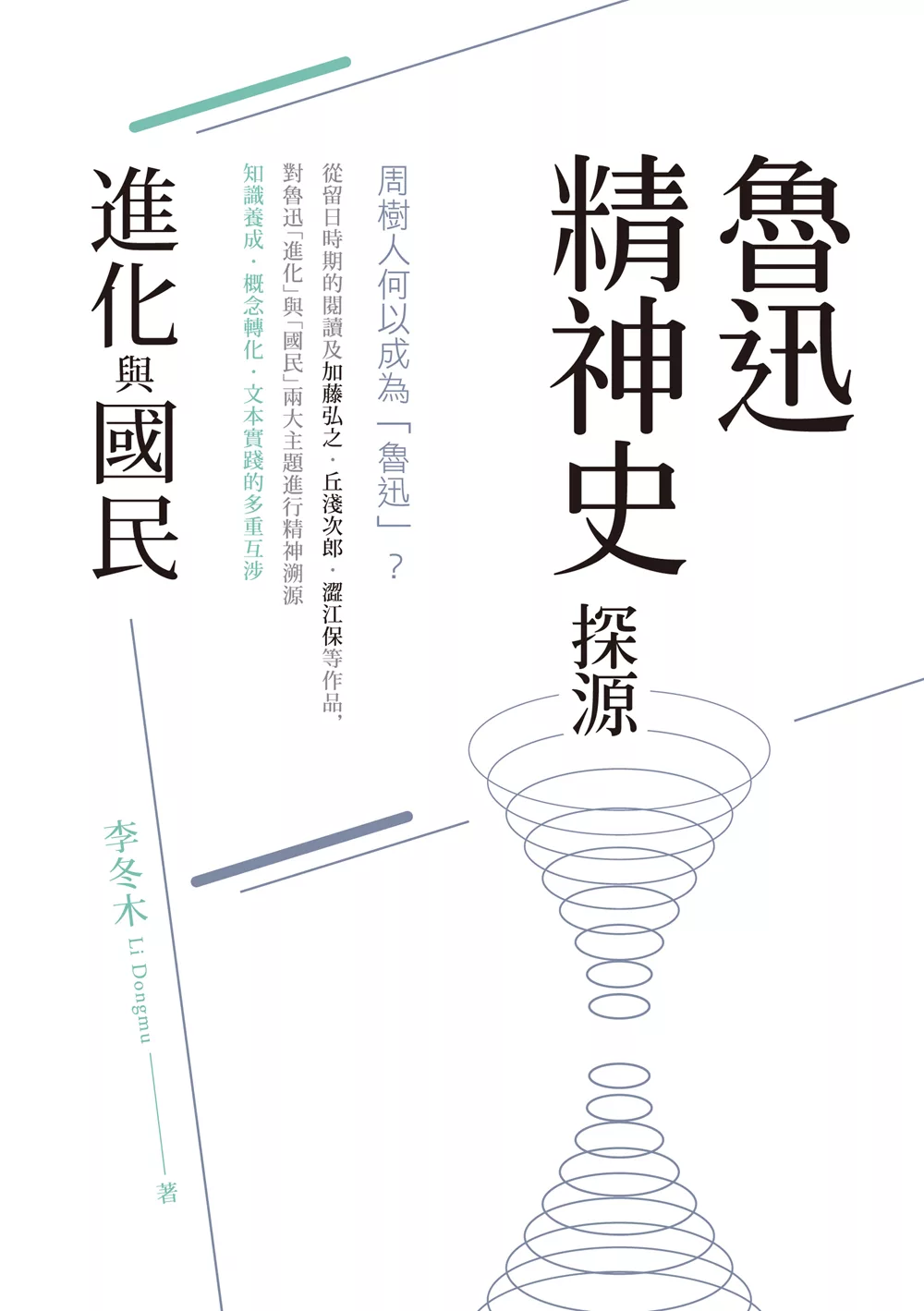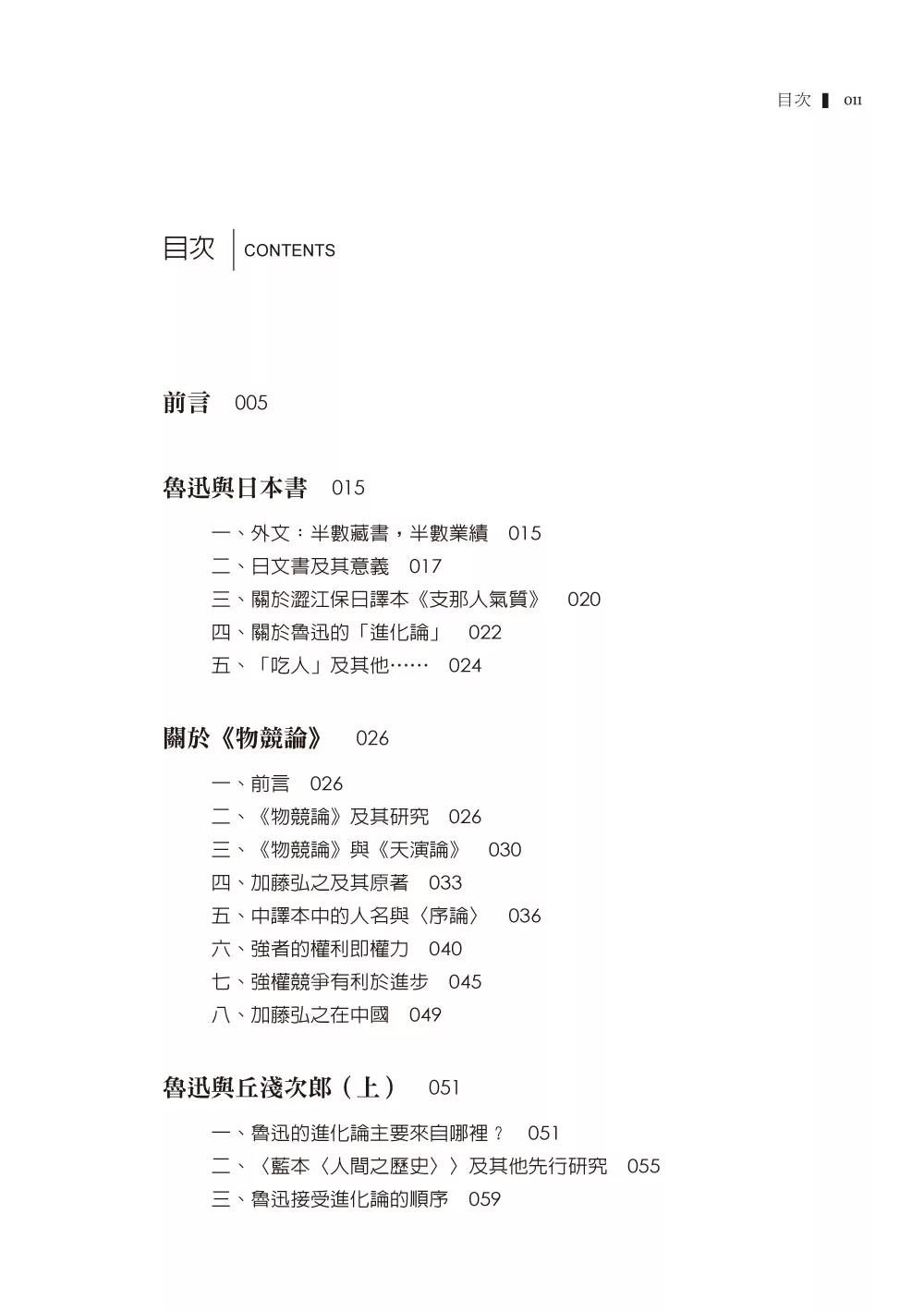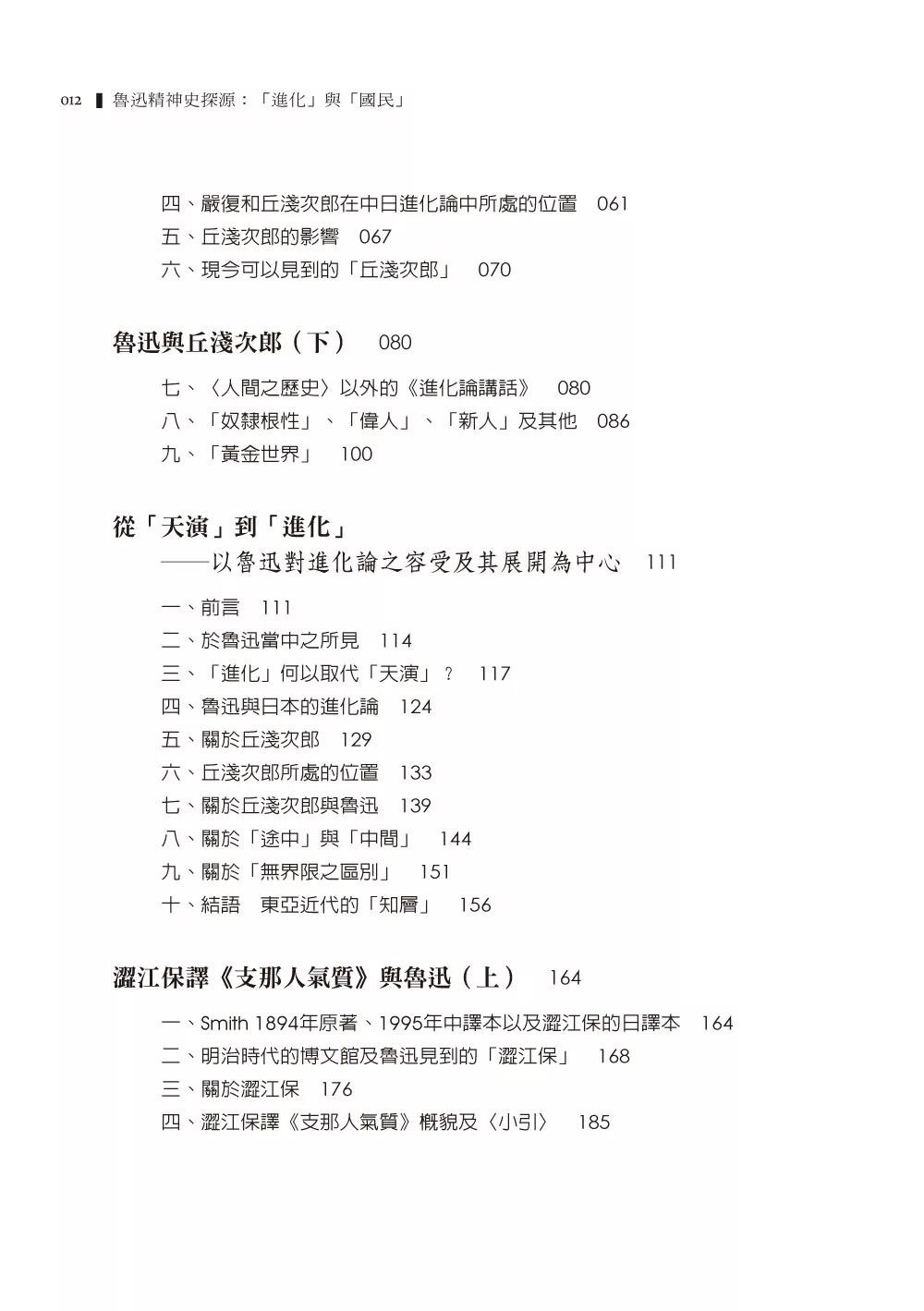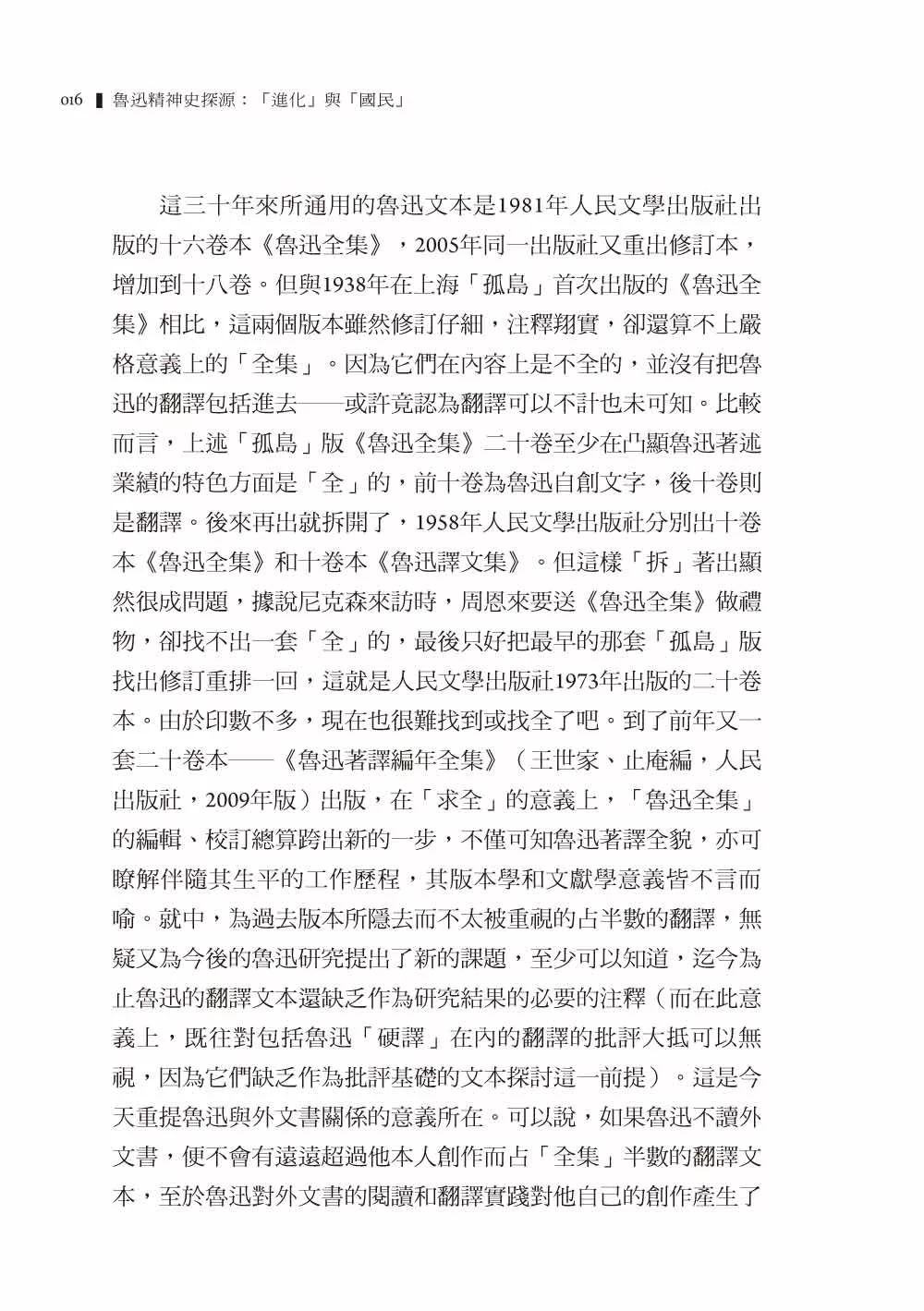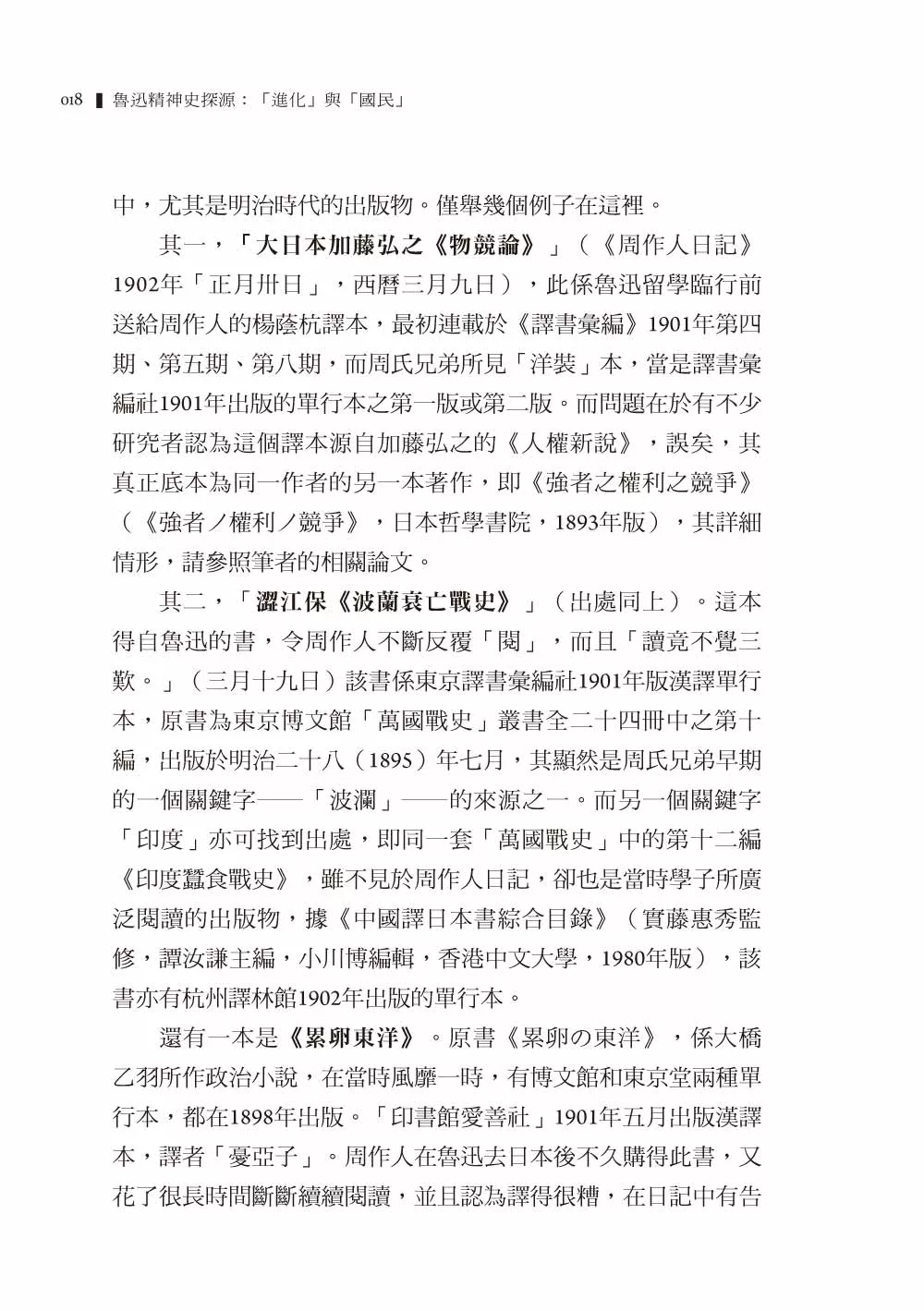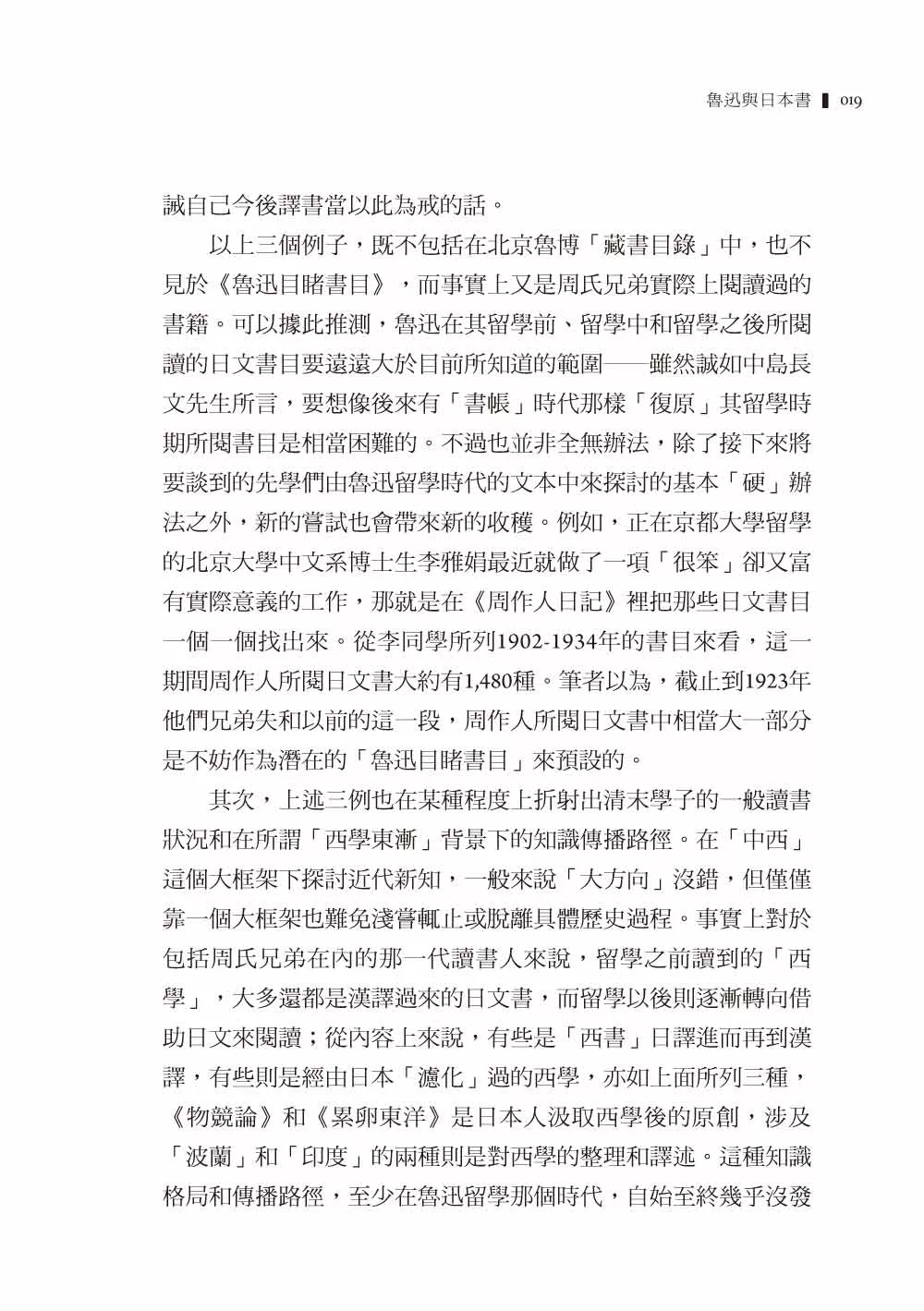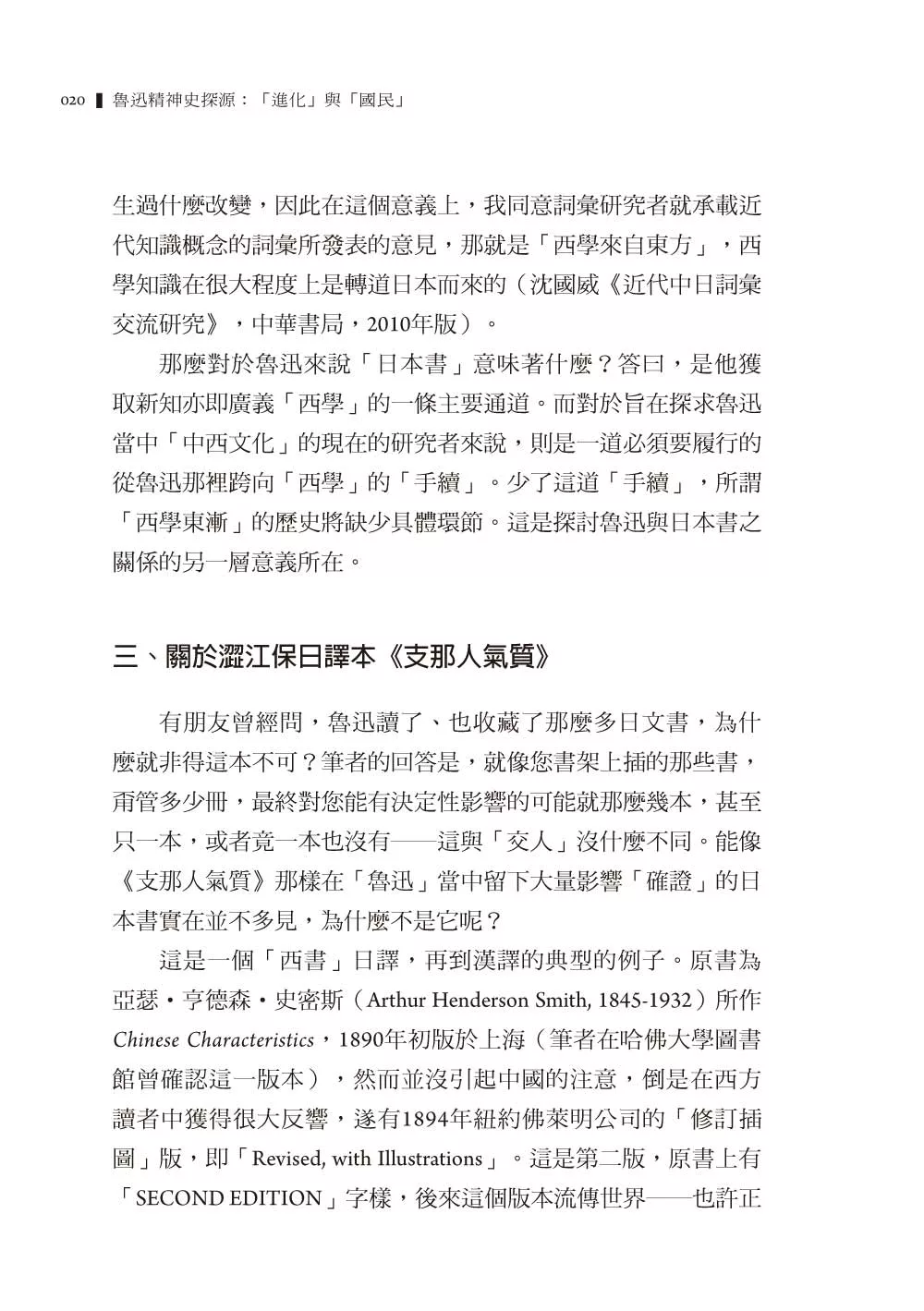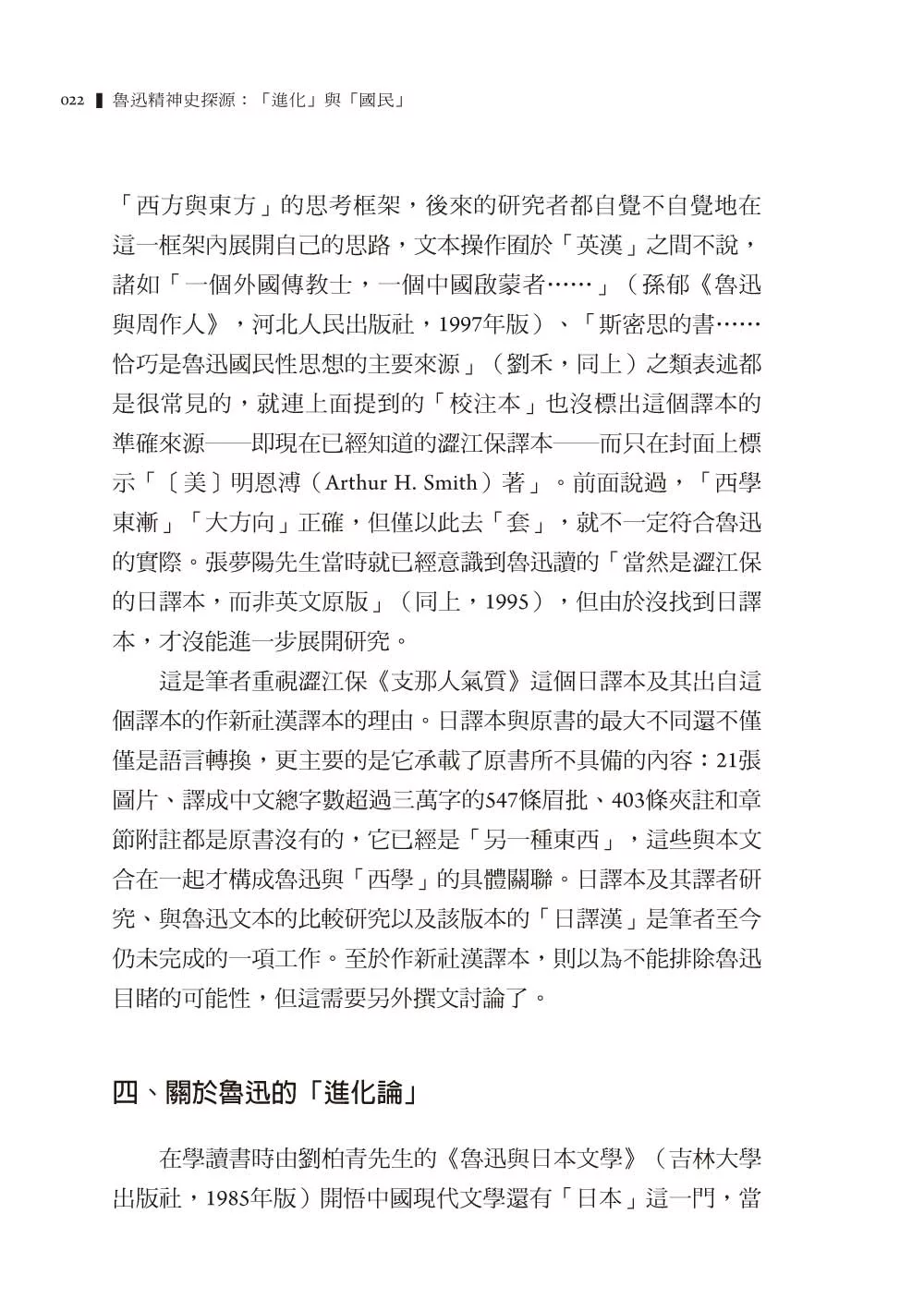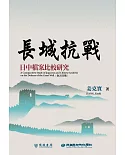後記
這十二篇論文發表於1998年至2011年間,有十多年的時間跨度,最早的一篇寫作距今已有二十二年,是名副其實的舊作。此次承蒙中研院老友潘光哲先生不棄,鞭策鼓勵,抬愛賜題《魯迅精神史探源》,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鄭伊庭先生的鼎力襄助,得以結集出版,這對作者來說,是一大幸事。能以舊作,就教於各方,令我感到無上喜悅和榮幸。
世間日新月異,新事物層出不窮,令人目不暇接。追蹤歷史舊跡又何嘗不是如此。令人倍感新鮮的發現與相遇,接踵而來,常使人流連忘返―這倒不是對舊時代、舊世界足跡的沉迷,而恰恰是因為其中蘊藏著新時代、新世界誕生的奧秘。本書收錄的各篇,皆側重於史實的追蹤和文本的重讀與發現,它們是魯迅精神史形成探源的一部分,是對以往被忽略了的魯迅閱讀史足跡的追蹤。這是個往往與超出「魯迅常識」相伴隨的世界,一旦步入其中,便不會太在意自己身後留下的足跡或無暇顧及。當然,這其中或許免不了為自己的懶惰辯解的成分,但它們的首次結集,卻是不爭的事實。
這也是一次由個人研究的視角對既往的一次回顧。哪怕是這麼微不足道的幾篇東西,也承載著居住在日本、中國大陸和臺北、香港的眾多師友和親人們的厚愛、教誨和鼓勵。在此,尤其要提到蔣錫金先生、劉柏青先生以及我的父母,他們都曾是本書若干小論的首批讀者,而如今卻都已仙逝他界。願他們的在天之靈也能分享我此時的喜悅。有些感謝辭在注釋中已經提到,如香港三聯書店的的侯明女士、佛教大學的辻田正雄先生等,更多的在文中無法一一述及。張夢陽先生在《支那人氣質》研究方面的引路之功,永世難忘。劉中樹先生、片山智行先生、吉田富夫先生、北岡正子先生、山田敬三先生、狹間直樹先生作為長輩學者,都曾就其中的若干問題給予過具體的指導和建議。我所任職的佛教大學、我的母校―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和吉林大學文學院,還有北京魯迅博物館、上海魯迅紀念館、復旦大學中文系、哈佛大學燕京研究所、立命館大學、廈門大學、南京師範大學等皆給予我厚愛,促使本書中一些問題的探討,得以通過講演和討論的方式直接與學者和同學們交流。還要特別感謝《東嶽論叢》的曹振華女士,她的熱情和執著,多次促成拙論的刊載。而在此次付梓之前,佛教大學楊韜副教授、博一張宇飛同學不厭複雜和繁瑣,幫我完成了各種文檔的轉換、輸入、整形和初校。謹此,一併致以衷心的感謝!
附言
關於書中涉及的問題在後來的研究推進,尚來不及做全面調查,僅就身邊的目睹所及,有以下兩種,可資參考。
關於《支那人氣質》,近年佛教大學文學部碩士畢業生山本勉先生的畢業論文,對澀江保與博文館「白眉」系列出版物《萬國戰史》之史實和文本展開了更加深入的調查研究,發現24冊當中,除了署名「澀江保」的10冊外,另有8冊的實際執筆者也是澀江保,這在澀江保生平事蹟的研究方面,可謂重大推進,而該作者的新近相關研究亦值得期待。參見山本勉〈明治時代の著述者渋江保の著述活動―出版物《万国戰史》を中心に〉(《佛教大學大學院紀要‧文學研究科篇》第43號,2015年3月)。
而作為關於整書研究的最新成果,是石井宗晧、岩崎菜子基於Arthur Henderson Sm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Revell,1894所做的「日本語全譯」本―《中國人的性格》(中公叢書,中央公論新社,2015年8月25日)。全書478頁,譯注多達350多個,並有解說和後記,是對既往研究的系統性承接。
圍繞著魯迅怎樣「看」「阿金」,也跟上來不少討論,尤其是竹內實先生,生前多次談及拙文,並對拙文的「虛構」說予以首肯,足以說明這一平臺構建的有效性。因那些論文都很方便查閱,容不在此一一列舉。
關於竹內好《魯迅》漢譯本,最近看到有北京的博士生同學建議:應把竹內日譯過去的魯迅引文,再直譯還原為中文,以觀他對魯迅的解讀(大意)。私以為,讀者的這一要求是正當的,且具探索價值。
作者謹記
2019年4月5日星期五清明節
於長春威尼斯花園巢立齋
前言
本書收論文十二篇,主要從「進化論」和「國民性」思想兩個方面探討魯迅(1881-1936)精神史源,以實證研究的方式,具體考察了在日本明治三十年代的思想文化背景下,留學生周樹人如何確立起其作為近代思想基礎的「進化」與「國民」的觀念,並將其反映到後來的創作當中的思想歷程。其中,著重探討了以加藤弘之和丘淺次郎為中心的日本明治進化論和以澀江保日譯版《支那人氣質》為中心的明治時期與國民性思想相關的出版物與魯迅之關係。
魯迅原名周樹人,因1918年在《新青年》上以「魯迅」的筆名發表短篇小說《狂人日記》而蜚聲文壇,並在此後生涯所餘的十八年間一直居於中國文壇的核心,直至今日,「魯迅」仍被認為是中國現代文學最具代表性的作家。那麼,周樹人何以成為「魯迅」?其精神史的來源和過程是怎樣的?就不僅僅是「魯迅」作為一個作家的個人成長史問題,而是關係到中國近現代思想和文學的根本問題。
一個人的成長,離不開他的閱讀,一個作家就更是如此,而一個作家年輕時代的閱讀又尤其如此。本書著眼於魯迅(那時他還叫周樹人)留日時代的閱讀,重點探討他的精神形成與日本書籍的關係。就當時中國人大規模留日這一時代背景而言,魯迅與日本書的關係,或許會為中國知識人的近代閱讀史呈現某種典型的案例。
〈魯迅與日本書〉,是關於上述問題的概觀,對書中其他各篇所探討的問題均有述及,故列入首篇,以呈現「魯迅與日本書」這一課題的整體研究思路。關於魯迅進化論思想的來源,嚴復作為「源」幾乎是公認的存在。然而,嚴復卻並非唯一。既往的研究過於偏重嚴復,客觀上淡化了魯迅與進化論的接觸面以及容受進化論的豐富性。
〈關於《物競論》〉探討的是嚴復之外的另一本進化論著作―《物競論》,具體檢證了該書的內容及其之於魯迅的意義,並且涉及了相關研究。《物競論》係加藤弘之(KatoHiroyuki,
1836-1916)著《強者之權利之競爭》(《強者ノ權利ノ競爭》,日本哲學書院,1893.11.29)一書的中譯本,譯者楊蔭杭(1878-1945),最初連載在《譯書彙編》1901年第四期、第五期、第八期,1902年由上海作新譯書局出版單行本。該書是魯迅在留日之前,繼《天演論》之後讀過的重要的進化論著作,並在臨行前把該書送給了其弟周作人,而後者在乃兄出國後又繼續閱讀。
〈魯迅與丘淺次郎〉(上),探討了魯迅留日以後接觸進化論的知識環境,並且把迄今為止的「魯迅學」當中並未包括的日本最著名的進化論傳播者「丘淺次郎」作為比嚴復更加重要、更加豐富的思想資源提出,涉及到的問題包括與此相關的先行研究、魯迅接受進化論的順序、中日兩國進化論比較、丘淺次郎其人及其著作和時代影響、現今可以見到的「丘淺次郎」等。
〈魯迅與丘淺次郎〉(下),通過「〈人間之歷史〉以外的《進化論講話》」、「『奴隸根性』『偉人』『新人』及其他」、「黃金世界」等幾個方面,具體比較和檢證了丘淺次郎文本和魯迅文本的關係,並由此揭示出,丘氏對魯迅的影響,時期並不只限於魯迅留學時期,範圍並不只限於個別文章,內容上也不只限於進化論,兩者之間存在著比現在所知更為複雜和深廣的關係。
〈從「天演」到「進化」〉,系統比較了進化論在中日兩國近代知識界的狀況,探討了在漢語當中,以嚴復為代表的「天演」概念系統何以會被日譯「進化」系統所取代的原因,並通過進一步呈現丘淺次郎之於魯迅的並不僅僅囿於進化論的深廣影響,具體揭示了在進化論容受過程當中的,處在流動狀態的東亞「知層」關聯。
《支那人氣質》,係羽化澀江保(1857-1930)譯自美國傳教士亞瑟‧亨‧史密斯(Arthur H. Smith, 1845-1932)所著Chinese Characteristics(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New York,
1894)的日文版,於明治二十九年(1896)12月由東京博文館出版。該書是魯迅思考國民性問題時的重要參考書,並與魯迅的「國民性」話語構成廣泛的關聯。但既往的研究主要基於史密斯的英文原書與魯迅的關係展開,忽視了澀江保日譯本的存在。而魯迅讀到的卻恰恰是日譯本,而非英文原著。〈澀江保譯《支那人氣質》與魯迅〉(上),是首篇探討澀江保的日譯本與魯迅關係的論文,不僅將《支那人氣質》首次作為問題提出,還詳細探討了以「日清戰爭」和博文館出版物為核心的出版背景,發掘了被歷史遺忘的明治時代的著述大家澀江保的貢獻以及魯迅關於前者的讀書史。
〈澀江保譯《支那人氣質》與魯迅〉(下),是關於該譯本形態和內容的探討,主要側重於不見於史密斯原書的「非原本內容」,即書前小引、眉批、正文中出現的夾註以及「黑格爾關於支那問題的論述」的長達25頁的引用。這些內容譯成中文,超過了三萬字,既是澀江保譯本的有機組成部分,也是Sm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作用於魯迅的名副其實的「原形態」。
〈《支那人氣質》與魯迅文本初探〉,是在前兩篇的基礎上,對兩者的文本關係所做的實證性初步探討。涉及的問題包括:魯迅本人對《支那人氣質》的述及;相關的先行研究;「面子」、「做戲」、「看客」;打擾死前的病人與〈父親的病〉;魯迅留學時期的革命「心像」與阿Q的形象塑造;辛亥革命與「辮子」;並非結束的結束語。對這些問題的檢證,不僅坐實了兩者的關係,也為進一步探討呈現了新的觀察平臺。
〈「乞食者」與「乞食」〉,是關於魯迅與澀江保譯《支那人氣質》關係研究的繼續。通過「乞食者」「乞食」「乞丐」「布施」「仁惠」這一組相關的概念所構成的角度,對魯迅與《支那人氣質》的關係再次進行考察,從而揭示出二者在精神結構上的關聯性。
〈「從僕」、「包依」與「西崽」〉,是通過另一組關聯概念的視角,對魯迅與《支那人氣質》關係所做的進一步的探討。所謂「從僕」與「包依」(ボーイ)在澀江保的日譯本中都是表示「僕人」的概念,體現著史密斯作為「支那人全體之撮要」所選擇的對中國人「氣質」的一個觀察點;所謂「西崽」(boy)是魯迅描寫某類中國人精神特徵的一個關鍵字,那麼,魯迅是否借鑒了《支那人氣質》?該篇通過三個關鍵字探討的正是這一問題。
〈魯迅怎樣「看」到的「阿金」?―兼談魯迅與「支那人氣質」關係的一項考察〉,是通過實地考察和文獻檢證對〈阿金〉(1934)這篇作品生成機制的探討。作品的創作和「阿金」這個人物的塑造,當然與魯迅在上海的生活環境和生活經歷直接相關,但是《支那人氣質》當中的「廚子」也是無法迴避的存在,沿著後者的視角看下去,「阿金」也就正處在「從僕」、「包依」與「西崽」的延長線上。
〈「竹內魯迅」三題〉,是翻譯竹內好《魯迅》(李冬木、趙京華、孫歌譯《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3月)一書的過程中為自己學習「竹內魯迅」而寫筆記的一部分。「竹內魯迅」關乎本書的所有篇目,可謂全書中的一個隱形存在。此篇以三個題目闡述了筆者關於「竹內魯迅」的看法,以及所得和揚棄。竹內《魯迅》漢譯本出版後,引起了極大反響,但筆者的意見止於此篇,至今並無補充。
以上各篇是在曾經的十幾年間,探索魯迅閱讀史當中的與日本書關係方面的部分所得。探索,與其說常與收穫的喜悅相伴,倒莫如說總是和困惑、焦躁乃至彷徨相隨。偶有所獲,雖會感到欣喜,但倘若記錄排列出來,又多顯記錄者的魯鈍與笨拙。不過,既然先行一步,還是把足跡完整地留下的好,可提示後人少走彎路,或許還能拋磚引玉也未可知―當然,這已是奢求了。
此次結集時不改初刊文字的想法如此,祈讀者諒解為幸。
作者謹記
2019年4月3日星期三
於長春威尼斯花園巢立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