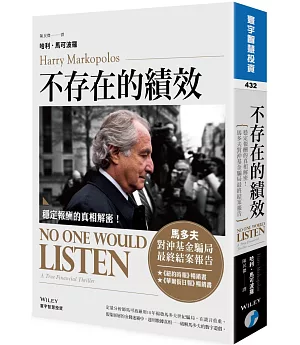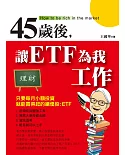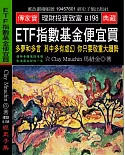序
金融監管迫不及待
哈利 · 馬可波羅是一名英雄。
但這個名聲與他原本想做的事無關,他既沒能阻止馬多夫建立史上規模最大的龐氏騙局,也沒能保住馬多夫投資者的資金。他所做的,是把他曾提出的警告整理成一份詳盡的紀錄文件,當馬多夫案最終內爆而崩潰時,身負杜絕舞弊、保護投資者職責的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就無法隨口瞎說而推卸責任。
龐氏騙局往往在「穩定的不平衡」狀態裡運作。也就是說,這樣的騙局雖然終究無法成功,但只要條件許可,它就有可能無限期地持續下去。某個事物得以長久存在,並不代表它是正當的。在馬多夫的故事裡,縱使其中處處插著紅旗,那個美好到令人難以置信的情境仍迷惑了投資者。馬多夫的績效紀錄,跟通用電氣連續一百個季度的利潤成長紀錄,或者跟思科公司在一九九八年至二○○一年連續十三個季度高於分析師預測一美分的股價相比,有什麼差異呢?馬多夫的績效紀錄太不真實了,因而也引發質疑。問題在於:我們是否應該只堅定杜絕龐氏騙局?或者對其他較為隱晦的操縱手法也應該有所行動?
有一次,我向一位華爾街分析師指出某家公司做假帳。這位分析師卻說,他更有把握看漲這家公司的股票—因為這麼做的公司從不會讓華爾街失望。多年來,我親眼目睹,乃至親身經歷,證管會如何為了保護大罪犯,犧牲他們本該保護的投資者。對於業內的小欺小詐、小規模內線交易,沒錯,還有對沖基金的小過失,證管會採取嚴厲手段,這確實是它該做的。然而,一旦面對大公司與大型機構時,證管會瞬間變得謹慎、溫和,只徵收起不了震懾作用的罰款、聚焦在文件紀錄等枝微末節,卻忽略了真正重要的事,比如正受騙的投資者。
馬多夫案就是這個問題的縮影。罪行尚未揭發前,他是大型的證券經紀經銷商、納斯達克前主席。他的名氣不是來自於基金經理的身分,更別說對沖基金經理的頭銜,因為他並不是。騙局東窗事發後,他成了眾所皆知的騙徒,人們稱他為對沖基金營運者。
即使如此,迄今,他的對沖基金仍是我所聽過唯一不收取管理費與績效獎金的。如果他的頭銜是對沖基金經理的話,我懷疑他是否還能把證管會蒙在鼓裡;證管會若知道他經營對沖基金的話,應該早就把他捉拿歸案了。華倫 ·
巴菲特說:「海水退潮後,你才知道誰沒穿褲子。」二○○八年的金融危機,讓我們看到許多人,包括馬多夫,原來一直都沒穿褲子。有效的監管意味著即使在漲潮時,也有能力阻止這些沒穿褲子的人。
如各位所見,證管會確實採取了一些改革措施,而哈利.馬可波羅也對這個機構的未來表示信心。但等證管會真正對某個尚未申請破產的大企業、華爾街機構提出訴訟(即在資金賠光前採取行動),我再下評斷。如果馬多夫的崩垮真有為我們帶來一絲光明的話,那指的必然就是證管會在這一瞬間被戳破了。哈利.馬可波羅讓這一切得以發生,我們都該向他致上謝意。
大衛.安宏 (David Einhorn)
前言
為正義而戰
二○○九年六月十七日,陰雨綿綿的午後,地點是曼哈頓下城的「大都會懲教中心」,大衛 · 科茲坐在一間只有單格窗戶的小房間裡,耐心等著與伯納 ·
馬多夫會面。馬多夫一手操縱了史上最大宗金融犯罪案,而這場價值六百五十億美元的龐氏騙局,卻完全沒有被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所揭發—儘管我在過去九年裡曾向他們提交了五次相關證據。科茲身為證管會總監察長,此時正在調查他主事的機構在這次事件中的全面失責。
科茲與副手諾爾 · 法蘭吉平並肩而坐,他們對面有個空位,空位兩邊坐著馬多夫的兩位律師—艾拉 · 索金和尼可 ·
迪巴洛。馬多夫終於被押送進這個房間,警衛小心翼翼地解除手銬。馬多夫曾經是金融業之王,廣受敬重—他是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的創辦者之一,也曾任該交易所主席;他擁有華爾街最成功的其中一家證券經紀經銷商,更是顯赫的紐約慈善家。現在,身著亮橘色囚衣的他,在四周暗灰色牆壁前格外顯眼;他落坐在兩位衣著光鮮的律師中間。
馬多夫答應會面,但是有一項條件:談話內容不得錄音或謄寫。科茲首先向馬多夫說明他有法定義務說出真相。一週後,馬多夫將被判決,這或許是他答應與科茲當面對話的原因之一。或者,這決定僅僅出於他的自負,只是想要緊抓住最後一次成為焦點的機會。馬多夫的動機有誰料得準呢?他的動機成謎,即使到了今天,這個人仍充滿謎團。
根據科茲事後回顧,馬多夫極有禮貌而且非常配合。「我們原本以為他對每個問題大概只會回應一兩個字,或者當他想多說些什麼的時候,一定會被律師打斷。可是當時的情況完全不是這樣,他爽快地回答所有問題,看起來似乎毫無保留。」在會面的三個小時當中,科茲和法蘭吉平寫下了大量筆記,幾乎就是對話的逐字稿。馬多夫首次透露這場龐氏騙局的全貌,還說明計畫是在無心插柳的狀況下開始的,甚至坦言,他很訝異證管會沒有抓到他。他毫不客氣地批評證管會調查員是白癡、笨蛋,都是一些只會吹牛的傢伙。科茲留意到馬多夫頻頻吹擂他在金融業裡的人脈。他聲稱自己認識許多重要人物—「這人我認識、那個人是我的好朋友、這個人他很熟、那個人跟他有特別的交情。」
但是當柯茲在談話進行到一半時提到我,馬多夫的態度就改變了。科茲翻著筆記本,問了一句:「你對哈利 · 馬可波羅這個人瞭解多少?」馬多夫瞬間輕蔑地揮揮手,一臉憤慨。他跟科茲說,我算不了什麼。「這個人在媒體前面風光,每個人都在看他,他自以為是預言家。但這都是過度渲染,你知道嗎?這個人根本就是業界的笑話。」
馬多夫說我不過是嫉妒他的成就。科茲意識到馬多夫視我為對手,而最令他不快的是,我搶盡了原本該屬於他的鋒頭,他不會就此罷休。會談最後,他為自己的投資策略辯解,而這些說詞早已被我擊破。當時他跟科茲這麼說:「你只需要看看這策略是為了哪些人而設計,你就會知道那是可靠的。他們都知道這個策略切實可行。他們懂得比哈利這個傢伙多太多了。」不,他們不懂。他們只看到錢。面對這個顯露危險魅力,還把我說成是笑話的男人,他們根本無法看透。
我必須先聲明,本人並沒有因為最後的勝利而得意。我是哈利 · 馬可波羅,這是我作為告密者向證管會揭發的第一起案件,本書內容正是此案件的真實調查報告。
我是如何成為告密者的?一切得從一九九九年說起,好友法蘭克 · 凱西讓我注意到了馬多夫。我對這位華爾街大亨的財務成就感到驚奇,想要更深入瞭解,並嘗試複製他的投資法卻沒有成功,於是我認為那樣的績效是不可能的。我發現裡頭有紅旗警訊,一支接著一支,直到無法再忽略這些警示訊號。
二○○○年五月,我把所有知道的事都告訴了證管會。我前後五次向證管會報告我的憂慮,但沒有人理會,直到一切都太遲了。作為舉發華爾街最有權勢之人的告密者,整個歷程宛如夢魘,我時刻擔心自身與家人安危。他操縱的騙局是市場史上最重大的罪行,這一點我非常肯定。十年後,馬多夫進了監獄,而這背後的一切,我們也都知道了。
我的調查小組由四個正直可靠的成員組成,我們一致相信必須為良善道德而行動。我們形成一道最後防線,守在馬多夫遍及全球的「聯接基金」(feeder funds)組織以及受害者之間;遺憾的是,這也是唯一的防線。我們極力阻止那些不對勁的事情。由於我們所做的努力,證管會將蛻變成一個全然不同的機構,如果這個機構還繼續存在的話;而我們監督與管制市場的方式也將會徹底改變。這就是我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