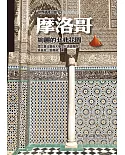序
「例外之地」與「臨時之所」
Exceptional Spaces, Tentative Locales
2018年光復節前夕,當臺灣被逐漸加溫的「九合一」選舉和公民投票炒熱的時候,因為收容大量偷渡客而曾經聲名大噪的「靖廬」新竹收容所,正悄悄吹響熄燈號,走入歷史。靖廬的正式名稱為「內政部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新竹收容所」,前身是日本神社,1991年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從軍方接收,成立「大陸地區人民處理中心」,2007年再由入出國及移民署接管,2015年再度更名沿用至今。在那個每年至少二萬大陸偷渡客來臺的1980-1990年代,靖廬作為兩岸關係的一道邊界,也是臺灣經濟榮景的另類象徵。如今,非但大陸偷渡客的記憶隨風而逝,由「陸客」和「陸生」取而代之,靖廬所容納的偷渡客亦悄悄轉變為東南亞移工。但是,「靖廬」熄燈改建公園,並不表示「收容所」將從臺灣消失、非法外勞立即就地合法,而是要另地新建,繼續在島內劃出一塊塊的「例外之地」與「臨時之所」,以「收容」那些已然在內的「外人」,阻斷「將來」(l’avenir)成為現在。
從「例外之地」與「臨時之所」的角度來看,靖廬並非前無來者。劉吉雄導演的《例外之地》討論的,便是1977-1988年曾經在澎湖西嶼鄉和白沙鄉設立的越南難民營。1976年越戰結束,胡志明領導的越共成功擊退美國大兵後,大量難民浮游怒海,四處奔逃。作為臨近地區及冷戰反共勢力的一環,臺灣自然也在難民逃難的範圍內,並將人道收容與反共任務結合一體。至1988年11月15日關閉,澎湖白沙鄉的講美營區,共計接收45批次,共2098名越南難民;這些難民有些經身分查核確定後,轉交聯合國難民署,送往第三國安置,有些則轉往臺灣,成為「新臺灣人」。有趣的是,當逃難潮退去,難民不再的時候,難民營開始收容來自大陸的「反共義士」。1雖然人數很少,但「反共義士」與「難民」錯身共處,一方面提醒我們大陸偷渡客與東南亞非法移工的置換與承續不只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另一方面,也讓我們看見人道與政治的共謀,跨越政黨與國界。所謂「身分」不過是人口治理與邊境管理必要的行政識別,用以確認敵我、內外,以明確邊界與國境,而不是什麼認同或理想之必然。因此,難民營也罷、收容所也好,都不過是國界中的「例外之地」、「臨時之所」;如同其他的監禁設施,它們都是維護社會秩序,國家疆界與政治認同的必要手段,即令它們往往以人道、良善與法統之名而為之。這樣的「生命治理」模式試圖維繫一個純淨、不受污染的國家空間,也突顯了所謂「邊界」─而非人道─才是國家機器最敏感、最不柔軟的一塊。然而,恰恰是這些邊界「過敏」的反應不斷提醒我們,所謂的「外人」已然在內,「將來」已是現在。
本期專題「營區與邊界」正是沿著這個思路展開的,因為難民問題以及隨之而來的各種情緒,從西方到東方,已經成為全球社會最為突出的倫理難題。一方面,在理念上,我們仍然標舉著「人道」理想,希望對受難的他者伸出援手,證明人類文明可以往「利他」的方向進步;另一方面,全球經濟衰退所造成的民生凋弊,使得各國政府在面臨資源排擠與民粹思潮的挑戰時,不得不向現實低頭。原該是「臨時之所」的各種營區(settlement)逐漸成為化外之地,既無處吸納,也無法拆除;同時,「境外之民」開始成為日常街頭的風景,迫使更多「例外之地」被建立與強化,以確保公民生活之純淨與平靜。作為全球的跨境行動者,難民、偷渡客、非法移工,乃至產品(例如最近最受注目的大陸豬肉製品),都在提醒我們所謂家國只是權力的虛構,而邊界不過是權力的手段。
這個觀點受到法國思想家阿吉耶(Michel Agier)的啟發。在本期收錄的兩篇翻譯─〈生命權力以其敏感形式來檢驗:當代異質空間民族誌計畫的簡要導論〉與〈製作不受歡迎者〉─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阿吉耶是如何從「不受歡迎者的製造」這個命題上展開他的當代民族誌觀察,從而在難民問題上重新開發與整合傅科(Michel Foucault, 1926-1984)與阿岡本(Giorgio
Agamben)的思想視野。如阿吉耶所說,「異質空間」(hétérotopie)和「生命權力」(biopouvoir)這兩個傅科發展出來的分析概念「並肩而行,相互召喚」,因為它們可以建立起一種問題意識,幫助我們探討關於「地方和認同的浮現及源起(而非其失落),並以流亡,而非拔根,做為二十一世紀主要的個人與政治境況」,從而促成人類學與哲學的對話。事實上,不只是人類學和哲學,當代流亡的政治境況同時是政治學與人文學的核心關懷,從巴勒斯坦人的返鄉與建國,到亞美尼亞大屠殺的種族創傷,乃至於緬甸對羅興亞人的迫害以及敘
利亞庫德族難民的流亡,我們一再見證的正是「地方和認同的浮現及源起」,以及奉其之名所執行的制度性與暴力性排除。因此,如何從這個論題出發,重新思索營區與邊界的作用和意義,就成為文化研究介入難民議題極為關鍵的思路和方法。不過,阿吉耶的研究有更深廣的關懷。如陳瑞樺在〈在共同世界的邊緣探問生命政治:阿吉耶的城市人類學與難民營研究〉這篇導言中所介紹的,阿吉耶之所以將傅科與阿岡本的思想視野整合,是因為他的思想來自法國「城市人類學」這個學術脈絡,上承巴隆迪耶(Geroges
Balandier)和阿爾塔伯(Gérard Althabe)所開啟的都市人類學與非洲研究,以及歐傑(Marc Augé)對於「非地方」(non-lieux)與超現代性的分析,從而將對都會研究的關懷更深入地轉向空間的多元性結構,尤其關注由「閾空間」、「外地方」與「間隙型城市」等概念組織出來的「複城」(la ville
bis)。陳瑞樺精準地指出,阿吉耶用「複城」來指稱邊緣地帶產生的城市及城市社會學的知識,是以「複城」不只是對象也是知識,更是一種在不穩定關係中浮現的「城中之城」。這也就使得我們對於城市的認識得以從人類學,乃至現象學出發,去探究「人的行動如何生產城市」,並以邊境與移動為線索去思考城中城與城外城(亦即城市與「例外之地」、「臨時之所」)之間複雜關連與共構。在這個意義上,難民既是研究當代城市形構的線索和方法,同時「城市」作為共同生活空間的理想也提供了我們重新思考營區與邊界的起點。為了讓讀者對阿吉耶的思想有更充份的認識,我們特別製作了一份阿吉耶著作目錄。感謝曾嘉琦小姐的協助。
除了譯介阿吉耶的思想之外,「營區與邊界」專題還包括了四篇論文與三篇評論。趙中麒的〈緬甸克倫難民的文化實踐與民族主義運動〉聚焦在難民營內的物質與社會佈局,來探究克倫難民如何在流亡中凝聚民族認同和維繫民族文化。他發現,雖然難民營是「例外空間」,卻不是「法外之地」,在難民營、聯合國難民署與泰國政府之間,其實有一整套綿密繁複的規範在形塑難民的生活。在經濟上,難民一方面被鑲崁在邊境貿易之中,另一方面也遊走在合法與非法的灰色地帶中,為當地經濟提供廉價勞動力。另外,雖然難民營收留的難民來自緬甸不同地區,不全是信仰基督教的克倫族,但在社會生活層次上的許多安排還是由克倫族所主導,以致在泰緬邊境的幾個營區彷彿成為國中之國,自成一格的克倫城邦,不僅有自己的政治組織與習俗儀式,還有小規模的軍事訓練與教育事業,將看似封閉的營區連向廣大的世界。潘美玲的〈在市場中實踐「西藏意識」:印度、尼泊爾流亡藏人的難民經濟〉則討論流亡藏人如何在尼泊爾和印度的難民營區內透過毛衣與地毯的製作與貿易,建立自主自給的經濟收入,並藉之實踐西藏意識,一方面向外尋求支持,另一方面對內維持歷史、民族與文化認同的延續。潘美玲認為,藏人經濟的發展是以求生為手段,正義為目標,以及傳統的延續為優先,因此展現一種既內在於資本主義體系,又不以資本積累為目的的經濟模式。流亡的處境固然艱困,反而強化了藏人的民族與文化意識,從而賦予「經濟」不同的意義。潘美玲和趙中麒的文章顯示,營區絕非與外界隔絕的自我封閉體,而是被各種政治力量所穿透,又在經濟與社會上與各方保持連繫的幽秘節點;同樣的,邊界也絕不是一條區分內外的想像曲線,而是被不同力量與連繫所貫注的空間。不僅邊界刻印在難民的身體上,會隨之移動,營區也在難民與物質的移動中取得了在現實世界中的存在。這些被標示或不標示的境外之地、法外空間,隨著難民的移動與難民經濟的發展,越來越被整合進全球化的經濟結構當中,只是我們往往視而不見,或見而不識。
洪伯邑和練聿修合著的〈「越」界臺茶:臺越茶貿易中的移動、劃界與本土爭辯〉將我們的視野從難民和營區轉向「物」的跨界移動與變身,從而提供了另一個理解營區與邊界的方法。對他們來說,物的移動更深刻地改變了我們對於邊界的認識,因為像茶葉這樣的農產品確實有「橘逾淮為枳」的風險,只是這個風險的意義不在於質變,而在於國家如何維繫自身的邊界,確保其純淨與本真。追索九十年代至當前,臺越之間茶葉製作與貿易的變化,洪伯邑和練聿修發現,越南茶和臺灣茶其實處於貌合神離,彼此依賴的關係中,此一關係隱含「臺灣的南向政策、農技轉移,臺灣茶進出口市場的消長、食安議題、食農體系全球化與本土農業保衛戰等多層意義」。換言之,判別越南茶和臺灣茶這件事本身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政治、經濟與權力的纏結,是在全球化跨界常態中,如何理解國家和邊界的智識與政治挑戰。在這個意義上,茶的物質性─從生產、製作到消費─所提供的穿越與顛覆動能,更甚於人,因為它所涉及的是「本土與境外,邊界與移動互為表裡的實作過程」。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從更為複雜而全球的動態過程去思考他者與自我的判別,看到「地方和認同的浮現與源起」本身即是權力的劇場。曾維龍的〈馬來西亞「後茅草行動」的華社變遷:以「動地吟」詩人群體為個案討論〉,雖然不在這個專題最初的設想與規劃之內,但東南亞華社本身即是一種邊界性的社群。藉著討論馬來亞西華人「動地吟」這個為期25年的詩歌朗誦活動,曾維龍指向了邊界性社群如何定義自身,介入當地社會的可能。最為有趣的是,透過華文這個語言媒介的跨國傳播,黃錦樹稱之為處於「盆栽境遇」的華社,其實與馬來西亞境外的廣大華文傳統與華人社群有著密切的關聯,不僅組織與參與「動地吟」的諸多詩人接引的是一種「現實主義詩學」,他們透過詩歌介入社會的嘗試也受到臺灣民主化運動的啟發。張錦忠在批評與回應中,亦對馬華社群的狀態與文學活動提供了不少精要的補充;他以文學行動主義來看待「動地吟」的這個角度,尤其突顯了邊界主體的能動性,以及文學跨越邊界,組構社群的社會功能。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的本土與在地本身,也是在多元的跨域連繫中建構起來的,邊界其實暗示著境內的多元構成,無法被國界所阻斷與隔絕。
三篇評論文章:洪世謙的〈評阿吉耶的《邊界:邁向世界主義境況的人類學》〉、朱元鴻的〈紀念包曼:一位永遠的異鄉人評論家〉和柯能源的〈旁觀他人痛苦的影像倫理:《海上焰火》與生命蒙太奇〉為整個專題補充了更豐富的思想元素。洪世謙的書評深入了阿吉耶的思想,闡述他如何從邊界與認同出發思考世界。朱元鴻則介紹了另一位值得敬重與懷念的思想家包曼(Zygmunt Bauman,
1925-2017),討論他的思想如何從「液態現代性」的反思回到康德「世界永久和平」的道德命題,從而在移民、鄉愁、部落主義等相關議題中,戳破那個由自戀文化所包裹起來的虛像自我。雖然談的是一個已逝的西方學者,朱元鴻夾議夾敘的春秋筆法對臺灣的狀況有許多深刻的觀照。柯能源的文章討論的是2016年獲得第66屆柏林影展金熊獎的紀錄片《海上焰火》(Fire at Sea,
2016)。這部電影由義大利導演羅西(Gianfranco
Rosi)所拍攝,以義大利南端島嶼蘭佩杜薩(Lampedusa)為中心,討論非洲與中東難民如何跨越邊界走向新生或末路的紀錄片,深刻地呈現了「觀看他人痛苦」的倫理困境。同為導演的作者(曾與夫人郭珍弟合拍《海上情書》[2014])以詩意的文字,精準點出羅西影像美學的深度,如何以島上的日常生活與逃難現場的影像互涉,建立在場與見證,藉著純粹展露事物本身的狀態,引領觀眾去追問為什麼,從而讓觀看他者的視角得以「迴向」到觀者本身,召喚出比同情更為深刻的自省。柯能源特別指出,影像的效果需要時間的沉澱,需要「不經意的喚回」才能更顯力道。這個觀察再次提醒我們,他者並不處在時間與空間的遠端或外部,被營區或邊界這樣去歷史化的時空所標示,而早已是「此時此地」。我們需要的是識別的能力與勇氣。
本期還收錄了一篇「研究紀要」:〈馴化水,也要馴化人:臺北市自來水生飲計畫的面子工程與技術展演〉。在這篇文章裡,王志弘和黃若慈從工程技術與都市治理的角度思考人與物雙重馴服的辯證關係。以臺北市自來水的生飲政策為例,他們指出人與物的關係不只受到技術的中介,也在治理邏輯的變化中不斷變化。這篇文章展現了「科學技術與社會」(STS)的觀點如何介入文化研究,也突顯了看似硬性的都市基礎建設,從來不只是關於技術與工程的施作,也涉及了文化的說服與身體的馴服。有鑑於文化研究向來傾向再現與文本分析,而缺乏對於社會與文化技術的思考,我們希望,這篇研究紀要能為讀者開拓更寬廣的研究興趣與視野。
最後,「營區與邊界」這個專題能夠成形,要感謝本刊編委陳瑞樺的規劃和推動,從徵稿啟事、爭取稿件、翻譯文章、取得授權,到審查流程等等工作都是瑞樺親力親為,令人感佩,也透露了學術工作之繁雜不易。秉持對學術的熱枕,本刊會持續規劃重要的前沿議題,敬請讀者期待,也歡迎有志規劃專題或論壇的讀者們主動與我們聯繫,讓《文化研究》更為豐富而精彩。
編輯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