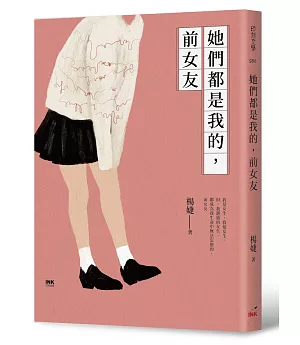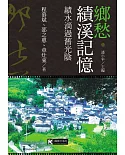女生的心眼,是世上最美麗也最恐怖的事
她是我的七月,也是我的安生。
挹注驚人誠實的散文書寫,揭露傷害的原型
——每個女生,都有忘不了的另一個女生
我是女生,我怕女生。
但,我遇過的女生,都成為我生命中無法忘懷的,
前女友。
每個女人的原型,都是女人。
在異女和女同之間,還有許多樣貌——
比如,害怕女生的女生。
童年第一個女生朋友,是送禮物送來的。
大學被女生排擠後,她看到女生就躲,卻偏偏挑中女校實習、搬進女生宿舍。
與學生間的扭曲情感、既如仇人也如家人的室友、國中時愛戀的女孩……
重返女生世界,終於回溯寫作的源頭——
她從來沒有忘記她,她卻再也不曾回頭。
新生代作家楊婕繼《房間》之後,正視內心黑暗,如實寫下關於女生之間的各種心眼──那些玻璃心、公主病,以及對愛的計較。
好評推薦
吳曉樂、林立青、廖梅璇、蕭詒徽──專文推薦
她寫,她太敢寫了。尼爾・蓋曼曾說過,寫散文如果不誠實,就別寫了。而楊婕,簡直是太誠實了。……楊婕多數的書寫,都可以濃縮成一句:你會愛(傷害)我很久嗎?——吳曉樂
楊婕的文字有一種魅力,在散文這個題材中,作者的自我揭露或者書寫內容要和讀者產生共鳴,越是能夠帶給帶給讀者共感的文字,就越令人愛不釋手,楊婕的作品就有這樣的特性。——林立青
女生對女生不再只有父權秩序裡的忌憚排擠,也有悉心呵護的姐妹情誼;也只有女生才看得出,那些彆彆扭扭、玻璃心,公主病,對愛的錙銖必較,都是一個小女孩好怕被人厭棄,強迫自己不要愛得太熱烈,衍生出的種種症頭。——廖梅璇
如果說,《房間》是在模糊霧中隱晦指名的寓言書,《她們都是我的,前女友》就是句句署名的生死簿了。……我在這本書裡,終於讀到了楊婕。——蕭詒徽
目錄
推薦序
認識楊婕與她對書寫的忠誠/吳曉樂
文藝少女說明書/林立青
翹翹板倒向另一端/廖梅璇
楊婕/蕭詒徽
輯一 孩子
文字的初始,是宇宙
扯鈴女孩
黑暗之光
最後一個孩子
原型女人
Lia
愛的教育
恨的教育
輯二 我的女性主義的第一堂課
海水有字
時間情書
地老天荒的愛情
我的女性主義的第一堂課
海邊與賽馬節
颱風眼
輯三 公主病
第一個朋友
怕狗婕
貝蒂
香香自助餐
林王鵝肉飯
輯四 越南室友
有人要跟我換房
卡娜赫拉
加油孟子
楊茄
卡娜赫拉掰掰
卡娜赫拉對不起
小單身
潔癖格鬥賽
我來
熱敷墊
這不是告別
荃
後記
索引
認識楊婕與她對書寫的忠誠/吳曉樂
文藝少女說明書/林立青
翹翹板倒向另一端/廖梅璇
楊婕/蕭詒徽
輯一 孩子
文字的初始,是宇宙
扯鈴女孩
黑暗之光
最後一個孩子
原型女人
Lia
愛的教育
恨的教育
輯二 我的女性主義的第一堂課
海水有字
時間情書
地老天荒的愛情
我的女性主義的第一堂課
海邊與賽馬節
颱風眼
輯三 公主病
第一個朋友
怕狗婕
貝蒂
香香自助餐
林王鵝肉飯
輯四 越南室友
有人要跟我換房
卡娜赫拉
加油孟子
楊茄
卡娜赫拉掰掰
卡娜赫拉對不起
小單身
潔癖格鬥賽
我來
熱敷墊
這不是告別
荃
後記
索引
序
推薦序
認識楊婕與她對書寫的忠誠
吳曉樂
談這本書之前,得談我對這個作家的階段性理解。楊婕的《房間》住在我的書櫃裡,當時在誠品翻,覺得頗有意思,刷卡帶回家。她的文字有強烈的風格,一沾上手,短時間內洗不掉,生辛且嗆,其後,找著她的臉書,默自觀看,先是很羨慕她嗜食肥肉的可愛天性,那篇震顫人心的〈我的女性主義的第一堂課〉亦未錯漏,緊接著是她與廖梅璇共同接受《BIOS Monthly》的專訪〈高潮就像永無島〉,楊婕在裡頭的一段描述如彗星擦亮天幕:「她很小開始性幻想;第一個暗戀的男孩,是因為某次不小心摸到對方的手─自此,她經常夢見:男孩裸著上身,和她躲在一塊大石頭後面,外面的世界正在毀滅。」
單單從這個意象我就膽敢預言此人的文字會一再給文壇捎來新氣象。她寫,她太敢寫了。尼爾‧蓋曼曾說過,寫散文如果不誠實,就別寫了。而楊婕,簡直是太誠實了。
縱使在房間之外,作家的步伐顯得有些凌亂,但她並不怕。一如她的性幻想,整本書的文字都逃不了一種設定:她跟著誰躲在一塊大石頭後面,而外面的世界正在毀滅。有趣的是,跟楊婕一同躲在石頭後的人,隨著際遇而有不同的人物,有些她喜歡,有些她忌憚,但多數時候她都是喜歡並且忌憚著。這本散文集也是一本過敏病記,作家的過敏原是人類。跟漫天飛舞的花粉一樣,作家閃躲得了一時,避不了一世,一旦走出房間,作家就得做足能否全身而退的心理準備。楊婕多數的書寫,都可以濃縮成一句:你會愛(傷害)我很久嗎?
她以割肉剔骨般的決絕削下個人經驗,並且在讀者面前,慎重地重新排列。從輯一開始,讀者即不難察覺,作家擁有一顆反覆給她帶來折磨的心。玻璃心。人情中的聚散,總能以任何形式帶給她痛楚。這種書寫的基調,相信很多讀者並不感到陌生,但我獨獨想指出一點來,楊婕所挑出來的對象,形象不一,且數量多繁。不僅點出了現代人類生活中人際的高度折疊和變換,也側寫了作家「變形蟲」般的天性,無論在怎樣的個體面前,她都能將自己拗折成,可以投射出對方樣貌的型態。她並且以近乎成癮的姿態,編排她的人際關係,你,我,我們,我們,我,你。這豈是一句「因誤會而在一起,因了解而分開」所能道盡?楊婕是一個精於描繪「裡」與「外」的作家,上一本書《房間》的內/外辨識,在此書仍有遺緒,而對於界線的校準,她嚴苛到近乎殘忍的境界,一旦對談中「不投機」的匕首乍現,都能讓她決心宣告,自這一秒起,我們不再是我們了。更令人傷感的是,在楊婕的筆下,「我們」往往是「我」的敵人:人際本身時常對個人的完整性造成難以逆反的毀傷。弔詭的是,作家何嘗不是深諳此道,她每一次出手,總也達成痛快的奇襲。
楊婕捨棄了二元論的蹊徑,帶來一系列坐立難安的觀賞經驗:受害者並不必然無辜,暴行者也有其嬌憨可愛的時刻。知識,老師,大人,並不等同善良;無知,學生,孩子,也不保證單純。觀眾們被故事裡的情節給牽到了審判前,卻無法分說雙方罪行輕重。故事的尾聲往往是一場無關痛癢的報復:作家登出這場遊戲,也許終止過敏的方式就是,遠離過敏原,總勝過日日仰藥,來抑制天生的心理機制。作家狼狽的道別方式,讀起來並不甚痛快,卻次次拽著讀者直視生命的本質。我們起初都像當好人,但我們最後都更像楊婕。
作家自陳,她對於人與人之間有種利益交換的味道。她每回於臉書上更新,屢屢有忠誠的留言與轉載,許多人從中坦白,對她的書寫泛起一股「不適的共感」,以此觀之,她與讀者的關係何嘗不是如此:該給的,我沒有閃躲,現在換你們,交出一些痛苦吧。
楊婕維持、甚至相當程度地鞏固了散文文類的透明性,她其實可以偷懶的,佯裝在寫別人的事,或者戴上假面,沒有,這樣一個玻璃心的女生,把自己給站到鎂光燈下。楊婕在書中拋出一項問題,「人可不可以捨棄自己的才華?如果我真像歐說的,深具天賦,我有權利,放棄這分天賦嗎?」但她用了整本書來刻畫另一個問題,「我有義務,不放棄這分天賦嗎?」
答案似乎是肯定的,誰讓埋在胸腔裡的玻璃心,實則有個別稱為,作家之心。
她注定得寫。
文藝少女說明書
林立青
接到這本書的稿件時,我著實的愣了一下:這是一本專寫女生和女生「關係」的書啊,怎麼會找上我呢?印象中應該是由一個前輩女作家來執筆才對的,這樣想的時候,卻發現我已經慢慢的看完了這部作品。
楊婕的文字有一種魅力,在散文這個題材中,作者的自我揭露或者書寫內容要和讀者產生共鳴,越是能夠帶給讀者共感的文字,就越令人愛不釋手,楊婕的作品就有這樣的特性,她擅長用自己的真實經驗說故事,其中夾雜著屬於作者的感動、義憤、猶豫或者羞澀,隨著作者將自己經歷呈現,我在閱讀時總感到自己似乎多懂了一些,又懂了一些未知的,細膩並且不經意就可能忽略的感受。
我和楊婕共見過兩次面,第一次時,在文訊的辦公室裡面,她戴著一個大大圓圓的粗框眼鏡,鏡框色彩鮮豔,像是一個鄰家小女生,那時我們正討論著要寫老作家們,那天我回到家以後才發現,她曾經在實習的時候邀請我到校演講,那個訊息客氣而有禮,又因為離我家很近,我立刻應邀前去。
我答應前去的時候,還不知道楊婕早已經出過書,是個作家,只以為她是個實習老師。事實上,我也不知道實習老師在做什麼,在學校實習需要有什麼樣的心理準備,更不清楚實習期間和學生互動的感受,我還記得當天演講的時候,我先順路到附近的工地估價,到了學校以後,全身勞工裝扮的上場,高一和高二兩個班的女生對於工地的保力達、反光背心都提出疑問,那些年輕的女孩聽著宮廟和工地的寄附文化而張大嘴巴。
現在想來,當時台下的女孩們,或許有些就是楊婕在這本書中描寫的對象,那些故作鎮定的,好奇張望的,等著身邊的人第一個發問的,很可能就是那些等著看著楊婕批改作文,期待評語的女孩,或許每個都是她筆下的人物,隨著我翻閱這本書時,那年我到學校的記憶開始鮮明如同她們的制服顏色,一個一個人物如同楊婕所寫的生動並且複雜,那些害怕面試的,身懷絕技和才藝的,對著「老師姊姊」撒嬌吃醋的,這些故事片段合一隨即掠過的青春,都在楊婕的筆下重新活了過來,老師或許不能和學生當成朋友,但卻可以在文字之中永遠保留那些對於年少青春孩子的愛護之情,永遠小作者九歲的留在文字之中。
我第二次再見到楊婕,是在饒河街的浪人食堂,一個為了無家者而開設的炸雞飲料店,那時我應約來為他們拉抬人氣,剛好碰到楊婕經過,正在裝紅茶的阿姨直說這女孩可愛甜美,於是直接邀約她前來擔任一日店長,隔幾天後,楊婕穿著黑色的T恤,上面印有「玻璃心」三字,在都是無家者的攤位中,頗得這些長輩喜愛,隔幾天後和其中一人聊起,還驚訝的說自己終於認識了一個作家,難怪這麼有才等等。
從現實生活之中,我對於楊婕的理解只僅於女作家,女老師等身分,若再上網Google,就能多添加幾個專欄作家或者是博士生,這些並不能幫助我理解一個人的痛苦和成長,情傷和猶豫,難過和感動,甚至這些身分阻礙了人理解更為複雜的情感,更多時候這些身分反而製造出疏離。
幸好楊婕給了我們這些文字,在文字中,我們能夠得知年少又特別害怕狗兒的女孩如何看待在家中失去自由,被圈關起來的老狗,那又愛又憐的文字令人心裡一陣酸楚;又因為她的文字,我們得以知道到府照顧尊長的移工夾在眾多親戚之間的為難,楊婕的文字為讀者留下了成長中女性的遲疑和猶豫,慈愛和為難。
本書開篇寫著「我是女生,我怕女生」,卻在故事之中藉由和不同女性之間的互動、生活、爭執和對話推進了理解和接受,所有的文字最後都回過來讓人看見那些伴隨著楊婕成長的女孩,透過這些互動和片段更加了解身為一個人的複雜,因為很可能像我在學校演講時僅有一次的見面,才顯得這本書的珍貴。
這樣的文字,應該被期待。
翹翹板倒向另一端
廖梅璇
年近三十,楊婕出了第二本書。
踏出處女作《房間》裡的潮黯公寓,人生途上走了一小段路,過去的創傷還沒沉澱,又迎來新的體驗,從學生身分轉換為實習教師,生命的比重滑移著,翹翹板在空中彈起沉降,倒向另一端。
楊婕在這本書寫令她觸動的女生男生和動物,文字如磁浮列車般流暢,只有挨近情感邊界時會頓挫一下,力道也不重,唯因之前如此滑順,於是讓人曉得了頓挫是重點所在,猶如生著倒刺的貓舌,舔在讀者心頭,介乎痛癢之間,是一種痠軟與抽搐。三十歲的人,都知道這種事過境遷的搔抓最難受。
寫痛苦而不撓破傷口,流為鮮血淋漓的展演是困難的。楊婕沒有下重手,隔著距離把包裹好的回憶攤開,一件件數算,語氣甚至帶著一點溫柔,夠誠實的人才做得到。
誠實有很多型態,楊婕的是膠囊型,包覆著一層自我保護的明膠。輯一「孩子」前半部書寫女校實習教師生涯,看得出她比誰都關心那些女學生。不過是個實習老師,她分明可以裝死,什麼都不做,卻忍不住總想拉著少女親近文字,哪怕是一點點也好;又怕投入太深,只換來學生的漠然,先套上軟蝟甲,反覆提醒自己,別混淆老師與朋友的角色,別太倚賴少女的義氣相挺,別讓她們上大學走光光了,剩自己還掛念著她們。
如此反覆掂量,正是因為嘗過太在乎的苦。輯一後半部幾篇文章,寫孩提青春時,坐在翹翹板另一端的遭遇。〈原型女人〉講曖昧過的國中女同學、〈愛的教育〉有以愛為名的恐怖國小老師、〈恨的教育〉遇上控制狂大學教師下指導棋,權力的金球在身分歲數落差間流轉,曾重重傷害過楊婕,但也教會她,權力關係從來不是僵滯的鏈結,脫離了這個情境,進入另一個,金球也可能轉到她手上。易位而處,方能看清愛不是愛,而是忐忑與傷人的衝動,可恨的人也未必如此可恨,人被框限在某種體制或處境久了,規則扎進肉裡生長,整個模樣都會歪斜掉。理解讓她的文字在通透裡折射出一汪暖意,不是廉價的同情,是對他人,對自己更深沉的認識。
因而,再往下讀那些她潛到意識深處撈出的殘酷片刻,尤其是〈我的女性主義的第一堂課〉、〈海邊與賽馬節〉、〈怕狗婕〉幾篇文章,不免替楊婕慶幸,還好她經歷苦澀後,沒有長成同樣殘酷的成人,沒有讓仇恨動力學繼續運作下去,在握有權力後,將己身曾承受的痛苦施加給弱勢一方。她反倒在少女的純真裡,找到療癒的力量,女生對女生不再只有父權秩序裡的忌憚排擠,也有悉心呵護的姊妹情誼;也只有女生才看得出,那些彆彆扭扭、玻璃心,公主病,對愛的錙銖必較,都是一個小女孩好怕被人厭棄,強迫自己不要愛得太熱烈,衍生出的種種症頭。不知當初楊婕是否以為,把玻璃心煉成金剛鑽,就可以百毒不侵。然而,從翹翹板一端倒向另一端,她仍然敏感,好在如今學會彌合傷口,強化玻璃只裂不碎,修好了還是玲瓏剔透的一顆心。
私心最喜歡〈怕狗婕〉這一篇散文,題目貌似搞笑,內容卻赤裸裸剖開成人世界的偽善,沒有過多的修飾,字裡行間卻痛到嗚咽。楊婕寫孩子對醜狗一往情深的維護,恨自己無能為力,恨愛得不夠徹底,害怕被悲傷淹沒,左思右想,只好先遺棄愛的可能,簡直就像後來對待女學生的態度。只是活到這個年齡,為那麼多人和動物流過淚,不得不對任何情感的萌生提高警覺。儘管她一再聲明,恐愛症頭已經好多了,那種小心翼翼,渴望與閃避,還是讓過來人心有戚戚焉。
高度自戀又自省,敘事熟極而流中閃現靈慧,楊婕的作品散發著矛盾的魅力。
那樣複雜,連我也不曉得如此形容她的風格,會不會踩到地雷,不小心誤觸了她的玻璃心,但好文章常來自於個性與文字融為一體的渾然。她在這個已經稍微對世界釋懷,卻尚未遺忘傷痛的年紀,確實寫好了自己。
楊婕
蕭詒徽
三年前楊婕問我對《房間》的感想,當時簡單回答四字「正正之師」。後來幾次碰面她都還提起,我猜她在意,而她在意是因為我沒有清楚解釋。在談這本書之前,我想要先說明我那個私下而簡短的評語,希望能撥開她心裡可能有的遲疑,同時也作為談論這本新作的對照基礎。縱然猜想她會更希望這部作品被獨立地看待,我依然決定從這裡開始,因為那份「變化」在我眼中確確實實是美麗的。
在《房間》中,許多篇章的收尾,我都讀到被更巨大的某種東西所引致的自我糾正。更確切地說,我感覺到她總是在關鍵時刻去除了故事中「個人性的、具個人雜質的部分」。如〈房間〉中外頭施工的噪音傳進房間,她聽著聽著,以「漸漸得到踏實的力量」收尾(《房間》P27);又如〈作親〉中提及與房東夫婦相處,在樸實之中「終能踏實地觸及自我。」(《房間》P37);與戀人在東海岸的晨間對話,「我說,這於你於我,都是我們生命中的璀璨時光。」當然,對讀者而言,楊婕可能是真心這麼想的、真心對萬物有著如此積極有愛的感悟。但對與她親身相處的我而言,這種對事件情節極盡體貼、使勁要從中找出「有禮貌的結論」的作法,卻總是有著一股違和感。
當我一一鎖定這些違和的部分,我發現,這種狀況通常發生在她述及自身的時候。不,應該反過來說,正因為她有或無意識地避免述及情緒與情節,才不得不陷入必須以某個範圍很大的結論收攏敘述的結果。於是,當她(即將)寫到情緒,她會自動地、不描述事件細節作為情感鋪陳,反而以概括性、統合式的說明簡單了結:「那座房間成了兩人的密室。情人在其中任意改變妳的線條。」(〈房間‧龜裂〉,P55)、「穿衣鏡接過往日歲月,一完整映照便背棄妳。」(〈房間‧穿衣鏡〉,P117);這種現象不只發生在「恨意」有關的內容中,也發生在與「愛」或「理解」等性質正面的描述裡:觀察了周遭鄰居的曬衣模式,似有所悟時,最後只說了「我想,該學著用曬衣的方式,和往事較量。」(〈房間‧曬衣情事〉,P44);《房間》中稀有地以中文化名出現的室友媛(似乎較以各種英文字母代稱的其他人物更親暱),當要說明媛對自身的救贖,敘述完幾個事件之後,也僅只是「那間藍色的宿舍如同海洋,寬闊、能夠容納。媛出門。媛睡覺。媛回來。媛的作息使妳有了落定點。」(〈房間‧女生宿舍〉,P74)
一旦將要表露自我,就立刻自動收斂。缺席的往日細節,像喻依永遠隱瞞著背後的喻體。如此為一個段落找尋結尾時,不得不畫一個較大的圈。而那去除了作者性格的說辭,也就自然會顯得「正正之師」了吧。
尤其,與上述描述「內景」時的情況相對,楊婕描述「外景」的技術實在很強。為寫這篇序重讀一次,我依然被《房間》中精奇的外景詩意震動:寫到午後到巷弄兜售點心的男人,「他的聲音讓我碰到傍晚。」(〈房間‧雨中婚禮〉,P170);寫到因濕氣而無法收下的衣物,「滿窗衣服動彈不得。」(〈房間‧曬衣情事〉,P43);寫到博士班宿舍走廊燈光幽暗,「女博士生們,就在其中變成一個個模糊的存在。」(〈房間‧鬼屋〉,P61);寫到把玩C贈送的燈泡,「反手按亮,幾秒後關掉。/像關掉一朵雲或關掉一枚貝殼般關掉。」(〈房間‧蟲洞〉,P123)。
寫得這麼好的外景,對我來說又更顯出寫及內景時的迴避。當然,也有人能夠在這樣的特徵中感到好處,解讀為寫景即是寫情,不寫作者的私經歷,反而讓人容易代入。我卻自覺這樣是讀者對其後的真實故事的傲慢,不願僅止於如此解讀。
或許因為我認識她。《房間》之後,我一直期待有一天,楊婕能用與描述外景時同等的功力,召喚她的內景。
然後,我的願望實現了。
讀過《房間》的我,在《她們都是我的,前女友》終於點開了原本只有幾段字的超連結─在《房間》中出場的別墅主人Y,在這本書中有了確切的位址、職業和交涉場景*;上面提到「任意改變情人線條」的那位情人,不再是三段話解決,這次有了整整一篇散文好幾千字,細述他究竟如何恐怖;就連在《房間》中老是以畫作名稱旁敲側擊的那位畫家,楊婕也終於明明白白這樣寫了:我喜歡梵谷*。
當然,上網搜尋〈星空〉和〈麥田群鴉〉也總會找到梵谷的。退一萬步說,這兩幅畫作其實著名到一看就知道是梵谷了。可是,從最早的作品一路閱讀、直到看見「我喜歡梵谷」這樣一句清楚的表白……這個直白到不行的句子,可以說是這部新作征服我的方式的隱喻:這是我作為讀者、終於被作者同等地信任的感動。
如果說,《房間》是在模糊霧中隱晦指名的寓言書,《她們都是我的,前女友》就是句句署名的生死簿了。這一點,除了從事件描述的方式,也能從表層的敘述者位置變化察覺:相較於《房間》中以第一人稱「我」與第二人稱「妳」作為主詞的篇章各半,《她們都是我的,前女友》以「妳」敘述的篇章只剩下一篇(〈林王鵝肉飯〉),作品和作者的距離更加趨近,作者也往讀者大幅靠近。以作品作為中介,我們以當中的經歷更加認識寫出作品的這個人,不再只能捕風捉影地尋找投射的對象。
願望實現了,但如果我能更張揚一點,我想要更精確地描述我的期待:在和盤托出內景的同時,楊婕描述外景時的技術性也減少了。這一點,我認為是她主動的選擇,為了不讓讀者在事件中失焦。但同樣身為寫作者,我仍舊貪心地期待她用如「也許衣服更像這條巷弄,而我不過是衣服的訪客。」(〈房間‧曬衣情事〉,P47)或者(在蟻群隱隱騷動的穴窟上)「地面是遲鈍的枯葉和泥土。」(〈房間‧裸住〉,P77)這樣具詩意企圖的句子來敘述事件。但是,此時此刻,我甘心她以說起越南室友的故事時那樣純粹的神情(是的,當讀到「Xin Chào ! tôi tên là Yang Jie」時,我看到了她的臉)來交換一種修辭美麗的姿態。
─而這又何嘗不是我的傲慢。拿出真心誠意相搏的模樣,誰能說不美。
本書某些作品中,還是出現我自稱為「正正之師」的結論式自動糾正,如談到實習學校的高中生時加了一句「青春不能被禁抑。」又或〈黑暗之光〉寫到對學生的隱微情愫,「我想念奇。」之後立刻接上「她將永遠比我小九歲,以孩子的形象,留在我心中。」(第一次讀到這裡,我在心中吶喊:怎麼沒停在「我想念奇」就好!)但是,由於其他部分的坦誠,這些地方已經不再會「擋住」故事了。
我在這本書裡,終於讀到了楊婕。
捨棄了單個句子的詩性之後,得以順暢而迅速地閱讀著楊婕的我,會在以整篇結構為單位的詩意中,被累積的力量一拳打穿(這也或許是她放棄單句琢磨的另一個原因,它們有時會分散情節的力道)。〈扯鈴女孩〉中,寫到甄在熱舞社的發表影片中一眼即可認出,結局卻是楊婕觀看甄就讀軍校之後的龍船比賽,「我將影片放大、重播看了老半天,還是認不出甄。」;〈原型女人〉中,寫到曾向自己出櫃而又遲卻地意識到自己也愛上的M,在人群中偶遇時,只一句「我不會認錯。」就顯示了用情至深。捨卻了小範圍的修辭,而得大範圍的震撼,頗有大巧不工之妙。
在楊婕的短篇作品中時常看到一種技術,是在一段敘述語意將盡之際,補述另一種語意來造成哲思上的驚喜。在《房間》裡是「花瓶砸到地上,沒有受損,妳不了解受損。」「有時睡覺是最好的選擇,有時不是。」在這本書中則是「歐說,我知道。我知道。失望卻溫柔著。」「夜色是糊的,你也是糊的。但字句清楚。」「或許她最喜歡的是我沒送出的那一張(貼紙),以為聊著聊著就能得到,而我也以為自己會給她。」
相較於《房間》,本作中各篇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互文,形成一種以整本書為範圍的內部連動,當中許多也成為她不同成長階段的參考點和對照組。〈黑暗之光〉中,「奇會注意到我,終究是因為我是老師,卻不像老師。」到了〈恨的教育〉,當年身為學生的自己卻也是「我喜歡歐,因為歐是老師,卻不像我碰到的其他老師。」;〈我的女性主義的第一堂課〉中,說著「笑死了,從來沒看過有人向別人要讚美的。」的恐怖情人讓楊婕「我腦中開始出現兩種聲音:一個是我本來的聲音,一個是他的。」到了〈怕狗婕〉中,終於看見所謂腦中的聲音是如何干涉著她的魂魄:「好笑死了,搞不懂妳在難過什麼,牠又不是妳養的狗。」此類前後篇章的聯繫,與其說是創作意圖,或許也是楊婕誠實地寫出個人史之下,自然出現的連續性。
認識楊婕的人,無論喜不喜歡,大概都會承認她是可愛的。那種可愛是由她時不時脫口而出的小劇場,和時時不禁與他人再三確認價值觀的叨絮構成的。讀《房間》的時候,我無法看到這一面的楊婕,也就是說,這一面的楊婕本來是由身為朋友的我所獨占的。然而,在讀《她們都是我的,前女友》時,面對她的坦率,我卻沒有因占有欲而生的相對剝奪感,反而笑得非常、非常開心。
嗨楊婕。作為讀者和朋友,我很開心當妳是作者的時候,也把我當朋友。
*此內容收錄於原稿中〈生活白痴〉一作,該篇後已自書中刪去。
*此內容收錄於原稿中〈色盲島〉一作,該篇後已自書中刪去。
認識楊婕與她對書寫的忠誠
吳曉樂
談這本書之前,得談我對這個作家的階段性理解。楊婕的《房間》住在我的書櫃裡,當時在誠品翻,覺得頗有意思,刷卡帶回家。她的文字有強烈的風格,一沾上手,短時間內洗不掉,生辛且嗆,其後,找著她的臉書,默自觀看,先是很羨慕她嗜食肥肉的可愛天性,那篇震顫人心的〈我的女性主義的第一堂課〉亦未錯漏,緊接著是她與廖梅璇共同接受《BIOS Monthly》的專訪〈高潮就像永無島〉,楊婕在裡頭的一段描述如彗星擦亮天幕:「她很小開始性幻想;第一個暗戀的男孩,是因為某次不小心摸到對方的手─自此,她經常夢見:男孩裸著上身,和她躲在一塊大石頭後面,外面的世界正在毀滅。」
單單從這個意象我就膽敢預言此人的文字會一再給文壇捎來新氣象。她寫,她太敢寫了。尼爾‧蓋曼曾說過,寫散文如果不誠實,就別寫了。而楊婕,簡直是太誠實了。
縱使在房間之外,作家的步伐顯得有些凌亂,但她並不怕。一如她的性幻想,整本書的文字都逃不了一種設定:她跟著誰躲在一塊大石頭後面,而外面的世界正在毀滅。有趣的是,跟楊婕一同躲在石頭後的人,隨著際遇而有不同的人物,有些她喜歡,有些她忌憚,但多數時候她都是喜歡並且忌憚著。這本散文集也是一本過敏病記,作家的過敏原是人類。跟漫天飛舞的花粉一樣,作家閃躲得了一時,避不了一世,一旦走出房間,作家就得做足能否全身而退的心理準備。楊婕多數的書寫,都可以濃縮成一句:你會愛(傷害)我很久嗎?
她以割肉剔骨般的決絕削下個人經驗,並且在讀者面前,慎重地重新排列。從輯一開始,讀者即不難察覺,作家擁有一顆反覆給她帶來折磨的心。玻璃心。人情中的聚散,總能以任何形式帶給她痛楚。這種書寫的基調,相信很多讀者並不感到陌生,但我獨獨想指出一點來,楊婕所挑出來的對象,形象不一,且數量多繁。不僅點出了現代人類生活中人際的高度折疊和變換,也側寫了作家「變形蟲」般的天性,無論在怎樣的個體面前,她都能將自己拗折成,可以投射出對方樣貌的型態。她並且以近乎成癮的姿態,編排她的人際關係,你,我,我們,我們,我,你。這豈是一句「因誤會而在一起,因了解而分開」所能道盡?楊婕是一個精於描繪「裡」與「外」的作家,上一本書《房間》的內/外辨識,在此書仍有遺緒,而對於界線的校準,她嚴苛到近乎殘忍的境界,一旦對談中「不投機」的匕首乍現,都能讓她決心宣告,自這一秒起,我們不再是我們了。更令人傷感的是,在楊婕的筆下,「我們」往往是「我」的敵人:人際本身時常對個人的完整性造成難以逆反的毀傷。弔詭的是,作家何嘗不是深諳此道,她每一次出手,總也達成痛快的奇襲。
楊婕捨棄了二元論的蹊徑,帶來一系列坐立難安的觀賞經驗:受害者並不必然無辜,暴行者也有其嬌憨可愛的時刻。知識,老師,大人,並不等同善良;無知,學生,孩子,也不保證單純。觀眾們被故事裡的情節給牽到了審判前,卻無法分說雙方罪行輕重。故事的尾聲往往是一場無關痛癢的報復:作家登出這場遊戲,也許終止過敏的方式就是,遠離過敏原,總勝過日日仰藥,來抑制天生的心理機制。作家狼狽的道別方式,讀起來並不甚痛快,卻次次拽著讀者直視生命的本質。我們起初都像當好人,但我們最後都更像楊婕。
作家自陳,她對於人與人之間有種利益交換的味道。她每回於臉書上更新,屢屢有忠誠的留言與轉載,許多人從中坦白,對她的書寫泛起一股「不適的共感」,以此觀之,她與讀者的關係何嘗不是如此:該給的,我沒有閃躲,現在換你們,交出一些痛苦吧。
楊婕維持、甚至相當程度地鞏固了散文文類的透明性,她其實可以偷懶的,佯裝在寫別人的事,或者戴上假面,沒有,這樣一個玻璃心的女生,把自己給站到鎂光燈下。楊婕在書中拋出一項問題,「人可不可以捨棄自己的才華?如果我真像歐說的,深具天賦,我有權利,放棄這分天賦嗎?」但她用了整本書來刻畫另一個問題,「我有義務,不放棄這分天賦嗎?」
答案似乎是肯定的,誰讓埋在胸腔裡的玻璃心,實則有個別稱為,作家之心。
她注定得寫。
文藝少女說明書
林立青
接到這本書的稿件時,我著實的愣了一下:這是一本專寫女生和女生「關係」的書啊,怎麼會找上我呢?印象中應該是由一個前輩女作家來執筆才對的,這樣想的時候,卻發現我已經慢慢的看完了這部作品。
楊婕的文字有一種魅力,在散文這個題材中,作者的自我揭露或者書寫內容要和讀者產生共鳴,越是能夠帶給讀者共感的文字,就越令人愛不釋手,楊婕的作品就有這樣的特性,她擅長用自己的真實經驗說故事,其中夾雜著屬於作者的感動、義憤、猶豫或者羞澀,隨著作者將自己經歷呈現,我在閱讀時總感到自己似乎多懂了一些,又懂了一些未知的,細膩並且不經意就可能忽略的感受。
我和楊婕共見過兩次面,第一次時,在文訊的辦公室裡面,她戴著一個大大圓圓的粗框眼鏡,鏡框色彩鮮豔,像是一個鄰家小女生,那時我們正討論著要寫老作家們,那天我回到家以後才發現,她曾經在實習的時候邀請我到校演講,那個訊息客氣而有禮,又因為離我家很近,我立刻應邀前去。
我答應前去的時候,還不知道楊婕早已經出過書,是個作家,只以為她是個實習老師。事實上,我也不知道實習老師在做什麼,在學校實習需要有什麼樣的心理準備,更不清楚實習期間和學生互動的感受,我還記得當天演講的時候,我先順路到附近的工地估價,到了學校以後,全身勞工裝扮的上場,高一和高二兩個班的女生對於工地的保力達、反光背心都提出疑問,那些年輕的女孩聽著宮廟和工地的寄附文化而張大嘴巴。
現在想來,當時台下的女孩們,或許有些就是楊婕在這本書中描寫的對象,那些故作鎮定的,好奇張望的,等著身邊的人第一個發問的,很可能就是那些等著看著楊婕批改作文,期待評語的女孩,或許每個都是她筆下的人物,隨著我翻閱這本書時,那年我到學校的記憶開始鮮明如同她們的制服顏色,一個一個人物如同楊婕所寫的生動並且複雜,那些害怕面試的,身懷絕技和才藝的,對著「老師姊姊」撒嬌吃醋的,這些故事片段合一隨即掠過的青春,都在楊婕的筆下重新活了過來,老師或許不能和學生當成朋友,但卻可以在文字之中永遠保留那些對於年少青春孩子的愛護之情,永遠小作者九歲的留在文字之中。
我第二次再見到楊婕,是在饒河街的浪人食堂,一個為了無家者而開設的炸雞飲料店,那時我應約來為他們拉抬人氣,剛好碰到楊婕經過,正在裝紅茶的阿姨直說這女孩可愛甜美,於是直接邀約她前來擔任一日店長,隔幾天後,楊婕穿著黑色的T恤,上面印有「玻璃心」三字,在都是無家者的攤位中,頗得這些長輩喜愛,隔幾天後和其中一人聊起,還驚訝的說自己終於認識了一個作家,難怪這麼有才等等。
從現實生活之中,我對於楊婕的理解只僅於女作家,女老師等身分,若再上網Google,就能多添加幾個專欄作家或者是博士生,這些並不能幫助我理解一個人的痛苦和成長,情傷和猶豫,難過和感動,甚至這些身分阻礙了人理解更為複雜的情感,更多時候這些身分反而製造出疏離。
幸好楊婕給了我們這些文字,在文字中,我們能夠得知年少又特別害怕狗兒的女孩如何看待在家中失去自由,被圈關起來的老狗,那又愛又憐的文字令人心裡一陣酸楚;又因為她的文字,我們得以知道到府照顧尊長的移工夾在眾多親戚之間的為難,楊婕的文字為讀者留下了成長中女性的遲疑和猶豫,慈愛和為難。
本書開篇寫著「我是女生,我怕女生」,卻在故事之中藉由和不同女性之間的互動、生活、爭執和對話推進了理解和接受,所有的文字最後都回過來讓人看見那些伴隨著楊婕成長的女孩,透過這些互動和片段更加了解身為一個人的複雜,因為很可能像我在學校演講時僅有一次的見面,才顯得這本書的珍貴。
這樣的文字,應該被期待。
翹翹板倒向另一端
廖梅璇
年近三十,楊婕出了第二本書。
踏出處女作《房間》裡的潮黯公寓,人生途上走了一小段路,過去的創傷還沒沉澱,又迎來新的體驗,從學生身分轉換為實習教師,生命的比重滑移著,翹翹板在空中彈起沉降,倒向另一端。
楊婕在這本書寫令她觸動的女生男生和動物,文字如磁浮列車般流暢,只有挨近情感邊界時會頓挫一下,力道也不重,唯因之前如此滑順,於是讓人曉得了頓挫是重點所在,猶如生著倒刺的貓舌,舔在讀者心頭,介乎痛癢之間,是一種痠軟與抽搐。三十歲的人,都知道這種事過境遷的搔抓最難受。
寫痛苦而不撓破傷口,流為鮮血淋漓的展演是困難的。楊婕沒有下重手,隔著距離把包裹好的回憶攤開,一件件數算,語氣甚至帶著一點溫柔,夠誠實的人才做得到。
誠實有很多型態,楊婕的是膠囊型,包覆著一層自我保護的明膠。輯一「孩子」前半部書寫女校實習教師生涯,看得出她比誰都關心那些女學生。不過是個實習老師,她分明可以裝死,什麼都不做,卻忍不住總想拉著少女親近文字,哪怕是一點點也好;又怕投入太深,只換來學生的漠然,先套上軟蝟甲,反覆提醒自己,別混淆老師與朋友的角色,別太倚賴少女的義氣相挺,別讓她們上大學走光光了,剩自己還掛念著她們。
如此反覆掂量,正是因為嘗過太在乎的苦。輯一後半部幾篇文章,寫孩提青春時,坐在翹翹板另一端的遭遇。〈原型女人〉講曖昧過的國中女同學、〈愛的教育〉有以愛為名的恐怖國小老師、〈恨的教育〉遇上控制狂大學教師下指導棋,權力的金球在身分歲數落差間流轉,曾重重傷害過楊婕,但也教會她,權力關係從來不是僵滯的鏈結,脫離了這個情境,進入另一個,金球也可能轉到她手上。易位而處,方能看清愛不是愛,而是忐忑與傷人的衝動,可恨的人也未必如此可恨,人被框限在某種體制或處境久了,規則扎進肉裡生長,整個模樣都會歪斜掉。理解讓她的文字在通透裡折射出一汪暖意,不是廉價的同情,是對他人,對自己更深沉的認識。
因而,再往下讀那些她潛到意識深處撈出的殘酷片刻,尤其是〈我的女性主義的第一堂課〉、〈海邊與賽馬節〉、〈怕狗婕〉幾篇文章,不免替楊婕慶幸,還好她經歷苦澀後,沒有長成同樣殘酷的成人,沒有讓仇恨動力學繼續運作下去,在握有權力後,將己身曾承受的痛苦施加給弱勢一方。她反倒在少女的純真裡,找到療癒的力量,女生對女生不再只有父權秩序裡的忌憚排擠,也有悉心呵護的姊妹情誼;也只有女生才看得出,那些彆彆扭扭、玻璃心,公主病,對愛的錙銖必較,都是一個小女孩好怕被人厭棄,強迫自己不要愛得太熱烈,衍生出的種種症頭。不知當初楊婕是否以為,把玻璃心煉成金剛鑽,就可以百毒不侵。然而,從翹翹板一端倒向另一端,她仍然敏感,好在如今學會彌合傷口,強化玻璃只裂不碎,修好了還是玲瓏剔透的一顆心。
私心最喜歡〈怕狗婕〉這一篇散文,題目貌似搞笑,內容卻赤裸裸剖開成人世界的偽善,沒有過多的修飾,字裡行間卻痛到嗚咽。楊婕寫孩子對醜狗一往情深的維護,恨自己無能為力,恨愛得不夠徹底,害怕被悲傷淹沒,左思右想,只好先遺棄愛的可能,簡直就像後來對待女學生的態度。只是活到這個年齡,為那麼多人和動物流過淚,不得不對任何情感的萌生提高警覺。儘管她一再聲明,恐愛症頭已經好多了,那種小心翼翼,渴望與閃避,還是讓過來人心有戚戚焉。
高度自戀又自省,敘事熟極而流中閃現靈慧,楊婕的作品散發著矛盾的魅力。
那樣複雜,連我也不曉得如此形容她的風格,會不會踩到地雷,不小心誤觸了她的玻璃心,但好文章常來自於個性與文字融為一體的渾然。她在這個已經稍微對世界釋懷,卻尚未遺忘傷痛的年紀,確實寫好了自己。
楊婕
蕭詒徽
三年前楊婕問我對《房間》的感想,當時簡單回答四字「正正之師」。後來幾次碰面她都還提起,我猜她在意,而她在意是因為我沒有清楚解釋。在談這本書之前,我想要先說明我那個私下而簡短的評語,希望能撥開她心裡可能有的遲疑,同時也作為談論這本新作的對照基礎。縱然猜想她會更希望這部作品被獨立地看待,我依然決定從這裡開始,因為那份「變化」在我眼中確確實實是美麗的。
在《房間》中,許多篇章的收尾,我都讀到被更巨大的某種東西所引致的自我糾正。更確切地說,我感覺到她總是在關鍵時刻去除了故事中「個人性的、具個人雜質的部分」。如〈房間〉中外頭施工的噪音傳進房間,她聽著聽著,以「漸漸得到踏實的力量」收尾(《房間》P27);又如〈作親〉中提及與房東夫婦相處,在樸實之中「終能踏實地觸及自我。」(《房間》P37);與戀人在東海岸的晨間對話,「我說,這於你於我,都是我們生命中的璀璨時光。」當然,對讀者而言,楊婕可能是真心這麼想的、真心對萬物有著如此積極有愛的感悟。但對與她親身相處的我而言,這種對事件情節極盡體貼、使勁要從中找出「有禮貌的結論」的作法,卻總是有著一股違和感。
當我一一鎖定這些違和的部分,我發現,這種狀況通常發生在她述及自身的時候。不,應該反過來說,正因為她有或無意識地避免述及情緒與情節,才不得不陷入必須以某個範圍很大的結論收攏敘述的結果。於是,當她(即將)寫到情緒,她會自動地、不描述事件細節作為情感鋪陳,反而以概括性、統合式的說明簡單了結:「那座房間成了兩人的密室。情人在其中任意改變妳的線條。」(〈房間‧龜裂〉,P55)、「穿衣鏡接過往日歲月,一完整映照便背棄妳。」(〈房間‧穿衣鏡〉,P117);這種現象不只發生在「恨意」有關的內容中,也發生在與「愛」或「理解」等性質正面的描述裡:觀察了周遭鄰居的曬衣模式,似有所悟時,最後只說了「我想,該學著用曬衣的方式,和往事較量。」(〈房間‧曬衣情事〉,P44);《房間》中稀有地以中文化名出現的室友媛(似乎較以各種英文字母代稱的其他人物更親暱),當要說明媛對自身的救贖,敘述完幾個事件之後,也僅只是「那間藍色的宿舍如同海洋,寬闊、能夠容納。媛出門。媛睡覺。媛回來。媛的作息使妳有了落定點。」(〈房間‧女生宿舍〉,P74)
一旦將要表露自我,就立刻自動收斂。缺席的往日細節,像喻依永遠隱瞞著背後的喻體。如此為一個段落找尋結尾時,不得不畫一個較大的圈。而那去除了作者性格的說辭,也就自然會顯得「正正之師」了吧。
尤其,與上述描述「內景」時的情況相對,楊婕描述「外景」的技術實在很強。為寫這篇序重讀一次,我依然被《房間》中精奇的外景詩意震動:寫到午後到巷弄兜售點心的男人,「他的聲音讓我碰到傍晚。」(〈房間‧雨中婚禮〉,P170);寫到因濕氣而無法收下的衣物,「滿窗衣服動彈不得。」(〈房間‧曬衣情事〉,P43);寫到博士班宿舍走廊燈光幽暗,「女博士生們,就在其中變成一個個模糊的存在。」(〈房間‧鬼屋〉,P61);寫到把玩C贈送的燈泡,「反手按亮,幾秒後關掉。/像關掉一朵雲或關掉一枚貝殼般關掉。」(〈房間‧蟲洞〉,P123)。
寫得這麼好的外景,對我來說又更顯出寫及內景時的迴避。當然,也有人能夠在這樣的特徵中感到好處,解讀為寫景即是寫情,不寫作者的私經歷,反而讓人容易代入。我卻自覺這樣是讀者對其後的真實故事的傲慢,不願僅止於如此解讀。
或許因為我認識她。《房間》之後,我一直期待有一天,楊婕能用與描述外景時同等的功力,召喚她的內景。
然後,我的願望實現了。
讀過《房間》的我,在《她們都是我的,前女友》終於點開了原本只有幾段字的超連結─在《房間》中出場的別墅主人Y,在這本書中有了確切的位址、職業和交涉場景*;上面提到「任意改變情人線條」的那位情人,不再是三段話解決,這次有了整整一篇散文好幾千字,細述他究竟如何恐怖;就連在《房間》中老是以畫作名稱旁敲側擊的那位畫家,楊婕也終於明明白白這樣寫了:我喜歡梵谷*。
當然,上網搜尋〈星空〉和〈麥田群鴉〉也總會找到梵谷的。退一萬步說,這兩幅畫作其實著名到一看就知道是梵谷了。可是,從最早的作品一路閱讀、直到看見「我喜歡梵谷」這樣一句清楚的表白……這個直白到不行的句子,可以說是這部新作征服我的方式的隱喻:這是我作為讀者、終於被作者同等地信任的感動。
如果說,《房間》是在模糊霧中隱晦指名的寓言書,《她們都是我的,前女友》就是句句署名的生死簿了。這一點,除了從事件描述的方式,也能從表層的敘述者位置變化察覺:相較於《房間》中以第一人稱「我」與第二人稱「妳」作為主詞的篇章各半,《她們都是我的,前女友》以「妳」敘述的篇章只剩下一篇(〈林王鵝肉飯〉),作品和作者的距離更加趨近,作者也往讀者大幅靠近。以作品作為中介,我們以當中的經歷更加認識寫出作品的這個人,不再只能捕風捉影地尋找投射的對象。
願望實現了,但如果我能更張揚一點,我想要更精確地描述我的期待:在和盤托出內景的同時,楊婕描述外景時的技術性也減少了。這一點,我認為是她主動的選擇,為了不讓讀者在事件中失焦。但同樣身為寫作者,我仍舊貪心地期待她用如「也許衣服更像這條巷弄,而我不過是衣服的訪客。」(〈房間‧曬衣情事〉,P47)或者(在蟻群隱隱騷動的穴窟上)「地面是遲鈍的枯葉和泥土。」(〈房間‧裸住〉,P77)這樣具詩意企圖的句子來敘述事件。但是,此時此刻,我甘心她以說起越南室友的故事時那樣純粹的神情(是的,當讀到「Xin Chào ! tôi tên là Yang Jie」時,我看到了她的臉)來交換一種修辭美麗的姿態。
─而這又何嘗不是我的傲慢。拿出真心誠意相搏的模樣,誰能說不美。
本書某些作品中,還是出現我自稱為「正正之師」的結論式自動糾正,如談到實習學校的高中生時加了一句「青春不能被禁抑。」又或〈黑暗之光〉寫到對學生的隱微情愫,「我想念奇。」之後立刻接上「她將永遠比我小九歲,以孩子的形象,留在我心中。」(第一次讀到這裡,我在心中吶喊:怎麼沒停在「我想念奇」就好!)但是,由於其他部分的坦誠,這些地方已經不再會「擋住」故事了。
我在這本書裡,終於讀到了楊婕。
捨棄了單個句子的詩性之後,得以順暢而迅速地閱讀著楊婕的我,會在以整篇結構為單位的詩意中,被累積的力量一拳打穿(這也或許是她放棄單句琢磨的另一個原因,它們有時會分散情節的力道)。〈扯鈴女孩〉中,寫到甄在熱舞社的發表影片中一眼即可認出,結局卻是楊婕觀看甄就讀軍校之後的龍船比賽,「我將影片放大、重播看了老半天,還是認不出甄。」;〈原型女人〉中,寫到曾向自己出櫃而又遲卻地意識到自己也愛上的M,在人群中偶遇時,只一句「我不會認錯。」就顯示了用情至深。捨卻了小範圍的修辭,而得大範圍的震撼,頗有大巧不工之妙。
在楊婕的短篇作品中時常看到一種技術,是在一段敘述語意將盡之際,補述另一種語意來造成哲思上的驚喜。在《房間》裡是「花瓶砸到地上,沒有受損,妳不了解受損。」「有時睡覺是最好的選擇,有時不是。」在這本書中則是「歐說,我知道。我知道。失望卻溫柔著。」「夜色是糊的,你也是糊的。但字句清楚。」「或許她最喜歡的是我沒送出的那一張(貼紙),以為聊著聊著就能得到,而我也以為自己會給她。」
相較於《房間》,本作中各篇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互文,形成一種以整本書為範圍的內部連動,當中許多也成為她不同成長階段的參考點和對照組。〈黑暗之光〉中,「奇會注意到我,終究是因為我是老師,卻不像老師。」到了〈恨的教育〉,當年身為學生的自己卻也是「我喜歡歐,因為歐是老師,卻不像我碰到的其他老師。」;〈我的女性主義的第一堂課〉中,說著「笑死了,從來沒看過有人向別人要讚美的。」的恐怖情人讓楊婕「我腦中開始出現兩種聲音:一個是我本來的聲音,一個是他的。」到了〈怕狗婕〉中,終於看見所謂腦中的聲音是如何干涉著她的魂魄:「好笑死了,搞不懂妳在難過什麼,牠又不是妳養的狗。」此類前後篇章的聯繫,與其說是創作意圖,或許也是楊婕誠實地寫出個人史之下,自然出現的連續性。
認識楊婕的人,無論喜不喜歡,大概都會承認她是可愛的。那種可愛是由她時不時脫口而出的小劇場,和時時不禁與他人再三確認價值觀的叨絮構成的。讀《房間》的時候,我無法看到這一面的楊婕,也就是說,這一面的楊婕本來是由身為朋友的我所獨占的。然而,在讀《她們都是我的,前女友》時,面對她的坦率,我卻沒有因占有欲而生的相對剝奪感,反而笑得非常、非常開心。
嗨楊婕。作為讀者和朋友,我很開心當妳是作者的時候,也把我當朋友。
*此內容收錄於原稿中〈生活白痴〉一作,該篇後已自書中刪去。
*此內容收錄於原稿中〈色盲島〉一作,該篇後已自書中刪去。
內容連載
文字的初始,是宇宙
那是高三的二類班級。我考上博士班,休學到女校實習半年。身為實習老師,我的任務就是隨堂跟課,觀摹教學技巧。
實習年級既在高三,沒有課外活動,我也不擅長噓寒問暖,就一直未與學生相熟。生活像打卡,時間到了進教室,下課再出來,我會在鐘響前兩分鐘先收好東西,免得下課後學生熱絡,顯得我一個人尷尬無比。
一開始都跟社會組導師班的課,直到十月底老師出國,交代我替她代二類組的課,才初次走進二類班。老師說,常去教室,讓她們熟悉妳,上課比較有反應,「我教書教了幾十年,沒碰過像她們這麼沒反應的學生,妳先看看,到時自己上台才不會太受傷。」
那是全年級國文墊底的班。一踏進去便能感覺到強烈的氛圍:充溢著有稜有角、屬於自我的性質,且不笑臉迎人對待闖入者。我上台做了簡短的自我介紹,就躲到最後一排靠門的空位。
看到學生便滿臉堆笑原就違背我的本性,既非導師班,沒有親切的義務,我遂配合整間教室的氣氛,放心地臭臉。沒人理我,我也不理任何人。
我像個旁觀者,旁觀一場體制內的戰爭。
這樣的日子過了兩個月。
那兩個月裡,沒有任何「老師」的角色扮演,我像教室的幽靈。偶爾發生一些窘迫插曲:例如教師節,全班合寫卡片給老師,老師高興地朗讀,我只能尷尬陪笑,就像不小心跑錯婚禮,偷窺別人日久生情的甜蜜。另一次全班合訂飲料,替老師多訂一杯傳到台上。我企圖讓自己隱形,避開這場景,下課前突然有一杯傳來,大家騷動著回頭看我─我看得出那不是真心想給我,而是顧慮我坐在教室,多了就傳來。沒喝下那杯不屬於我的飲料,鐘打後拿回行政單位給同事。
十月底老師出國那週,配合模擬考時程排復習考,只留一節要我檢討週三夜間的國文手寫題。模擬考名次墊底後,老師要求全班週三留校考國文。
那天傍晚進教室監考,她們作文遲遲寫不完,或許因放學了,我稍稍卸下「老師」的包袱,在黑板戲謔寫上「7:00姊姊會來收」,塗兩個青筋符號就出去吃飯了。七點多回來,黑板上多了一個kuso我外型的生氣人臉,後面三個選項:「a屍、b垃圾、c錢」。她們問我要收哪一個?我佯裝不悅,全班大笑。那是我初次見到這群孩子在課堂外的生命力,青春不能被禁抑。
那是高三的二類班級。我考上博士班,休學到女校實習半年。身為實習老師,我的任務就是隨堂跟課,觀摹教學技巧。
實習年級既在高三,沒有課外活動,我也不擅長噓寒問暖,就一直未與學生相熟。生活像打卡,時間到了進教室,下課再出來,我會在鐘響前兩分鐘先收好東西,免得下課後學生熱絡,顯得我一個人尷尬無比。
一開始都跟社會組導師班的課,直到十月底老師出國,交代我替她代二類組的課,才初次走進二類班。老師說,常去教室,讓她們熟悉妳,上課比較有反應,「我教書教了幾十年,沒碰過像她們這麼沒反應的學生,妳先看看,到時自己上台才不會太受傷。」
那是全年級國文墊底的班。一踏進去便能感覺到強烈的氛圍:充溢著有稜有角、屬於自我的性質,且不笑臉迎人對待闖入者。我上台做了簡短的自我介紹,就躲到最後一排靠門的空位。
看到學生便滿臉堆笑原就違背我的本性,既非導師班,沒有親切的義務,我遂配合整間教室的氣氛,放心地臭臉。沒人理我,我也不理任何人。
我像個旁觀者,旁觀一場體制內的戰爭。
這樣的日子過了兩個月。
那兩個月裡,沒有任何「老師」的角色扮演,我像教室的幽靈。偶爾發生一些窘迫插曲:例如教師節,全班合寫卡片給老師,老師高興地朗讀,我只能尷尬陪笑,就像不小心跑錯婚禮,偷窺別人日久生情的甜蜜。另一次全班合訂飲料,替老師多訂一杯傳到台上。我企圖讓自己隱形,避開這場景,下課前突然有一杯傳來,大家騷動著回頭看我─我看得出那不是真心想給我,而是顧慮我坐在教室,多了就傳來。沒喝下那杯不屬於我的飲料,鐘打後拿回行政單位給同事。
十月底老師出國那週,配合模擬考時程排復習考,只留一節要我檢討週三夜間的國文手寫題。模擬考名次墊底後,老師要求全班週三留校考國文。
那天傍晚進教室監考,她們作文遲遲寫不完,或許因放學了,我稍稍卸下「老師」的包袱,在黑板戲謔寫上「7:00姊姊會來收」,塗兩個青筋符號就出去吃飯了。七點多回來,黑板上多了一個kuso我外型的生氣人臉,後面三個選項:「a屍、b垃圾、c錢」。她們問我要收哪一個?我佯裝不悅,全班大笑。那是我初次見到這群孩子在課堂外的生命力,青春不能被禁抑。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79折$229
-
新書79折$229
-
新書79折$229
-
新書79折$230
-
新書85折$247
-
新書9折$261
-
新書9折$261
-
二手書91折$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