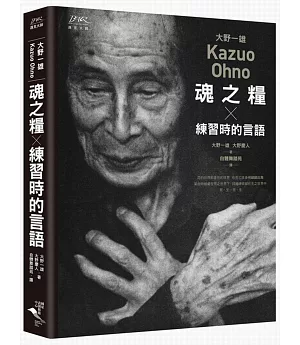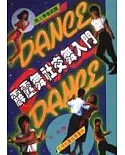譯序
亡靈,生靈,性靈 大野一雄與舞踏的三位一體
⋯⋯在我們返回日本的航程中,那些被放棄的遣返者,
許多人從頭到尾被放置在船倉低層的甲板上,直到餓死。
當較接近日本的海岸線時,我們開始欣喜若狂,盼望著我們或許可以就這樣到達陸地。
但最後我們沒有及時做到,
因為每經過一天就有許多遣返者失去生命。
我覺得自己真是混蛋,我完全做不了任何事情好讓他們不會死去。
就在那時,水母般的生物開始朝我們靠過來;
那些有毒的海洋生物成群地聚集在輪船邊,
見到牠們從海中央漸漸趨近我們,
我感覺牠們也想與我們一起回來……
⋯⋯每當有人死了,我們會將他們裹在布裡,在他們的屍體上綁條細繩。
然後將他們帶到艦橋上,從那兒我們將他們死去的身體扔進底下遠遠的海水裡。
就在屍體落入海中之際,船上的汽笛會哀傷地作響,
彷彿它在為那些被扔入海裡之人感到惋惜。
日出,日落,船上的汽笛聲懷著悲傷響徹了太平洋⋯⋯
⋯⋯我們沒有選擇,只能拋下他們,任其躺在海床上。
那時我想著一回到日本我就要創作一段水母之舞,
而且要以我全部的心,全部的靈魂去排練出來⋯⋯
2000年10月18日,一雄先生於東京的演出中,出人意料地說了以上這段將近十分鐘的話,還是因為慶人先生上台提醒,他才停下獨白,起身跳舞。
二戰時大野一雄被徵召入伍,作為在中國駐軍的一員。數年後調至新幾內亞,隨後成為戰俘,戰爭結束遣返日本。
在經歷戰場的殘酷前,大野一雄有過富足且具文藝氣息的童年。後來就讀於體育大學,曾被找去觀賞安東尼雅.美爾西(Antonia Mercé, La Argentina) 的佛朗明哥舞。畢業後擔任體育老師,得其學校校長的指引受洗為基督徒。之後三四年,大野一雄分別加入過石井漠舞團,以及師承德國新舞蹈先驅瑪麗. 魏格曼(Mary Wigman)的江口.宮舞團。
戰後大野一雄返回學校復職,也回到江口.宮舞團。後來他成立自己的舞團,進行多次現代舞公演。接下來,就是他和舞踏創始人土方巽的相遇了。
相對於一雄先生,土方巽出身貧寒,不過在家鄉時即已接觸到現代舞。高職畢業後開始赴東京,過著打零工、居處簡陋的生活,其舞蹈和藝術性格也在這當中磨礪而成。他見到大野一雄舞團的第一回公演且為之震撼。幾年後在另一現代舞團登台,並結識了同場演出的大野一雄。1959年,土方巽發表了顛覆性的作品《禁色》,共同演出者為大野一雄的兒子大野慶人。大野一雄則加入同一年的重演。舞踏就此正式開展。
究竟什麼是舞踏?
一般藝評將舞踏列為二十世紀後半三大現代舞流派之一,可再分為狂亂醜惡,相當程度依據從七○年代開始編成的舞踏譜為身型動作基準的暗黑舞踏, 以及衍自暗黑舞踏的身體並結合當代美感思維,於八○年代後特別為歐美所重視的當代舞踏或現代舞舞踏。至於大野一雄,許多人或因其資歷而與土方巽並稱為前者的始祖,或因他在國際舞台上廣受歡迎而歸在後者。
事實上,從一開始,土方巽就在他的作品裡為大野一雄保留自由發揮的空間,大野一雄則是在土方巽的舞踏能量中逐漸轉化自身的舞蹈觀和身體觀。六○年代末他退出土方巽的舞踏工作,之後數年完成三部以O氏為名的影片, 從中我們看到大野一雄像是在經驗他自己的暗黑舞踏。1977年,土方巽擔任導演,大野一雄推出了可說是第一部表達出個人靈魂與身體的舞踏作品《阿根廷娜頌》(Admiring La
Argentina)。
大野慶人則是從《禁色》後繼續接受土方巽的編導,同樣在六○年代末離開土方巽,也中止了舞台演出。自《阿根廷娜頌》起參與他父親的公演製作, 後來再次接受土方巽指導,創作出全新形式的舞踏段落,自1985年的《死海》開始,與大野一雄一同在世界各地演出。
大野一雄、大野慶人,還有笠井叡、中嶋夏、田中泯等,這些舞踏者都曾受到土方巽的指導或啟發,也都沒有參與舞踏譜時期,而是以各別的天賦資質和經驗技能,創造出自體式、個人式的舞踏。再加上土方巽自己在許多獨舞片段中的表現,已可證實這是舞踏之中極具價值但尚待深入研究的第三脈絡。
形式之外,舞踏的本質和源頭又是什麼?
有些論述將焦點放在戰爭下的時代衝擊,原子彈與美日安保條約等引發出來的反西方、反體制運動;有些則著重在當時的前衛藝術、思潮、人物,以及日本的傳統文化,像是Expressionist Dance、Surrealism、Eros、Jean Janet、Antonin Artaud、三島由紀夫、澀澤龍彥、歌舞伎、能劇等等。另外也有從土方巽自身人格、成長背景著手的研究。
這些都是舞踏的重要養分,構成了舞踏的骨與肉。只是對真正的舞踏者、真正體驗過舞踏精髓的人來說,某種東西並沒有在上面被點出來。
「⋯⋯作出死者的姿態,再次死去,讓死者又一次以其全部重現他們的死亡—這些是我想在我裡面所經驗到的。死過一次的人可以在我裡面一再一再地死去⋯⋯」「⋯⋯我羨慕我們那些十分照顧他們腳底感受的祖先們。」
將土方巽這幾句話綜合來看,首先值得闡述的是身體,身體上的某位置, 可能是細微的一點,也可能是大片區塊,從那裡觸發出隱密但鮮明的內景式感受,然後這感受以一種無法系統化的路徑傳布全身,進而通透內外,激盪成屬於該舞踏者的動作型態和內心世界。舞踏從身到心皆來自此等難以定位的波動,使其本質實際上相當迥異於其他體系的現代舞。而這樣的身體過程在《魂之糧×練習時的言語》裡隨處得見。
死者或亡靈確實是舞踏的精神核心,相較於泛靈論更多了直逼死亡跟前的迫切感。不過,從土方巽特定的編導作品,以及他在過世前所吐露的心思,其實看得出來某些事情是他尋求但尚未充分觸及到的。同樣在本書裡大野一雄提到史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的融合為一,還有宇宙分送靈魂至胃、腸子、血液、骨髓等話語,以及他在舞台上那些深深進入某種愛與感動的時刻,
可知對大野一雄來說亡靈是能重生的,並且蛻變成性靈、神性的存在。
作為他的導師和他的父親之綜合體,一個新的舞踏意識,一種與人類整體生命或生靈的連結,已悄悄在大野慶人身上完整地呈現。2016年大野慶人帶著《花與鳥》首度至中國演出,他想跟觀眾說的話是:
此刻,我的舞蹈即是祈禱。我想表達出生命是珍貴的。我期望看見一個沒有戰爭的世界到來,每一個人都可以在那裡享受著和平。
靈魂是任何人都可談的詞語,然而深藏在詞語背後,那從不同面向都足以撼動生死,直至永恒的力量,才是有志於研究舞踏、學習舞踏之人應有的關切。
2000年於東京的那場演出,是一雄先生最後一場正式公演,之後他的身體就愈趨衰弱。然而即便僅剩一隻手能動,他還是能讓那隻手揮舞出不可置信的舞踏。2010年,一雄先生去世。
舞踏並沒有停下腳步。數年前慶應大學的土方巽資料館應邀來台舉辦展覽和各項交流。長期得到法國政府贊助的「山海塾」仍在許多國家巡演。慶人先生除了表演、出版新書與DVD,每週還會在橫濱上星川的排練場帶領工作坊, 歡迎任何人前來參加。大野一雄舞踏研究所舉辦了多次大野一雄藝術節,主持者溝端俊夫先生於近年成立非營利組織Dance Archive
Network,讓一雄先生與慶人先生的諸多珍貴資料與世人能有更好的接軌。
《魂之糧×練習時的言語》譯自《魂の糧》、《稽古の言葉》,係由黃莉惠、江佳霖與筆者共同譯成。出版過程中有祁雅媚的協助,尤其是總編輯黎家齊的支持。在台灣,道與藝已是許多藝術工作者乃至一般人士共同追求的境界,不過種種來自傳統或當代的框架也依舊存在。一旦能超越兩邊,超越各式各樣身心靈的侷限,同時掌握得住核心,那將是何等的美與自由啊。本書或許能在這個層面上對讀者作出一些貢獻。
畢竟,這原本就是一雄先生想傳遞給我們的訊息。
大野一雄 給宇宙的訊息
臨近死亡的邊緣,人會重新來到一生中那些喜悅的時刻。
他的眼睛會睜得大大地凝視著掌心,以一種平靜的感受看見死亡、生命、喜悅、與哀傷。
每天這樣地研讀著靈魂,這是否就是旅程的開始?
我迷惑地坐在死者的遊樂場裡。
我渴望能在這裡跳舞、跳舞、跳舞、不停地跳舞,就像野草的生命一樣。
我看見了野草,我就是野草,我與宇宙成為一體的。
像這樣徹底的質變即是靈魂的宇宙定律,也是它自身的研習歷程。
在大自然蓬勃豐饒之處,我看到了舞蹈的根基。
這是因為我的靈魂想要用這身體確實地碰觸到真理嗎?
在我的母親將要過世時,整個晚上我只能撫摸她的頭髮,
一句安慰的話都說不出來。
之後我才明白,當時並不是我在照顧她,反而仍是她在照顧著我。
對我而言,我母親的手掌心就是珍貴無比的野草。
我渴望能舞出野草之舞,這是我心最大的願望。
自體舞踏苑 謝明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