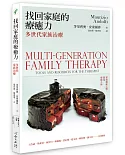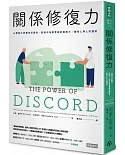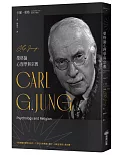推薦序
童話:在夢與神話間行旅的女性
夢、神話以及童話等素材,向來為精神分析重視,運用廣泛。榮格學派對它們的象徵意涵尤為看重,視作原型在集體無意識不同層次上的重要表現。其中,古典榮格學派分析師瑪麗-路薏絲.馮.法蘭茲(Marie-Louise von Franz)對童話分析尤為擅長,《童話中的女性》(The Feminine in Fairy Tales)結合夢境與童話,論述女性困境,探求出路,引人入勝。
夢、神話與童話匯集於原型,對被意識心智潛抑或者忽略之處加以補償。終極的原型則表現為自性(Self)的神話,是為宗教的基礎。但對於女性,或者是兒童而言,宗教,尤其側重陽性的西方一神教,於陰性面向有欠缺,弱化了女性自我(ego)的認識觀點,於是從神話再製而成的童話,成為女性補償心智的夢境,心靈實質崇仰的宗教。
榮格(Carl Jung)在 1925 年間曾造訪中部非洲地區的艾爾貢(Elgon)原始部落,發現當地土著若出現「大夢」(big vision),必須將夢境內容公諸於眾。而如何判斷意象大小呢?當地人說,凡有那種要公開一吐為快的強烈感受者,就是大夢。榮格認為,那是當集體無意識強力襲來時,個體無法承受,故爾若斯。
集體無意識在夢境中常以原型的人物和故事形態顯現,這些意象和內容結構越接近心智無法理解如「生從何來?死往何去?」的問題時,便形成神話,成為宗教前身。
人類學自十九世紀興起以來,對宗教源起的爭論,幾乎無日無之。其中基於進化論思想者,以宗教人類學之父、英國人類學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主張「萬物有靈論」(animism)為代表的觀點最為流行,認為那是人類最初、最原始的宗教形式。這個想法,為「巫術—宗教—科學」連續發展的進化結構模式奠立基礎。
不過,宗教人類學法國學派先驅的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則認為,作為宗教儀式象徵物的動物圖騰,反映該社會群體的宇宙觀以及社會結構,因此「圖騰信仰」(totemism)才是宗教的最基本形式、「宗教乃是對社會本身的集體崇拜」,只有透過社會的「集體表徵」(représentations collectives)才可能認識到特定社會的集體意識。
以研究原始部落民族的象徵性思維著稱的法國人類學家呂西安.列維-布魯爾(Lucien Lévy-Bruhl)繼承涂爾幹「圖騰信仰」的學說,認為原始民族的思考沒有對立性,不對意識和無意識作區分,帶有巫術性格的神話人物,是與社會群體相關的集體表徵。對榮格而言,他所指稱的原型與列維-布魯爾的「集體表徵」並無二致。
列維-布魯爾指出,原始民族思考的特色之一是不以理性為準的「前邏輯」(pre-logical)的邏輯;而宗教的神聖人物,尤其在複雜的一神教系統內的神,則是理性邏輯的產物。原始社會對於神話和宗教是混淆的,集體表徵除了神話人物之外,也涵括了宗教的神,它們都是「神的故事」。因此,集體表徵的集體性上升到國族的層次,充滿陽性邏輯。如榮格便批評基督教因忽略與壓抑了陰性面向,而無法完整涵括心靈。
如前所述,艾爾貢人需要公開大夢。既然有大夢,當然有「小夢」(little
vision)。小夢屬於個人,它們所補償的,除了個人情緒外,也會是特定族群心靈長期潛抑後集聚而成的情結。這些夢境,藉熟悉的原型出現,也可能具神話的集體表徵性質,藉神話人物顯現,但說的卻是另一套故事;或者根本就是神話的變形,敘說著凡人觀點。因此,這些小夢其實不完全「小」,只是不屬主流,而被典型的「大」所淹沒。
這就是童話,神話—宗教連續觀點的另一面,通常以被社會長期忽略的女性或者孩童為主角,說著他們想跟世界說的故事。
比如,波瑟芬妮(Persephone)是大地女神荻米特(Demeter)的女兒,被地獄之主黑帝斯(Hades)強虜為后。荻米特透過萬神之王宙斯(Zeus)介入協調,波瑟芬妮可以在春季約六個月的時間回到大地與母親團聚,這時,地面充滿生機,希臘人稱其為春天女神;而當她回到地府,回復到冥后身分後,不僅大地凋零,甚至本身也變得冷酷無情,連死亡都被吸進她的黑暗中。希臘人因此不敢直呼其名,而以「少女」(Kore)代之。這位暗黑少女唯一一次出現憐憫心的事跡,是被音樂詩人奧菲斯(Orpheus)打動,釋放他的妻子尤麗狄絲(Eurydice)還陽,但終因尤麗狄絲未能守住不得回望地獄的承諾,功虧一簣,不得不死。類似事件的另一次,則是賽姬(Psyche)為求其夫小愛神(Eros)回頭,應小愛神之母愛神阿芙蘿黛蒂(Aphrodite)要求,下地府求助,帶回冥后所交待、一個絕對不能打開的盒子。賽姬於回程,不敵好奇心開蓋,放出睡魔,而立刻沉睡。還好,經過丈夫向其母與宙斯求助,才將她救回,列入神籍,終獲不死之身。
神話層次的大夢,往往直指人性,因著生死、愛憎、貪著、仇恨與癡迷等根本性的痛苦矛盾,而產生震撼的結果;儘管神話主角也會是女性,但表現的往往是符合男性阿尼瑪(Anima)形象的投射,或者是女性片面阿尼姆斯(Animus)的風格,缺乏女性的整體性。我們看到令人生畏的冥后,與負向智慧老人的暴君原型無異;而我見猶憐的賽姬則傾全力於滿足所有人(包括善妒的婆婆,以及自尊心太強的丈夫),惟缺少自己的個性與需要。
同樣的大地甦醒沉睡、死亡復活循環,同樣因為感天動地而終於不死的賽姬等神話,如果重新以女性心靈角度改寫,就成了睡美人的童話版本。美麗的公主無需哀求憐憫,英俊的王子自會拼命去喚醒她,暗喻著男性反過來去滿足女性情慾,與神話觀點大相逕庭。女性在童話裡,成為主角,成為補償神話築夢不足的缺憾。
《童話中的女性》從女性視角分析童話微言大義,補充國族大夢片面神話觀點之不足。馮.法蘭茲利用榮格心理學理論潛入童話內在,分析之深刻,令人折服。
洪素珍(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