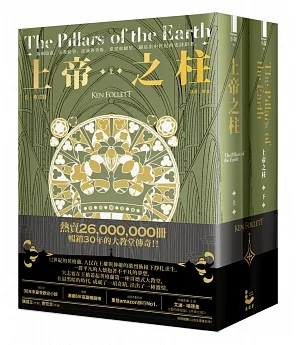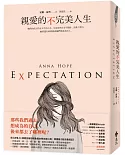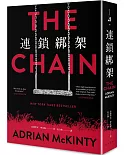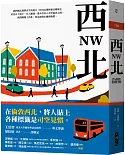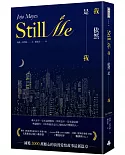序(摘錄)
世事難料。
《上帝之柱》讓很多人大感意外,包括我在內。我原以創作驚悚小說出名,在出版業,當你成名後,聰明的做法是:這輩子就一直寫一樣的東西,一年一本。丑角不該嘗試演哈姆雷特,搖滾歌手不該創作交響樂章,我也不該冒著英名毀於一旦的風險,寫些出乎意料、野心太大的東西。
況且,我又不信神,不是虔誠的教徒。我的經紀人說,我最大的問題在於我欠缺飽受摧殘的靈魂。大家最沒料到我會寫的東西,就是關於蓋教堂的故事。
所以《上帝之柱》不像是我會寫的書,我也差點就不寫了。我提筆寫了一些,擱在一旁,一擱就是十年。
這故事是這樣來的。
我小時候,家人是信名為利茅斯弟兄會的清教派。對我們來說,教堂就是在毫無裝飾的房間中央擺張桌子,桌子四周圍著一排排的座椅,不准掛畫、立雕像、擺放各種裝飾品。那個教派也勸阻教友參訪其他的教會,所以我成長的過程中幾乎對歐洲豐富的教堂建築一無所知。
二十五歲左右,我在倫敦的《晚間新聞》當記者,利用閒暇時間開始寫小說。當時我才發現以前我都沒注意到周遭的城市景致,筆下的人物出去冒險時,一提及建築,總讓我覺得詞窮。所以我買了尼古拉斯•佩夫斯納(Nikolaus Pevsner)所寫的《歐洲建築史綱》(An Outline of European Architecture)。那本書帶我進入建築的殿堂,尤其是在教堂方面。
我拜讀完佩夫斯納的著作不久,報社剛好派我去英國東部的彼得伯勒市(Peterborough)。我早就忘了那次是為了寫什麼報導,但我永遠記得我發稿後做了什麼。我得等一小時才能搭上火車回倫敦,所以我想起佩夫斯納對中世紀建築的迷人描述,便去造訪了彼得伯勒大教堂。
那正是那ㄧ種難能可貴的時刻。彼得伯勒大教堂令我心蕩神馳。
後來,參訪教堂變成我的嗜好。每隔幾個月,我就會開車到英國的古都,住進飯店,研究當地的教堂。每個教堂都獨樹一幟,各有它引人入勝的故事。多數人是花一兩個小時參觀教堂,我則喜歡花一兩天仔細觀察。
但始終有個問題困擾著我,為什麼會興建這些教堂?
中世紀教堂的興建是個驚人的歐洲現象。興建者沒有強大的工具,不懂建築工程的數學,生活貧困(即使是當時最富有的王子,生活條件可能都不如現代監獄裡的囚犯)。但他們卻有辦法建造有史以來最美的建築,而且建得那麼好,在幾百年後的今天仍屹立不搖,供我們研究與讚嘆。
但要講明原因不是那麼簡單,這有點像是去了解二十一世紀的人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探索外太空一樣。這兩個例子中,都有錯綜複雜的因素影響著:對科學的好奇、商業利益、政治對立、凡塵世人對神聖天界的憧憬。在我看來,似乎只有一個方法可以鋪陳那些相關的因素,那就是寫一本小說。
出版社很緊張,他們想要另一部間諜小說。朋友也替我擔心,他們知道我喜歡廣受好評的感覺。我不是那種書賣不好就推說書很好、是讀者不識貨的作家。我寫作是為了娛樂讀者,我很樂於那麼做,作品滯銷會讓我很難過。沒人勸我放棄那個教堂小說的念頭,但很多人都對此抱持保留的態度。
不過,我並沒有打算寫一本「很難」的小說,我想寫一個充滿精采人物的冒險故事,有野心、邪惡、感性、英勇、精明的人物。我希望一般讀者能像我一樣,對中世紀教堂的傳奇沉迷不已。
當時我已經發展出一套沿用至今的工作模式,我先寫小說的綱要,列出每章的情節梗概,簡略勾勒出人物特質。但這本書和我的其他小說不同,一開始我寫得很輕鬆,但隨著故事綿延數十年,人物從小成長到大,我覺得要為他們創造曲折的人生愈來愈難。我發現創作一部長篇小說遠比寫三本普通小說困難許多。
故事裡的英雄必須是某方面的先知,這對我來說很難。要我對一個注重來世的人物感興趣很不容易(很多讀者也是如此)。為了讓修道院長菲力普更慈悲為懷,我給了他一個非常務實的信仰理念,關心眾人在世上的靈魂,不止是在天上而已。
菲力普的性事也是個問題,中世紀的修士與教士理論上都是禁欲獨身者,一個人對抗自己的色欲顯然是個充滿張力的故事,但我對那主題興趣缺缺。我成長於一九六○年代,向來覺得順應誘惑是再自然不過的了。最後,我決定把菲力普設定為某種少數份子,覺得性愛其實沒什麼大不了的,他是我筆下唯一一位樂於禁欲獨身的角色。
隔年,一九八七年三月,我才寫好三分之二的大綱,但我覺得那應該夠了,於是我開始寫作。
十二月時,我寫了兩百多頁。
那進度實在是太糟了,我已經投入創作這個故事兩年,卻只寫出不完整的綱要和幾個章節而已,我不能下半輩子都耗在這本書上,但我能怎麼做?我是可以放棄,改寫另一本驚悚小說;又或者,我可以更努力一點。當時,我都是週一寫到週五,利用週六上午處理商業信件往來。一九八八年一月左右,我開始從週一寫到週六,利用週日處理信件。我的寫作量大增,多寫一天是原因之一,但主要還是因為我在工作中注入更多的熱誠。小說怎麼結尾的問題,後來在我靈機一動下,想到我可以讓主角涉及真實的湯瑪士‧貝克特(Thomas
Becket)謀殺案,問題就這樣迎刃而解了。
我記得我是在當年的年中完成第一版草稿,在既興奮又焦躁下,我更積極地改寫,開始每週連寫七天,丟下商業信件不管。我在一九八九年三月完稿,距離一開始動筆,整整花了三年又三個月。
我精疲力竭,但相當高興,覺得自己寫了很特別的東西,不止是另一本暢銷書而已,可能還是一本優異的通俗小說。
但認同的人不多。
我的美國精裝書出版商威廉‧莫洛出版社(William Morrow &
Co)只印了和《與獅同眠》差不多的本數,他們賣出那個數字時,就已經很滿足了。我的倫敦出版商比較興奮,《上帝之柱》在英國賣得比我之前的小說還好。不過,世界各地出版商的初步反應都只是鬆了一口氣:弗雷特終於完成他的瘋狂案子,成績還算不錯。那本書沒有得獎,甚至沒獲提名。有些書評家對它多所讚譽,但大多數都對它不太在意。這本書在義大利登上暢銷書榜第一名,那裡的讀者一向對我不錯。平裝本在英國曾經登上暢銷榜榜首一週。
我開始覺得我錯估了一切,或許那只是另一本讓人愛不釋卷的小說而已,是不錯,但沒那麼好。在古斯塔夫‧路柏出版社(Gustav Lubber Verlag)任職的德文版編輯瓦爾特‧弗黎采(Walter Fritzsche)長久以來一直想出版一本關於興建大教堂的小說。他甚至和一些德國作家談過這個想法,但一直沒談成,所以他對我的作品相當興奮,一讀到文稿,就覺得他的夢想實現了。
在這之前,我的作品在德國的成績只算差強人意(我書中的壞人常是德國人,所以這也沒什麼好抱怨的)。弗黎采對《上帝之柱》相當熱衷,他覺得這會是一本驚人之作,會讓我在德國變成最受歡迎的作家。
連我都不相信。
但他說得沒錯。
路柏出版社把書賣得好極了。他們找來一位年輕的藝術家阿希姆•基爾(Achim Kiel)畫封面,但他堅持把整本書當成藝術品來設計,出版社也大膽採納了他的概念。他的設計費很貴,但他成功傳達了弗里確的想法:這本書有其獨到之處(後續多年,他一直幫我設計德文版的作品,為路柏出版社創造他們一再採用的風格)。
我第一次獲知讀者認為這本書很特別,是路柏出版社登廣告慶祝銷量突破十萬冊的時候。除了美國以外,我從來沒在任何國家賣出那麼多本精裝本(美國人口又是德國的三倍)。
兩年後,《上帝之柱》開始登上常銷書榜,在德國暢銷書榜上出現八十幾次。年復一年,《上帝之柱》就一直掛在榜上(到目前為止,已經登上三百多週的排行榜)。
有一天我查了一下美國平裝書出版商新美國書庫(New American Library)給我的版稅明細表。這類明細表都是經過精心設計,避免讓作者知道他的書到底賣得怎樣,但經過數十年的努力,我已經學會解讀這類明細表了。當時我發現,《上帝之柱》大約每半年賣五萬冊。相較之下,《針之眼》約賣兩萬五千冊,和我其他書的銷量差不多。
我查了一下英國的銷量,也發現一樣的情況:《上帝之柱》的銷量是其他書的兩倍。
我開始注意到我的書迷來信中,提到《上帝之柱》的次數比其他書還多。在書店辦簽書會時,愈來愈多讀者告訴我《上帝之柱》是他們最愛的小說。很多人要我寫續集(總有一天我會的),有些人說那是他們讀過最棒的小說,其他書從來沒為我贏得那樣的讚賞。英國某家旅行社還來找我規畫《上帝之柱》假期,這一切看來愈來愈像是一股風潮。
最後我終於知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了。這是一本靠口碑賣起來的小說,印證了出版界一個眾所皆知的道理:最好的廣告是你買不到的那種,是靠讀者口耳相傳的個人推薦。那就是推銷《上帝之柱》的力量,是你們辦到的,我親愛的讀者。出版商、經紀人、書評家、文學獎普遍忽略了這本書,但你們沒有。你們發現這本書不一樣,不同凡響,推薦給朋友,口碑就這樣傳開了。
就這樣,一本不被看好的小說,一位不被看好的作家,我還差點就沒寫了,然而這卻是我最好的作品,有你們的賞識。
我很感謝,謝謝大家。
弗雷特
赫特福德郡,斯堤芬尼治
一九九九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