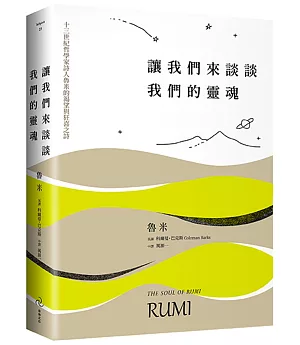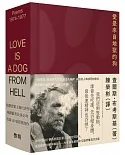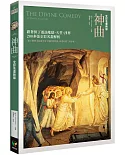序
魯米的生平和他所生活的時代
十三世紀的中東處於一個政治急劇動盪、硝煙彌漫的時代:基督教十字軍東征仍在繼續,他們從西歐出發,穿越安納托利亞半島;勢不可擋的蒙古大軍的鐵騎從亞洲大草原朝歐洲長驅直入。
這也是一個燦爛的靈性覺醒的時代,世界上最偉大的三位謳歌神之臨在的詩人就生活在這個時代,他們在世的時間有重疊的部分:一位是阿西西的聖方濟(St. Francis of Assisi, 1182-1226),他生活在世紀之初;另一位是梅斯特.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
約1260-1328),他生活在世紀之末;第三位則是賈拉魯丁.魯米(1207-1273),他生活在這個世紀的中葉。他們都是偉大而臣服的靈魂,也是神奇的詩歌大師。
魯米出生在名叫巴爾赫(Balkh)的城市附近,位於現今的阿富汗,當時屬於波斯帝國的東部邊界。他出生於1207年9月30日,家族世代都是伊斯蘭法學家、神學家和神祕家。他的父親巴哈爾丁.瓦拉德(Baha ud-Din Walad)寫過一本心靈日記,題為:《從自我到靈魂之愛的筆記》,魯米對這本筆記極為珍視。
在魯米年幼時,就在成吉思汗的軍隊入侵之前,他的全家逃離了巴爾赫,蒙古帝國的版圖向西擴展到波斯,並最終長驅直入,直到亞得里亞海。魯米一家旅行到大馬士革,並一路來到尼沙布林,在那裡,他們遇到了詩人法里度丁.阿塔爾。阿塔爾看出少年的魯米是一個偉大的靈魂。據說,當阿塔爾看到魯米跟隨父親巴哈爾丁向他走來時,他說:「走過來一個大海,後面跟著一個海洋。」為了紀念這次相逢,阿塔爾把他的《真主之書》送給了魯米。
魯米一家最終在土耳其中南部的科尼亞定居。他父親繼續領導當時的苦行僧教團。多年之後,魯米才二十多歲時,他父親去世了。魯米繼承了父親的職位,指導教團的神學、詩歌和音樂的學習,以及其他與靈修有關的事務,也包括烹飪和飼養動物。作為一位虔誠的學者,魯米贏得了廣泛的聲譽。他的教團有一萬多名學生。
教團的工作就是打開心靈,探索合一的奧祕,如饑似渴地探求真理,並試圖道出真理,為生而為人的榮耀和艱辛歡慶。他們為此採用靜默、唱頌、詩歌、冥想、故事、講道和說笑話等多種形式。他們既禁食,也歡宴。他們一起散步,觀察動物,動物的行為是他們學習的經文。他們烹飪、在花園裡勞動,他們也種植果樹和葡萄園。
他們提出了很多人類的根本問題:欲望的目的是什麼?夢是什麼?一首歌又是什麼?我們如何知道另一個人的靜默有多深?心靈是什麼?成為一個完人是什麼意思?宇宙的起源是什麼,個人的覺知如何與這個源頭相連?他們用許多方式提出浮士德式的問題:是什麼支撐著世界,讓它不致崩塌?我們如何在自律和臣服之間達成平衡?這些靈性層面的問答滲透進了詩歌、音樂、運動以及教團的各種活動中。他們知道,答案不一定經由推理而來,而會經由音樂、意象、夢境、以及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事而來。
也有其他與現實生活相關的探討。我應該如何謀生?我如何能讓我的親戚離開我家?你能幫我延緩債期嗎?苦行僧也有世俗的工作要做:石匠、織布工、書籍裝訂、雜貨店店員、製帽匠、裁縫、木匠。他們是手工藝者,而非放棄世間生活之人,他們積極而又肯定,也流露出喜悅和狂喜。有人稱他們為蘇菲或神祕家。而依我看,他們是在追隨他們的心靈。
大約就在這個時期,科尼亞東北部偏僻山區的一個名叫伯爾罕.馬哈其的冥想者回到了教團,他並不知道他的老師、魯米的父親已經去世。當他回來之後,伯爾罕決定要用他的餘生來教導和訓練老師的兒子。在九年時間裡,他帶領魯米進行了多次、有時是連續的四十日禁食。魯米熟練地掌握了這種神祕傳統。他教導學生們敞開心靈,寫詩來鼓勵他們這樣做。「神祕」一詞在這裡並不是指一個祕密的世系或任何祕傳教義。這個詞就像「靈性」一詞一樣,我儘量避免使用這個詞,但我做不到。「神祕」或「靈性」經驗常常無法用經驗來驗證,或者說,照相機無法把它拍下來、秤不能稱出它的重量,甚至語言也很難描述它。它並不完全是身體的、情感的或思維的,儘管它常常包含這三個方面。就像我們內心深處的愛一樣,神祕經驗既無法證明,也無法否認。它確實會發生,而這正是魯米詩歌所棲居的人類存在的領域。
魯米的第一個妻子去世後,他又結過一次婚,他有四個孩子。我們確實對魯米那時的日常生活有些瞭解,因為他的大兒子蘇丹.維萊德(Sultan
Walad)保存了魯米的一百四十七封私人信件。我們可以從中瞭解到,他非常緊密地參與教團的生活。在一封信中,他懇請一個人延期十五天向另一個欠他錢的人收債。他請一位有錢的貴族借給一個學生一小筆錢。一個親戚搬到一個虔誠的老婦人擁擠的家裡,他詢問有什麼解決的辦法。在信中也會突然冒出幾句詩行。魯米做著很實際的世間工作,同時也是一個內心充滿狂喜的詩人。
在1244年10月底,魯米遇到了大不里士的夏姆士(Shams Tabrizi,
1185-1248),這成了魯米人生中的中心事件,它激發魯米成為也許是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神祕主義詩人。夏姆士是一個充滿神性的人,他穿著一件黑斗篷。蘇菲故事中提到,他周遊各地,尋找一個能承受他深刻而強烈臨在的朋友。夏姆士是一名石匠,他可以在靈魂的狂喜狀態和日常的體力勞動之間自由轉換。每當學生們圍繞在他身邊——他們總是這樣,他就會披上他的黑斗篷,然後告辭。
夏姆士心中一直有一個疑問:「難道我沒有朋友嗎?」
最後,一個聲音傳來:「你願意用什麼來交換?」
「我的頭。」
「你的朋友是科尼亞的賈拉魯丁。」
有關他們第一次見面的情形有好幾種說法。一種說法是,魯米在科尼亞一個小廣場的噴泉邊教導學生,他在朗讀他父親的筆記。夏姆士穿過人群,把那本書和別的書都扔進水池。
「你是誰?你想幹什麼?」魯米問道。
「現在,你必須活出你一直在閱讀和談論的智慧!」
魯米把目光轉向水中的書。
「我們可以把書撈上來,」夏姆士說,「它們會和原本一樣乾。」
夏姆士從水中拾起一本書給魯米看。那本書是乾的。
「扔了它們。」魯米說。
當魯米擯棄了書本,他開始了一種深刻的靈性生活和詩歌創作。「我原以為屬於真主的品質,如今我在一個人的身上看到了。」他作為神學家的時期也結束了。他和夏姆士一起靜修數月之久。他們的密談和神祕友誼從此展開。
但是,教團中的一些人非常嫉妒夏姆士,他們不信任他,並怨恨他讓魯米放棄了教學。他們逼迫夏姆士去大馬士革,但魯米又把他叫了回來。最後,似乎是魯米的一些學生,很可能包括他的一個叫阿拉丁的兒子在內,殺死了夏姆士,並隱藏了他的屍體。魯米悲痛欲絕,開始繞著他花園中的一根柱子吟詩,這些詩後來被視為有關尋找神聖伴侶的最真實的記錄。當然,他的轉圈也成了梅夫拉維教團動態冥想的起源。這同時也是自律和臣服的象徵,這是與星空、原子和作為宇宙源頭和本質的旋轉形式相呼應的舞蹈。但也要牢記,魯米的狂喜始於悲痛。
他口說出詩句,筆錄者把它們記下來,魯米再在記錄稿上修改,但他的大部分詩作可以說是自然的即興創作。他的《大不里士的夏姆士作品集》可以視為他們神聖友誼的內在對話。有一段時間,魯米四處尋找夏姆士,直到有一天在大馬士革他突然意識到,自己無需再尋找了。他感覺到,並且知道,夏姆士就存在於這份友誼中,並且他(魯米)自己就是這份友誼。他的詩歌就來自於那裡。
這部由頌詩組成的詩集,由一系列的兩行對句組成,有時只有短短八行,有時候則要長得多。這種形式是一種從一個意象到另一個意象、從一個思緒到另一個思緒的非理性、直覺式的跳躍。這種靈活的詩歌形式成了魯米的熱切渴望的合適載體。魯米和夏姆士在心靈中相遇,他們的神聖友誼在詩歌中擴展,超越了性別和年齡,超越了浪漫愛情,超越了任何的師生概念。這些詩歌包括〈陽光〉和〈任何人說的話〉。他們的友誼就是他們所居住的宇宙。不是經由愛相連,他們就是愛本身的活躍氛圍。魯米的詩歌呼吸著這樣的氣息。它們清新而感人,在七百年之後的今天,依然讓我們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魯米在他生命的最後十二年中寫下了一首超級長詩,這首詩的名字就叫《瑪斯納維》(Masnavi),共有六萬四千詩行,分為六卷。這在世界文學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它就像海洋一樣波濤洶湧,涉及許多主題。它是自我的詮釋,又充滿了遠見卓識,有時會對靈魂的健康和《古蘭經》中的段落加以幽默的評論,書中充滿了民間傳說、笑話,以及對當時在世人物的評價。魯米把這部詩歌巨著獻給了他的抄寫員胡薩姆.切利比(Hussam
Chalabi)。他們一起在科尼亞散步時、在穿過梅拉姆的葡萄園時、在授課時、在街上或在澡堂時,魯米都會向胡薩姆口述詩句。胡薩姆曾是夏姆士的學生,所以,這首長詩也可以看成是魯米與這位摯友的對話的延續。這部詩集奇特的多樣性的統一,也體現了魯米領導他教團的方式:有時,他會參與教團的整體成長;有時,他則會強調個人的需求。《瑪斯納維》的讀者可以從這部詩集的任何地方讀起,並在其中暢遊。它是一股詩歌之流,它的副歌是狂喜的歡呼:「這沒有終點!」或者,「這無法言說,我已沉溺其中!」
魯米在1273年12月17日黃昏時分去世。每個月都會有上千人憑弔他在科尼亞的陵墓。據說,各大宗教都派代表參加了他的葬禮。他們把魯米和他的詩歌視為幫助他們加深自己信念的一種方法。他也常常被稱為莫拉維(Mawlawi)或毛拉納(Mawlana),意思是「大師」或「主人」。每年的12月17日,全世界都會紀念這個他與神性合一之夜。這也被稱為他的婚禮之夜。魯米感覺這種合一就像呼吸一樣自然,他知道這就是每一個想要讚頌的衝動的核心,並且,他認識到,它就是他稱作「心上人」或「摯友」的臨在。他並不屬於某個有組織的宗教或文化體系,他宣稱,他屬於這彌漫整個宇宙、並讓它充滿活力的神聖臨在。
我屬於心上人,我已看見兩個
世界合而為一,我呼喚它,並知道
它是最初,最終,外在,內在,
只有那呼吸,將人類呼吸。
譯跋:
魯米在《瑪斯納維》中講過一個寓意深刻的故事。在巴格達,有一個人繼承了巨大的家產,但他不知珍惜,揮霍一空。在窮困潦倒之際,他向神祈禱。最後,他在夢中聽到一個聲音告訴他:「你的財富在開羅。去那裡的某個地點挖掘,你就會找到你想要的財富。」於是,他歷盡艱辛,一路跋涉,終於來到開羅,但他已身無分文,只能乞討為生。巡夜的警察誤以為他是小偷而抓住他。「等一等!」他向警察解釋道,「我並不是小偷,我住在巴格達,剛剛來到開羅。」接著,他道出了自己做的夢和埋在地下的寶藏。警察對他的話深信不疑,對他說:「雖說你是個好人,但你有點兒笨。我也做過這樣的夢。在夢中,有個聲音告訴我,在巴格達某某街的某個地方,埋著一座寶藏。」警察說的正是這個人住的地方!他甚至還提到了這個人的名字!警察說:「但我並沒有按夢中的指示去做。看看你,你這樣做了,在世上流浪,落得沿街乞討,窮困潦倒!」那個尋求者卻在心中暗想:「我所渴望的,原來就在巴格達我自己的家中!」
魯米借這個尋求者之口總結道:「生命之泉就在這裡,我一直在其中暢飲,但走過漫漫長路,我才明白!」
有趣的是,巴西作家保羅.柯爾賀根據這個故事改編的小說《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在全球暢銷3500萬冊。美國詩人科爾曼.巴克斯翻譯的魯米詩集《在春天走進果園》也創造了詩歌出版的奇蹟,在美國售出50萬冊,掀起的魯米熱潮蔓延整個西方世界。
魯米的詩歌,之所以在當代美國乃至全世界受到如此廣泛的喜愛和歡迎,原因有很多,根本的一點是,魯米不僅是一個滿懷渴望與狂喜的詩人,他更是一位大師,一位開悟者。他深邃浩瀚的心靈世界決定了這些愛的詩歌的高度和品質。翻譯和閱讀魯米,我感覺就像是在玩一個神祕而有趣的拼圖遊戲。我想像自己徜徉在魯米生動而優美的詩歌海洋裡,一路採擷它的粼粼波光,這些智慧的閃光就像一片片拼圖的碎片,我嘗試拼湊、還原出詩人所要展現的一幅宏偉絢爛的心靈世界的畫卷。
虛幻與真實
作為伊斯蘭教神祕派別的蘇菲派,其最大的特點在於:「一切非真,唯有真主」。這句話一方面道出了世間一切的虛幻本質;另一方面,它也肯定了神是唯一的真神和造物主的地位。我們是神的受造,來到這個幻相世界。我們受著兩股能量的吸引,一種是動物能量,一種是靈性能量。只有當我們活出動物的力量,我們才會明白,這些滿足並不是我們真正想要的。我們在這裡還有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追隨神祕的渴望,並且超越它們,回到我們原來的家——神的懷抱。因此,我們在這裡「並不是為了牟利,也不是為了歡愉,甚至不是為了喜悅」,而是要「把你的生命交給你內在的那一位」,如果你不這樣做,魯米說,你就是在浪費你的生命。他也為我們描繪了那些逃亡者的形象,他們會忍受與神的「分離之苦,但依然歡笑。他們快樂地活,快樂地死,始終容光煥發,因為他們知道正在到來的回歸。」
「我們是這裡的異鄉人。」魯米對我們身處其中的時空幻境有著深刻的認識。一方面,物質世界就像泥沼一樣,我們面臨深陷其中的危險。另一方面,他也明白,這一切只是造物主的一個設計而已。雖然我們的身體感官搖擺不定、模糊不清,欲望讓我們執迷和昏睡,但我們心中始終有一團清澈的火焰。並且,神會為我們派來先知和嚮導,並賜予我們恩典和祝福。這就像是在玩一個發現寶藏的遊戲,而寶藏就在我們自己心中。或者說,我們身處天堂,在夢中夢見另一個有形有相的幻相世界,當我們開始相信夢中的世界,我們就忘了自己真正在哪裡。而當我們認出夢境的虛幻不實,我們就會從夢中醒來。
這一歷程就是靈魂的進化過程。從礦物、到植物、再到動物、到人類,「我們已由我們最初的樣子改變了千萬次,每一次的展開都好過上一次」。我們在這裡所要做的就是轉化的工作,把欲望轉化為渴望,把憤怒和仇恨轉化為喜悅和愛,是要「讓不可見的靈性經由你而閃閃發光」。
寂滅與回歸 蘇菲派認為,心靈才是我們最根本的存在狀態,而愛則是一條寂滅之路。我們最初的狀態是非在,我們的回歸之旅就是要回到與神合一的境界。而這樣的回歸,並非發生在死後,相反,魯米敦促我們,要「在我們死前死去」,這就是消融於心靈之中。
這樣的合一經驗就是魯米所說的法納,我們因品嘗到了神的甜蜜而狂喜。但我們還會從法納中回來,這也許就是所謂的「看山還是山」的階段,所不同的是,我們內心懷著一份清明、一份不可動搖的平安,活在當下的每一刻,展現出靈魂之美。
在魯米眼中,存在包含於非在之中,是本質的彰顯形式。在〈戀人若能赴死〉一詩中,魯米寫道:「一個偉大的靈魂來到夏姆士面前。『你在這裡幹什麼?』回答:『那裡有什麼可做』」這裡指的就是我們所處的現象世界,那裡則是我們所來自的合一境界。兩者的區別,就是有無之別。在魯米看來,存在就像是一隻魚鉤,「任何被抓之人都會失去自由的喜悅。被釘於四大元素,就是一次十字架受難。」而非在則是「我們在其中暢遊的海洋」。已經深深認同於頭腦和身體的我們,對寂滅、非在和虛空有著本能的恐懼,魯米則為我們展現了另一種截然相反的視角:我們「以為自己將要消解於非在,但非在更害怕它會被賦予人形!」
魯米提醒我們,我們的靈魂就像國王的獵鷹,有著高貴而神聖的品質,並且擁有自由意志,能夠擺脫自我而體驗到靈魂的喜悅。他形象地用水滴回到大海的比喻告訴我們,這種表面的放棄並不是一場災難,而是回歸,是一場合一的婚禮。
愛與臣服
魯米詩歌中所談論和描繪的愛,與我們通常所認知和理解的愛是截然不同的。愛是「最後一包三十磅重的貨物,當你把它裝上船,船就會底朝天。」魯米所說的愛,就像是「一個瘋子,執行著他瘋狂的計畫,撕扯下他的衣服,在山中奔跑,喝著毒藥,現在,安靜地選擇寂滅。」這樣的愛與神有關,實際上,愛就是「神的一種品質」,對於神來說,一切都是愛,一切都處於愛之中,甚至可以說,神就是愛本身,那是一種無限而永恆的境界。在這種狀態,愛是無條件的,也一無所需,甚至沒有愛的對象。戀人、心上人、愛,三者已合而為一。而我們所瞭解的世間層面的愛,則是局限的、必須依附於事物、帶有各種條件、需要討價還價、隨時會中止和收回。魯米稱這種愛是「沒有實質的影子」,但他也說:「這樣的愛,也是無限之愛的一部分,少了它,世界就不會進化」,「神就活在一個人和他所想要的事物之間」,「多麼神奇,神就在吸引你的事物之中。」
魯米告誡我們,要用這樣一種方式墜入愛河,它會把你從任何束縛中解放出來,要「將自我清空,並用愛填滿。」作為回歸神的方式,愛既狂野,又令人困惑。因為這樣的愛會讓你「失去你曾經認為有價值的一切」。但這樣的愛會帶來覺醒。我們由此而進入臣服的階段。「我完全信任神。我是一只等著被踢的皮球。我自己什麼也不做。這就是當你不再嘗試、讓吸引你的源頭完全掌控時所發生的情形。」這樣的臣服會讓我們變得「無助和愚鈍」,對任何事都不再確定。在〈誰借我之口發言〉一詩中,魯米有驚人的一問:「誰把我帶到這裡,誰就必須帶我回家」乍一看,這是一種酒醉後的冒犯和挑釁,但再細細想來,這又何嘗不是一種深深的臣服。他在另一首詩中又說:「我來到這裡,並非自願,同樣,我也無法離開。」
摯友與神
可以說,是大不里士的夏姆士造就了作為偉大心靈詩人的魯米,而魯米的這些詩歌則是對這位摯友的渴望、思念和讚頌。夏姆士到底對魯米意味著什麼,魯米的這句話道出了其中的祕密:「我原以為屬於神的品質,如今,我在一個人的身上看到了。」夏姆士就是神的化身,這就是魯米所說的「大不里士的夏姆士,你的容顏,是每一門宗教想要牢記的一切」的真正含義。因此,每當魯米提及摯友時,他同時也是指太陽,更是指光明的本質——神,或心上人。在魯米眼中,神是所有可見和不可見的事物、存在與非在的至高無上的創造者。但魯米對這位造物主並無絲毫敬畏或恐懼之情,相反,他處處表露出一種戀人之間才有的愛的親密:「心上人是一頭獅子。而我們是他爪下跛足的小鹿。」
對我們來說,神或許是一個難以理解的抽象概念,而在魯米的世界裡,神是最真實的現實。「如果你想瞭解神,那就享受戀人的陪伴」;「無論我尋找什麼,我始終在尋找您」;「我的心上人是不是無處不在?」;「帶來快樂的一切,都是摯友的芬芳。讓我們驚奇的一切,都來自於那光明。」
他認識到,「只有與您合一才會帶來喜悅」,「慈愛的神才是唯一的喜悅」。當我們在愛中與神合一,我們只剩下一種海洋般的感覺,一種消失於陽光中、既空又滿的感覺,這就是狂喜的核心。他最終認識到,那位摯友就是「你最本質的自我」,「開啟者和被開啟者是同一回事!」
自我與自性
「我是誰?」這是每個人都問過的問題,但並不是每個人都已找到令自己滿意的答案。魯米的回答或許會帶給我們啟發或共鳴。「你是誰?內在的視力?心靈?半明半暗的神性,這是不是你?」;「你是靈魂,你是愛,不是一個精靈、天使或人類!你是一個神人或人神!」這樣的答案我們也曾聽說過、思考過,但並沒有可靠而確鑿的證據,我們大多數人大多時候把自己認同於身體、頭腦、個性、身份、地位、關係、名聲和財富。而在魯米所描繪的更廣闊的心靈畫卷中,這樣的認知會顯得荒謬可笑。我們就像受了女巫魔咒的喀布爾王子一樣,沉溺於感官世界,任由命運擺佈,不得安寧和自由。他說:「當欲望之鳥看著物質世界所提供的一切,並追逐著它的欲望,它真的是在啄食它自己」,「我們都在悲喜之間被拖來拖去,就像脖子上拴著兩根繩子。」
魯米得出的結論是,必須否定自我,放下頭腦。當你把頭腦踢開,「一千條新的道路就會清晰展現」。這就是先知和完人給我們帶來的啟示:「無我才是你真正的自我……而大多數人都這樣活著:就睡在清澈溪流的岸邊,卻依然口乾舌燥。在夢中,你跑向海市蜃樓。當你一路奔跑,你為看到了綠洲而自豪。」他要求我們要像烏姆魯勒.蓋斯和塔布克國王一樣,「離開虛假的自我,活在更真實的自性之中。」魯米把這種自我超越稱作「另一種死亡」、「愛的殺戮」。經由這樣的轉化,「你曾經是火,現在,你是光。你曾經是一粒生澀的葡萄,現在,你豐滿多汁,如今,你是一顆甘甜的葡萄乾。一點星光變成了太陽。」
開悟與看見
我曾有過這樣的疑問:一個開悟者和常人到底有什麼樣的不同?我的答案是,並不是他們比常人多了什麼,並不是他們多了與眾不同的稟賦、神通或特殊的恩典,而是他們比常人少了什麼,他們少了常人所不願放下的自我和對幻相的執著。他們看自己、看世界的眼光完全改變了。魯米說:「經由夏姆士的眼睛,看到的水滴全都是寶石。」英譯者科爾曼.巴克斯問他的上師:「我在你眼中看到的智慧,是否有朝一日也能來到我的頭腦中,並用它去看世界?」巴瓦回答道:「直到這個我成為我們。」這個簡單的回答道出了開悟的本質,開悟者可以說是一個無我之人,至少,他對自性的認同已幾乎完全取代了對自我的認同。
就像盲人摸象一樣,感官認知有著明顯的局限和缺陷。魯米提醒我們,還有另一種看的方式。我們都有「能看到永恆的眼睛」,那就是靈性的視力,這種眼光「看待事物的方式,與它們所是的樣子正好相反」,「對那些用靈魂之眼看的人,甚至身體的死亡都是美麗的」。這就是內在之眼,它能看見肉眼所看不到的另一種光明。這就是與神的合一之光,「當你看到合一的輝煌,二元性的吸引力就顯得讓人心碎而又可愛,但不再那麼有趣。」
頭腦與靈魂
魯米的生命觀並不局限於生死之間的短暫間隙,他所看到的是一幅更為壯闊的靈性生命的圖景。他已看穿死亡的虛幻不實,身體的死亡就像是睡眠一樣。不朽的靈魂在這裡是為了成長和盛開。他說:「靈魂在這裡是為了它自己的喜悅」。而外在世界則是內在世界的反映和彰顯。大多數人為自然之美所吸引,但我們並沒有意識到,我們只是愛著溪水中的倒影,而完全忽略了它的源頭——靈魂的存在。「要努力去聞真正果園的芳香。品嘗葡萄園中的葡萄園。」
在這裡,我們的靈魂就像是〈印度鸚鵡〉中那隻籠中的鸚鵡,牠被束縛於身體之中,失去了本有的自由。而我們從這裡逃脫的過程,就像是從頭腦中孵化出靈魂之鳥。魯米指出,正如年老的哲人臨終前所認識到的,他的頭腦對他並無幫助,「我一直愚蠢地四處奔忙,想要躲開聖人。」而只有靈魂才能讓我們獲得平安和喜悅,讓我們更加接近真理。
魯米觀察到,人們的心靈是相通的,「在彼此之間,我們有道路相連。」這是靈魂與身體的一個重大區別。每一個人的身體都是相互分離和獨立的,而靈魂則彼此相連,甚至不分彼此,「穆薩在爾撒的靈魂中,正如爾撒也在穆薩的靈魂中。」同樣,生命也是一個整體,「許多生命,在一個生命之中。」
靈魂,或靈魂的總和——靈性,到底是什麼呢?愛或神可以說是它的同義詞。當魯米進入與神合一的狀態,他感覺到「戀人和摯友,是同一個生命」。從個體靈魂到無我的靈性,還需要經歷一次轉變,這就是魯米所謂的「羚羊追蹤獅子」。這種純粹靈性的觀念最終必然會得出結論:我們是一體的,這就是哈拉智所道出的真理:「我就是神。」
修行與悟道
魯米鼓勵人們從經驗中學習,哪怕我們像蠢笨的驢子一樣為世事而奔忙,「我們暫且眼瞎一會兒也有好處,這有助於我們的學習!」他認為,最切實可行的修行,並不是遁入荒野,與世隔絕,而貴在循序漸進、持之以恆。「逐漸減少你給你動物靈魂的食物,更多品嘗滋養你清澈光明的食物」;「堅持每天修習。你的專一,是門上的銅環。」要培養自己的覺察力,「要和你心靈的主人一起,時時檢查你內心的狀態」;要學會權衡取捨你面前的誘餌和大海中的自由,「請回想一下,你靈魂的摯友對你的呼喚。」並且,要培養與摯友的友誼,最終達成無我和與神合一的狀態。
「如果沒有巨大的悲傷,沒有人能進入靈性。」這是魯米的經驗之談。他認為,悲傷和痛苦有著獨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因為它們能打開我們的心扉,讓我們找到愛,並把我們帶向摯友。而摯友對我們的幫助之一,就是為我們帶來心「困難、悲傷和疾病」,所以說,甚至你的缺陷都是彰顯榮耀的方式。「會傷害你的,也會賜予你祝福。黑暗就是你的蠟燭。」魯米也常常提及渴望的重要性,他說:「渴望是奧祕的核心。渴望本身會帶來療癒。」正是我們的乾渴,把我們引向神的不竭泉源,正是我們的渴望,為我們帶來平安,讓我們擦亮自我之鏡。他還說:「如果我從來不曾感到過這渴望,我就不可能知道,愛是什麼。」
魯米把修行的過程形象地描繪為一種轉化,是蠟燭燃燒、化為光明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靈魂從知道的靈魂那裡受益,」謝赫或老師,有時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都需要很多的學習,謝赫的很多提醒,很多翻轉和很多攪拌。慢慢地,內在的黃油就會出現。不要過早放棄攪拌的工作!」另一方面,魯米也反覆提醒,要認出我們自己內在的神性智慧,「在你的內在有一眼泉水。不要拿著空水桶轉來轉去」;「在你的頭頂,有一籃新鮮麵包,你卻挨家挨戶乞討麵包皮。」
魯米強調,要「用冥想和靜默擦亮你的心靈」,他形象地告訴我們:「你陳舊的生活,原本是逃離靜默的一路狂奔。現在,無言的滿月已經升起。」靜默是深入內在生命核心的必經之路。我們要停止讓核桃殼發出聲響,而去品味核桃中油脂的靜默,「那甜美的喜悅,就是我們費力打開核桃的原因。」經由靜默,「靈魂會變得甜蜜,並會更加繁盛,」而純粹的靜默,是一首虛空之歌,會帶來平安,並導向與神合一。
閱讀魯米的詩歌,不僅會帶來心靈的愉悅,體味到靈性的自由,也會讓我們深入自己的內心,喚醒有關自己源頭的沉睡記憶。當我們徜徉在魯米豐富而廣闊的意象海洋中,我們享受著他所帶來的愛的盛宴和喜悅的美酒。但最為重要的,我們有機會走進一個偉大靈魂為我們展現的心靈世界,並進入語言所無法觸及、活在我們每一個人內在的神性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