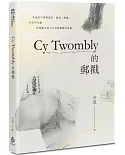推薦序
從大學至碩士班時期,儘管就讀的科目是外國文學,因個人興趣之故,卻也閱讀了不少台灣的中文新詩,尤其醉迷於洛夫詩中的魔幻意境。不過,出國攻讀西洋文學博士後至今,因研究與教學過於繁忙,便鮮少閱讀中文新詩了。此次研修旅居異鄉之時,收到馮冬的邀請,為其詩集《思辨患者》寫篇序言,才得有機會重溫年輕時的興趣。
對許多人而言,身處異地的境況特別能夠激發詩心,乃因漂泊離散的狀態常迫使人不得不與內心裡那沉默的自己對話,並逐一審視與檢討自己的身心需求。而詩人與眾不同的地方在於,他無須將自己放置於異鄉便能詩心湧現,因為詩人不時將自己拋入離散的狀態,不時使自己與環境格格不入,以免安逸於現狀而讓思維的觸角遲鈍。此乃詩人不得不為之的宿命,甚或是比一生還要漫長的詩歌的詛咒。以此觀之,詩人可說是位變態,或以馮冬的話言之,是位「患者」;唯有讓自己處於德國哲人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所謂常態「失能」(breakdown)的狀態,才得以喚醒與體悟生命的本質。
如同這本詩集的題辭所揭示的——「因此我將/相似於許多事物,卻不是/它們中的⼀個」——詩人注定是孤獨的。但這不是意味著詩人自诩高高在上或孤芳自賞,而是詩人必須站在主流價值觀的對立面。當眾人服膺理性,以量化的方式理解世界,以致必須依賴「對稱結構」才得以過著井然有序的生活,否則世界便會變得「一片荒蕪」(〈沒有詩意的理性〉)。理性擅長的是簡化外在與內在世界:
彩虹的顏色繁複,但是我們卻慣以為彩虹由七種顏色構成;每片葉子的形狀、顏色、脈絡等皆不同,但我們卻習慣忽略個別差異而以「葉子」一詞統稱之;心情的跌宕起伏也非只有喜怒哀樂等四種情緒等等。詩人的孤獨即在於不從眾,他必須擺脫邏輯理性的掌控,如此才得以感受到情感的細緻波動,且語言的使用不致僵化失血。簡言之,詩人的思辨流動不居、超越分類,此正是理性所要賤斥的對象:
「理性唯一不能接受的,是詩意將一切歸結為『願望』的存在」。
而詩人的願望無非是詩歌可以改變人心,進而改變世界。誠如法國超現實主義詩人布荷東(André Breton)
曾言:「馬克思說『改變世界』;韓波(Rimbaud)說『改變生活』。此二名言對我們而言是一體的。」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今日,要以詩歌來進行思想革命分外辛苦,甚至如狗吠火車般。然而,嚴肅詩人如馮冬者並未放棄。的確,詩人是位孤獨的患者,但他卻未顧影自憐而是奮力吶喊,儘管聲音常淹沒於人性墮落的洪流中。在這百頁詩集裡,馮冬運用變色龍般的想像力,口吻時而批判、時而嘲諷、時而柔情、時而冷漠、時而自嘲,化身為各類「人」——「民工式的人」、「沒有軌道的人」、「治癒河流的人」、「天空行走者」等等——試圖讓每位讀者皆可尋回並喚醒自己內心深處那位既熟悉又陌生的「患者」。閱畢馮冬的詩集不免思忖,如果每個人都能成為「患者」,這世界必能正常許多。
趙順良
2017 年11 月於麻省劍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