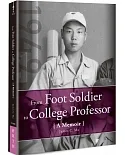序
誰願虛度一生?走過價值低微或無價值甚至反價值的一生?出生1945~1960年的知青一代,被毛澤東忽悠為「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似乎生當其時,趕上好時代,必能成就一番大事業。如今,知青一代歲近遲暮,精華已盡,發現一生盡落在時代凹陷處―叫一聲知青真沉重!
本集以知青為軸,實錄筆者上山下鄉,列示「深遠歷史影響」,多陳事實,少發議論。
筆者「上山」大興安嶺八年(1970~1978),顧城〈一代人〉簡括知青一代宿命―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羅瑞卿之子羅宇(1944~ ),文革蹲獄近五年,才明白「告訴你什麼就是什麼」的紅色教育實為規定思維不准思考。1979年,他向胡耀邦吐槽:
你們把我們都教傻了,還得我自己在共產黨的監獄裡想清楚共產黨。
2016年11月9日,一位「支邊」浙江老知青函告筆者:
我們這一代經歷了不許思考、不想思考、到不會思考。
上山下鄉使我早早了解國情。每年探親回杭,八千里路雲和月,饑貧現實當然比紅頭文件更教育我。眼見為實的「局部」使我本能地質疑報刊上的「整體」,反骨漸凸。一心為共產主義「時刻準備著」的青年,竟萌生「不同政見」。迫於紅色恐怖,所有不滿50歲前只敢暗存於心,不敢發露於外。同時囿於學力,五旬之前看到的赤難尚浮淺表,真正的國家內傷,很晚才知道。撮述一例――
1958年初春,北京高校右派師生發配昌平農場勞動,與下放幹部同一食堂,但打飯不同窗口。幹部們打出香噴噴的紅燒肉、炸雞炸魚、肉包子、白饅頭,右派師生打出的卻是窩窩頭、鹹蘿蔔、無一星油水的菜湯,天天如此,頓頓如此。
最難受的是打得飯來,和幹部都站在一張八仙桌前吃,各吃各的。美味佳餚能看能聞卻只見它們被送進別人的口中大嚼,而自己吃進去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而平時大家幹的是一樣的活兒,或抬著同一副筐。
「八九點鐘太陽」不知道校園外等著我們的竟是這樣的「新社會」。知青最終成「愚青」,相當一部分終身自錮「鐵屋」,自覺摒蔽「反動資訊」,思維嚴重歪擰,還自我感覺良好,自封「國家功臣」―上山下鄉為坍塌的國家經濟撐起一角。這批老知青成為標準文革遺民,至今承襲文革邏輯,還認為上山下鄉「很有必要」、「人生財富」,咒罵筆者「沒有靈魂」、「厚顏無恥」、「攻擊共和國」。紅袖章仍在箍束這批老知青,他們已無力走出文革泥淖,自願為毛共歲月殉葬。
本集〈老知青文化內傷〉,一位興安嶺老友(中國美院教授),2013年憤於筆者成了「反動港刊」的角兒,抹黑「共和國」,喝令我「走正道」―必須為中共「歌德」。這聲對我的咒罵再次印證思想之力,體現文革的「影響深遠」。
歷史很怕對比。杭州書香子弟夏衍(1900~1995),14歲公費入省立甲種工業學校,20歲公費留日(九州工大),深得政府恩澤。
1927年4月,夏衍學成回國,5月加入中共,破壞安定團結,成為政府掘墓人。知青一代大多初中畢業就被剝奪升學權利,趕入「廣闊天地」,還須時刻感恩「偉光正」,至今不許質疑「新社會」―觸犯天條的大逆不道!時代前進耶倒退耶?不該找找原因麼?
「對景傷前世,懷才誤此身。」(和珅絕筆)大部分知青生不逢時,抱憾而終。無論自覺不自覺,都無法掙脫歷史局限―終身攜帶文革底色,多少惆悵煙雨中。大多數老知青當然不同意中共的「淡化」,意識到有權利也有義務批判上山下鄉,為後代多少留下一點「千萬不要忘記」。
筆者最終還是成為「謬種」,台版拙著《烏托邦的幻滅―延安一代士林》及本套叢書,為馬列主義送葬、為紅色革命送終。
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既傷身世,更悲國事,歲至暮齒,思緒遠馳。狐死首丘,代馬依風;自由民主,人類方向。惟願生入玉門關,能見民主大開張。即使未能及身而見,也堅信天安門前的紅旗打不久了,中國不能獨立全球文明之外,民主自由的旗幟一定會高高升起。難道中國還有別的選擇麼?
2017-8-8 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