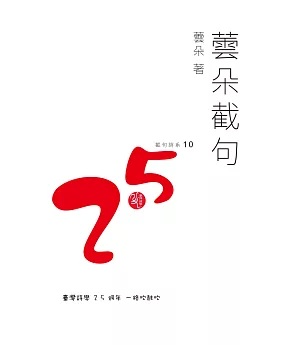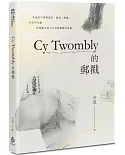自序
今年最長的一首詩/蕓朵
截句一詞很新,橫空出世。
2016年底,白靈老師在臺灣詩學的年度聚會上,攜來一本書;大陸小說家蔣一談的《截句》。書的作者有一天突發奇想,把他小說中的句子截取出來,匯成一本《截句》出版,作者認為小說中的文句,也有如詩句般精練而美麗的文字,而這些句子也許如鑽石般晶瑩剔透,卻隨性地散落在小說各處,若是收集起來,或許可以看出作者在創作上的另一種面目,從側面看出創作者在文字功力上的段數。
同時,在小說流暢的敘述文字之外,截斷其部分情節的流動,而放大某些具有特色或是意義的句子,以類新詩分行的形式將這些句子以不超過四行的形式排列,將細節放大後的效果也許可以呈現另一種角度的美學。換言之,若從斷章而產生的歧義,從整體切割之後激發的文字效果,有時,可能也會像轉個彎的文學思維,體現創作者獨立而企圖創新的野心。
於時,白靈老師提出大家一起來寫截句的構想。2017上半年,便成為詩壇上詩人競寫截句的時空舞臺。令人期待的是,詩人的截句與小說家的截句自是有不同的美學觀。詩是精緻的文字,當詩以如絕句般的短詩出現時,意象的掌握與標示自然必須重新處理,不能像小說一樣充斥著無限制的警句,也無法像詩的意象系統般體現龐大而有機的統一。
所謂截句,顧名思義是截取句子,從小說、詩、散文中截取句子而來,可以是精練的警句,或是美好的意象,特別令人驚豔的句子,或神來一筆的靈光乍現,在在特別提醒人們關注的眼神。
截句在形成上,可以截取某首詩中的特別有趣或有意義的句子,也可以是再創作的四行小詩,也許是一個景觀窗,也許是一小塊視角,也許是新鮮的,也許是一首詩中重要的眼睛,如古人所謂的詩眼,從煉字或煉句所產生的特有的句子,可以有題目,也可以沒有題目。
《蕓朵截句》一書內容的來源,有些是從已經發表的詩中截取一、二個句子,或是某些特殊的句子,某個有趣的意象,或是一小段精緻的情感,這些沒有題目,只有號碼,而沒有題目,就以另一種留白的方式給讀者想像空間,但也有的詩就是四句以內的小詩,這些詩則是針對題目,書寫完整的內容。
有曾經發表過的,有今年新作,也許是完整的,自成一個完整體系的四句小詩,或是無題而根據心情隨手拈來的句子,有一行,二行,三行,四行,最多不超過四行。
在詩集中,我以數字編碼,從N0.01到N0.106,沒有特別的意義,採用隨機性的次序,因此,讀者在閱讀時,也是隨性的,不必從第一頁翻到最後一頁,可以隨著閱讀者的心情,隨意翻開你想要的任何一頁,翻開任何時候的任何心情,只要讀者高興開心就好。而詩句旁邊的照片,無論是書法還是照片,都是一種暗示,也是給讀者多重的想像。
詩,給人越多的解讀空間越好,每個人閱讀一首詩時,都可以從個別的角度出發,無論是歧義性、多元性或複雜性,都足以更強烈地造就一首詩的豐富內涵。這就像羅蘭巴特的理論中提到的:「作者已死。」當作者的面目模糊時,讀者的身分就突顯出來。
所以,截句也許只有四行以內,也許表面上看起來僅僅是一個意象,但或許從意象上能看出不同內涵,不同指向,不同的暗示,或是不同的意味。像是一顆鑽石,旋轉一下,從不同角度都可能綻放出七彩光芒。
這種隨意性,是此本書想要傳遞的訊息。
因為截句之後,如果原作是母本,截句就像是與母體分離後的小孩,自然有獨立的生命體。這個生命體可以自由呼喊,自行分裂,自由想像,自己長成自己的樣子,甚至規劃自己未來的容貌,這是我對於截句未來長大之後的幻想。
而這個幻想由作者提出,拋出一個球,接著由讀者接住想像的球體,開始進行讀者的閱讀想像,當作者已經提出該有的目標之後,讀者就是完成目標的人。每一個讀者拿到詩集,閱讀詩句的當下,都在重新組合並創作屬於讀者本身的截句情節。而每一個讀者在翻閱的過程中,每次的次序都是隨機性的,每個隨機性都是閱讀的一次完成。舉例而言,如果你隨意翻開,看到以下的詩句:
每顆青春痘
都只有一次春天
這二句詩,看起來是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句子,但是,你可以自行想像前面的情節,也許青春痘的主人是青少年,或是中年人,也許男,也許女。而當他/她面對自己的青春痘時,也許是痛惡的,因為年輕,太多青春冒出的熱情,滅火猶且不及,那有時間浪漫聯想?也或許,年歲大些,也許過了沒有青春痘的年紀時,那麼,春天就是一種回想、懷念與感歎。歲月是多到可以虛擲的,或是開始感到有那麼一點時光匆匆的感嘆,也或許你只是莞爾一笑,覺得有道理,然後笑著再翻開下一頁?
青春痘的前面,由讀者完成,青春痘的結局,也是讀者。
截句沒有特殊的人稱,特別的限制,或是特別引導你必須跟著它走,也不用順著作者的意念,找到詩中的主旨,它是一種隨機隨意性的閱讀,也是一種率真隨性的詩樣心情。
所以,讀者才是想像的主體,也是詩的真正完成,把作者放到隱形的區塊去吧,讓讀者自行決定閱讀的順序,想法,意象,讓讀者自行決定他的閱讀,讓讀者成為主體。
但話說回來,除了讀者,換個角度看看作者的立場。
對我而言,前述對於截句的體會之外,還可以再說一件事,如果我把這樣的隨機性看成隨機後的有機,所有的數字號碼連成一氣,成為一首長長長長的詩,而這首詩是由一百多首小詩組成,這樣看來,又是什麼?
這首詩,就是我今年寫的最長的一首詩。由最短的句子,最短的詩組成,一首今年前半年思考的總結。
截句之外,我從作者的角度再反思,詩作有新有舊,書法是新寫成的,照片從手機裡翻找,有些是以前拍的,有些是這半年拍的,書法作品的部分是央請愛好攝影的李子文同學拍攝,師生倆人,在假期的校園裡尋找拍攝的背景,隨著陽光的明滅,不斷搬移作品的位置,與光影追逐,順著光,隨著光蹲低或爬高,我們在自然光線的照映下,留取最美好的角度。那是這詩集出版前一段甜美的小曲。
為了截句,我將自己調整成一條短短的小蟲,腦袋裝的是小小的意象,小小的情境,小小的情敵或是小小的愛情,小小的思維不去建構大的有機組合,小小的詩意與小小的詩味,像是小小趣味的截取,偶然的遇見,就是瞬間的愛戀,沒有過去,沒有未來。
這種小趣味的美學,像是晚明小品。不問過去來由,不問未來去處,就在當下,我們享受一下西湖的美景、明月的光芒、清晨的露珠,也是如此,截取的小趣味不必過度思考過度的偉大建構,凡是靈光乍現的,都歡迎。
所以這半年的寫作,彷如在寫一首長詩,是我,也非我,是詩,也非詩。有時歡喜有時悲,有時簡單有時複雜。若想成是一段記憶,一段心情描述,一段生命的計算方式,那便是了,是蕓朵2017年上半年的寫的一首長詩。
於山實齋,20170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