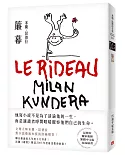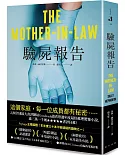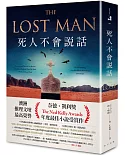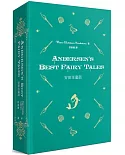作者序
里斯本有一定數量的餐館是這種型態的:在某一家外觀體面的酒樓上,有一間標準的餐廳,它有著鐵路不通的小鎮餐館特有的堅實感和家常風味。這些二樓餐廳,除了星期天,顧客寥寥無幾,你總能遇到一些相貌平平的怪人,那些生活舞臺的配角。
有一段時間,我手頭拮据,又想圖個清靜,便成了某家這類二樓餐廳的常客。每當我在七點左右去那裡用餐時,幾乎總能看到這樣一個人,起初他並未引起我的注意,後來我才開始對他產生興趣。
他個頭很高,身材相當瘦,大約三十歲。他坐著時背駝得厲害,但站著時沒那麼明顯。他衣著隨便,但不完全算是不修邊幅。他那蒼白無趣的臉上,露出一種飽受磨難的表情,看不到任何趣味,也很難說那種表情暗示著什麼樣的磨難。它似乎暗示著各種磨難:艱難困苦、焦慮煩惱,以及飽經滄桑後的波瀾不驚。
他總是吃得很少,飯後抽一枝自己捲成的紙菸。他大膽觀察著其他顧客,談不上有什麼疑惑,而只是出於超乎尋常的興趣。他並未細細打量他們,似乎只是興致使然,無意要分析他們的外在行為或記住他們的外貌體態。正是這點特徵使我對他感興趣。
我開始更密切地觀察他。我注意到,某種才氣以某種模糊的方式使他的容貌變得生動起來。但沮喪——冷淡苦楚的鬱積——始終籠罩在他的臉上,所以很難再從他臉上看到什麼其他特徵。
我偶然從餐館的一個服務生那裡得知,他在附近一家公司工作。
有一天,樓下的街上發生了一件小事——兩個人在互相毆打。二樓餐廳的每個人都跑到窗邊觀看,包括我和眼下正描述的這個人。我隨口和他說了幾句話,他也同樣附和了幾句。他的聲音遲疑不決、平淡無奇,彷彿因完全沒有指望而變得萬念俱灰。然而,我這樣看待我的晚餐同伴,或許是荒謬的。
不知道為什麼,從那以後,我們就互相打招呼了。後來有一天,或許因為可笑的巧合,我們都遲至九點半才去吃晚餐,竟因此而隨便聊了起來。在某個適當的時刻,他問我是否寫作,我說是的。我提到了最近剛出版的文學評論雜誌《奧菲歐》。他不僅稱讚,而且是高度讚賞,這令我大為吃驚。我告訴他,我很吃驚,因為這本雜誌的撰稿者只對少數人說話。他說,或許他就屬於少數人之一。此外,他補充道,這種藝術對他來說並不完全新奇。他羞怯地說,由於沒有地方可去、沒有事情可做、沒有朋友可拜訪,也沒有興趣讀書,他晚上通常就待在家裡,在他的租屋裡,寫點東西來打發時間。
XXX
他的兩個房間放置著表面奢華的家具,無疑地,不能不為此犧牲某些基本物件。他頗費心思地挑選有著柔軟舒適坐墊的座椅。他同樣精選了窗簾和地毯。他解釋說,這樣的室內設計使他能夠「為單調生活保留尊嚴」。在現代風格裝飾的屋子裡,單調生活變成一種令人不安的東西,一種身體不舒服。
沒有什麼東西驅使他去做任何事情。他獨自度過自己的童年,從未參加任何團體,也沒有修什麼課程,從不屬於任何群體。他的生活環境有一種奇怪但又普遍的現象——事實上,或許所有人的生活環境都是如此——按照他的惰性和逃避傾向,被剪裁成本能的畫面和相似物。
他從來不必面對社會或國家的需要。他甚至逃避自己本能的需要。他從來沒有動力去交朋友或談戀愛。在某種意義上,我算是他唯一的知己。但即使我總是假設自己與他有什麼關係,他也未必真正把我當成朋友,從一開始我就知道,他需要託付一個人來保存他留下來的這本書。起初,我覺得很難做到,但我現在很高興能夠從心理學者的觀點來看問題,盡可能將自己當作他的朋友,致力於完成他將我拉進來的目標——出版這本書。
在這方面,客觀環境看來竟然對他有利,因為有我這種性格、對他有用的人,出現在他的身邊。
推薦序
書寫的極限—佩索亞與散文藝術
佩索亞雖被稱為詩人,然他最常被討論的卻是《不安之書》(又名:《惶然錄》),一種界於散文與詩的奇書。他常將自己稱為散文作者,並在書中談到散文的藝術,許多年來這本書是我的隨身書,並用毛筆抄寫過無數遍,常在抄寫時落淚,他是如此空無,又是如此溫柔,文字像飄散的音符具體降落在眼前,或像一陣細雨飄落原野,或是不斷捲來的海浪,讓人如睹其人,既透明又玄妙,他的心靈朝你開放層層展開,結合東西方哲思,介於紀伯倫與特拉克爾之間,與其說是神秘主義者,不如說具備先知氣質的創作者,他創造了一個多重分身的異名者,如百年後《駭客任務》中的電腦自由穿梭者與《全面啟動》的多重創傷者,或是同時擁有許多帳號與假名的現代人,他是他所描述的詩人的最高層級「具備罕見的智力能夠超越自身(depersonalise),
同時又有足夠的想像力可以活出那些與他自身全然不同的心靈, 使作品中有多元的聲音。」,他的書寫沒有開始沒有結尾,亦沒有邊際,讓我們幾乎觸及書寫的極限。
有關他的異名者書寫及思想已被討論太多,很少人論及他對散文的看法;「散文」這在西方文學中一直被忽視的文類,他卻一再提及散文的重要性與寫作方法,甚至細膩地談到文字的運用:
大致來說,我與自己寫下的散文幾乎一致……我使自己成為書裡的角色,過著人們從書裡看到的生活。我的一切所感都只是感覺(與我的意願背道而馳),以便我能記下我的所感。我的一切所思都立刻化為詞語,混入擾亂思想的意象,排成別樣完整的韻律。經過這麼多的自我修訂,我毀掉我自己。經過這麼多的獨立思考,我不再是我而是我的思想。我探測自己的深度,並放棄這種探測。我終其一生想知道自己是否深刻,唯有用肉眼來探測——像井底幽暗而生動的倒影——映出我那張對自己的觀察進行觀察的臉。(第一九三篇,一九三一年九月二日)
自己與散文一致,也就是忠實紀錄自己所思所感,並探測自我的深度。散文家是對自我探索有著狂熱欲望的人,他對自我是什麼,自我投射出的人事物特別敏感,是對任何小節都不放過的人,然散文家書寫的「我」與現實的我有著辯證關係,過去在「載道」傳統下書寫的我是神聖化的我;而在現代「獨抒性靈」的要求下出現的我是魔鬼性的我或異己者,散文作者已失去了神聖性,日趨低下,這時佩索亞提出深刻、空我、多次元的我,這已擴大了散文視野與可能性,「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幾個,是一些,是極大數量的自我。所以,那個鄙視周遭的自我,不同於那個在周遭中受苦或自得其樂的自我。我們的存在是一塊遼闊的殖民地,由不同種類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和感知。」(第三九六篇),如此散文能書寫得更寬闊,它像是無限增生的黑洞或蟲洞,讓創作者向內探索,上天入地,並化入人群。
在文字使用上,他主張避開一般人會使用或過於正常的句子,用字必須準確地表達所感,如描寫一個男性化的女人,一般人會使用「這女孩的動作像個男孩。」、「這女孩是個男孩。」或者「那個男孩。」;他會使用「她是個男孩。」這樣的句子,因為這樣更是違常的,用字要說得更準確,更絕對,更直觀,超越常規、共識和平庸。他對文字的要求是讓語詞更具思想的明確性:
如果我想說我存在,我會說:「我是。」如果我想說我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而存在,我會說:「我是我自己。」但如果我想說我作為自我演說、自我作用的個體而存在,行使自我創造的神聖功能,我會把存在變成及物動詞。如果要達到宏偉壯麗、超越語法的至高境界,我會說:「我存在。」我在這兩個詞裡闡釋了一種哲理。這難道不比那些滔滔不絕的空話更可取麼?從哲學和措辭裡,我們還能有什麼更多的索求呢?
清晰的思考,必須有精確的文字作載體,才能產生力度,然文字的精確是在反覆推敲下的有層次且非凡的語言,如此它的穿透度更高,如在玉壺中的冰心,透出瑩徹的冷光。只要你進入他的文字,很快被感染,如此冷冽又溫柔的穿透力少有人及。
佩索亞的文章跟他居住的里斯本息息相關,如同卡繆的北非與波特萊爾的巴黎,想像那條朝著冰藍大海如對遠方傾倒的斜坡大街,似乎有股引力帶人到不可知的遠方,並在遠方魂飛魄散,自我太渺小,只能分化為幻影,而這城市如海市蜃樓,藝術與人生並置在同一條街上,或者天堂與地獄同在,沒有衝突,如山坡那頭行走於斜坡之頂紅色的電車,穿黑衣披黑頭巾的婦人撫琴唱著「法朵」,擁擠的或黃或白建築物與咖啡店,這是一個色彩明亮與黑暗交織的城市,詩人藏身於其中一個小房間,想像整個城市都是他,而他是空的舞臺,讓分身A、B、C、D……自由穿梭,不斷對著大海低語:「在我的內心中,有著何等的地獄、煉獄和天堂啊!可誰能看到,我所做的一切都與生活相悖——我,是如此平靜,如此安詳?」這樣一個用自身的全部來寫作的創作者,怎不動人肺腑?!
周芬伶/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