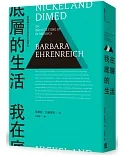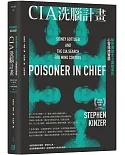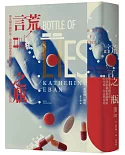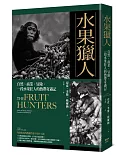推薦序
勝者為王敗者寇:《鋅皮娃娃兵》的悲劇
在這網路橫行的時代,「記者」行業已不再像過去沒有網路的日子那般受人尊敬。不久前,我看到一則網路笑話。一位媽媽嚴厲地對著自己的孩子說:「如果你現在不好好唸書,將來就去當記者。」不知為何,光這句話足以讓我和身邊的朋友笑了很久。近年來台灣平面新聞記者與播報人員的專業水準普遍下降甚鉅,
經常隨意擷取網路上三人成虎的消息,未經查證就直接播報,或是錯別字錯得十分離譜,或者訪談時提出令人傻眼的問題,上述問題比比皆是,不但令人無法信任,有時更讓人啼笑皆非。
2015 年秋天,當瑞典皇家學會宣布當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為斯維拉娜˙亞歷珊德羅夫娜˙阿列克謝耶維奇(Светлан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Алексиевич, 1948-)
時,著實「攪亂」了俄國文壇一池春水。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創作慣以新聞文體和紀實報導形式呈現,文本常用第一人稱敘述者陳述,用字遣詞往往以口語為表達形式,擅用強烈情緒的修辭色彩,故事情節緊貼著重大歷史與政治事件,在傳統已至當代的俄國文壇與發展中既非主流,亦不為當今的俄語讀者熟知。為此,2016 年 7 月當代著名的俄國女作家托爾斯塔雅(Татьяна Никитична Толстая,
1951-) 在自己的新書發表會上甚是吃味地批評諾貝爾獎,認為現在這個獎項玩著政論題材的遊戲,得獎的首要考量是政治與政論體裁,而且是大聲者贏,全然忘了有文學這麼一回事。她更批判阿列克謝耶維奇所寫的形式與內容,純粹是使人(受訪者與讀者)擠出眼淚,而不是文學,如此創作甚至連藝術都沾不上邊。然而讀者須知,托爾斯塔雅是蘇聯著名作家亞歷塞伊˙托爾斯泰(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1883-1945)的孫女,父親又是獲史達林獎而名滿蘇聯的物理學家,她誕生在一個捍衛蘇聯政權的知識分子家庭中,與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政治立場兩極對立。
不可否認地,過去一個世紀以來六位以俄語創作的諾貝爾文學得獎主,除了蕭洛霍夫(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Шолохов, 1905-1984),以及敢寫卻不敢離開蘇聯的巴斯特納克(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
1890-1960)之外,當中就有四位是膽敢公開站在政權與官方對立面的作家,包括阿列克謝耶維奇,但她是這六位中的唯一女性。對於托爾斯塔雅這樣成名甚早且始終受到體制眷顧的文壇寵兒而言,較難明白當一個人決定要在震耳欲聾的權威聲音中以一枝孤獨的筆對抗集體的強權需要多大的勇氣,及其背後的價值意義何在。所謂「文學」,並非僅是俄蘇學術圈內,雄霸的形式主義文藝所讚揚的創作而已,也不是只有語言符號編織而成的、華麗宏偉又才氣縱橫的藝術境界。在後結構、後殖民、後共產與後女性主義一再被提及的二十一世紀,天花亂墜的語言、眼花繚亂的符號與五花八門的理論,只有更多沒有減少。此時,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字裡行間再度透露著最基本的人文精神與傳統人道主義,似乎相當不合時宜。同時,她在作品中強調為下一代追求真相與探索真理(правда)的「信念」,在普丁主政下的俄羅斯風雲再起之際,顯得愚笨,既逆勢逆耳又格格不入,套用托爾斯塔雅的話語:「阿列克謝耶維奇以一種粗糙不精緻的方法創作,猶如殺雞使用牛刀(как
серпом по яйцам,直譯應為「用鐮刀切蛋」)。」追查過去的真相並教育下一代真理的信念對當今的俄羅斯並不重要,因為它被認為導致了蘇聯的滅亡。重要的是,俄羅斯現在因為一位強有力的領導者而再度團結起來這一事實。更何況五連任的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Лукашенко,
1954-)是普丁的重要政治夥伴,亦是俄羅斯企圖回到蘇聯時期強盛的重要憑恃。因此,可以想見,以華麗詞藻、用字遣詞精雕細琢聞名,聰明又才氣縱橫的托爾斯塔雅才是官方力捧的俄羅斯文學主流。
然而,追求最精緻的語言往往因為雕琢過度,失去原本人類本/該有的情感溫度。初見阿列克謝耶維奇創作的讀者,往往受限於自身的閱讀習慣與文化,對以一手口述資料說故事的形式是否真具有文學性產生懷疑。然而,如果我們能耐心地坐下來,靜靜地閱讀,甚至是聆聽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中每一位「我」的自白、告白與祈求,他們的聲音在過去強者撰寫的歷史上只屬於空白。在「莫斯科不相信眼淚」的蘇維埃強權之下,弱者與失敗者不被同情,所以「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在嚴峻的氣候與政治環境,與內亂、外患不斷,戰爭頻仍的國家裡,
不啻是斯拉夫民族生活的金科鐵律,更是生存法則。在蘇維埃家庭教養與國家教育體制內,這個曾經打敗拿破崙與希特勒的偉大民族是無法示弱和承認失敗的。他們崇尚陽剛,渴望強權,這是他們賴以為生、保家衛國的方式。《鋅皮娃娃兵》一書,細數這些教養與教育下的蘇聯男孩子,因為集體地過度輕信國家與民族自尊心無限膨脹,而毫不猶豫地投入阿富汗的戰場。為國捐軀者,獲得一具外殼鍍鋅的棺材,故被作者稱為「鋅皮娃娃兵」,但那些少了雙腿或胳膊的,縱使在世,
也因蘇聯-阿富汗戰爭(1979-1989)的失敗而無法獲得社會廣大群眾的尊敬,成為了沈默、無助又抬不起頭的一群弱勢團體。
阿列克謝耶維奇為這些社會弱勢與失敗者記錄,讓他們的聲音能為世上其他人,甚至是下一代人聽見。即使這些第一人稱敘述者的口語使用的語言有多麼平凡,而髒話與詛咒頻繁地掛在嘴中,但是這些聲音內含諸多情緒,需要他人理解,
更待世人共感。同時,這些口述紀實或嘲笑、或控訴、或回憶、或懺悔等,《鋅皮娃娃兵》揭露了戰爭的殘酷,死亡的恐懼,真相的無情,以及社會的涼薄。閱讀與觀看蘇聯歷史、文學、紀錄片與政治電影時,在官方鼓吹的激昂戰鼓聲中,我們容易震懾於偉大的善惡兩極,是戰爭與和平的起因。然而,若能安靜傾聽阿列克謝耶維奇作品中每位、甚至是一弱者的懇求與禱告,這些聲音一開始會細微地鑽入我們的腦海中,然後久久縈繞不去。接著猶如擴大機一般,這些細微的聲音在心中不斷放大而產生了不停質疑的聲音。對於戰爭前因後果的思索與人性的探究,對於人道-人之所以為人,而非超人或神人-的理解,在於我們有共通的感情,但是對於「感情」的細緻討論,卻是蘇維埃教育中較為缺乏的。然而,
正是這種共通情感透過阿列克謝耶維奇的紀錄文字激發了我們的良心,折磨著我們的心靈。使我們不能輕易地放過自己,將戰爭的一切簡化為僅僅是善與惡、勝與敗、王與寇的對立與對決,然後假裝看不見就將歷史這一頁掀開過去,最後失去對人文精神和人道主義的信任與信念。
蘇聯-阿富汗戰爭肇因於由蘇聯扶植的第一任阿富汗民主共和國的領導人塔拉基(Nur Muhammad Taraki, 1917-1979),也是蘇共黨書記勃列日涅夫(Леонид Ильич Брежнев, 1906-1982)在莫斯科大學時的學弟,在 1979 年 9 月慘遭其副手阿明(Hafizullah Amin,
1929-1979)的毒手。政變後,由曾經留學美國的阿明取代了塔拉基的地位。雖然在蘇聯解體後不少秘密檔案釋出,在在證實了當時勃列日涅夫對於塔拉基的死深感難受,然而阿明上位後公開表示離蘇並親美的傾向, 阻礙了蘇聯在阿富汗的利益,才是導致蘇聯出兵最主要的原因。因此,勃列日涅夫在當年年底簽署了進軍阿富汗的決議, 暗殺阿明並支持親蘇的卡爾邁勒(Babrak Karmal,
1929-1996)上台,引發阿富汗內戰。蘇聯為確保卡爾邁勒政權穩固,只得增兵,大規模壓制反對勢力。勃列日涅夫當時躊躇滿志,原以為可以在一個月內解決阿富汗內戰問題,鳴金收兵,未料反政府軍受到美國資助,將蘇聯軍隊捲入游擊戰中。蘇軍為求快速勝利,報復游擊隊的方式往往是將整個村莊夷為平地,因此爆發阿富汗全民聖戰,致使蘇聯此後十年必須耗費三至十萬不等的作戰部隊在阿富汗長期駐紮,死傷達百萬人之多。
然而,上述這些死傷人數的數字與蘇聯軍隊報復阿富汗人民的手段等史實, 卻從未在蘇聯主流媒體上被揭露。讀者可以從《鋅皮娃娃兵》中明白,蘇維埃政權編造了多大的謊言讓人民相信,蘇聯派軍入駐阿富汗是基於兄弟情、國際主義的目的,幫助對方造橋鋪路,建立起社會主義國家。就在 1986 年 7
月蘇聯尚未解體之前,如阿列克謝耶維奇在前言中寫道,她突然驚覺這場戰爭已經無聲無息地進行七年。但境內人民除了偶爾從電視實況轉播中得知一些敘述英雄事蹟的消息之外,對戰爭本身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卻全然不知。而國家竟然能讓這場戰爭的諸多參與人沈默,而且沈默了這麼久!阿列克謝耶維奇就在眾人皆信/醉時她獨醒,遍訪蘇聯各地參與過這場戰爭的見證人與受難家屬,以記錄方式寫下他們的經歷與見聞,試圖喚醒大眾,歷史是可以建構、宣傳與說謊,特別在共產政權之下。
「不容青史盡成灰」是身為記者的阿列克謝耶維奇抱持的信念,也正因這一職業使後來成為作家與紀錄片導演的她相信,挖掘真相、探索原因、追求真理並改變社會是極其重要、極富教育意義的。而這些信念與信仰,從十九世紀以來一直為俄羅斯作家與文學作品所彰顯,與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文以載道」有異曲同工之任重。儘管她的作家同儕或是同胞都認為,時代不停在改變,回首過去意義不大,展望未來才是希望,然而輕易將過去歷史放下、得過且過的人,不但縱容自己在思考上的懶惰,也是任由獨裁極權與戰爭悲劇一再發生的同謀者。《鋅皮娃娃兵》記錄了這些戰爭見證者的心路歷程,除了表達作家的反戰立場、反對任何形式的殺人行為,以及為失敗者與弱者著書的慈悲胸懷之外,更重要的是藉由這些口述資料來告訴並警惕世人,人云亦云、盲目輕信的愛國主義,以及國家至上的保護主義為這個世界製造了多大的災難。多少戰爭與罪惡假這些冠冕堂皇的名稱以行之?
於是,阿列克謝耶維奇無法沈默,即使她完成了《戰爭中沒有女性》(У войны не женское лицо,
1985)一書之後,宣稱她已心力交瘁,對於人間的諸多殘酷不忍卒睹,沒有辦法再寫關於戰爭的書了。可以想像,她再提起筆寫《鋅皮娃娃兵》需要極大的勇氣,而這勇氣包含著斯拉夫民族堅毅的性格,更具備了傳統俄羅斯文學對道德良心的堅持與信仰。她無懼威權的恫嚇、威脅與旁人的冷嘲熱諷,也不管世界如何在變,依然堅持走自己的道路,始終如一。
在這網路橫行的時代,資訊發達的世界,人們「知」的範圍與權利比任何時代來得更廣泛充足。然而,或許正因為得來過易、快速且人云亦云,我們其實某方面同新聞從業人員一樣,競爭效率而失去了挖掘真相的信念,觀看表象卻沒有探索原因的耐性。因此,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得獎,為新聞從業人員注入一劑強心針,鼓舞了不少記者重新審視進入這一行業的初衷,而非僅在意收視率的勝敗,
抑或誰王誰寇的結果。至於追求真理,或許會有不少人問,那是什麼東西?儘管如此提問使人沮喪,然而,如同阿列克謝撰寫《鋅皮娃娃兵》的目的一樣:就算以孤筆抗強權猶如以卵擊石,吾往矣!即使在最極權黑暗的時刻,身為記者與作家且被政治迫害的她也沒有絕望過,吾人又有什麼悲觀的權利?阿列克謝耶維奇其人及其創作,正是這個知識爆炸時代最缺乏的,也是這個資訊發達的世界最迫切需要的另類聲音,值得讀者閱讀,再三思考。
陳相因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