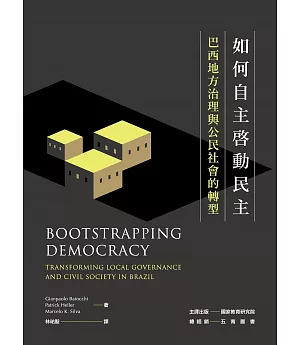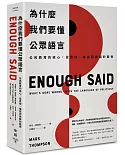前言
我們並不打算寫一本關於民主如何被啟動(bootstrapping)的書。正確地說,我們想探討參與式預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
PB)這個參與式民主的知名例子,而且在實證的層次上檢驗它。這個檢驗最重要的是檢視那些發生在文獻預測上看起來不會發生的地方,但卻獲得成功的參與式預算個案。起源自1980年代晚期的巴西,參與式預算是一種理念,認為民眾可以而且應該在他們所居住的城市中的預算制定扮演直接的角色。雖然這個理念非常簡單,但是魔鬼卻藏在實際運作的細節裡。我們發現參與式預算帶來不同的結果,而本書試圖整理這些結果,並且利用這些發現,具體地指出建立參與式民主的地方制度的可能性與面對的挑戰。回顧起來,在所有我們的發現裡,最讓人驚訝的就是在地行動者在設計不同的參與式預算模式時,展現了高度的創造力與聰明才智。在這些個案中,我們發現名符其實的參與式預算模式被建立,在地行動者與國家部門(行政人員、政治人物與技術官僚)熟練地採取一個廣泛流傳的國家「藍圖」,並且根據在地的情況加以改造。在描述這個現象時,我們的經驗是最好能夠用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用詞來指涉它。「啟動」(bootstrapping)在英文中代表運用少量的起始資源而達成較大與重要的成果,在資訊工程中,這個名詞意味用一個小程式乘載(「啟動」)一個作業系統。1在商業裡,這個名詞代表運用低額的創業基金的企業家精神。在薩伯爾(Charles
Sabel)(2004)所運用的發展理論中,這個名詞被當成一個比喻,用來指涉建立一個有能力持續調整制度的過程,「在此制度中,每一個動作都啟發著下個動作」,而這樣的制度也從社會學習中獲益(7)。薩伯爾關切這種利於成長的制度,而且他認為這種具有啟動作用的制度「是發展的結果,也是發展的起點」。(7)
我們借重以上幾種不同用法的精神,特別是把「啟動」看成某種社會學習之動力形式的概念。參與式預算不是某個模型或是藍圖,而是一個由社會運動與過去十年的地方政府實驗者所發展的各種參與式實踐與理念的總和,以及適應在地條件的制度性過程。如同我們所見,啟動民主有著更為擴充的意義,假定某種雙重的能動性:一方面,依照一般的用法,這個名詞代表著問題解決(problem-solving),以及特別是對於如何將在地公民社會納入協調地方政府的工具性回應;另一方面,與一般的用法不同,這是一個讓公民賦權的道德與政治計畫。
可惜的是,由於這是英美特有的詞彙,「啟動」一詞可能會影響我們表達的流暢性。當我們想到這個用詞時,我們的第一個反應是在葡萄牙語中沒有明確的詞彙,可以對應本書所使用的啟動者(bootstrappers)。對於他們,我們感到十分抱歉。我們考慮更多熟悉的拉丁用語,像是「發明」(inventing)、「設計」(designing)與「創造」(creating),但是我們認為這些詞彙在英文中更容易聯想到實驗室、象牙塔、辦公室或工作坊裡不帶感情的觀察者,而不是巴西城市中的地方政治的競逐場域。巴西的用語“dar
um
jeito”(就是「找個方式」的意思)正確地捕捉思想創新的意義,但是卻有些貶意而且強調非正式的部分。我們想要某個名詞,既能觸及潛能,又能涵蓋建立民主制度無可避免的混亂、衝突、策略計算與原則性的實用主義。在我們的用法中,特意不只強調為了讓參與式預算運作的新方式與設計,我們也關注新的結盟,巧妙地讓國家與公民社會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不清,而這是真正的參與所不可或缺的。確實,我們發現的是,對於參與式預算建築師的最為重要之物,正是在「把公民社會帶進來」以及保存公民參與的自主邏輯與能量之間找到正確的平衡。
環境如何引導由下到上的民主深化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的相關性更是不僅限於拉丁美洲的「粉紅浪潮」(pink
tide)國家。正是這個原因,我們想要一個強調面對困難時的能動性的書名。從我們的觀點來看,社會科學最讓人挫敗的診斷,就是斷定民主的賦權必須存在某些先決條件,而這些先決條件都是來自對於西方民主國家的發展軌跡的考察。而在事實上,我們也可以指出過去二十年絕大多數的民主創新,都是發生於「低度發展的民主國家」中。而且,儘管本書裡的故事並非建立參與的藍圖,也不是從外部所造成的改變(其實恰好相反),這些故事讓我們對可能的情況有更廣的想像,包括一個從南半球出發而向北半球傳遞的想像。畢竟,用社會理論家同時也擔任過巴西部長級官員昂格爾(Roberto
Unger)的話來說,有意義的社會變遷就是「粉碎脈絡」(context-smashing)的改變。2
本書從思索與研究設計開始,但是本書的完成,包括讓學術研究變成一個探索的過程,有賴許多人大大小小的幫助,因此無法在此一一就他們提供的幫助致謝。在機構方面,我們獲得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Rio Grande do Sul的聯邦大學(Federal University)、華生國際研究中心(Wat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與巴西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Brazilian National Council on Scientific Research, CNPQ)的支持,並從世界銀行(World Bank)得到慷慨的經費。所有的研究因為我們在巴西的非營利組織夥伴而變得可能:愉港(Porto Alegre)的CIDADE、聖保羅(Sãn
Paulo)的POLIS以及勒希非(Recife)的ETAPAS。個別的市級行政官員在適當的情況下接受我們的訪問,而訪問有時要花上好幾個小時。巴西的研究團隊,包括Ana Neri dos Santos、Charice Barreto Linhares、Cristiane Vianna Amaral、Daniela Oliveira Tolfo、Georgia Christ
Sarris、Isabela Valença Vaz、Roberto Rocha Coelho Pires、Tatiana de Amorim Maranhão,他們用完美的專業主義與固執的決心完成他們的工作。
我們獲得許多來自學術界的幫助。我們主要的幫助來自於喬德胡理(Shubham Chaudhuri),他協助這個計畫的發展,在他因為工作所需離開之前,與我們在計畫早期有所合作。他將城市配對的想法在巴西的小型家庭工業(cottage industry)滋長,我們原本也希望能在研究的後期仰仗他的能力。我們也要特別感謝伊凡斯(Peter
Evans),他參與了這個計畫的每個階段,以及史丹佛(Stanford)大學的編輯Kate Wahl所提供的支持與深刻的建議。我們的手稿從Phil Oxhorn、Michael Walton、Rush Alsop與André Herzog之處得到許多有用的意見,他們在研究早期給予我們反饋,而我們特別受益於Michael
Walton對於本計畫的支持。一路下來,我們從非常多的同事得到深具洞見的評論與建議,像是Dietrich Rueschemeyer、Richard Snyder、Sonia Alvarez、Jeff Rubin、Millie Thayer、Agustin Lao Montes、Vijayendra Rao、Adrian Gurza Lavalle、Brian
Wampler、Einaar Braten、Judith Tendler、Christian Stokke、Olle Tornqüist、Jonathan Fox、Leonardo Avritzer、Erik Olin Wright、Archon Fung、Frances Moore Lappe、Sergio Baierle、Regina Pozzobon、Marcus
Melo、Roberto Pires、Peter Spink、André Herzog、Peter Houtzager、Michael Kennedy與John Markoff。我們很幸運在布朗大學與一些很棒的研究生合作,我們特別感謝Diana Graizbord、Esther Herández-Medina和Jennifer
Costanza。如果沒有CNPQ給席爾瓦的博士後獎助,與華生中心給他一年的學術收容,本書的完成是不可能的。
本書第五章所發展之論點的早期版本被刊登在Social Forces(2008)。一些第四章所報告的發現也可以在由史托克(Stokke)、童奎斯特(Tornqüist)與韋伯斯特(Webster)(2009)所編的書中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