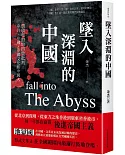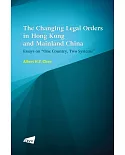二十世紀落幕了。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在歐洲的視角內,將這個世紀界定為從1914年世界大戰爆發至1991年蘇東解體為止、作為“極端的年代”的短二十世紀。與他的看法不同的是,在本書中,作者將中國的二十世紀界定為從1911至1976年的作為“漫長的革命”的短二十世紀——這是一個極端的但同時也是革命的時代。
本書作者論述了中國在這個“短世紀”中的兩個獨特性:第一個獨特性集中於這個“短世紀”的開端,即在革命建國過程中的帝國與國家的連續性問題。第二個獨特性集中於這個“短世紀”的終結,即革命與後革命的連續性問題。全書由10篇論文組成:
1. “亞洲覺醒”時刻的革命與妥協——論中國的“短二十世紀”的開端
2. 文化與政治的變奏──戰爭、革命與1910年代的“思想戰”
3. 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視野下的抗美援朝戰爭
4. 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六十年代的消逝
5. 1989社會運動與中國“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再論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
6. 自主與開放的辯證法——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周年之際
7. 兩種新窮人及其未來──“後階級社會”的階級問題及其尊嚴政治
8. 代表性斷裂與“後政黨政治”
9. 代表性的斷裂——再問“什麼的平等”?
10. 兩岸歷史中的失蹤者──《臺共黨人的悲歌》與臺灣的歷史記憶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汪暉
中國大陸近十年來最受爭議的知識分子、學者,被譽爲新左派領袖,現任清華人文與社會高等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曾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博士後研究、美國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華盛頓大學訪問學者、柏林高等研究所、海德堡大學研究員。汪暉目前研究工作集中於現代中國思想的研究。
主要著作有:
1. 《去政治化的政治:短二十世紀的終結與九十年代》
2. 《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四卷本),增訂版2008
3. 《死火重溫》
4. 《亞洲視野:中國歷史的敍述》
汪暉
中國大陸近十年來最受爭議的知識分子、學者,被譽爲新左派領袖,現任清華人文與社會高等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曾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博士後研究、美國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華盛頓大學訪問學者、柏林高等研究所、海德堡大學研究員。汪暉目前研究工作集中於現代中國思想的研究。
主要著作有:
1. 《去政治化的政治:短二十世紀的終結與九十年代》
2. 《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四卷本),增訂版2008
3. 《死火重溫》
4. 《亞洲視野:中國歷史的敍述》
目錄
1“亞洲覺醒” 時刻的革命與妥
-----論中國的”短二十世紀”的開端
一、中國的短二十世紀:兩個獨特性
二、革命與連續性的創制
三、帝國與國家、北方與南方
四、民族自決與”落後的北方”
五、三種政治整合:議會多黨制、行政集權與革命建國
33文化與政治的變奏
-----戰爭、革命與1910年代的”思想戰”
序論:”覺悟”的時代
一、從”文明衝突”到”文明調和”
二、洪憲帝制、政體危機與”新舊思想”問題
三、調和論與二十世紀新(舊)文明
111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視野下的抗美援朝戰爭
一、”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有利”: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條件
二、人民戰爭轉向國際主義聯盟戰爭的政治意義
三、並非結論:停戰體制與去政治化條件下的戰爭
161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六十年代的消逝
一、中國與六十年代的終結
二、去政治化的政治與黨國體制的危機
三、去政治化的政治與現代社會
四、霸權的三重構成與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識形態
231 1989年社會運動與中國”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
------再論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
一、1989年社會運動的歷史條件與”新自由主義”的反歷史解釋
二、1990年代的三個思想階段及其主要問題
三、為什麼從現代性問題出發
305自主與開放的辯證法
-----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周年之際
一、獨立自主及其政治內涵
二、農民的能動性
三、國家的角色
四、主權結構的變異
五、政黨國家化的悖論
六、金融危機還是經濟危機
329兩種新窮人及其未來
-----階級政治的衰落、再形成與新窮人的尊嚴政治
前言
一、新窮人與新工人的誕生
二、不確定的主體:農民工、工人階級或新工人?
三、打工短期化、法律維權與政治正義
四、工人國家的失敗與代表性的斷裂
371代表性斷裂與”後政黨政治”
一、全球政治的代表性危機
二、重構二十世紀中國的代表性政治原理
三、“後政黨政治”的條件
四、理論辯論與政黨的”自我革命”
五、人民戰爭與群眾路線
六、階級重組與階級政治的衰落
七、“後政黨政治”與憲政改革的方向
389代表性的斷裂
----再問”甚麼的平等”?
序言:政治體制與社會形式的脫節
一、再問”什麼的平等”?
二、齊物平等與”跨體系社會”
453兩岸歷史中的失蹤者
----《臺共黨人的悲歌》與臺灣的歷史記憶
489當代中國歷史巨變中的臺灣問題
----從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談起
一、兩岸政治關係的危機與統派的式微
二、反服貿運動與反TPP
三、政治認同的至關重要性與兩種規則的衝突
525人名索引
-----論中國的”短二十世紀”的開端
一、中國的短二十世紀:兩個獨特性
二、革命與連續性的創制
三、帝國與國家、北方與南方
四、民族自決與”落後的北方”
五、三種政治整合:議會多黨制、行政集權與革命建國
33文化與政治的變奏
-----戰爭、革命與1910年代的”思想戰”
序論:”覺悟”的時代
一、從”文明衝突”到”文明調和”
二、洪憲帝制、政體危機與”新舊思想”問題
三、調和論與二十世紀新(舊)文明
111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視野下的抗美援朝戰爭
一、”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有利”: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條件
二、人民戰爭轉向國際主義聯盟戰爭的政治意義
三、並非結論:停戰體制與去政治化條件下的戰爭
161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六十年代的消逝
一、中國與六十年代的終結
二、去政治化的政治與黨國體制的危機
三、去政治化的政治與現代社會
四、霸權的三重構成與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識形態
231 1989年社會運動與中國”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
------再論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
一、1989年社會運動的歷史條件與”新自由主義”的反歷史解釋
二、1990年代的三個思想階段及其主要問題
三、為什麼從現代性問題出發
305自主與開放的辯證法
-----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周年之際
一、獨立自主及其政治內涵
二、農民的能動性
三、國家的角色
四、主權結構的變異
五、政黨國家化的悖論
六、金融危機還是經濟危機
329兩種新窮人及其未來
-----階級政治的衰落、再形成與新窮人的尊嚴政治
前言
一、新窮人與新工人的誕生
二、不確定的主體:農民工、工人階級或新工人?
三、打工短期化、法律維權與政治正義
四、工人國家的失敗與代表性的斷裂
371代表性斷裂與”後政黨政治”
一、全球政治的代表性危機
二、重構二十世紀中國的代表性政治原理
三、“後政黨政治”的條件
四、理論辯論與政黨的”自我革命”
五、人民戰爭與群眾路線
六、階級重組與階級政治的衰落
七、“後政黨政治”與憲政改革的方向
389代表性的斷裂
----再問”甚麼的平等”?
序言:政治體制與社會形式的脫節
一、再問”什麼的平等”?
二、齊物平等與”跨體系社會”
453兩岸歷史中的失蹤者
----《臺共黨人的悲歌》與臺灣的歷史記憶
489當代中國歷史巨變中的臺灣問題
----從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談起
一、兩岸政治關係的危機與統派的式微
二、反服貿運動與反TPP
三、政治認同的至關重要性與兩種規則的衝突
525人名索引
序
自序
在1911年革命尚在孕育之中的時刻,1907年,年僅26歲的魯迅在一篇古文論文中,用一種古奧的文風,談及他對剛剛降臨的世紀”的觀察:
意者文化常進於幽深,人心不安於固定,二十世紀之文明,當必沉邃莊嚴,至與十九世紀之文明異趣。新生一作,虛偽道消,內部之生活,其將愈深且強歟?精神生活之光耀,將愈興起而發揚歟?成然以覺,出客觀夢幻之世界,而主觀與自覺之生活,將由是而益張歟?內部之生活強,則人生之意義亦愈邃,個人尊嚴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紀之新精神,殆將立狂風怒浪之間,恃意力以闢生路也。
魯迅用兩句話概括了他所說的“二十世紀之新精神”,即“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這兩句話中的“物質”指由英國工業革命所引導的“十九世紀物質文明”,即資本主義經濟﹔”眾數”則指由法國大革命所開創的”十九世紀政治文明”,即憲政民主及其議會一政黨制度。魯迅宣稱:”十九世紀”,的創造力在其世紀末已經式傲,自由平等正在轉變為凌越以往專制形式的新的專制形式。因此,正在降臨的新世紀為中國所確定的目標是超越歐洲雙元革命及其後果,建立一個每一個人都獲得自由發展的“人國”。
這是中國歷史中最早的關於”二十世紀”的表述之一。對於當時的中國人而吉,這個概念如同天外飛來的異物,因為在此之前,並不存在所謂”十九世紀”,也不存在”十八世紀”。1907年是光緒丁未年,或清光緒三十三年。光緒是滿洲入關後的第九位皇帝。在魯迅的文章中,作為”二十世紀”對立面的”十九世紀”並非指涉此前的中國歷史,而是由法國革命和英國革命所開創的歷史時代。但對於魯迅而言,只有將”二十世紀”這一異物作為我們的使命,中國才算獲得了”自覺”。為什麼如此呢?因為十九世紀歐洲的”雙元革命”正是晚清中國的改革和革命浪潮所確立的目標。從1860年代起,在兩次鴉片戰爭失敗的陰影下,中國開始了以富國強兵為內容的”洋務運動”;伴隨甲午戰爭(1894)的失敗,這場”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運動直接地轉變為以戊戌變法為標誌的政治改革運動,其內容之一,便是模仿歐洲立憲政治,建立國會,將王朝改變為”國家”。這場政治改革運動的失敗標誌著一個民族革命時代的降臨,在洶湧澎湃的革命浪潮中,共和國正在平地線的另一端漸漸升騰,而推動這個新中國誕生的力量不就是歐洲的民族主義、市場經濟、物質文明和政治體制嗎?因此,即便中國不存在西歐和俄國意義上的”十九世紀”,為了超越晚清改革和革命的目標,”二十世紀”也將是中國的使命或獲得”自覺”的契機。
在這個意義上,”二十世紀”不僅是”十九世紀歐洲”的異物,也是內在於”二十世紀中國”的異物。異物不是一個,而是許多個:倡導”君主立憲”的康有為同時寫作了不但超越他自己提出的”君主立憲”主張而且超越整個”十九世紀”全部內容的《大同書》,呈現了一幅綜合了儒家思想、佛教理念和烏托邦共產主義的世界圖景;激進的民族革命者章太炎用”齊物平等”的思想深刻地批判了”十九世紀”的國家主義、種族主義、政黨政治、憲政民主和形式平等,他本人也成為這場革命運動內部的”異類”;即便是1911年革命的領袖孫文也試圖將兩場對立的革命-即”十九世紀”的民族革命和富強運動與”二十世紀”的社會革命──綜合為同一場革命。如果主權國家;民族認同、政黨政治、公民社會、工業革命、城市化、國家計畫、市場經濟,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教育體制和媒體文化,構成了這一時代中國社會變革的基本內容,那麼,作為異物的”二十世紀”就潛伏於其內部。換句話說,二十世紀中國的大部分變革內容乃是”漫長的十九世紀”的延伸或衍生,但又內在地包含了其對立面和否定物。用魯迅的語言來說,即”二十世紀之新精神,殆將立狂風怒浪之間,恃意力以闢生路也。””意力”表達的是一種能動性,一種超越客觀條件而從事創造的能量,但這種超越客觀條件的創造性能量並不是純粹的主觀性,而是一種將鬥爭目標納入更廣闊範圍的產物。
在中文裏,”政治”的含意取決於句體的語境,但並不存在political與politics之間的嚴格區分。在一個多民族帝國的地基上創建一個單一主權的共和國,同時讓單一主權國家內在地包含了制度的多元性; 通過否定政黨和國家的文化運動來界定新的政治,同時創造出一種區別於歐洲十九世紀的政黨和國家的政治類型;以人民戰爭的形式推進土地改革、政權建設及政黨與大眾之間的循環運動,形成一種具有超政黨要素的超級政治組織,在一個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均未成熟的社會裏推進一場指向社會主義的階級運動,將政治性和能動性展開為階級概念的重要內容......總之,在一個以多民族的農業帝國裏不但發生了階級政治,而且發生了“社會主義革命”,這一現象不能直接從現實條件內部推演出來,毋寧是政治化的產物。 。
2004年,在為《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所寫的序言中,我曾說:”在漫長的二十世紀裏,中國革命極其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社會的基本構成,我們不可能僅僅在”中國”,這一範疇的延續性中說明現代中國的認同問題。我希望今後的研究能夠在這方面提供新的歷史解釋。”我想補充的是:也正是這個世紀將“中國”帶入了一個難以從“過去”中衍生而來的時代,從而任何對於”中國”的界定都無法離開對於這個世紀的解釋。這本論文集就是從《興起》結束的地方開始的,他集中於探索二十世紀中國及其政治過程。在過去十年中,我已經將“二十世紀” 從“漫長的”修訂為“短促的”,其核心部分是從1911年辛亥革命前後至1970年代中期“文革”結束前後的“作為短世紀的漫長的革命”。在這個世紀中,政治化與去政治化是相互糾纏、反復出現的現象,但也可以視為不同時期的主導趨勢。因此,我們不妨從政治化、去政治化和重新政治化的脈絡探索這個世紀的潛力。
我從三個路徑出發思考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化,即政治整合、文化與政治、人民戰爭。這三個主題誕生於革命與戰爭的時代,但又以不同的形式出現於其他歷史時期。政治整合將對國家形式的探索展開為一個政治競爭的過程──這裏所指的政治競爭不僅是不同政治力量之間的競爭,而且是不同的政治原理之間的競爭,從這一激烈的競爭過程中產生的”國家”包含了強烈的政治性,因此,僅僅抽象地說明”國家”或“民族一國家”是無法把握“國家”與政治過程的關係的,持續的文化運動刷新了對於政治的理解,重新界定了政治的議題和領域,創造出一代新人;人民戰爭不但是從根本上改變現代中國城鄉關係和民族認同的政 治動員過程,而且也對我們熟悉的政治範疇如階級、政黨、國家、人民等等進行了改造與重構。離開了政治化的複雜過程,我們幾乎不能歷史地把握這些政治範疇在二十世紀語境中的獨特意義。這三種政治化的過程滲透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方方面面:政治化既體現為激進的革命與策略性妥協的過程,也表現為將青年問題、婦女解放、勞動與勞工、語言與文學、城市與鄉村等等問題納入“文化”的範疇,讓政治成為一個創造性的領域﹔既體現為將軍事門事、土地改革、政權建設、統一戰線融為一體的“人民戰爭”,也呈現為人民戰爭對十九世紀以降的各種政治範疇的轉化,例如政黨與大眾運動之間的邊界模糊了,政權不同於傳統的國家機器,階級成為階級化過程(如農民成為無產階級政治力量),等等。在1950-1960年代,即便在主權概念籠罩之下的國際政治領域,抗美援朝戰爭和中蘇兩黨論戰,也提供了軍事和國際關係領域的政治化案例。
二十世紀的政治創新是與持續的戰爭、革命和動盪密切相關的。伴隨1989-1992年的世界性轉變,由中國革命和俄國革命為標誌的社會主義運動以失敗告終。“短世紀”以這一悲劇性的方式告終為人們理解二十世紀提供了一種否定性的視角,即將政治化過程本身視為悲劇的根源,進而拒絕一切與這個世紀的政治直接相關的概念──階級、政黨、民族、國家、群眾和群眾路線、人民和人民戰爭等等。然而,這些概念在什麼時候、在什麼意義上是政治化的,又在何種條件下趨向於去政治化?以階級概念為例,它在二十世紀的政治動員中產生了巨大的作用,但這種動員包含了兩種可能性:其一,即便在身份或財產權意義上並不隸屬於某個階級,也可以成為某一階級的馬前卒或戰士,如農民或出身統治階級的知識分子成為“無產階級”的主體甚至領袖;其二,階級出身成為僵固不變的制度化的身份標記,成為衡量敵我的基本標準。兩者都可能產生動員,但前者是政治化的,後者卻是去政治化的。再以政黨為例,人民戰爭條件下的政黨與群眾路線有著密切的聯繫,所謂“從群原中來,到群眾中去”,由此產生了巨大的政治能量和活力﹔但在執政條件下的政黨卻常常與群眾相互隔絕,蛻變為一般性權力機器,形成了政黨國家化的現象,亦即政黨的去政治化現象。因此,與許多試圖在這些範疇之外尋找新政治的方法有所不同,我試圖對這些範疇自身及其演變進行分析,從中理解政治化與去政治化的樞紐和邏輯;即便這些範疇全部源自“十九世紀”,我也試圖從中找到內在於它們的異物,因為正是這些異物使得這些舊範疇在特定語境中煥發出巨大的能量。
在同一個意義上,探尋新的政治也不可能離開對於這些異物的解釋。從對文化政治的解釋到對人民戰爭及其演變的思考,從對後政黨政治的追溯到對齊物平等的研究,本書的各個章節就是對於這些內在於二十世紀政治實踐的異物及其可能性的探究。就像布洛赫(Ernst Bloch)筆下的“希望”一樣,作為被壓抑的現實,異物很可能會以新的形態、在不同以往的關係中,作為未來再度出現於我們的時代。
在1911年革命尚在孕育之中的時刻,1907年,年僅26歲的魯迅在一篇古文論文中,用一種古奧的文風,談及他對剛剛降臨的世紀”的觀察:
意者文化常進於幽深,人心不安於固定,二十世紀之文明,當必沉邃莊嚴,至與十九世紀之文明異趣。新生一作,虛偽道消,內部之生活,其將愈深且強歟?精神生活之光耀,將愈興起而發揚歟?成然以覺,出客觀夢幻之世界,而主觀與自覺之生活,將由是而益張歟?內部之生活強,則人生之意義亦愈邃,個人尊嚴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紀之新精神,殆將立狂風怒浪之間,恃意力以闢生路也。
魯迅用兩句話概括了他所說的“二十世紀之新精神”,即“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這兩句話中的“物質”指由英國工業革命所引導的“十九世紀物質文明”,即資本主義經濟﹔”眾數”則指由法國大革命所開創的”十九世紀政治文明”,即憲政民主及其議會一政黨制度。魯迅宣稱:”十九世紀”,的創造力在其世紀末已經式傲,自由平等正在轉變為凌越以往專制形式的新的專制形式。因此,正在降臨的新世紀為中國所確定的目標是超越歐洲雙元革命及其後果,建立一個每一個人都獲得自由發展的“人國”。
這是中國歷史中最早的關於”二十世紀”的表述之一。對於當時的中國人而吉,這個概念如同天外飛來的異物,因為在此之前,並不存在所謂”十九世紀”,也不存在”十八世紀”。1907年是光緒丁未年,或清光緒三十三年。光緒是滿洲入關後的第九位皇帝。在魯迅的文章中,作為”二十世紀”對立面的”十九世紀”並非指涉此前的中國歷史,而是由法國革命和英國革命所開創的歷史時代。但對於魯迅而言,只有將”二十世紀”這一異物作為我們的使命,中國才算獲得了”自覺”。為什麼如此呢?因為十九世紀歐洲的”雙元革命”正是晚清中國的改革和革命浪潮所確立的目標。從1860年代起,在兩次鴉片戰爭失敗的陰影下,中國開始了以富國強兵為內容的”洋務運動”;伴隨甲午戰爭(1894)的失敗,這場”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運動直接地轉變為以戊戌變法為標誌的政治改革運動,其內容之一,便是模仿歐洲立憲政治,建立國會,將王朝改變為”國家”。這場政治改革運動的失敗標誌著一個民族革命時代的降臨,在洶湧澎湃的革命浪潮中,共和國正在平地線的另一端漸漸升騰,而推動這個新中國誕生的力量不就是歐洲的民族主義、市場經濟、物質文明和政治體制嗎?因此,即便中國不存在西歐和俄國意義上的”十九世紀”,為了超越晚清改革和革命的目標,”二十世紀”也將是中國的使命或獲得”自覺”的契機。
在這個意義上,”二十世紀”不僅是”十九世紀歐洲”的異物,也是內在於”二十世紀中國”的異物。異物不是一個,而是許多個:倡導”君主立憲”的康有為同時寫作了不但超越他自己提出的”君主立憲”主張而且超越整個”十九世紀”全部內容的《大同書》,呈現了一幅綜合了儒家思想、佛教理念和烏托邦共產主義的世界圖景;激進的民族革命者章太炎用”齊物平等”的思想深刻地批判了”十九世紀”的國家主義、種族主義、政黨政治、憲政民主和形式平等,他本人也成為這場革命運動內部的”異類”;即便是1911年革命的領袖孫文也試圖將兩場對立的革命-即”十九世紀”的民族革命和富強運動與”二十世紀”的社會革命──綜合為同一場革命。如果主權國家;民族認同、政黨政治、公民社會、工業革命、城市化、國家計畫、市場經濟,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教育體制和媒體文化,構成了這一時代中國社會變革的基本內容,那麼,作為異物的”二十世紀”就潛伏於其內部。換句話說,二十世紀中國的大部分變革內容乃是”漫長的十九世紀”的延伸或衍生,但又內在地包含了其對立面和否定物。用魯迅的語言來說,即”二十世紀之新精神,殆將立狂風怒浪之間,恃意力以闢生路也。””意力”表達的是一種能動性,一種超越客觀條件而從事創造的能量,但這種超越客觀條件的創造性能量並不是純粹的主觀性,而是一種將鬥爭目標納入更廣闊範圍的產物。
在中文裏,”政治”的含意取決於句體的語境,但並不存在political與politics之間的嚴格區分。在一個多民族帝國的地基上創建一個單一主權的共和國,同時讓單一主權國家內在地包含了制度的多元性; 通過否定政黨和國家的文化運動來界定新的政治,同時創造出一種區別於歐洲十九世紀的政黨和國家的政治類型;以人民戰爭的形式推進土地改革、政權建設及政黨與大眾之間的循環運動,形成一種具有超政黨要素的超級政治組織,在一個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均未成熟的社會裏推進一場指向社會主義的階級運動,將政治性和能動性展開為階級概念的重要內容......總之,在一個以多民族的農業帝國裏不但發生了階級政治,而且發生了“社會主義革命”,這一現象不能直接從現實條件內部推演出來,毋寧是政治化的產物。 。
2004年,在為《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所寫的序言中,我曾說:”在漫長的二十世紀裏,中國革命極其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社會的基本構成,我們不可能僅僅在”中國”,這一範疇的延續性中說明現代中國的認同問題。我希望今後的研究能夠在這方面提供新的歷史解釋。”我想補充的是:也正是這個世紀將“中國”帶入了一個難以從“過去”中衍生而來的時代,從而任何對於”中國”的界定都無法離開對於這個世紀的解釋。這本論文集就是從《興起》結束的地方開始的,他集中於探索二十世紀中國及其政治過程。在過去十年中,我已經將“二十世紀” 從“漫長的”修訂為“短促的”,其核心部分是從1911年辛亥革命前後至1970年代中期“文革”結束前後的“作為短世紀的漫長的革命”。在這個世紀中,政治化與去政治化是相互糾纏、反復出現的現象,但也可以視為不同時期的主導趨勢。因此,我們不妨從政治化、去政治化和重新政治化的脈絡探索這個世紀的潛力。
我從三個路徑出發思考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化,即政治整合、文化與政治、人民戰爭。這三個主題誕生於革命與戰爭的時代,但又以不同的形式出現於其他歷史時期。政治整合將對國家形式的探索展開為一個政治競爭的過程──這裏所指的政治競爭不僅是不同政治力量之間的競爭,而且是不同的政治原理之間的競爭,從這一激烈的競爭過程中產生的”國家”包含了強烈的政治性,因此,僅僅抽象地說明”國家”或“民族一國家”是無法把握“國家”與政治過程的關係的,持續的文化運動刷新了對於政治的理解,重新界定了政治的議題和領域,創造出一代新人;人民戰爭不但是從根本上改變現代中國城鄉關係和民族認同的政 治動員過程,而且也對我們熟悉的政治範疇如階級、政黨、國家、人民等等進行了改造與重構。離開了政治化的複雜過程,我們幾乎不能歷史地把握這些政治範疇在二十世紀語境中的獨特意義。這三種政治化的過程滲透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方方面面:政治化既體現為激進的革命與策略性妥協的過程,也表現為將青年問題、婦女解放、勞動與勞工、語言與文學、城市與鄉村等等問題納入“文化”的範疇,讓政治成為一個創造性的領域﹔既體現為將軍事門事、土地改革、政權建設、統一戰線融為一體的“人民戰爭”,也呈現為人民戰爭對十九世紀以降的各種政治範疇的轉化,例如政黨與大眾運動之間的邊界模糊了,政權不同於傳統的國家機器,階級成為階級化過程(如農民成為無產階級政治力量),等等。在1950-1960年代,即便在主權概念籠罩之下的國際政治領域,抗美援朝戰爭和中蘇兩黨論戰,也提供了軍事和國際關係領域的政治化案例。
二十世紀的政治創新是與持續的戰爭、革命和動盪密切相關的。伴隨1989-1992年的世界性轉變,由中國革命和俄國革命為標誌的社會主義運動以失敗告終。“短世紀”以這一悲劇性的方式告終為人們理解二十世紀提供了一種否定性的視角,即將政治化過程本身視為悲劇的根源,進而拒絕一切與這個世紀的政治直接相關的概念──階級、政黨、民族、國家、群眾和群眾路線、人民和人民戰爭等等。然而,這些概念在什麼時候、在什麼意義上是政治化的,又在何種條件下趨向於去政治化?以階級概念為例,它在二十世紀的政治動員中產生了巨大的作用,但這種動員包含了兩種可能性:其一,即便在身份或財產權意義上並不隸屬於某個階級,也可以成為某一階級的馬前卒或戰士,如農民或出身統治階級的知識分子成為“無產階級”的主體甚至領袖;其二,階級出身成為僵固不變的制度化的身份標記,成為衡量敵我的基本標準。兩者都可能產生動員,但前者是政治化的,後者卻是去政治化的。再以政黨為例,人民戰爭條件下的政黨與群眾路線有著密切的聯繫,所謂“從群原中來,到群眾中去”,由此產生了巨大的政治能量和活力﹔但在執政條件下的政黨卻常常與群眾相互隔絕,蛻變為一般性權力機器,形成了政黨國家化的現象,亦即政黨的去政治化現象。因此,與許多試圖在這些範疇之外尋找新政治的方法有所不同,我試圖對這些範疇自身及其演變進行分析,從中理解政治化與去政治化的樞紐和邏輯;即便這些範疇全部源自“十九世紀”,我也試圖從中找到內在於它們的異物,因為正是這些異物使得這些舊範疇在特定語境中煥發出巨大的能量。
在同一個意義上,探尋新的政治也不可能離開對於這些異物的解釋。從對文化政治的解釋到對人民戰爭及其演變的思考,從對後政黨政治的追溯到對齊物平等的研究,本書的各個章節就是對於這些內在於二十世紀政治實踐的異物及其可能性的探究。就像布洛赫(Ernst Bloch)筆下的“希望”一樣,作為被壓抑的現實,異物很可能會以新的形態、在不同以往的關係中,作為未來再度出現於我們的時代。
內容連載
“亞洲覺醒”時刻的革命與妥協
──論中國的“短二十世紀”的開端
一、中國的短二十世紀:兩個獨特性
二十世紀終於落幕了。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站在歐洲的視角內,將這個世紀界定為從1914年世界大戰爆發至1991年蘇東解體為止的、作為“極端的年代”的短二十世紀。與他所界定的從1789-1848年的“革命的年代”形成了對比,“極端的年代”充斥著暴力卻並不蘊含類似“雙元革命”(法國革命和英國工業革命)所提供的那種創造性的歷史遺產。與他的看法有所不同,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一書中:我將中國的二十世紀界定為從1911-1976年的作為“漫長的革命”的短二十世紀這是一個極端的但同時也是革命的時代。辛亥革命正是這個“漫長的革命”的偉大開端──不僅是中國的短二十世紀的開端,而且也可以視為”亞洲的覺醒”的一系列開端性事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事件。將這兩個相互重疊但視角不同的”短二十世紀”拼合在一起,我們可以分辨出二十世紀中國在這個”短世紀”中的兩個獨特性:
第一個獨特性集中於這個“短世紀”的開端,即在革命建國過程中的帝國與國家的連續性問題。二十世紀是以亞洲的民族革命和憲政民主為開端的,我們可以將的1905年俄國革命、1905-1907年伊朗革命、1908-1909年土耳其革命、1911年中國革命視為“亞洲的覺醒”的開端性事件。
──論中國的“短二十世紀”的開端
一、中國的短二十世紀:兩個獨特性
二十世紀終於落幕了。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站在歐洲的視角內,將這個世紀界定為從1914年世界大戰爆發至1991年蘇東解體為止的、作為“極端的年代”的短二十世紀。與他所界定的從1789-1848年的“革命的年代”形成了對比,“極端的年代”充斥著暴力卻並不蘊含類似“雙元革命”(法國革命和英國工業革命)所提供的那種創造性的歷史遺產。與他的看法有所不同,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一書中:我將中國的二十世紀界定為從1911-1976年的作為“漫長的革命”的短二十世紀這是一個極端的但同時也是革命的時代。辛亥革命正是這個“漫長的革命”的偉大開端──不僅是中國的短二十世紀的開端,而且也可以視為”亞洲的覺醒”的一系列開端性事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事件。將這兩個相互重疊但視角不同的”短二十世紀”拼合在一起,我們可以分辨出二十世紀中國在這個”短世紀”中的兩個獨特性:
第一個獨特性集中於這個“短世紀”的開端,即在革命建國過程中的帝國與國家的連續性問題。二十世紀是以亞洲的民族革命和憲政民主為開端的,我們可以將的1905年俄國革命、1905-1907年伊朗革命、1908-1909年土耳其革命、1911年中國革命視為“亞洲的覺醒”的開端性事件。
網路書店
類別
折扣
價格
-
新書85折$442
-
新書85折$442
-
新書9折$468
-
新書9折$468
-
新書93折$484
-
新書95折$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