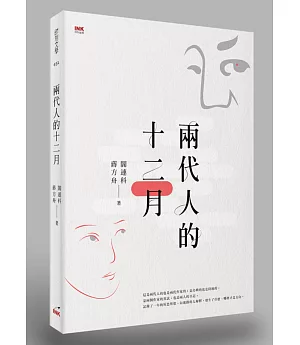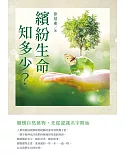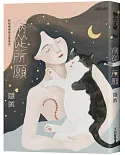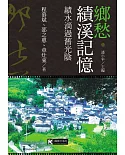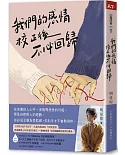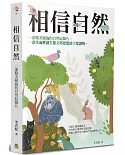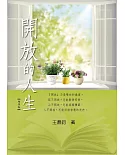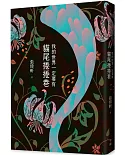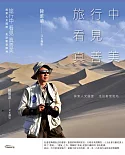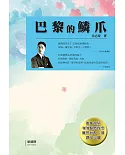代序
共同的相遇
二年前,日本的NHK電視台,安排我到日本的任何城市和鄉村隨意的走走和動動,除了他們的國家機密和軍事之所外,民間的哪,凡你欲去之處,都可任由你的走動和探訪(旅遊的千載之機),但條件是你不要去誇日本的哪好和哪好,一定要多說哪兒不好或者不夠好。他們不讓你總是看見他們的好,更希望借你的陌生之眼,發現和看見他們那些醜的、髒的乃至糟粕的。之後他們會依據你的發現和胡言,做出一個專題片,即所謂的「外國作家學者看日本」。
這是NHK的一個常年計畫,每年都安排一個國外的學者或作家到日本隨走和胡言。就那時,我有一個想念,覺得應該借此問答、對話出一本《中國人應該向日本學什麼?》的小書來。也就立刻想到最好能邀上方舟同行去問答、對話這本書。因為她既有作家的文學之敏,又兼具新聞專業的職業之銳,且讀書甚多,人也謙遜,對上代作家有恭敬之心,這就容易指派和欺負,讓自己覺得不僅自己年長,而且所知甚多,學識也似乎寬寬廣廣。可惜後來,因為中日關係的砰砰啪啪,這些計劃和想念,都旱死在了剛發芽的土地裡。
到了二○一三年秋,我去南京的先鋒書店自誇銷賣新作《炸裂志》,而那時,她恰在那兒宣傳她的《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的隨筆集。就是在那兒,彼此都有一場的演講中,我似乎窺看到了兩代人的鴻溝到底有多深;知道了我的局限和下一代人(作家與讀者)的距離與聯繫。知道了面對現實這兩代作家共同的關心和彼此矛盾、意見相左的一些根由和不可調和的無奈與未來。時間是人與人的橋。也是人與人永遠不可丈量的海,如同孤島與看不見的陸地之距離。因為想要丈量這距離,想要告訴海說島和陸地間無論水域多麼寬廣它們也是聯繫的,也就續念和方舟對話這本書。對話這兩代人要共同相遇、面對的現實、日常和突發。
也就有了這本《兩代人的十二月》。
有了我這落日間的賤狗之吠和她晨起時分的鸝之鳴。有了兩代人的聯繫、分歧和各走各道又必然殊途同歸的路。有了共同面對現實的糾結、矛盾、焦慮、寬容、逃避、躲閃和對世事相同或完全不同的認識和判說;共同要面對世界的無奈和心不甘此的暢言與萎縮,以及彼此面對真相欲言又止的尷尬相。這是兩代人的也是兩代作家的;是島嶼的也是陸地的;是表面現實的,也是無邊無際的時間都無法填滿的陷阱和深層精神鴻溝的。
怎麼辦?
那就隨它吧。
真的就只能隨它嗎?
《兩代人的十二月》,面對這些不是一本無懈無疵的書。相反這本書中留下的憾漏如從水中撈出來的網。但那網上畢竟還掛著點點滴滴的兩代作家的思想、情感和麵對現實與世界的真誠和警覺、直言和帶著現實鹽味的水。它不求解決什麼,也絕不期望解決多少是多少。它所能夠做到的,就是那一年兩代人或說兩代作家在要共同相遇的面對中,把彼此的所思所想留下來,就像把虛掩的鴻溝挖開給人看一樣。
閻連科
二○一五年一月九日
序言
前面的話
在編輯本書的某一日,閻老師給我傳來微信,問:「你說我們是不是太被文藝綁架了呢?」
我思索良久,腦海中想到的是在校改完《愛麗絲中國遊記》後,沈從文在存底本上留下這樣的題識:「越來越難受,這有些什麼用?一面是千萬人在為爭取一點原則而死亡,一面是萬萬人在為這個變而彷徨憂懼,這些文字有什麼意義?」
我妄自猜測閻老師同我一樣,時常感受到這種無法自拔的失落——這些文字有什麼意義?
這樣的感覺在最近的一年尤其頻繁。中國在巨變,世界在巨變。文學家置身之外,無法參與歷史,無法改變現狀。每天的現狀都和昨天的現狀不一樣,文藝家能捕捉的東西何其少?動作何其緩慢?哪怕捕捉了世界變化中的吉光片羽,影響和力量又何其渺小?
這些想法對於文藝家們來說幾乎等同於自殺——懷疑自己所做一切的意義。
冬天,我去看一個導演的作品首映。在播電影之前,導演帶著笑嘟囔了一句:「這個時代都這樣了。」觀眾帶著同情和理解,笑著附和。隨即開始播放電影,一對俊男美女所主演的,「充滿了時代氣息」的電影,迥然於這個導演之前的作品。
在感覺到文藝的力量式微時,這個導演代表了一種選擇:時局太壞,破罐破摔。娛樂至死,至死方休。
看完電影回來的路上,我一路躲避狂風,姿勢惶恐可笑,內心卻忽然有種異常的安定:既不願與時局妥協,也不願意自我放逐。不願意停止對現實的關注——當然,我知道這種關注的力量很小,小得就像鼴鼠打洞,並妄想撬動地殼。
這本書,就是用我和閻老師,兩隻鼴鼠,用打洞扒出的土造出的一座小山。我們用了一年的時間,每個月或對談,或在同題之下各寫一篇文章互文。
往大了說,這是兩個作家的嘗試,既立足於寫作本職,又謀求參與社會,千方百計地找出盡職責的手段。
往小了說,這是兩個人的日記,記錄下一年的所思所想,像是在分岔的小徑立下兩個用記憶編織成的稻草人,向迷路的人解釋,發生了什麼,哪裡才是方向。
蔣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