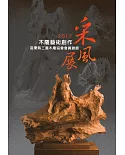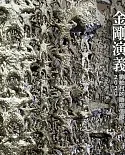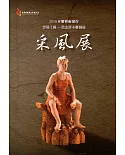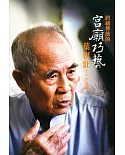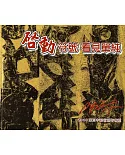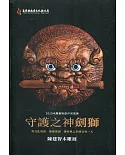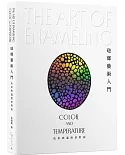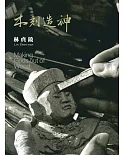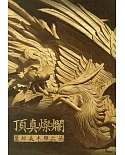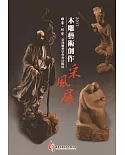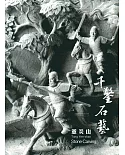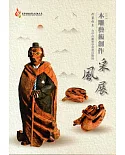導讀
文字與書法——談「誠」作為移動的雕塑
董陽孜不願被歸為「書法家」。她的藝術來自文字,來自對文字結構與意涵的呈現,但已跨越書寫文字的界限,積極尋求文字呈現形式的創新突破。她的「誠」字雕塑,因此可視為文字的當代呈現,以一種非傳統的,三維空間式的元素結構關係,反思文字原有的規則,甚至反思現代藝術中的雕塑本身。
文字的傳統呈現,不論是在紙絹、金石或摩崖,皆是平面性的書寫。或許稍有不同,在各種書寫過程中,容有一些前後、上下、左右的考慮,基本上沒有繪畫或雕塑所需面對的三維空間問題,甚至,連字的結構本身也是平面的。因此,當書家嘗試在書寫上追求美感的表現時,不論是經由使筆的運動,或者是結組的變化呼應,皆不離此二維性。這可說是文字書寫的本性。不僅漢字書寫如此,其他文字如英文之拼音文字者亦皆然。但是,文字的呈現就永遠要受到這個二維平面的約束嗎?大多數的書法家可能認為這個問題毫無意義。離開書寫,書法何以存在?不過,對喜於挑戰傳統的現代藝術工作者而言,那卻是個吸引人的議題。
創造書法的新空間
董陽孜也對這個「非書法」的文字呈現問題感到高度的興趣。是的,第一步其實不難想像, 放棄「書寫」所定義的一切行為即可。然而,接下去如何將概念落實才是挑戰所在。如果要突破文字呈現的平面制約,最富立體性表現的雕塑形式應該是個可以取法的方向。但是, 真的能夠將文字「雕塑化」嗎?
早在一九七○年,美國的普普藝術家羅伯.印地安那(Robert Indiana)就開始實驗這種「文字雕塑」。他的Love
Sculpture原型只是郵票上的平面設計,將L、O、V、E四個字母作方形排列;後來的雕塑版則將無體積的字母轉成塊狀,而成可以站立的雕塑,出現在全世界許多城市的公共空間之中。臺北一○一大樓前也有一座,可見其大受歡迎的程度。若要論這件作品的巧思所在,觀眾總要被那傾斜欲倒的O形字母所吸引,不過,其整體結構的原則還是在於對原來水平橫線排列的破壞,將單線變成一大量體的方塊。可是,如就文字呈現之「雕塑化」目標而言,Indiana之作似乎仍讓人覺得意猶未盡,這可能是英文字母本身性格所限。
英文是拼音文字,每一個字由若干字母組合而成。除了遵守一個固定的拼組方向外,它的字母本身大致都是不可再行分解的固定單元,而且數量也不多,只有二十六個,書寫的形象相對穩定,不刻意追求變化。Indiana文字雕塑的四個字母基本上都是標準化的書寫,即使作了重排,還是維持著它們的平面性,只能由正面的角度「讀」之。然而,被稱為方塊字的漢字則複雜的多。它由兩百七、八十個偏旁部首中的幾個基本元素組合而成,每一元素又可分解成點、橫、撇、捺等筆劃,其結組也不受限於線性的單向,而是在方塊中作多種方向的布置堆疊。這個漢字結構的性格,如果不再拘泥於書寫時筆順的要求,便產生一種組合的高度自由可能性,甚至容許進行三維空間維空間式的重組。董陽孜的「誠」字構成就是看到了這個可能性,將「誠」字的各單元分解、再分解,又進而重新組合成一個可由不同角度觀看的立體「雕塑」。
被雕塑化的「誠」字構成,處處透露出作者「去書寫」、「去平面」的用心。董陽孜沒有採用西方普普藝術家文字雕塑的人造方塊單元,而是從最根本的筆劃開始改變,用四處尋來的風化奇木段落,將二維空間的線條游動,化成或懸浮於空中,或墜落至地上的塊體,有的獨立,也有的直接取用了古木的盤根錯節,筆劃之間的關係因此亦得以自由地從前後、左右加以重構。「誠」字的筆劃重構最複雜的部分出現在右半邊的「成」。那個部分的立體構成當然不似書寫的一目瞭然,但在古木交錯之間,卻意在呼應如草體書寫時的動態,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經過交錯而自然呈現的大大小小,不規則形狀的空間成為原本字體結構中空白的立體性詮釋,一切似非人力所成。傳統書法之論著中常以「屋漏痕」指稱一種近乎自然的筆墨境界,董陽孜在此以奇木為線條,似乎亦可作此想像。
化腐朽為神奇
風化奇木之運用,首要者在於彰顯其自然之性,最忌人力的妄加斧鑿。董陽孜之「誠」字構成,從這個角度來說,實與現代定義中的「雕塑」有別,反而與中國古典美學傳統中講究從自然中萃取藝術之理的信念有相通之處。畫家相信一堵朽壞土牆的斑駁高低平面中,
正隱藏著一幅真正的山水畫,有識者只要知道如何抉取,便可得山水之奧妙。書法上「屋漏痕」之說,也不僅是比喻而已。它正如書者觀察古木上的蟲蝕痕跡,從「偶然成文」之中,感悟筆墨的藝術境界。在這個傳統裡,藝術始終來自天地造化。倉頡所造之字,不也來自於仰觀天象,俯察鳥獸之跡嗎?在此,藝術家最好的策略就是「無為」,讓「自然」自己成為「藝術」,藝術家的任務只在「從自然中發現藝術」而已。這個古典理念最能說明董陽孜以風化奇木構成「誠」字雕塑的創作行為。不論是瘤塊,或是枝條、樹根,都保留著原樣,未加刻意修飾,然而,在此「無為」底下實際卻隱藏著她的「發現之眼」。只有透過這個「眼」,
她才能在一堆堆、一段段歷經歲月淬煉的自然木體結構中, 重新「發現」費了多年尋找的「誠」字形象。如此的過程,正好是倉頡造字傳說的逆反。倉頡從自然觀象之中創造、開始了文字藝術,董陽孜此舉則從文字又回到了自然。
換一個角度說,董陽孜在風化奇木結構中尋找、發現「誠」字的過程是她「無為」之下的「有為」創作。「誠」字作為她追尋的對象,不止是個「形體」而已,更要者在於它「真而不偽」的內涵。這本是人類文明之中普受尊崇的價值,偏偏在現代社會裡的人卻最擅長使用各種手段來矇蔽這個價值。「誠」的「言」字偏旁尤其提醒人們言詞與行為,內心與外表相互矛盾的謬誤,隨時都在你我身邊發生。「誠」不能只是宣傳用的抽象教條,它因此也更需要一個能落實其價值意涵的實體。董陽孜訴諸文字的藝術創作,向來重於尋求觀眾的共鳴;
她在這件「誠」字雕塑中選擇風化古木作為素材,應該也是以其樸質無華、自然而無造作的本質作為激發共鳴的觸媒吧?
正如Indiana的Love
Sculpture以各式版本出現在許多城市的公共空間中,董陽孜的「誠」字雕塑也開始了一段不停移動的旅程。它首先出現在高鐵車站,後來又到了捷運站、政府辦公大樓以及不同風土的城鎮,向不同的空間與觀眾傳達「誠」的訊息。其中在臺北一○一大樓與臺南孔廟的那兩個展示,最令人感受深刻。「誠」字在那各自代表著商業與文化極致表現的空間中,應該會引發迥異的共鳴吧?觀眾的反應也會是因人而異嗎?而當觀眾之中有人高喊支持時,我們也學會反思:他是真心誠意的嗎?
不論如何,董陽孜的「誠」字雕塑雖然已經作成,但其移動的旅程則仍未結束。它的移動本身其實也是「誠」之呈現「完成」其意義不可少的部分。從董陽孜的創作初衷來想的話, 或許,我們該讓「誠」字雕塑繼續不斷地移動下去。
石守謙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教授
推薦序
腦力激盪的震撼
幾年前內子寶年和我與陽孜聊天時,談起中華文字之美、書法之傳神,都同意這些絕非以字母組成的文字所可比擬。多年來腦中也常閃過一個念頭,中華書法的表現與保存,可惜皆只停留在二維空間,無論碑帖、石刻或書卷皆然,可以呈現、可以保存的方式十分受限,前人的絕美作品只能在故宮的玻璃櫃內欣賞。在天馬行空的閒聊中,我說如果我們可能把美麗的書法藝術立體化,成為三維空間的雕塑品,並使用耐久耐候的材料,設置於室內與戶外,相信影響更廣,可見度更高。
類似這樣的聊天與異想天開好幾次,我們幾乎是用激將法的方式,挑戰陽孜,說她的字既能騰雲駕霧的飛舞,她的藝術根柢又雄厚,又常感歎現在臺灣的年輕人對書法的興趣與修養日漸式微,我們覺得她最適合來試著將書法立體化。這樣的聊天,當時並沒有立即具體的行動計劃,但顯然已在她的心中埋下種子。
一次聚會中,陽孜突然問起,假如要選擇一個字,做成立體的雕塑品時,那一個字最適合來開始,並能引起共鳴呢?在來回的推敲中,寶年提出「誠」字應是現今社會中最需要、也最應被大聲疾呼的。這字一出,大家都覺得很好,只是一如常例,陽孜馬上說,這「誠」字十分難寫得好,也很難找到合適的材料表達。這點寶年和我倒不擔心,因為知道她一定有辦法可以讓它實現的。
之後幾年,找適合的材料製作,找對的場地展出,找願意出資辦此展覽的問題一一解決,我們因為各自忙自己的事,其實參與參與的並不多,只是斷斷續續提供些參考意見,或應她之邀一起作說帖及建議書等。要說有什麼貢獻,大概頂多是幫她找了幾位熱心而有興趣的年輕人如郭瑋克、黃毓潔夫婦及CNEX的蔣顯斌等陪她一起想、一起玩,開車一起四處找合適的木材,這過程也變成很有趣的「郊遊」活動。我們也參加了其中的一兩次,看完後並一起去她發現並認為十分有特色的餐廳大快朵頤。
約三、四年前接到她的電話,已找到最後一撇、最難找的奇木,可以試組合成完整的「誠」字,並在三義一家鐵工廠架起,請我們一起去看看。這時候她也已取得高鐵董事長歐晉德之首肯,願提供高鐵烏日站大廳出入口處展示。這次在三義木材場的成果組合,陽孜十分慎重且興奮,除了我們這些原始人馬外,並約了石守謙院長夫婦及CNEX的製作團隊一起去看。
見到偌大的一個立體的「誠」字架在約兩公尺高的半空中,可以從四面及遠近各個角度看,大家都十分興奮,沒想到中國書法真的可以以雕塑藝術之姿,合適的尺度,驕傲完整的呈現。
烏日高鐵站的首展十分成功,雖然那個場地對展示不是最理想,但藝術品本身的氣勢及「誠」字所引起的共鳴,得到極佳的迴響。在陽孜還在思考未來要如何處理這作品,什麼地方有可能收藏這龐大的雕塑之際,即已陸續接到邀請,如臺中市、臺北一○一、新北市、高雄捷運中央車站、臺南孔廟、宜蘭羅東文化工場、馬祖、臺東、金門等十處,其中臺北一○一的展出,因地緣之便,就由我們事務所幾位年輕同仁協助布展。據陽孜說,未來在海峽對岸也有展出,讓中華文字書法結構之美,能感動在大陸的年輕人。
對於中華文化精髓的文章、文字、書法,重新引起社會大眾重視的呼籲,陽孜念茲在茲,有高度的熱誠與使命感。憑藉一己之力,策劃出不計其數的書法藝術跨界展與出版品,規模之大、次數之多及每次皆有不同的創新嘗試,我們從旁看來,都覺得瞠目結舌、不可思議。但她之所以拚了命這樣做,從我們對她的瞭解,並非是為了個人表現、野心或利益,她心中所一再牽掛的,是中華文字與書法藝術的式微,學校不教、不要求寫毛筆字,年輕人也日漸不了解不關心這極為寶貴的文化資產,因此她要大聲疾呼,引起社會的關注;同時她也藉每次不同展出的內容、場所的挑戰,找不同的年輕設計者一起激發創意,鼓勵及培植他(她)們呈現不同的效果,讓社會大眾領略此文化無限的可能,讓年輕人重新啟發興趣,並擁抱這千百年流傳不朽的文化寶藏。
近聞大陸中小學重新要求學生寫毛筆字,日本、韓國也都仍重視毛筆字的價值,甚或主張為其國家原有文化的一部分,我們呢?我們「去中國化」的結果,是像英文諺語所說:「將嬰兒與洗澡水一起倒掉」嗎?
中國書法立體化呈現,可成為雕塑,可長久於室內外展示,可禁得起時間的考驗,如同西方千百年來呈現於廣場、紀念空間或甚至普通市集的雕塑藝術品,「誠」字之領頭成果,希望成為未來國內各藝術院校可參考的方向,也為中華文字及書法藝術的發展帶來全新的契機。
潘冀
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