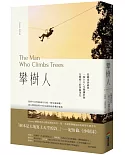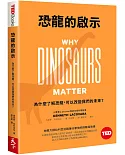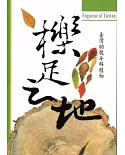前言
財富的種子 The Seed of Wealth
為了宗教信仰,為了發財致富,為了獲得知識,為了尋歡作樂,為了權利,為了打倒對手,天下蒼生四處奔波⋯⋯。長期以來,歐洲各國競相追逐商業最高利益,試圖控制東方資源,角逐的結果是新大陸的發現。在所有政客、商人、水手、地理學者們的夢裡,未知世界遼闊的土地上到處是黃金,寶石閃閃發光,而且,那些神奇香料的芬芳也與之相伴飄浮而至。——瓦爾特.羅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一五○九年
數百年來,植物一直是世界貿易的主要品種。從食物、衣料到藥品,乃至工業原料,無一不與植物有關。近三百年來,從地中海到亞洲、遠東,歐洲各國擴張的權力與影響更是與植物緊密相連。羅利的話一針見血。旅遊也罷,探險也罷,無一不是因利益而驅動。經濟擴張的需要驅使列強們一次又一次地航海探險,尋找新的貿易航海路線與新的市場。利潤驅使著歐洲各國邁出口岸,擴張疆域。一些植物——原本平凡的茶、棉花、甘蔗、橡膠樹(rubber)、煙草,在歐洲人翻雲覆雨的攪和下,竟變得異常特別,與之牽涉的區域更因此而變得面目全非,命運由此而全然改觀。因此,在對新大陸的開發和建設中,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開始刀槍相向,再也不是奴僕之於主人。
誰有實力,誰控制了資源,就是誰說了算。
如羅利爵士所見,十六世紀初的香料買賣是當時最有利可圖的交易之一。如肉桂(cinnamon)、丁香(cloves)、荳蔻(nutmeg)、薑(ginger)、胡椒(pepper)——這些人們喜愛的香料,甚至價比黃金,今天看來似乎令人難以置信。人們圍繞著香料打算盤,最早的出海遠航就是為了尋找遠方神秘的香料。
在那個年代,人們用香料來保存食物,甚至得了病也只能用薰香的辦法來醫治,日常生活中處處都可見到香料的影子,香料因此需求巨大。數百年來,香料滋潤著人們的生活,更使人們的生活變得豐富多彩。它是藥品可以治病;是調味料,可使飯菜美味;是香水、潤膚劑、春藥,使人心曠神怡。
但是,數百年來香料的貿易卻一直被阿拉伯人控制著。他們創建的貿易網路錯綜複雜,從地中海一直伸向遠東。由海上運來的香料:錫蘭(Ceylon,今天的斯里蘭卡)的肉桂,印度的胡椒、丁香,東南亞的丁香、荳蔻,在阿拉伯人控制的碼頭登陸後,沿著絲綢之路輾轉運向西方。
這種買賣利潤巨大,阿拉伯商人費盡心機對香料產地守口如瓶,甚至想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把香料說得神乎其技,玄妙無比;西方人只能無奈地看著阿拉伯人的生意越做越大。
古代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曾講述過這樣的故事,說肉桂是長在淺水窪裡,阿拉伯人去收集肉桂時,要把全身蒙住,只露出眼睛;還得趕著牛作掩護,保護他們免遭那些棲息在淺水湖畔裡的蝙蝠攻擊。又據說,毒蛇盤踞的深山幽谷裡,和可怕的大猛鳥的巢裡都有肉桂,得等鳥巢掉地時才能採到。
中世紀早期,勢力日益強盛的伊斯蘭帝國(Islamicempire)的影響遍及地中海區域,以至於西自西班牙,東至印度東部,都可看到阿拉伯人戰馬奔騰的影子。十字軍東征歸來的戰船,帶回了豐富的香料、寶石、織錦和絲綢,讓西方人大開眼界,更充分地意識到了海那邊的財富之豐饒。但令人十分沮喪的是,耀武揚威的阿拉伯人牢牢地控制著東方貿易路線;只有熱那亞(Genoa)和威尼斯(Venice)諸城與他們有貿易協定。這些城市很快就成了北地中海地區最有實力的貿易中心。
當蒙古人把自己的疆域從中國擴展到黑海時,西方人對亞洲的好奇心更加有增無減。傳道士和商人們覺得,這時沿絲綢之路東行,可能比較安全些。最有名的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1324)之行,就發生在這段時期。從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最令他印象深刻的,就是在印度和馬來群島(Malaysia)看到了大量豐富的香料。他說,中國的杭州一天就運來了五噸的胡椒——考慮到當時歐洲對香料的孜孜以求,這個數字也許有點兒誇張,因為這意味著當時杭州的香料年產量,竟是整個歐洲的兩倍。馬可•波羅還饒有興趣地記錄了中國社會各階層人士的生活:有錢人可以吃用好幾種香料醃製的肉,下層民眾的盤子裡只能嗅到大蒜氣味。
中國明朝時期國力強盛,技術先進,文化燦爛。相較之下,一四○○年時的歐洲相對落後。它地域狹窄,飽受戰亂和黑死病的蹂躪,民不聊生。直到十五世紀,歐洲人的海域也不過八百多英里(約一千三百公里),茫茫大海裡只有海盜船的朦朧帆影。然而,到了「大發現時代」(Ageof
Discovery),僅僅一百二十五年,利益就驅使著歐洲的大艦小船駛過了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找到了美洲、非洲、亞洲的財富寶藏。尤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這兩個小國,居然把世界攪得翻天覆地。他們擺脫阿拉伯人的控制,自由航行於無邊無際的大海中。這些海濱國家有著歷史悠久的航海傳統,以當時的造船航海技術而言,遠距離航行雖困難重重,但也並非沒有可能。伊比利亞(Iberian)商人了解到,如果直接從原產地得到香料,他們甩掉的就不僅是高高喊價的地中海貿易商,還有層層剝削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中間商;這樣,他們就將獲得非同凡響的利益。
十六世紀,有一個人向世界表明,葡萄牙得天獨厚的天然環境,即將成就葡萄牙的基礎大業。這就是葡萄牙王子「航海者亨利」(Henry the Navigator, 1394-1460)。
亨利因在葡萄牙海岸的拉各士(Lagos)附近的撒哈爾(Sagres)建立了「航海學校」 ,而被稱為「航海者」 ,這時「改變世界的歐洲人」的一系列偉大的發現,即將開始。葡萄牙人對遠航計畫守口如瓶,亨利的航海學校也就鮮為人知。不過,人們還是知道,該學校進行的是全方位的訓練,學習地圖繪製,使用航海器械,航海技術的學習更是主要項目。
實實在在的地域拓寬和潛在影響,使歐洲未來的四百多年,在世界的角色地位整個翻轉。歷史學家J.M.羅伯特(J.M.
Roberts)就發現,到了一五○○年,歐洲人已經變得那麼自信不凡了。「改變一切的信心越來越強……歐洲向未來敞開了大門,它獨特的發展理念與別的文化迥然不同。」正是這種唯我獨尊的霸主心態,指引著歐洲對殖民地瘋狂掠奪,以前所未有的貿易方式,把新發現的生產資源,統統吞進了自己的國內市場。
一四六○年,「航海者亨利」去世。葡萄牙人雄心不減,繼續非洲西海岸的探險,希望找到一條到達東印度群島(East Indies)的航線。一四八七年,由巴托洛梅托•迪亞士(Bartolomeu Dias)率領的一支探險隊繞過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來到阿爾格奧海灣(Algoa Bay)。
非洲南海岸就是從這裡蜿蜒北伸。與此同時,佩得羅•科威漢(Dom Pedro de Covilham)到達印度,回來時對印度卡利卡特(Calicut)和果阿(Goa)兩個地方旺盛的香料貿易稱羨不已。
此時此刻,繞非洲好望角直達印度的航行似乎已經成為可能。可是,一四九二年,聽說哥倫布(Columbus)聲稱發現通往東方的西行航道時,葡萄牙人對派遣探險隊開始猶豫了。葡萄牙人最後的結論是哥倫布搞錯了。一四九七年,葡萄牙派遣達•迦馬(Vasco da Gama)率領四條航船經非洲南部海域航行,平安到達了印度的卡利卡特。
達•迦馬以為他帶給當地領導人物的禮物得體適當,卻還是被那些熟悉歐洲的亞洲富豪嗤之以鼻。他沒有得到熱情的歡迎,也沒有收到足夠的香料,他的船並未滿載荳蔻、丁香、薑、桂皮、胡椒等香料而凱旋。不過,一紙印度方面同意與葡萄牙人進行合夥買賣的協議,仍然使他不虛此行。一四九九年,達•迦馬勝利班師。如今,里斯本(Lisbon)已是歐洲的香料貿易中心。
葡萄牙人的東進很快地就使自己實力增強,與盟國的合作更加鞏固,還在著名的香料群島摩鹿加島(Moluccas)主島的馬來群島(Malaya Archipelago)上建立了自己的要塞和貿易基地。葡萄牙人第一次到達這裡是一五一三年,四年後,葡萄牙人就開闢了貿易航線與中國人做起了生意,隨後得到中國政府許可,把澳門島當成了貿易基地。
在後來的半個世紀裡,他們獨佔了整個印度洋的貿易,但香料仍是葡萄牙人最青睞的商品。在摩鹿加群島的交易裡,特別重要的是丁香、肉荳蔻、荳蔻皮(mace,摩鹿加群島班達島Banda Islands生長的荳蔻樹果實的不同部位之稱)。
當葡萄牙王國衰退而無法繼續擔當海上霸主角色時,荷蘭接管了香料群島,印尼殖民地也被荷蘭東印度聯合公司緊緊控制在手裡。荷蘭在這個地區的貿易霸主地位在十七世紀達到鼎盛。他們控制麻六甲海峽(Malacca Strait),通過台灣的貿易站與中國進行周邊貿易。而此時的英國,則一直馬不停蹄地在許多國家和地區建立公司,如美洲公司(Muscovy
Company,建立於一五五五年)、遠東公司(Levant Company,一五八一年)、英國東印度公司(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一六○○年)等,最為赫赫有名的是東印度公司,最後成了印度洋地區的經濟霸主。
這緩慢擴張的國際貿易網和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使英國在後來的兩百多年裡成為世界大國,而它的財富很大一部分則來自於植物。
本書所講述的七種植物對歐洲海外貿易的形成至關重要,它們的登場常常出人意外,甚至荒謬可笑。所有這些植物都與英國海外殖民地的發展、擴張緊密關聯,並對英國國內的社會變化影響深遠。許多我們今天看來普普通通的日常用品,僅僅是由於缺少栽培,一時間竟顯得奢侈、稀有、難以獲得。以茶而言,除了中國,當時世界絕大多數地區對茶毫無所知。直到「植物獵人」羅伯特•福瓊(Robert
Fortune)從中國走私帶回了茶樹標本,並在印度建立了茶葉種植園,西方人才得知這種神秘美味的東方植物。這雖是中國的不幸,印度殖民地區卻因此獲利豐厚。
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的特徵之一,就是經濟植物學的道德法律界限模糊不清。比如,從亞馬遜流域(Amazonianbasin)引種運走大量的橡膠樹樹苗,嚴重地危及了巴西經濟,卻為馬來亞(Malaya)帶來滾滾財源,這裡大片建立的橡膠園使該國獲利頗豐。
橡膠與十九世紀後期和二十世紀初期的汽車、飛機,以及專業化生產與戰爭的機械化緊密相聯。和其他歐洲國家一樣,大英帝國的經濟實力因橡膠而振興。運輸方式的改變,使得大量的製成品可以經由鐵路、輪船迅速運向世界各處新建的殖民地;這些地區的需要和存在的問題,也與母國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一九○○年時,從倫敦出發,六周內就可以到達大英帝國的任何地區。
三百多年前,第一批到達美洲海岸的移民必定覺得孤立無助。一六○七年,維吉尼亞公司(Virginia Company)在切薩皮克海灣(Chesapeake
Bay)詹姆斯城(Jamestown)幾經周折建立起的殖民地,還是那麼搖搖欲墜,彷彿隨時都會垮台;而在成功地種植了從西印度群島帶來的煙草後,這個殖民地得以穩定的生存下來。更妙的是,這種使殖民地賴以生存的植物,後來在殖民地的獨立運動中又佔有相當關鍵性的作用:新生的種植園主對他們與母國的貿易前景十分不滿,紛紛揭竿而起,與宗主國撕破了臉。
傳統的觀點認為:殖民地的作用就在於向宗主國提供原料,並消化歐洲產品。長期以來,以精美的手織細棉布和花布聞名世界的印度棉紡業的命運,就正好說明了這種關係。
十七世紀,棉花的出口為英國東印度公司提供了不菲的利潤。然而,隨著英國工業技術的發展,國內棉紡業需要品質更好的精細棉紗,於是,品質更好的美洲原棉代替印度棉進入了英國市場。英國不再需要印度棉,卻將棉製品運到了印度,印度成了英國產品的傾銷地,價格比當地產品還要便宜。在貿易格局如此劇烈的改變狀態下,即使是英國國內市場也是山雨欲來,眾多利益牽涉者都在醞釀著自由貿易運動,以求改革貿易結構。
製糖業也是相似的情景。美洲南方腹地大規模的棉花種植是由奴隸制度所維繫,而加勒比海群島甘蔗種植園的高密度勞動力,主要也是由黑人們來承擔,惡名昭彰的三角貿易使這些來自非洲西海岸的黑人,淪為奴隸。製糖業的苦役使種植園猶如地獄,而種植園主與其家人住的卻是漂亮優美的房屋,過著奢侈的生活。歐洲需要大量的糖,加勒比海甘蔗種植園主在國家經濟事務中的發言權,自然也是響噹噹的。
在國際貿易中,各種植物間的聯繫常常相互影響。某種植物對人們生活的影響,常常伴隨著另一種植物在人們生活中的需求而增強,糖和茶葉的輸出量,就呈現相互增加的態勢。不過,最不公正的聯繫則是,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鴉片(opium)和茶葉貿易。
英國商人非法進行鴉片貿易,用在印度種植的罌粟製成鴉片走私進入中國,誘人吸食上癮,造成全中國的毒品危害,從而以換來的白銀來支付購買茶葉的款項,滿足西方對中國茶葉日益增長的需求。東印度公司不可能獲得足夠的白銀以滿足購茶的需要,自給自足的中國人對西方產品又不很感興趣。為了確保歐洲市場的茶葉供應,東印度公司就把鴉片當成了換取白銀的籌碼。這一招倒是有效地保證了英國市場對茶葉的需求,最後的結果卻是害人害己:歐洲人也為土耳其鴉片吃盡苦頭,各個國家怨聲載道。
相反地,金雞納樹(cinchona)的大面積栽培(註:其樹皮可用於生產抗瘧疾藥的奎寧quinine),卻主要是出於政治的需要,商業利益次之。西方各國爭搶土地和原材料,爭奪非洲等「處女地」,經濟需要導致了國家之間的尖銳對立,不惜大動干戈。十九世紀後期,英國為了更大範圍擴張領土,要求大量的奎寧供應,既要滿足國家官員和軍隊的需要,也須兼顧大種植園勞工的需要。於是,派遣「植物獵人」從金雞納樹原產地祕魯運來了樹苗,大力發展建立金雞納樹種植園。最初在印度種植,後來擴展到英國的許多殖民地,從緬甸、斐濟(Fiji)到坦噶尼喀(Tanganyika)、牙買加(Jamaica)和喀麥隆(Cameroons),都有金雞納樹種植園。奎寧使移民們得以戰勝瘧疾,在荒涼的非洲和東南亞立足並安家落戶。移民的妻兒老小來到了這些地區,這裡的風景從此改觀。
就是這樣,這些與人類生活密切相關的植物,在歷史進程中佔據著微妙而關鍵的重要地位。它們的栽培、收穫、運輸、加工處理等一系列的過程,無庸置疑地改變了前殖民地區的生態環境、人口分佈和經濟模式,甚至連這些殖民地上的主人們也都因此而變得面目全非。現在,那些當年的蠻荒之地所留下的恩恩怨怨,仍如空谷回音,仍然影響著人類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