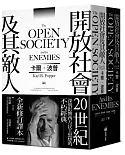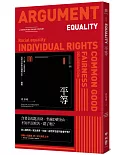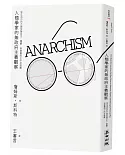導讀
都是「現代」民族國家惹的禍
2014年五月下旬,讓南地(Nandy)及人們擔憂卻也在料想中的事終究發生了:印度人民黨(BJP)勝選二度上台,2001年在古吉拉特邦(Gujirat)發生族群屠殺慘劇時任首席部長的莫迪(Narendra Modi),當時放任地助長了暴力衝突,被認為是具有高度爭議性的政治人物,今天成為印度的新總理,這意味著被公認為以右翼興都民族主義(Hindu
nationalism)為基地打造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工程又向前邁進一大步,種族與族群的分化與對立勢將持續上升,南亞天空中的愁雲慘霧看來短時期內難以散去。
在上述的語境中,翻譯出版南地1994年的名著《民族主義的不正當性:泰戈爾與自我的政治》,就有了強烈的當下意義,讓中文的讀者得以看到,二十世紀早期還處於殖民地狀態的印度,就出現了泰戈爾的經典作《民族主義》
(1919),體現了質疑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的思想,這條思路雖然終究沒法擋住民族主義的惡性氾濫,但是卻一直存活下來,成為珍貴的批判性思想資源。閱讀南地、重讀泰戈爾不禁讓人唏噓,問題當然不僅侷限於印度,在民族主義依然在世界各地大行其道的今天,我們到底該如何理解與面對這股揮之不去的幽靈。
《民族主義的不正當性》的副標題將問題指向了「自我」,泰戈爾在論述層面上直接重擊民族主義,不留情面地告誡二十世紀初期的日本、美國、印度,特別是像日本這樣正在興起的國家,其危機不在於模仿西方,而在於輕易的接受了西方民族主義的動力,還把它當成是自己內在的生成;而南地的分析指出泰戈爾之所以能夠由衷地提出警訊,正是因為他一直在面對隱藏在心中的民族主義自我,只有透過打開躲在內心深處好些個秘密的自我,經過它們之間不斷的搏鬥,擊敗那個被民族國家所誘惑的自我,才可能在交戰中超脫出來,清醒的面對民族主義的構成。因而,南地的分析走入泰戈爾的小說世界,讓世人能夠具體的體會到民族主義一旦落實所造成的實際困境:《戈拉》(1909)發現民族主義的自我防衛排他性,在日常生活中就直接對峙於印度文明宗教與文化包容的多樣性;《家與世界》(1916)暴露民族主義運動如何瓦解了傳統社群生活,呼喚出宗教暴力的魔鬼,家毀人亡,人與人間的互信與互助崩解;《四章》(1934)透視所謂現代工業化巨變所帶來的動盪,開始產生了組織化的暴力與民族主義掛鉤的新形式。南地認為泰戈爾這三部小說,都是在與親密的好友烏帕迪亞這個第一個現代興都民族主義革命分子對話,泰戈爾之所以能體會好友複雜的心境,正是因為自己胸中藏有相通的地方:出身歷史悠久的南亞文明,殖民地精英在面對英國統治時,總是希望能透過改革來找回尊嚴,但是在路徑、方向上會有不同的看法;用南地的話來說,烏帕迪雅是泰戈爾的疊影,後者最終選擇了在當時看來不合時宜的道路。
對泰戈爾而言,「民族」、「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都是現代歐洲歷史的產物,「現代」意識形態的形成是對於歐洲自身歷史的反動,特別是在進化論的世界觀下,民族國家是一系列將人民組織起來的政治、經濟機構的結合體,試圖拋棄宗教神學的制約,以民族的自保與自利為前提,透過主權、理性與法治的科學之名,造成的是衝突與掠奪,這種現代全面轉化的安排割除了更高層次社會生活的要求,在推翻時懸置了精神世界在宇宙中的位置,因此「現代」意識形態不具有普遍性,印度所在的南亞大陸有其自身的軌跡,也有它內在的問題(如種性),它的解放不能透過借用別人的歷史來完成,強加、內化歐洲的世界觀將會走向自殺的毀滅道路。
南地自1970年代出道起就深受泰戈爾與甘地的影響,這兩位所謂的民族英雄對民族主義都有相當的警戒,他們在根本上認為印度數千年以來的文明不能也不應被化約、收縮到狹隘的民族概念,所以在他們操作民族的觀念中,都帶有自我批判的深刻內涵。甘地從來就將他所引領的自由運動當成是爭取平等的普世性鬥爭的一部分,也指出歐洲的民族主義一旦武裝化就成為帝國主義,而非暴力和平運動的基礎正在於指向自身的反省,承擔苦難是自由的前提,特別是在以宗教生活為根基的社會裡,將政治與信仰脫鉤會是災禍的源頭,拔除了不斷內省的實踐,政治必將淪為黨派利益的爭奪。
可以說,南地是以特定的方式承繼了泰戈爾與甘地對民族主義的警覺。
南地在1990年代以《民族主義的不正當性:泰戈爾與自我的政治》介入思想界的辯論,是有跡可循的。雖然族群衝突在南亞的歷史中一直存在,但是大規模的暴力出現在南亞民族國家建立的過程裡,1947年印度獨立是以與巴基斯坦分裂所帶來的災難為建國的記憶,上千萬的穆斯林與興都在死難中大遷移。此後印度內部的族群衝突並沒有結束,建國的第一代領導人甘地可以說是因為反對印巴分裂、反對族群與宗教暴力而遭刺殺,接下來的第一任總理尼赫魯及其所帶領的國大黨也都或多或少承繼著甘地路線,讓操弄族群宗教民族主義的政黨沒有太大的空間。然而五〇年代後隨著都市化、中產階級的逐漸擴大,「現代」「世俗化」生活所帶來的自我的孤立、恐懼、失根感,在七、八〇年代後成為政治勢力操作衝突矛盾的土壤,興都民族主義勢力逐步抬頭,以宗教作為政治動員的工具,將數千年來原本非組織化、多元、異質、零散而又廣泛的民間宗教信仰,編造成新的泛印度宗教,稱之為興都教(Hinduism),透過不同的組織形式相互呼應,在各個領域操作,特別是以回教為對立面,建立「民族」認同,推動民族國家打造運動。
1990年起,南地與其他同仁組成研究團隊,紀錄、研究北方省阿約提亞市(Ayodhya)正在發生的燒毀清真寺事件,1995年出版了極為重要的田野調查報告Creating A Nationality: The Ramjanmabhumi Movement and Fear of the Self,以1990-1992
年的運動為前景,拉出更為寬廣的歷史脈絡,解釋了宗教形式(如節慶的繞境行走)如何成為組織動員的手段:1960年代成立、組織遍佈各地與國際的右翼宗教組織VHP,發起了1990年十月的第一波行動,搭配著1980年代成立的外圍激進青年團體Bajrang
Dal進行破壞,經過幾波動員,最後1920年代成立至今聲名狼藉的準政治組織RSS,在1980年成立的BJP(被認為是前面這些組織的政黨形式)的暗中配合下,1992 年十二月集結了來自全國二十萬的極端興都分子,在阿約提亞發動暴動,摧毀了Ramjanmabhumi這個清真寺,焚燒了回民的住宅,造成大量傷亡,回民流離失所,由此一點爆發擴大成全國範圍的族群衝突。
正是在第一線觀察體驗到民族主義暴力的語境中,南地寫成了這本小書,透過重訪泰戈爾試圖與年輕一代對話,語重心長的想要提醒人們南亞大陸早就存在著「小心民族國家!」的信念,不能因為民族主義在殖民地時期曾經發揮反帝的作用,而遮蔽民族國家的框架與形式,以種族、族群、宗教、語言為人群分類基準,透過現代國家統治範疇的擴張與中產階級公民社會的共謀,包圍庶民生活,所帶來的潛在政治禍害。
整體而言,南地長期的知識工作,是在泰戈爾與甘地思想的基礎上,更有系統地尋找走出民族國家陷阱的出路。他認為民族國家是歐洲啓蒙主義世界觀下整體配套的組成,與「現代」、「民主」、「科學」、「進步」、「理性」、「世俗」、「主權」、「資本主義」,「工業」、「機械文明」等等觀念所指涉的運作相互串聯。簡單的說,民族國家是西方現代世界觀的政治形式,在天地萬物相通的宇宙論裡,宗教、信仰所指向的精神世界,在上帝已死、以人為中心的現代世界觀裡被邊緣化時,民族國家幾乎被置換為新的終極投射對象,要抵抗民族主義,必須從根本上質疑「現代」意識形態所編織的整體結構與各個相關範疇,不能再使用「現代」來丈量、排斥、貶抑「非現代」(non-modern)的範疇。所以在南地的思想體系中,「現代」不再是歷史(分期)概念,而是歐洲歷史四個世紀中所形成的整套意識形態,逐漸推銷到全球各地,為殖民地與戰敗的文明地區所內化。其中一個走出現代的枷鎖的方式就,是要重新開放還活著的、非現代的資源、生活形式、思想內涵。南地甚至提出,像南亞大陸這樣的第三世界對於人類未來文明的貢獻,正在於它還保有了第一世界、第二世界都極力清洗、扼殺的非現代生活方式,諸如成千上萬的廟宇與神明,乃至於沙蠻(shaman)與乩童,中醫與民俗療法;當世界被抹平、同質化的同時,「現代」的整套知識體系、生活方式、世界觀也正在快速的面臨全面性的挑戰與崩解,當初甘地以農村為本的反機械文明被斥為封建落後,今天成為環境生態運動的先驅,因此,處於不確定性年代時,如何保存不同文明的生機與一切的可能性以提供人類未來更為寬廣的選擇,用南地的語彙來說,捍衛無數自成體系的小文化(little
cultures)能夠繼續存活的空間,就成了當務之急。
南地1937年出生於印度吉爾各答地區,在孟加拉文化圈的孕育中長成,受的是心理學的訓練,曾有臨床精神醫學的洗禮,1970年代起出道至今四十多年,活躍於印度思想界,在世界範圍內成為第三世界的代表性人物。繼《貼身的損友:有關多重自身的一些故事》(台北:台社/唐山,2011)、《民族主義,真誠與欺騙:阿希斯•南迪讀本》(上海:世紀文景/人民,2013)之後,我們藉他2014年七月再次訪台擔任亞洲現代思想年度講座之際,出版《民族主義的不正當性:泰戈爾與自我的政治》一書,繼續深化中文世界對於南亞印度思想的理解,特別是對民族主義熱潮的反思提供參照的資源。藉此機會感謝戰豔的翻譯與吳曉黎的校訂工作,以及亞際書院、夢周基金會、世新大學台社國際中心與行人出版社的支持,當然得感謝南地先生的授權與長期合作的友誼。
陳光興
(2014年六月於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