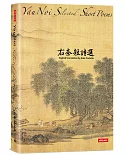主編序
生活的證據,時代的新聲
中文新詩發展迄今大約百年,文體變革帶來嶄新的思想風景。一九二○年三月,第一本中文新詩集《嘗試集》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初版。胡適在自序上說,民國五年他在美國留學時開始寫作新詩。這一番嘗試,果然為中文書寫打開新局——形式影響內容,或者也可以說形式就是內容的基本面貌。新詩形式在此確立,是新文學發展的重大成就之一。《嘗試集》之命名,出自陸游「嘗試成功自古無」,胡適反用其義而推陳出新,他的嘗試無疑是成功的。這部詩集做為二十世紀之先聲,正可印證胡適所主張的:文學革命運動,不論古今中外,大概都是從「文的形式」下手,要求文體的大解放。
文學教育就是情感教育,文體的改造或許可看作是現代心靈的美化工程。胡適以降,徐志摩、聞一多、李金髮、冰心、卞之琳、馮至……,各自創造出語言藝術的新天地,在文學史上留下不可取代的價值。殖民地台灣的賴和、楊華、張我軍等詩家,用白話文寫出心聲,同樣繳出傲人的成績單。沿著歷史脈絡讀下來,覃子豪、紀弦、周夢蝶、余光中、瘂弦、洛夫、鄭愁予、楊牧、陳黎、向陽、焦桐、陳克華、鴻鴻、顏艾琳、孫梓評、吳岱穎、林婉瑜、羅毓嘉……,每一個世代的書寫面貌各有傳承新變,在社會變遷中開闢文學天地,長期累積的成果大有可觀。
在教學現場,一直沿著文學史脈絡來理解新詩,箇中的選擇、判準自然有其道理。然而,我私心期待著一本引人入勝的新詩讀本,不以交代文學史為主要任務,而是把一套美好的語言座標勾勒出來。每一種文學選本,各自反映編選者的美學標準。選集中收錄的作品,除了彰顯個別作家的成果,更可看作編選者苦心孤詣營造的基本價值。台灣的新詩選本為數甚夥,有以年度編選的,有以主題編選的,也有以區域來編選的。它們各成體系,各自精采,使新詩的美學論證找到最適切的展示空間。這些多元且豐富的選集文本,讓讀者方便進入新詩的國度,從中領略選家的才情、見識,與品味。
說到詩的見識、品味,新世紀第一個十年過去,我終於等到了《生活的證據:國民新詩讀本》。吳岱穎、孫梓評兩位傑出的詩人,用最敏銳的眼光,精挑細選華文世界的新詩文本,構築出詩與生活的燦亮星圖,同時揭櫫新詩文體與國民性,不吝在這本選集裡分享他們的才情。
在分輯編排上,本書不以詩人紀傳排列,也不以文學社團、文學史編年為分類依據。此書最大的意義是,傾聽生活的聲音,直接面對我們生存的世界。現代心靈可能遭遇到的種種問題,都在這本新詩選裡顯豁出來,所以名曰「生活的證據」。這樣一來,或許更能符合教學需求,更能讓普通讀者藉此理解語言文字的藝術如何回應生活。兩位選家拋卻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種種學術套語,真誠地以自己的感受與學識,懇切寫出他們如何理解一首詩。吳岱穎長久致力於新詩教學,孫梓評一直在編輯檯上披沙揀金,他們的合作正好可以辨識出我們這個時代特有的聲音。在《生活的證據:國民新詩讀本》中,勾勒出中文新詩的自我抒情、生活感受、社會關懷、文化認同、語言實驗……特別選錄陳綺貞、蛋堡的歌詞作品,透露著詩與音樂可以如此纏綿。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尚未出版詩集的林育德、詹佳鑫等年輕詩人,已經在這本選集裡初綻異采。林育德為此書編寫台灣新詩簡史,篇末列有詹佳鑫撰寫的詩人小傳,也讓這本書更具教學的實用性。
語文的學習需要日積月累,需要下工夫練習才能精熟。不管在哪一個國家,本國語文一定列為國民教育的核心課程。因為,理解與表達的能力,關係到一個國家的人民如何認識自我、如何與他人對話溝通。語言文字不僅是人際溝通的工具,更是我們探索意義世界的關鍵。語文能力之優劣,直接影響到國力。民主社會若要有深刻的對話溝通,必須先讓國民的「聽、說、讀、寫」變得愈來愈優異。想要提升閱讀理解與書寫表達的能力,除了仰賴學校教育,我認為還要有一系列的國民讀本,提供更多自主學習的機會。這就是規畫「中文好行」書系的初衷。
在這個書系裡,有美麗的文字風景,也有迷人的意義路標。書系裡的每一本書,可以用作自主學習,也可以做為共同學習討論的讀本。這一套書編選的起點與定位,是提供正道大法,讓國、高中階段的青少年精進語文能力。背後則隱藏著一個更大的心願:希望促進親子共讀,邀請家長們一起參與青少年的學習。同時也希望,這一套簡要易懂的國民讀本,可以讓久別校園的社會人士重溫讀書之樂。讀書的快樂、理解的快樂,將會陪伴著自己面對生活中的煩悶無聊,找到一個美好的意義出口。
擁有學習動能的生命,不會枯竭無趣。透過不斷學習讓生活變得更有趣味,也是我們現代人的重要課題。《生活的證據:國民新詩讀本》是我看到最有趣、最具美感的一本新詩選集,吳岱穎、孫梓評針對選錄詩作所寫的評析筆記,細緻、優雅而完整,簡直是另一首奇麗瑰偉的詩。「不學詩,無以言」,詩是日常語言的美化。在這個時代,幸好有這樣美麗的聲音。我們需要詩,需要用詩的力量拒絕低俗、抵抗粗暴,看見幸福的光。
文/凌性傑(詩人,建國中學教師)
編者序
洋蔥的價值
一
我第一次認識洋蔥的價值,並不是在餐桌上咀嚼那炒得軟黃透明的肌理在蛋塊中滲出絲絲甜味的愉悅瞬間,而是在電影裡。
當然也不是在周星馳的電影裡看著好姨薛家燕躺在大叉燒上,一邊翻滾一邊嚷叫後流下一滴眼淚說自己「有一種哀傷的感覺」,那樣煽情誇張無厘頭的覺悟,而是《美國心玫瑰情》當中,一枚塑膠袋被風吹得盤旋迤邐,穿透生死美惡卻又寧靜無聲,意義鋪天蓋地無窮無盡席捲而來的神奇時刻。「是洋蔥,」我對自己說:「那就是洋蔥了。」
當然,這部電影當中沒有出現過一個關於洋蔥的鏡頭,洋蔥存在於影評裡。影評人說這部電影的結構就像洋蔥一樣,層層剝開了生存的暴力與荒謬。透過電影緩慢又緊湊的敘事,這一切展現為一個巨大的隱喻,而我用另一個比喻包裹它:緊密包裹自己,不輕易將內在示人的洋蔥(好洋蔥,不買嗎?)。
如果沒有深入追索的決心與毅力,事物的核心便隱淪於表象中;一旦啟程出發,開始尋找意義的旅行,這被掩蔽起來的真實便漸次呈露展現,天地萬物因此有了內在的聯繫。那是否,就是詩存在的狀態?
一種近似於洋蔥的狀態?
二
其實反觀自視,向內墾掘,我們的內心也是一顆洋蔥。
當然也不是像情歌裡唱的那樣,一層一層剝開內心,就能發現甚麼深處壓抑的祕密。它比較接近鈞特.葛拉斯說的:「回憶就像一顆要剝皮的洋蔥。洋蔥皮層層疊疊,剝掉又重生;如果用切的,洋蔥會讓你流眼淚,只有剝掉它,洋蔥才會吐真言。」
因為記憶層層疊疊交相滲透;因為我們所曾經歷的一切,都已成為現在這個「我」的一部分;因為它自我複製、自我解釋、自我保護,因此除之不盡,去而復來。它如此堅實,而我們堅持活在世俗意義的「當下」,無視於隱藏其中的各種矛盾與謬誤,是以時常處在無明痛苦之中。
無法認清自我的時刻,無法表述自己的時刻,胸懷裡漲滿洋蔥嗆人的淚水,就要溢出眼眶,而視線早已經模糊了世界。還能不回頭嗎?還能堅持這樣表象式的活著,再沒有任何自省的可能嗎?
面對這發自內在的疑惑,我感到一種迫切的需要,對詩的需要。
三
「一首詩是一顆洋蔥,」我對自己說:「就像是一種信仰,只有進入其中,才能明白淚水的意義。」
把信仰比作洋蔥並非我的發明,而是遠藤周作。《深河》裡的大津背叛了天主教修會,在恆河之岸默默實踐他所認知的基督之愛,照護所有貧病乃至於死亡的人們,以異教的儀式為他們送行。遠藤周作藉大津之口,給耶穌起了「洋蔥」這個名字,試圖讓女主角美津子理解他心中的宗教觀,申明真正的愛究竟為何物。
一個意象,穿透文字紛擾的表象,穿過千百年來從無休止的爭論與激辯,直指意義的核心。「是洋蔥,」我告訴自己:「這就是洋蔥的價值,詩的價值。」
面對這太過豐美的世界,我所擁有的只有極其有限的語言。滯澀齟齬的文字,令我常懷恐懼,心存憂傷。每當我提筆書寫,希望在概念與概念、語詞與語詞的碰撞之中,藉由那瞬間閃逝的微弱星火,照亮真實存在於這世間的「那個什麼」,總是感到如洋蔥內瓣一層一層的隔膜,阻我思路穿之不透。我所做的,不過就是嘗試「剝開洋蔥」這麼簡單的事情,但那實在太困難了。事實是,詩之艱難一如生之艱難,有時更甚於科學理性所能涵括解釋者。
但,如果生命是一種信仰,詩豈不也能成為一種信仰嗎?
每每在科學館的地下室,週五傍晚的詩社社課,我與學生們在言詞上交鋒,展開挖掘詩意的辯論。我們臚列語詞,旁搜遠紹,探求玄虛窈冥不可測見的線索,試圖釐清事物與表象之間可能的聯繫。但一個半小時的社課,即使眾聲交響砲火不斷,往往也處理不了一個語詞當中可能包含的詩意。因此也就更加明白, 創作者所面對的是何等艱鉅的挑戰,而我們真正能做的,只有相信意義就存在這「剝洋蔥」的過程中。
四
道之所存,詩之所存,詩就是我唯一的信仰。
天地萬物,偶然亦是必然。正如海德格所認為,唯有詩可以溝通天地神人,出入表象與現實、世俗與本真。即使物自體不可知,無法抵達,詩也能帶我們永恆地趨向它。每一首詩都是詩人探求真理的紀錄,而每一個希冀探求真理的人,都應該是詩的讀者。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這條路上走得更遠一點,更長久一點。
我和梓評合作的《國民新詩讀本》就是這樣的一本作品,它是我們的實驗記錄,紀錄我們如何試圖重現原作者的創作過程與寫作目的;它同時也是我們的期中報告,報告我們這二十年來的創作生涯裡,從閱讀他人的作品中所獲致的一點心得。在這裡,我們從創作者還原成為閱讀者,誠實面對我們自己從閱讀詩作中得到的感動;但我們同時身兼引路人的角色,希望將這份感動傳達給更多的讀者。
為免嚼飯餵人之譏,每一首作品後的賞析均不甚長,僅僅點到為止。或指出方向,或標明路線,希望讀者如同拿起旅行指南,開始規畫自己的旅行一樣,整理行裝出發前往,印證書上的記載,更看到獨有自己能看見的風景。
如果讓我選擇,我仍然想用洋蔥來比喻這一切:不管我們說得如何天花亂墜,剝之又剝,切之又切,洋蔥最終還是要拿來吃的。
它價錢便宜,營養豐富,滋味甜美,悠遠,深長。
好洋蔥,不吃嗎?
文/吳岱穎
編者序
給十七歲 和岱穎合編《生活的證據:國民新詩讀本》
突然空出來的一個下午,誤打誤撞,來到西子灣。多少年沒有來了?腦中還隱約印著一個畫面,一群朋友,前前後後,倚著英國領事館官邸的磚紅色半圓拱窗,留下青春照相。為了重回那個位置,只得走進如今被據為茶館的長廊,點一壺熱茶,打算在山坡上等日落。
那年夏天,是不是就是因為認識這群朋友,我才開始讀詩,寫詩?他們之中,有人為我解釋李金髮,有人一齊朗誦鄭愁予,有人在信裡抄寫蔣勳,十七歲是詩的年紀,當置身荒謬課堂,聊賴的老師和更形聊賴的同學們,共演一齣自絕於聯考制度之外的即興劇,書包裡和考卷作伴的那些被退稿的詩,是前途無效的車票,卻也有效地收容了彼時多芒刺的我。
無效的有效。跟書架上排列整齊的流行歌卡帶,影劇版剪下的奇士勞斯基劇照,戲院窗口偷來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海報一樣,都無法幫助我在考卷上成功回答三角函數或立體幾何,亦不能更精進、熟用英文的不同時態或句型;然而,每每情緒飽脹欲裂,花苞一般的身體,卻不經意在各種新識的詩行(當然,也包括那些卡帶,劇照,海報)中,獲得了理解。理解即治療。詩是陌生人施給的重要對話,安撫充滿破綻的我。
一直以來,我不是能理直氣壯說出理想詩歌為何的人,是拙,也是情怯。我怕一旦說出什麼,就像用容器將詩瓢起,詩不是應該更自由,流動的嗎?有人把詩當成信仰,我約莫是不忠的信徒;有人將詩視為黃金事物,我卻更情願它是一把椅子。鴻鴻詩集《在旅行中回憶上一次旅行》後記裡說的,「發現自己經常寫到桌子椅子,我的床。很好。這些是我每天能安心正視的少數幾件事物。」
大概也因為這樣,很長一段時間,我相信「詩是一種生活方式」(瘂弦語)。生活的內容包括什麼?栽種於胸口的一句告白,知識的求索,家族所餵養的光亮與陰影,忽然湧出的詩的可能……然後,迎來了世紀末與新十年,人人踏上網路,後解嚴時代眾聲喧譁,更多「反,正因為愛」的議題被書寫,生活於此島,除非刻意掩耳,遮眼,很難不被(自己)問起有關「公理和正義的問題」,而明白何以鴻鴻說「詩是一種對抗生活的方式」──
從小山上眺望,西子灣與旗津共同伸出兩條長臂,抱擁住一片海,船隻進出,遠方遙似煙波。風一陣一陣。遊客也是。聲音在洋樓之畔流動,混合著各色口音,或者亦包括當年我們談笑的內容?工作人員或警衛低聲喊:「那裡不讓坐!」微斥拍照而攀上護欄的異地遊客。風懶了,人疏了。遠洋的船還沒有從樹葉們的縫隙間離開。像哪個負氣的畫家隨手一抹,天色漸漸糊去。今天不會有夕陽了。
在生活與對抗生活之間,我仍擺盪,惶惑。(或許這是不應該的?)
但詩,一旦來過,就是活過。
就像,海平線雖然沒收了夕陽,生活仍慷慨遞來收據:天黑了,一艘大船從霧藍色碼頭深處駛出,巨大船身的頂部甚至比旗後山上的燈塔還高。我靠近岸緣,為它留下一張照片:給十七歲,也給每一個路過詩的人。
文/孫梓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