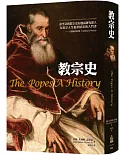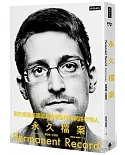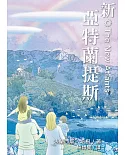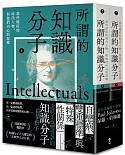專文推薦
真正的謙卑/褚士瑩
最近同時看了兩本值得一起對照閱讀、思考的書,一本是六十多歲的尋常家庭主婦瑪琳娜的回憶錄《沒有名字的女孩》,另一本是靈長類動物學家瓦爾(Frans de Waal)的學術研究《矮黑猩猩和無神論者:在靈長類動物中尋找人性》(The Bonobo and the Atheist: In Search of Humanism Among the Primates)。
回憶錄的故事主角目前和丈夫及兩個女兒居住在英國的鄉間,但在一九五四年她四歲時被綁匪遺棄在哥倫比亞的原始叢林裡,孤立無援的她在不知所措之際,碰上了一群卷尾猴。年幼的她跟著猴子們學習了覓食、攀爬以及躲避危險等生存技能,甚至學會了猴子的語言,而得以跟牠們一同嬉鬧、分享食物,或是清理彼此的身體和毛皮。這群猴子是她的救命恩人與朋友,讓她忘記孤獨,感受到「家」的溫暖。歷經五年的叢林生活,她懵懵懂懂地跟著一對獵人回到了人類的社會。但在那裡等著她的並不是期待中的溫柔擁抱,而是無情殘酷的欺凌鞭打,她曾淪為奴隸、童工,甚至憑藉著從猴子那裡學來的靈巧身手,搖身一變成為街童竊盜集團的首領,直到十四歲那年,這個飽受生命苦難折磨、已經沒有了名字的女孩得到好心人收養,給自己取了「瑪琳娜」這個名字,終於開始逐漸實現那個建立自己家庭、安穩生活的夢想。
靈長類動物學家瓦爾則是終其畢生精力,研究人類的近親黑猩猩和矮黑猩猩,他提出具有說服力的論據,證明動物不需要宗教也能表現出一些看起來非常像人類的道德行為,證明宗教並不是讓人類具備高尚情操的必須條件。
瓦爾在實驗室的實驗中,看到黑猩猩即使在沒有「好處」的情況下,也會幫助其他黑猩猩獲取食物,甚至在同伴獲得食物之後會拒絕接受獎勵。在野外也是如此,比如年輕的黑猩猩會幫年老體衰的老猩猩送水,也會收養來自其他猩猩家族的孤兒。瓦爾也觀察一群野生恆河猴,年輕力壯、甚至脾氣暴躁的成員,對於族群當中得到相當於人類唐氏症的猴子,也會特別容忍有耐性,不會因為這些染色體異常的同伴的脫序行為而欺負牠。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瓦爾是誰,但是如果提到在TED演講中播放的一段影片,你可能就有印象了。在那個實驗裡,來自同樣族群、互相認識的兩隻猴子,分別被關在兩個籠子內。研究人員要求猴子拿出石頭交換食物,其中A猴的回報是「黃瓜」,B猴的回報是「葡萄」。相較於黃瓜,葡萄是牠們更偏好的食物。因此在實驗中,A猴看到B猴拿到葡萄,自己卻多次拿到黃瓜後,表達了複雜的情緒,不僅會將收到的黃瓜往實驗人員身上丟,還會拿石頭往牆上敲,甚至是用手拍打玻璃窗,動作相當大,顯然是生氣了,證明動物也有公平的概念,但是華爾街的股市營業員卻沒有。是的,那個科學家就是瓦爾。
無獨有偶的,當我第一次在《動物行為》期刊讀到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戴維斯分校的研究人員證實鳥類也會為同類辦葬禮,傳統想法受到顛覆的內心,也有同樣的巨大撼動。
科學研究指出,西方灌叢鴉(烏鴉的一種)看見死去的同伴時,牠們會大叫著相互通知並且停止覓食,降落在死鳥的身邊、聚集在牠的周圍,為其舉辦葬禮。為了證明這不是巧合,研究人員甚至多次把一系列的物體(包括不同顏色的木塊、死去的烏鴉、逼真的機械烏鴉、象徵獵食者的大角貓頭鷹標本等)放到後院中,觀察這一區域的西方灌叢鴉如何反應。結果烏鴉對於木塊的反應相當冷淡。然而,發現一隻死去的鳥時,牠們會發出警告的叫聲,警告遠離這裡的其他烏鴉。然後這些烏鴉就會在死去鳥類的周圍聚集,形成雜亂無章的大型聚會。牠們發出的叫聲會吸引新的烏鴉來到葬禮上。這些烏鴉也會停止搜尋食物,這種行為上的改變會持續一整天。有趣的是,這些本來在野外會攻擊生病的烏鴉,或是攻擊競爭對手烏鴉的鳥類,絕對不會撲向這隻死鳥的身體。
至於貓頭鷹標本出現時,這些上當的烏鴉則會以為獵食者已經到來,也會趕緊聚集在一起,並且發出一連串的警告叫聲,甚至會猛撲向標本,試圖嚇走它。
其實我們都不是第一次看到類似這樣的研究,比如長頸鹿和大象,也會在最近死去的近親身體周圍徘徊,證明了動物對死亡擁有一種精神性的概念,會留意到牠們死去的同類,甚至會為逝去的同類哀慟。
反觀人類社會,互相抨擊、踐踏卻是自認為高高在上的人類社會當中的潛規則,宗教和哲學的自負,讓很多人難以接受這種多數時候人類行為其實不如野生動物的觀點,我們不但認為自己與所謂「低等」的動物不同,甚至自以為是地用「道德」的想法,對於其他弱勢者施加即使在動物社會中也會自我節制的暴力和霸凌。我們在瑪琳娜的回憶錄裡看到,在瓦爾的研究中看到,在華爾街的貪婪中看到,在台灣反對多元成家的遊行當中也看到,這些都是強而有力的證據。但是如果我們繼續選擇傲慢的姿態,扣上宗教與道德的大帽子,遮住可以看見事實與科學的眼睛,那才是人類專屬的真正悲哀。
本文作者為國際 NGO 工作者/作家
前言
「約翰,停車!我想出去一下。」
聽到媽媽說的話之後,爸爸立刻看了一下後照鏡,確定後方沒有來車,就把車子停到一個英式鐵路小站旁。他們兩個人好有默契,好像已經做好了祕密協議一樣。但是,其實沒有人知道媽媽想要做什麼。天色已經慢慢變暗,這條安靜的約克郡小路四周全都是深色的樹籬。這些樹籬很高,彷彿就像蠻橫自大的軍事防禦措施,將整個開放空間完全包圍了起來。
媽媽興奮得立刻衝出車外,跳進樹籬中,消失在我們的視線範圍內。我的腦海登時出現好多種可能,現在究竟發生什麼事情了?
我盯著那堆灌木叢,希望能夠看到媽媽要回車上的跡象。過了一會兒,我終於看到她那頭凌亂的黑髮。她小心翼翼地從樹籬中爬回來,兩隻手似乎抱著什麼東西。我看著她嬌小的雙腳踩過樹籬,然後慢慢走回路邊。她跳回車上,一邊喘著氣,一邊對我跟姊姊露出招牌式的拉丁微笑。她的大腿上坐著一隻體型龐大、看起來不太開心的野兔子。「我抓了寵物給妳們喔!」媽媽非常開心地說。
這是我對母親的第一份記憶,當然,這也是我的第一隻寵物「摩普西」。對於媽媽做的事情,我其實不太驚訝。畢竟,如果你一直待在她的身邊,就會了解她非常古怪的個性與各種無法預期的舉止。今天不過是另一個平凡的日子而已。
媽媽常說:「在哥倫比亞,像我這樣的生活其實一點都不特別。只要問問任何街上的小孩,就會聽到很多故事。」她從來不覺得自己的故事有什麼特別之處,因為在一九五○、六○年代的哥倫比亞,綁架、誘拐、毒品、犯罪、謀殺與虐童,只不過是平凡無奇的生活主題。
你或許會好奇,為什麼我的母親選擇在這個時候分享她自己的故事。好吧,老實說,她從來都沒有這個打算。她不是那種想要追逐鎂光燈,進而成名或者獲利的那種人。她真正想要的東西只是一個家─這是她內心最深處的目標與夢想。
這本書的開頭,是作為女兒的我替自己母親寫下的生命故事。當我體認到媽媽已經不再年輕,而她的記憶力也開始逐年衰退時,我選擇以這種方式來記錄自己家庭的遺產。我也希望能夠藉此了解母親過去所承受的苦難,如果她沒有經歷這些苦難,就不會有我和姊姊瓊安娜。
要釐清母親腦海裡面那凌亂、糾結的記憶,其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兩年來,我們喝了無數杯的咖啡,潛入她的記憶中,並在二○○七年四月前往哥倫比亞進行勘查,這才開始將她那些瑣碎雜亂的記憶碎片慢慢拼湊出完整的圖像,讓這本偉大的書籍終於得以問世。
我們並沒有盤算過任何相關計畫,卻很快地發現,出版母親的故事可以帶來很多好處。例如,或許她真正的家人會因為讀到這本書而跟她重逢;此外,全世界尚有好幾百萬的父母親也在類似的情況下失去了自己的小孩,我們希望母親的故事能為他們帶來一些安慰。
這件事也讓那些對我母親而言很珍貴的慈善團體有機會能被看見,像是由我們家族成員成立的非營利慈善單位「棄嬰代養家庭」(SFAC ; Substitute Families for Abandoned Children)和「新熱帶靈長類動物保育組織」(NPC ; Neotropical Primate
Conservation)等等。同時,我們也希望透過一個渺小人類戰勝無數逆境的故事,鼓舞仍受困於黑暗世界中的人們。
人們經常問,我是如何得知媽媽的故事。從來都不是她叫我們乖乖坐好,然後就開始說故事給我們聽。事實上,每天生活裡所發生的事都可能會讓她回想起過去在叢林的日子。舉例來說,香豆莢就可能會讓媽媽想起過去在那個「魔法世界」所發生的繽紛故事。我非常喜歡看著她回想過去時的興奮表情,像是她看見某種植物的圖片時,或者在市場上發現某個品種的香蕉,而那正是那群猴子的最愛。
這個故事不僅記錄了她所講述的故事,同時也包括了她的各項行為舉止。她是一個相當狂野、充滿活力的媽媽,而這一點讓我跟姊姊體認到,她的確是由另一個物種所扶養長大的人,她永遠都是我們的「猴媽媽」。有時候,她會因為自己非正統的教育方法而遭受批評,但是她學習的對象其實就是當初那群猴子大軍。從媽媽身上,我和姊姊就能清楚知道,那些猴子一定是全世界最有愛心、最有趣、最有創造力的父母。
典型的查普曼家庭外出探險日就是母親和我們兩個女孩子在樹上爬來爬去,父親則在樹下研究各種樹皮跟苔蘚(他的口袋裡也必然帶著採集樣本的玻璃瓶);有時我們也會進行動物救援任務,或者會因為想要探索一條小路,也可能是追逐一隻引起我們好奇心的小動物而迷路。總之,這樣的日子一定是以媽媽的烤牛排畫下完美句點─不管什麼季節,我們都會帶上輕便式的烤肉架,就算是雪季也不例外。感謝我的家庭,我幾乎沒有什麼走在小徑上的「正常」散步經驗,反倒是在回家後,會在頭髮裡發現夾帶的樹枝。
我們家的日常生活寫照有著不少令人尷尬的事實,自從搬家之後我就體認到,我們跟一般的家庭是有那麼一點不同。我們向媽媽要求食物的方式完全不同於常人。有時候,像是玩遊戲般,媽媽會拿著一碗甜麥片粥要求我跟姊姊做出最棒的猴子表情。我真慶幸社福機關沒有來視察過我們家。
晚餐過後,我們會花好幾個小時的時間互相梳理清潔對方的身體,把彼此頭髮上的髒東西挑掉。這是一個非常令人放鬆的活動,也是打發時間的最佳選擇,儘管我們三個人在事後看起來就像是嗑過藥一樣地瘋狂。我還記得有次頭蝨大舉入侵我們的校園,那次可算得上是我們理毛事業有史以來的最高點了吧!
談到寵物。原則上媽媽准許我們養寵物,但不能把那隻動物關在籠子裡,那會讓她覺得很難過。因此,我們有好幾隻兔子在院子裡跳來跳去。當然,牠們有時候也會跑去鄰居的院子裡,不過顯然這種放養的模式並不適用在小鳥身上。
由於媽媽不太識字,因此我也不太記得她曾經為我讀過任何床頭故事,不過她倒是會編自己的故事給我聽。她會說一些非常神奇的故事,而這也造就了我少數幾個不怎麼光彩的特質之一,像是在隔天睡過頭而遲到。但是這些扣人心弦的故事卻讓我學到了人生中最寶貴的課程,雖然她總是說自己的人生有殘缺,不過這並未阻止她讓我們得到最好的教養,儘管她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無緣享受這樣的過程。
經過了四十年,哥倫比亞已經變得很不一樣了。現在的哥倫比亞充滿活力、非常進步,稱得上是安全的地方。但是在一九五○年,我的母親還很小的時候,綁架、非法買賣、貪汙、毒品與犯罪等事件層出不窮;而一九四○年代晚期的自由派人士改革,最後只帶來了將近十年的叛亂行動與賊亂橫行。他們將這段時間稱為「暴力時代」,大量的殺戮、虐待、誘拐與強姦,都是相當普遍的事情,整個社會瀰漫著一股恐懼與不安。這個時代的動亂不安造成了成千上萬的死亡事件(包括無辜的小孩)。媽媽的血液中仍然存在著對當時那個哥倫比亞的記憶,她在生下姊姊之後,甚至不願意讓護士把姊姊帶走,因為在她的回憶中,醫院就是犯罪集團用來偷竊嬰兒的大本營。
直到一九九七年,哥倫比亞仍然是嬰兒綁架率前三高的國家。過去的幾十年來,每個星期六晚上的《綁架之聲》(Las Voces del Secuestro)會從午夜十二點播放到早上六點,節目裡的電話會不停響起,所有希望找回自己家族成員的人都會藉由這個節目傳遞各種訊息。那些訊息實在令人覺得心碎。
那些遭到綁架的小孩因為他人的貪婪而受苦,正如我媽媽的經歷一樣。我的母親就是活生生的證據,她讓我們了解生活環境絕對不會是一個人的末路。事實上,正是基於她一路所受到的特殊教養,才讓她成為今日這樣一位堅強、惜福、慷慨、無私與積極正面的女子─當然,也非常狂野與不符合傳統。
在我和姊姊的成長過程中,媽媽從不允許我們生太久的悶氣。相反地,她會激勵我們:「打起精神來!站起來,用妳自己的力量創造出一些新東西!要懂得惜福。還有,快點動起來!」她認為萬事萬物皆有其價值:喘息之間、每個新的一天,以及她生命中莫大的喜樂─作為一個母親、祖母、妻子與朋友。因此,請讓我向各位讀者介紹這麼傑出的一位女人,她想告訴你們一個傳奇的故事。瑪琳娜,我的母親,同時也是我的偶像。
凡妮莎.詹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