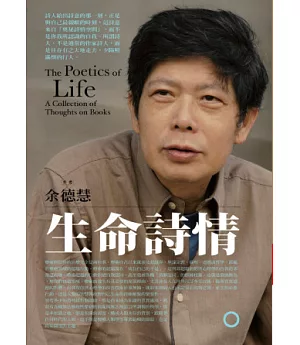推薦序
跟著余德慧讀書 李維倫
人找書來讀,書也找人來讀。前一句理所當然,後一句又該怎麼說呢?
這本以余德慧教授生前所寫的書籍推廌序為主的書就可說是「書找人讀」的例證。本書所蒐集的書序大致落在二OOO年之後,但也有遠至一九八四年;內容包括了臨終生死、靈性修行、心理助人、以及人間情懷的抒發等。大致上我們可以這樣說,台灣這十數年來關於生死靈性與助人轉化方面的相關書籍,多會找到余德慧教授來寫序,為讀者大眾做個導引。余德慧教授與這些書之間就形成了一片閱讀風景。如今心靈工坊將這片風景集中呈現在讀者面前,我們看到的不只是一位學者的文筆思考,更是台灣近年來在人文心理靈性上的一股思潮風光。有了這本書,我們就可以跟著余德慧讀書,像是有了一個閱讀的總脈絡,指引我們踏上安定心靈之旅。
余德慧教授又是一位怎麼樣的學者,讓這些書來找上他呢?我想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所長林安梧教授對余德慧的形容最為貼切:出入生死、幽明來去。據余德慧教授的師長舊友言,他早年浪漫倜儻,對人情世事常有不拘世俗的看法;關注華人社會中的心靈受苦,但又是一位非典型的臨床心理學家。一九九五年從全台首學的台大移教花蓮東華大學,自認為最好的選擇,並專注於臨終照顧與宗教靈性的研究。至此余德慧教授出入來去的,不只是人間世俗的範疇,還有生死幽明之境;其學問文章,也就成了學生與讀者大眾在生死聖俗間的思想中介。
雖然其為人為文從浪漫倜儻到生死幽明,余德慧教授所中介呈現的閱讀風景之旅卻是要倒過來走,也就是從生死瀕臨知見自我誤識,再回返修行工夫寬諒人間殘酷。本書的編輯大致上也是以此為順序,容我說明如下:
跟絕大部分心理學家不同的是,余德慧教授深深質疑以「心智自我」造就出來的現實。這個心智自我並非某一個人所擁有,也不是因智能高低而有所分別;它是在世界上的常人共享且用以建立「常觀」、驅逐「異常」的思維態度。對心智自我來說,人生最大的「異常」也是最想去除的,卻是人人都將抵達的死亡。然而余德慧教授從他的實務研究上看到,死亡不是人生的挫敗而是恩寵;其所恩寵者即是讓人得以脫離自我的誤識進入存有的寧靜之中。當人在世急急忙忙汲汲營營,感到時間的困窘時,死亡卻贈予人們最屬於自己的時間。這話聽起來矛盾,但余德慧教授用種種說法說明給我們聽;這認識不容易,但有余德慧教授起了個頭,我們大家就有機會體會到「生死共命」。
余德慧教授對於宗教靈性的理解,自然不會隨心智自我的價值起舞。對他來說,靈性修行不是世俗成功的勳章,卻可能在道德裂隙中滋生。許多宗教的教門論述要人們行善福報得善終,他卻提醒這其實是心智自我的編織,極可能對人生的不堪處行使殘酷。余德慧教授雖不以教門為準,但也不以教門為忤;他並不帶給我們二分對立的思維,而是引領我們進入存有的原初處境。
余德慧教授堅持自己是一位臨床心理學家,而深識存有原初性的他自然拒絕心理受苦被精神病理診斷學綁架,因此他對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就有了獨樹一格的看法與實踐。余德慧教授認為心理受苦實是倫理受苦,是人間的倫理規範使得情感難以有出路,因此他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原初倫理,接引受苦之人的原初情感。余德慧教授並不反對心理師專業化的建制,但期許心理師成為真正的心理治療者,讓受苦者依靠。這樣的心理治療者要能夠反出專業知識的限制,深入廣袤的人性空間,同時也要能帶領受苦之人悠遊於人情義理之間。這樣的治療者技藝並不容易養成,但最關鍵的要看心理助人者要不要認了這條路。
如此看來,就能明白余德慧教授對底層生活者不可言喻的溫愛。底層生活不僅指貧窮生活;富有之人也會有靈魂深處的煎熬,一無所缺者極可能遺失了匱乏。余德慧教授敏感於說三道四泛泛之談所遮蔽起來的人間圖像,他要為人生不堪聞問處與倫理不及處尋得人間寬容。這樣的傾向,我認為,即是他舊友口中的對人情世事不拘世俗;現在看來,恐是余德慧教授一生無法擺脫的柔軟慈悲。
如此,從本書的三個主題,「瀕臨/生死道場」、「靈知/身心轉化」以及「祕思/詩意綿延」,我們得以見識余德慧教授帶領的一路閱讀風景。在當今台灣媒體以殘酷的爽快來荒蕪我們的心靈生活時,或許這片風景可以讓我們溫潤寬諒滿溢胸懷。
而我正是因這片風景而獲得滋養之人,謹為之序。
本文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推薦序
看似無序卻有序:傾聽地閱讀余德慧教授「說」書 林耀盛
文之序:閱讀沒有固定起點,盡是通往充滿詩意人文涵養深度風景的窗口
這本書,是紀念余德慧教授逝世週年的致敬作品。余老師生前飽讀各類書籍,以柔軟慈悲的溫潤心思,搭配講真話的批判風骨所寫出的各式序言、時論、散文,以及專刊(欄)文章,分散各處。如今,以余老師為書本推薦導讀或書寫序言作為主體,搭配其他重要文類的選輯,結集成為這本書。
書籍、翻譯或論文合輯,出版時經常包含序文。序文是一種開端,一種導論,一種介紹,但可能也是一種個人風格閱讀觀點或是意見評述。序文,可以正經八百、引經據典;當然,也可以音隨詩響,純然是一種風雅頌賦比興的隨唱,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也可以是長篇大論,當然也可以是充滿禪意的極短篇,頓悟後的嘎然而止。
有時,序文涉及一種臨床現場的評論(clinical/critique),所以,隨著不同現場的文本,逐漸建立評論系統書寫,也是一種原創作品的傳統。藉由序言所引介的書籍,可以延伸到所介紹圖書之外的相關書本,這就不僅是導論寫序的書籍本身的閱讀,更是繁殖至其他書本觀點的接引,書中書、書外書、乃至不同書本的並置閱讀,納入序言的寫作系統,使得序言評述也成為一種意義/異議文類。如此,序言也是一種寫序者涵養論點的呈現,審度忖思序文,也可以成為理解、接近撰序者的一種沒有固定起點(任何一本書的序言都可以是起點)的開端。因此,余老師撰稿的序言、時論或專刊(欄)文章的合輯,無論是推薦何類書籍、不同寫序風格的展現,或是其他文章的系列書寫,某個層面來說,這本書也是一本進入余老師思想遺產起點的重要原創作品。
當初,這些散落各類書本、雜誌的序言或文章,如今以「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般的包容匯流起來,成為各位手上的這本書,這是另一扇閱讀、觀覽余德慧教授在學術思想之外,另一面充滿詩意人文涵養深度風景的窗口,值得細品與珍藏。
進一步看,余老師的文字思想所沉澱出來的風格藝術,創造出書寫藝術就是「大地之歌」,這「歌聲」是一種本真的命運性的「痛苦」,這本真的「痛苦」卻是一種真正的快樂。詩人里爾克(Rilke)是貧困時代的詩人,曾說這種快樂是生成詩人的本質。詩人因此「痛苦」而感受到深刻的愉悅,進而歌唱這種愉悅,這就是藝術何以可能的內核根基。藝術總是充滿各種創造真理的場域,以苦痛鍛鍊出來的生命詩歌,有時雖會體現出各種奧秘主義的體驗現象(各位可在此本書中發現如此的痕跡),但終究是立足大地、仰望天空、等待拯救,以生命成就書寫藝術,在苦難中的愉悅所凝聚轉化通透出的真知灼見與本真行動。
余老師的文字,有時許是「後現代諾斯替(Postmodern
Gnostic)」靈知派風格。諾斯替認為我們苦苦追求的知識,其實是為了體驗與修行。諾斯替知識作為一種精神活動,與哲學的理性認知有著極大的差別:一方面,它與啟示的體驗緊緊聯繫在一起,或者透過神聖的奧秘知識,或是通過內部的覺悟,以對真理的接受取代理性的論證,它作為對人狀態的調整,本身就肩負起拯救的職能。另一方面,諾斯替派,是徹頭徹尾的異質,先天就必須被標示為異教徒,擺明了對自我存在的抵抗,而不是自我的撫平;擺明了一種對知識的急遽拉拔,而不是緩慢的醞釀;同時它也擺明了自身的異端,由此也產生自我裂解的必要。如此的異質觀點,也反映在余老師對於書籍的閱讀方式,直逼到書籍背後的底線,以自我裂解的方式編織進入書本內裡,然後以渾成的生命經驗,讀出奧秘性體驗,再一語說破當代人的癡迷。
文之序:是存有異化的見證,書寫的回憶也喚起存有的遺忘
如此,每一篇排列看似「無序」的「序言」,卻是有序地點現出一種卡夫卡式的風格。
卡夫卡(Kafka)的《在地流放》,早已預言了機器發達資本主義,終將異化人性的故事。強權者使用一種古老的機器,機器將花體字母刻畫到罪犯的背上,印刻的傷痕增加,圖案不斷累疊,直到犯罪者的背上,有了預見力,能夠自己辨認出這些字母,讀出自己所不知曉的罪名。這就是扛著罪名的脊背。同時,犯罪刑台刻字的凌遲,也成了一種景觀。卡夫卡的作品中,隱喻地說,背上一直都背負著某種責難的罪名。余老師的多重序言,某個程度上,也是。
余老師的文字思想,有人認為艱澀難懂,有人認為語法費解,但那是用生命刻鏤出來的閱讀經驗分享。余老師早已認出人性異化與科技支配的雙重過失,嘗試指出人文精神的復甦,是可能的療遇之道。若不回到人文精神的臨床反思,人類將不過如思想家傅科(Foucault)所說的,人是短命的歷史化身,猶如「沙灘上的足跡」,浪濤襲打而來就蕩然無存。余老師的風格,是向來不被既有的意念或概念限制,而能通透自由的智慧越界,更能「不動心」(ataraxie)。不動心,即使面對責難,或被視為異端,仍以智慧勇氣面對各種挑戰,顯現不受到任何情緒影響的寧靜狀態。閱讀余老師每篇書籍的序言,就可體會書寫當下,所背負的各種可能責難的心思狀態。
當然,這個罪難的標記,或許是在我們自己身上,只是,我們喪失辨識的清明心思。不過,透過余老師的文字,可以直抵「黑太陽」,讓我們直面生活中的生死大事,以及碰撞身心靈性轉化道場的艱苦功課,使我們可以從「存有的遺忘」與「記憶的剝奪」處境下,找到歸來的路途。精神分析寓意下的「黑太陽」,是一種「抑鬱」,是一種悲痛的深淵,一種無法溝通的哀愁,有時候,而且是長期性地,從我們的身上取走文字、行動,甚至生命本身的意義。但如此的「抑鬱」,也「意欲」將我們帶往「異域」,這是一種「流離失所」的擔憂狀態。思考的困難、書寫的痛苦,是置身精神異鄉的徵候,也是老師透過文字書寫表達,樂於推薦書籍的翻轉時刻。於是,當迷路時的守候,是為了找回追憶、思念與往昔;有時,不是找不到路,而是路向太明確,以致於猶豫,生怕是否回到不再熟悉的陌生地,且主人還在那裡嗎?
或許,不是近鄉情怯,應該是想像家是一種離不開的方式,擔憂一腳陷入「精神異鄉」的漂泊;但不曾遠離,就不會懂得回家。因此,家是一種弔詭的所在,鄉愁是遠離,失所是遠去,哪裡是存在者的家?有道是:人無法選擇自然的故鄉,但人可以選擇心靈的故鄉。我們心靈的歸宿,不斷在找路、迷路,或是封鎖出口,或是等待歸鄉。但無論如何,坐下來,傾聽地閱讀這本「說」書,會讓我們感受到,即使是人們記不得路,書寫仍然召喚著這個回憶,它以此召喚著自己,把自己從回憶中叫回來。
文之序:一場存在交談的餘音,讓彼此進入境域融合的伴行關係
這麼一來,閱讀本身彷彿就是一趟自我精神分析的路程。關於精神分析的實際操作,佛洛伊德(Freud)認為就像棋譜一樣,往往只有開局與結局的呈現,其過程依個人的不同而變化萬千。許多方式是依個人的習慣而定,分析師也應依被分析者的特質與個人的理由作適當的調整。本書的閱讀位置,當然不是去複製體驗或製造定論,而是透過本書所收藏的不同書本的序言或感懷文類,當閱讀每一篇文章時,彷彿是在下不同的棋子,讀者以自我佈局的策略,深刻體會不同書寫文字所構成的棋盤局勢。每一次的閱讀經驗的啟動,就像是歷經棋盤局勢變動中,不斷尋找自我精神的位置。如此,寫與讀、說與聽的互為關係,也同時開啟自我分析的路程。
詩人賀德齡(Holderlins),有一句著名詩句:「自從我們是一場交談,並且互相聽到起」。聽到,不僅要相互聽到對方,還要求彼此真正能聽取而交融互疊,打開每一個有限視域的局部性。這種積極的聆聽向度,一旦打開之後,交談對話才真正進入互動的相融時空,也才開始相互回響應答,彼此產生交互奏鳴的餘(余)音後遺效應。如此,再遭遇怎麼樣的黑太陽,也就可以尋找到相互同行的伙伴。
於是,我們在如此互相傾聽地閱讀,以正念/覺照/脈伙(mindful)的處境脈絡下所形成的伙伴關係,緊密形成一個共同參與、共享共有,且充分交流之存有共同體的新組合結構。關於mindful這個字,余老師有深意的以音譯方式,指出這是在生活裡,採取一種非常精緻的內在覺照。但這個音譯的延伸意涵,其實也是點出了覺照不僅是個人的事情,而是在一種共在、成為伙伴關係的脈絡下,以覺照的心思互相理解。如今,聽余老師的「說」書,這本書的序言文體組合結構,正提供了一個視域融合的平台,使我們透過閱讀理解置身所在,進而回應變動時代的罪愆,為生活的倫理困境尋找出路。
當然,序言總有未能說出的另一個地方,如此也讓各本書的生命保持在隱晦之中。與其說未能說出的隱晦是一種禁止,不如說它呼喚著被破解。
永恆缺席的字母,破解的密碼,要能道出一切,只能發明字母,解譯閱讀的密碼。閱讀成為一種存在,是呼喚這個密碼的姿態。本書是各式各樣序言、文類拼盤所構成、端出的精神食糧,所承載的詩意與書義,彷如「人生殘缺,一碗承受」。正因還有未能說出的,所以,說得更多了。
餘(余)外之音,留待讀者的細膩諦聽。
本文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推薦序
追尋一個逝去未遠的身影 彭榮邦
最近的這三年,我陸續失去了兩個親近的人,一個是與我結褵七年的妻子,一個則是與我相識二十多年、帶我走進人文心理學領域的恩師余德慧教授。短時間裡痛失兩個親近的人,讓我對於「失去親人」這件事情,有著深刻的體會。我這裡所說的「親人」,不必然是血緣之親,而是關係之親。親人和我們的關係總是盤根錯節、交雜著愛恨情仇,但是他們的一顰一笑、一舉一動,總是不自主地牽引著我們,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生命樣貌、我們的存在安適感,以及我們的自我感受。因此,失去親人不僅是失去一個同在之人,它對我們的生命而言,亦是一種深刻的撕裂傷,原本是面容相對之處,頓時成了毫無回應的虛空。
一年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就「失去親人」這件事來說,似乎總得走過完整的一輪春夏秋冬,我們才會深切地體認到「逝者已矣」,那個我們親愛的人,真的和我們已經不在同一個世界了。
余德慧教授的辭世,至今也快一年了。這一年來,我們幾位師承余德慧教授的弟子們,每個月在老師家裡有一次名為「余居於世」的固定聚會。「余居於世」取自「寓居於世」(being-in-the-world)的諧音,一方面點出余德慧教授的思想傳承(深受德哲海德格影響的現象學心理學),一方面也點出這些弟子們的心思——希望余老師開拓出來的學問道路可以餘(余)音迴盪、長居於世,不會因為他的嘎然辭世而斷了香火。
然而這個香火該怎麼延續,甚至,我們到底要傳承什麼樣的香火,其實一開始並不清楚。我們就是固定聚會,時間一到就往老師家報到,每次都有人輪值報告,之後再由其他人回應。一開始我總覺得老師還在看著,或許是隱身在屋裡的哪個角落,任我們七嘴八舌,狡黠地笑著。後來比較沒有這樣的感覺了,卻察覺到在每個人身上,多少都有余老師的某些話語姿態、某種特屬於他的身影。這樣的感覺,在幾次聚會之後愈發強烈。我逐漸發現,雖然余老師的肉身已經消逝、化為塵土,但是他卻彷彿投影在我們每個人身上,只是化身千萬,藏在那些被他點亮的思想裡,在那些與他交會的生命經驗裡。
斯人已逝,卻未遠離。我們只是沒有發現,我們在悵然中一再追尋的身影,其實並不在未知的他方,它早在我們身上成為某種生命的微光。只要我們重拾這些微光,它們終究會匯聚成為更大的光亮,有如內在的火炬。而在火炬之下,我們會看見余老師巨大的身影,與我們一同前行。
余德慧教授為許多好書寫過序言,它們彷彿遺珠一般,散落在各處。感謝心靈工坊在余教授過世週年之際,費心將這些序言編輯成書,讓這些智慧話語不至於成為遺珠之憾。我知道余德慧教授的文字曾經在許多人困頓的時刻,點燃了些許光亮。或許這些讀者可以藉由閱讀這本書,和我們一起追尋那個逝去未遠的身影。而那些還沒有接觸過余德慧教授文字的讀者,我相信,這本書總有一些段落,會成為你生命中的微光。
本文作者為慈濟大學人類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前言
身心靈書籍的演變
大約在六十年代,美式的「心靈解放運動」透過反越戰的熱潮而崛起,提摩喜(Timothy Leary),一位因試驗品嚐LSD而遭哈佛大學解雇的心理學教授,帶領加州的越戰抗議者比出心靈解放的手勢,同樣被哈佛大學開除的伙伴雷達斯(Ram
Dass)則以心靈導師的身分領導美國身心靈運動,在學界,存在主義的心理學家、哲學家以及現象學家參與了身心靈療癒的理論工作,而使得身心靈運動在學術界的一角獲得歇腳的機會,在七十年代慢慢醞釀出「新時代運動」,參與的學者融合物理學、數學、心靈學、中國的老莊、西藏的佛典、中東的蘇非、印度的瑜珈、北美印地安的薩滿,提出一連串的身心靈修練之道。
這身心靈療癒運動一波波往前推移,在八十年代末期,新時代運動遭身心靈界的批判而走下坡,繼之而起的是九十年代的實踐身心靈運動,這個運動以臨終照顧為核心,發展出許多生死有關的實踐議題,也帶動身體-心理-靈性為主軸的心理照護。這條身心靈運動的本質既非勵志,亦非宗教修行,而是繼六十年代的政治抗議所轉變成精神養生的綜合體。
首先,它不是勵志。身心靈運動從社會抗議轉入內心活化,因此有很強烈的反俗世性格,在理論上,俗世的心靈被稱為Ego(自我),在勵志的脈絡下,「自我」是被肯定的,無論己立或立人,都必須使自我精壯,而精壯的自我成為處事成功的要件。中國傳統的勵志書,如《了凡四訓》、《菜根譚》、《小窗幽記》都有明顯的處世技巧的探討。《了凡四訓》強調行善可以成功升官、延壽,《菜根譚》則以二元的對比與辯證指出各種應事理法、尺寸拿捏之道,而這些精壯自我卻是身心靈所批判的,認為「自我」所造就的現實其實是阻礙心靈開發的元兇,人無法獲得心靈本心的認識,正是因為受阻於「自我」的「妄識」。
身心靈運動的「反自我」是有原因的。許多實踐的身心靈運動是從人的苦難處出身的,尤其是末期癌症到死亡之間的時間,病人特別受難,一方面外在世界已經逐漸證明其無益於身心靈療癒,即使擁有最好的醫療、最成功的事業、最美好的人間關係,都與眼前的死亡疏離,繼續把心智投入這世界其實是徒勞的,另一方面,「內向轉向」(inward
turning)成了一種死亡前的反歸家園,我們真實地感受的內心的害怕、愛、喜悅與痛苦,也希望有相關的論述來支持內在轉向之後的精神領域。
其次,它不是宗教修行。一般宗教修行以教門的教義為修行的框架,依教奉行。但是身心靈療癒並不遵行任何宗教的教義,雖然身心靈運動者可能會在泰國叢林修行,或者在西藏及其鄰近地區(緬甸、尼泊爾、北印度或不丹)追隨喇嘛古魯,但是他們的論述自由出入於老莊、佛、基督、蘇非之間,他們冥想的論述可以摻和禪的靜坐、道的丹功與天主的冥想,身心靈修練者從不忠於任何宗教的意識型態,也不舉旗迎這拒那,望似聯合國的雜牌軍,其實反而是朝向更自由寬廣的心靈世界。
再者,它不是哲學。身心靈運動的論述全非哲學論述那套語法。表面上身心靈書籍與存在哲學很親近,但是那只是觀念的親合,在根本的意涵是非常不相類的。身心靈書籍不太理會思辨,反而類似宗教文本,對某些觀念大力推展。身心靈書籍論述有非常清楚的選言綜合,他們雖然毫無顧忌地使用哲學家的話,但絕不是去質疑它,而是用來輔助自己的觀點。一般的身心靈哲學也不會參考這些身心靈書籍。
實踐性的身心靈書籍通常會在某些特殊領域發揮特定的效果。以索甲仁波切的《西藏生死書》來說,這是一本綜合藏佛大圓滿教法的實踐版,人們可以從前半部獲得具有啟發性的「反俗世」念頭,但在後半部則以臨終照顧的具體施為為著眼點,索甲將藏佛臨終中陰的各種情況放入具體的病人處境。他的弟子龍緹可則是從生活經驗層面,將自己喪夫的過程以及她如何參與安寧照顧的方式,搭配索甲的論述而成為非常實用的準則書。最富有代表性的《好走:臨終時刻的心靈轉化》(The
Grace in Dying:how we are transformed spiritually as we die)這本書則以蘇非的心靈圖誌為引導,細數臨終的各種狀態,以超個體心理學的論述來疏導人們對死亡的恐懼。許多讀者在他們的親人過世之前,發現這些書是他們在徬徨無依的時刻,所給予的最大的指引。
這世間的知識日益膨脹,但對身心靈的認識卻幾乎不存在。瞭解生理的醫師越不過心理那一圈,瞭解自我心理的心理學家越不過靈性那一圈,而似乎瞭解靈性的宗教師卻常常引經據典到與事實脫節,甚不知所云。許多初接觸身心靈書的讀者常常會覺得不得其門而入,一方面人們越來越不相信那看不見的「領域」,如靈魂、能量、本心等慣用名詞,不是覺得過度抽象就是覺得實證性不夠,另一方面,身心靈書的背後假設與一般知識書很不相同,如果讀者用他的習慣態度來閱讀,往往難以接受身心靈書的論點。
我個人因為長期在臨終病房擔任志工,也做了多年國科會的專案研究,包括對臨終神聖、臨終啟悟、臨終陪伴等議題,使得我不得不注意身心靈書對家屬的幫助。許多朋友在他們親人往生之前,徹夜哭著讀這類書籍,使我動容。我發現,對面臨深淵的人來說,身心靈書籍要有幾個特性才能發揮身心安頓的力量:(一)作者必須有經歷深刻體驗的受苦歷程,並能將受苦與離苦的中間步驟說清楚,而不是談玄說道,信口開河;(二)必須將實徵與理論扣緊,讓引導的圖像具體跟著實情走;(三)作者有深刻的啟悟經驗;(四)不傳任何特定宗教。
我曾經讀過最具震撼力的身心靈書是哥倫比亞大學神學教授盧雲神父(Father Henri Nouwen),在他毅然放棄教職,到一家重殘病患之家擔任義工,在他過世的那一年,他寫就一本小書《亞當--神的愛子》(God's
Beloved)。亞當是他照顧的一個重殘小孩,無法言語、生活無法自理。盧雲的經驗剛好顛覆一般宗教的觀點,別人憐憫亞當,說他可憐,盧雲卻發現亞當的沈默神性。這是很深刻的東西,盧雲鑽研神學四十年,不如他當義工一年的啟悟。
身心靈書寫的不是知識而是體驗。許多假身心靈書會偷渡超心理學、宗教意識型態。身心靈書籍的正典性來自於對身體的重視。但是對身體的重視不在於養生(如道家的成仙之道),而是某種現代意義的「道成肉身」:身體是修練場,我們在身體的作為裡創造精神(神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