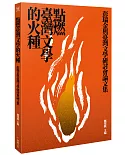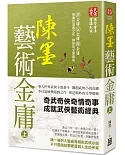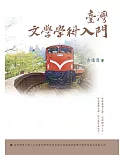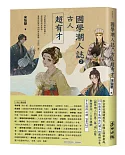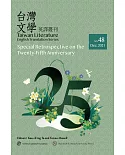後記
距離我上一學術專書《想像台灣:當代小說中的族群書寫》(2007)至今,已是七個年頭,這之間我經歷了研究關懷的大轉向,從原來解嚴後台灣純文學小說中的族群論述,到跨國脈絡下的台灣推理小說。這中間,我從一個原來因為具有高度政治性、極為喧囂的學術議題,來到泉源隱隱作響、看似一片荒蕪的應許之地,而我的使命,是要努力將它栽植成一畝歧徑花園。
學術場域中的朋友們總是問我,為什麼會研究推理小說,為什麼會對常人所不欲見的犯罪景觀感到興趣?雖然我總是回答,因為這是一個台灣研究中長期被忽視,但其實相當值得開發的學術領域;這是我們這代,隨著許多師長們從既有學門、領域走出來為台灣文學研究拓荒的五、六年級世代年輕學者,必須負有的使命,建構出這個領域的主體性,開創出這個領域豐富的跨國性。
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在《存在與時間》(Being and
Time)中說人是「邁向死亡的存有」,推理小說何嘗不是。它的故事雖然總是從死亡開始,但所有角色的一舉一動,最終都還是要朝向死亡的謎底,是一種直面死亡、重臨死亡、珍視死亡,透過死亡的重量照見生命的意義,尋找救贖的一種藝術形式。因此有別於其他文學類型,在推理小說中我們傾聽死者的話語,與死亡對話,尋找曾經的生命真相,不僅是安慰生者,更是給予死亡高度的尊重。對我來說,研究推理小說的意義更在於此。
2007年出版第一本學術專書時,父親剛從一場大病中痊癒,那是我生命中他第一次住院。2011年初,我開始著手準備這本書,他二度入院,這次他卻離開了我們,而我也成為了生命中擁有最哀傷的內核、一個真正必須在未來的日子裡,不斷與死亡對話,開啟生命真相的人。但慶幸的是我已然學習到,死亡的尊貴之處,唯有在我們「餘生」的存有之中,方能尋找到意義。
在完成本書的過程中,最要感謝的是日本工學院大學吉田司雄教授對我在推理小說學術思考上的諸多啟發,另外包括名古屋大學坪井秀人教授、東京大學藤井省三教授、愛知大學黃英哲教授、日本大學山口守教授、橫濱國立大學白水紀子教授、垂水千惠教授、北海道大學押野武志教授、北海道情報大學諸岡卓真教授,以及前推理文學資料館館長權田萬治先生、東京創元社顧問戶川安宣先生、講談社田村良先生、評論家大森望先生、玉田誠夫婦,對我在日本進行研究與發表論文的過程中,給予許多建議與幫助。
此外許多國內外學界的前輩、朋友,包括王德威教授、廖炳惠教授、梁秉鈞教授、黎湘萍教授、阮斐娜教授、林大根教授、金良守教授、李瑞騰教授、陳芳明教授、江寶釵教授、黃美娥教授、林芳玫教授、楊翠教授、蔡建鑫教授、張文薰教授、陳建忠教授、須文蔚教授、吳明益教授、徐詩思教授、涂銘宏教授、黃淑嫻教授、魏豔教授、林建光教授、陳淑卿教授、封德屏總編輯等,以及論文投稿過程中的諸位匿名審查委員,在此也一併致謝。他們或是對於我在研討會上的發表,以及投稿期刊的過程中,給予我論文上的許多意見與提醒,讓我的論述能夠更嚴謹;或是對於我投入這個領域研究上的肯定,提供發表與成長的機會,對我來說都是莫大的鼓勵。
當然,本書中的諸篇章之所以能夠完成,國科會、教育部、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中心、文學院等單位研究計畫的支持居功厥偉。而包括金儒農、林佩珊、陳盈妃、廖師宏、林歆婕、楊勝博、楊若慈、楊若暉、鄭心慧、施佩吟、郭如梅、李文瑄等研究助理的協助;以及在日本發表論文時提供翻譯協助的日本北海道大學博士生李珮琪、成田大典、井上貴翔等,也都相當感謝。
此外,也是最重要的,是國立中興大學以及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同仁們,邱貴芬、廖振富、李育霖、朱惠足、高嘉勵、汪俊彥諸位老師給予我最大的支持與關懷,若不是因為這個環境給予我最大的學術空間與自由,以及豐富多元的學風,我無法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發展出如此突破性的研究。
最後,要感謝我的家人。母親無微不至的關懷,是我在學術場域努力的原動力。父親雖然畢生都受到半世紀前中日戰爭的影響,甚至長期對日本懷有強烈的負面情緒,但對於我與日本學術界的研究與連結,卻從未有過任何一絲反對的意見。他讓我知道,父子之情永遠可以超越國族情感,而我從沒有一刻停止思念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