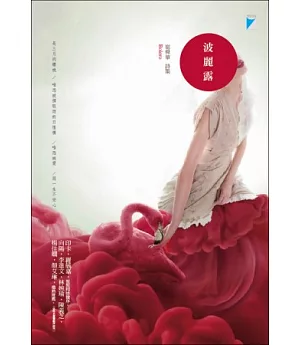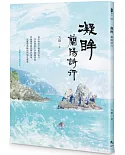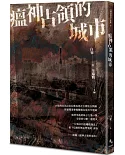推薦序一
給我們的女媧∕羅毓嘉
「成人之後
我對世界毫無戒心
春天來時,爪上的傷痕總是發炎
金色的膿血滴落地面
泥濘裡
開出碩大的杜鵑」
──〈一生〉
舜華寫詩,我也是。舜華日益清瘦,像她的詩句,不知怎能負起種種交纏糾結衝突與拉扯,但世界著實很難,便讓她顯得簡單。她寫了超過五百首詩她準備出詩集了邀請我給《波麗露》寫序,當時我一口應允了,卻更該問她──我怎麼能夠?聚首的時候我們甚少談詩,慶幸在酒食煙霧裡的一個個夜晚能令我們齊將白日的疲憊褪盡了,勉力帶著各自的釋然各自回家。
那光景常是生活的罅隙,在露天的酒吧我們飲了一杯又一杯酒。然後,我趕赴下一場酒攤有時我們同路往城市之南,有時候我跳上計程車而有時誰來載她,城市明媚的夜色罩著酒意薄醺,搖曳像豐饒的海。
舜華寫詩。她請我給她的詩集寫序。
認識舜華的詩先於她的人,在網路論壇,新聞台,讀她寫,「那裡展開道路,你來之前∕新的磚石鋪就,新的溫差∕令敏感的女性輾轉難眠∕臨廄眺望,焦碌異常∕你來之前,我趕赴濾清一場枝節∕沖一壺上好茶葉∕剪落透明的指繭」〈你來之前,我的忙碌〉,一度猜測她的人應該像她的詩,清瘦,繡金,時有細節豐滿而輕盈。
若要我為她寫序,我能找尋個合理的切入點,或許從女性詩學談性別的傾斜,或從中文系的傳承與流變談她詩中意象的篩揀,我能耙梳外在的條件因果與敘述,若以這些寫序,都成立,都簡單,但並不能夠。並不足以說明她的詩,她的人,更不足以為一本書,成一篇序。理當要完整照顧一本書的層次,我幾度下筆又刪去,先擬了草稿,一夕醒來重讀她的詩行,卻驚覺我的序文竟沒一行能用。
這讓我躁慮地翻看星相是否正逢月空亡。是她的詩令我顯得迷信。
「像一臺播放呢喃雜音的點唱盤
失去音樂,也許覺得還好
還能一步步向上拾階
還能專心,問一句話
燃一炷香」
──〈信神〉
詩是人生當中難得的雪景,好詩,卻更像是把火,將綿密的雪原給全數燒融。
她寫詩。如絲綢般披開如雪如浪的詩,想起我第一次見她。
那是《2009臺灣詩選》的發表茶會她戴頂白色毛帽茸茸的頭頂,長靴蹬著會場大理石的地面把所有人都變成馬,於是我閃躲。遠看她清冷的薄唇非常像她的文字,「使用精瓷茶具沖泡雜穀麥片時∕從肩膀脫下純棉白色睡袍∕任其掉落於遠東婦女的手織地毯上時∕……∕思考關係,以及彼此關係間的關係」〈你那麼帝國主義他那麼病〉,但之後,卻明白了舜華的詩不是姿態,而是不確定的姿勢之間,一再的轉換與詰問。詰問怎會在行走時愕然失去了路,「曾如霧中降下的雨∕刺啄我朦朧的感官∕與其它容許被言說的形式」〈行走時失去了路〉。
清冷的荒原,卻充斥聲光燈色,一個怎樣的時代讓我們喝乾一杯再乾一杯,沒有答案。還是問,越繁華就越是寂寞。
是繁華,讓愛充滿毀滅。
時代的改變無疑讓我們這代詩人再難專事寫作。於是打開城門放生活進來,磨耗了,於是尋求愛的慰藉,放任隻獸啃噬我們的血肉。她換了幾次工作,我們接著談生活的艱難,相應於背叛與照護的種種音色我們飲酒,食麻辣鍋,撈出幾塊鍋底鴨血豆腐食畢了就大聲碰杯,笑中帶淚,譏嘲彼此的順利不順利。生活與愛無疑是她詩行間透露著的,艱難的本質。
生活的安定不安定,愛恨都是信任不信任。猜疑與憤怒,溫柔和依靠,背叛與照護,愛起來她寫「你衣著簡便∕體魄康健∕耕作勞動時帶著知更的機敏∕我在屋內捲菸,斜倚床沿∕用親手採集的棉與麻∕編織秋天輕軟的風景」〈九月的時候我已深深愛上你〉,又揭開愛離去後徒留的傷口,有的已經結疤更多則不。
當舜華說起信匣裡曾不斷傳來惡意的簡訊,我試著聆聽她內在激烈的尖叫與碰撞如她在風中會有一襲亂髮,那些壞的主管壞的情人,一日起始一日終結,無詩無歌的時代開展了日常生活的無歌無詩,我們掌心還有酒一盞,還能慶幸我們「彷彿就此釋懷過往∕你那麼帝國主義∕他那麼病」〈你那麼帝國主義他那麼病〉。慶幸自己還能愛,但愛為什麼總是帶來傷害,讓人不安,為什麼,她的詩貼得身體那麼近,最後卻必須發現愛到極處並不生恨,卻是再不能愛?
「將左手反縛背後
成為一把鎖,鎖起脊椎
鎖起開放的身體
鎖起淫逸、不安的戀情
……
是三月的櫻桃
唯恐被摘取而終日惶慄
唯恐被愛
而一生不安心」
──〈安全感〉
和舜華相比,想來我算是生性樂觀到無可救藥的那種人了。有次,在手機上的對談我這麼說,「我們都曾受過傷害。無論嚴重不嚴重但總是會好起來。」她則說害怕自己無法好轉無法抵抗,她接連問了幾個為什麼她問。問了但沒有答案,怎麼會有?眾多傷害的線索,折磨的細節,苦痛的黃昏與自己負重的整個晚上,連續發佈了幾則自棄的訊息我打電話給她,但不能幫她承擔一個世界墜落的試煉。
幸好幸好,那些都成了詩的原點。若沒有了詩,生活會是什麼?
這問題我們都想過,但不敢問。甚至不敢設想,所以持續地寫詩像飲酒抽菸餐食間,舜華不斷拿個小杯斷續吐著口水的一個晚上。一個晚上她吐出了可能有三十西西我想那是靈魂和甚麼的中介物。而詩人難道不是世界的中介物嗎?一個詩人她活在豐饒的時代「大量的物質,雕花精瓷∕供應每日清晨∕一刻鐘的自我輕賤」〈閉居者〉,「將久病的肌膚寫成了字∕嵌入淺眠的掌紋∕若你碰觸我,便可閱讀」〈六月〉。
吐出絲,寫成字,經年累月於是有了這冊《波麗露》。
「有如南島未降的鵝毛細雪
給予世界一點細節
我們感到缺乏主張
因而想罷了手
因而想回頭張望」
──〈十二月〉
讀舜華的詩她明顯是個好的詩人,讓我閱讀讓我發著熱度意圖抄寫。抄寫〈煉人絮語〉,抄寫〈我的夢重疊著他人的夢〉,每一個細節她縫補她錄記,她寫下的所有事物,生於傷害、煉於烈火,卻生成了彩石,她騰身飛起,補滿我們蒼白的天空。
若女媧生在當代我想那就是她。
「為什麼生存是容易而∕艱楚的?容易得∕像過敏時草率丟棄的噴嚏∕艱楚得像一夜爭吵後∕伸出手臂∕挽留掩門離去的愛人」〈我心中的瑰寶〉因為目見這生活當中無盡蔓延的細屑與破碎,感覺無可奈何但仍戮力將之縫補;因為堅信世界的美善,堅持對愛的信仰能補滿了天空遽然張裂的破口,「在重修五次的課堂上∕你提問──為什麼∕女人有知更鳥的咽喉?∕為什麼做愛∕適合在仲夏時節∕一場淫蕩的雷雨之後?」〈我心中的瑰寶〉發問然後復原,堅信痊癒的可能,遂日日煉石,以詩補天。
於是在《波麗露》的最後一行,她寫「最後你說:∕繁∕轉瞬間,愛人的眼睛∕萬花盛開」〈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
我必須這麼說──盤古闢地,女媧補天;世界因盤古而生,但無女媧,就不可能真正完滿。在這一切善美均近崩壞的時代,愛情升起而又覆滅,幸而有詩,在天空崩裂之時將你我守護。
舜華的詩無疑是備受期待的,而我更願意相信,她就是我們這個世代的女媧。
推薦序二
被挫敗的偶然與即興而來幸福的泉湧∕印卡
日子紛紛洄游,時間彷彿回到2004年我們仍在北海岸那一班往福隆的列車上──當時崔舜華身著紗籠裙,那是她還迷戀民族風的時期,也是感情史著實煎熬的一段。在那段因為創作結緣,偕同去東北角的日子,作為後來者,我們的創作史在「明日報」崩解後輕易被甩尾掉了。曾經輝煌過的「我們這群詩妖」與「隱匿的馬戲班」可以勾勒出台灣六年級詩人的樣貌,解釋起一時風行的多媒體詩歌,但卻很難輕易地描述七年級詩人,套裝理論的闕無,使得部落格興起後,幾乎在許多評論者在「明日報」事件後,對日後部落格的興起,RSS的出現,難以做出對這些文學活動的反應。在網站走向手工業時期,網路世界日漸離散而又因為社群媒體的出現重新傳播管道,若將明日報做為世紀初台灣網路文學泡沫化,或許回頭來看《壹詩歌》後來,七年級詩人在不同層面反動地發創同仁刊物或是回頭來文學結社,也有了莫名的意義。
也許是因為余玉琦的促就下,我們在2007年出版收錄了崔舜華、夜蝕柒、林達陽、席米蘇、廖啟余、印卡、林哲甄、余玉琦、郭勉麟的同人誌《貳捌》。同時期,台大有《文火》,師大有謝三進主導的《海岸線》,日後發展影響了《波詩米亞》、然詩社甚至後來的風球詩社,《好燙詩刊》。這背後的意識型態不單單是簡單尋求發表空間,作為前世代的網路泡沫化,除了網路發表外,同仁刊物無疑成為後來文學社團發展的補償性內化。
在那一段期間,後來常被我戲稱為她詩歌斷代中的威尼斯時期。如〈暗色的行囊〉一詩中,看似幽微卻壯闊磅礡的波光,有時在她後來的詩歌中也鮮少見到了。
在威尼斯的小船上
你向我,向我
告別,舉起暗色的行囊
月色如大雪,覆擁整座運河
黑瑪瑙的波光
你向我告別,小船
搖蕩,如蘆葦的韻腳
沒有船伕,沒有槳,沒有風
或人世中的任何一點聲響
甚至你騷動的鼻息
萬籟寂沉,因為我沒有
玫瑰般的雙唇,能吐
夜鐘般的音節
供你優雅吞咽,恰似你時時有味咀嚼的
那只全麥的傷口……
這首詩中「玫瑰色的雙唇」後來在舜華的詩歌之中成為了常見的主題,《波麗露》中,如同蜂鳥般的雙唇或是詩中再言「再奪回那兩片嘴唇∕說出的話也不是我的」,自當可看見不同於哲學家Irigaray所言「自體愉悅」(autoeroticism)。自體愉悅概念來自於「兩片唇」:成雙成對的「二」無時無刻愛撫著彼此,但在崔舜華的詩歌是情慾對象的封閉性、語言的獨斷性。男子彷彿她的姊妹,語言無法超脫傷口而乃致傷口的一部分,是其詩語言為何始終挑動讀者悵然的緣故。
關於這本詩集的名稱《波麗露》,我拿到書稿著實想了一下,想必是因為前些日子崔舜華開始學起了烏克麗麗。某種程度上崔舜華在我輩的寫作者中,她大多的作品是根植於生活與情感的經驗。就拉威爾所著寫的這首西班牙與阿拉伯風味,呈現兩種固定元素(節奏、旋律)的一再循環的節拍節奏,但在崔舜華的詩歌中呈現出的是另一種複調,在遠處的是舞曲,再近處的則是越變越小的世界裡∕生存充滿軟而倒錯的邏輯。也就像是哲學家Alain
Badiou在《愛的多重奏》裡談到:「示愛,是邂逅事件到真理建構過程的開端,用某種發軔把偶然的邂逅固定下來。這種開端充滿新世界般的經驗,但當人們回顧時候覺得這非偶然而是一種必然。」這本詩集中所呈現的愛情大多在屬於那些流動的誓言中,危險的平衡中。
比如在拉丁語或希臘語中,物質(materia and
hyle)既不是一種簡單、直截的確定性,也不是像空白石板一般等待著外在意義的指涉,而是在某種意義上建立在時間變化的連動性上。這種連動性無疑是崔舜華這本詩集《波麗露》不斷出現的陰性空間,如其詩中所言──體腔,與體腔的擠壓∕遠方有人演奏精悍的舞曲∕波麗露──一種在音樂帶動所展現女性身體。若再究其物質在哲學意義上的發展,希臘語中hyle就是來自林間的薪柴,準備著被加工使用,而materia在拉丁語中除了指那些用作房屋或是船隻的梁木外,更包括從母體而來滋養的養分。在一些女性哲學家討論中,物質往往被追溯回母性或是母子共生空間(chora)中,如崔舜華一首敘事組詩〈世紀.事記〉:「諾亞,把陸上的走獸∕空中的飛禽,都鎖入了∕多難的子宮∕漂流汪恣的羊水之上」,或是這本詩集沒收錄到的絕佳之作〈高原的風〉:
很簡單啊
你要我怎麼樣地去愛
像瓶身裝滿渴欲
要我走那樣的路
造那樣的字,暗藏那些注視
就像高原的風颳裂我體內
每一處微細而酸敏的神經
當我欠身,翻坐起
在空無一人的荒漠高地
高原的風是鹼色的海
高原的風有神的臉色
每一次的相識
吹開草原的前襟
都像誕生了祕密
雖然關於宮籟的討論很多,但如果可以從亞里斯多德的觀點,把運動無計可施對效應的描述轉移到笛卡爾觀點對宮籟細部區域的運動拓樸到詩歌語言之中,〈高原的風〉一方面是Wallace Stevens〈罈〉或是覃子豪〈瓶的存在〉巧合的陰性改寫;另一方面這首詩或是《波麗露》詩集中可以清楚觀察到在崔舜華中詩歌意象從宮籟、肉身到衣著(前襟)服裝中的動力學(Dynamics)。
在我眼底,這本詩集避開集結早期之作甚為可惜,比如〈無糖綠茶〉所呈現少女澄靜的行述性(performativity),崔舜華作品中,不同其他當代女詩人往往詩中說話主體呈現著高度的流動,我時常私底下將崔舜華的作品分為威尼斯、農婦、王母以及懷妊者這些女性角色在其詩歌意象群各有不同系統,以及情感狀態的分野。而在崔舜華的詩歌中,如同先前提到自體愉悅概念來自於「兩片唇」:成雙成對的「二」無時無刻愛撫著彼此,除了行述性高度變化,在單一詩歌中不同詩段也呈現不同敘事觀點的流動,比如〈葬禮〉的衣塚、淺臥春泥的我,以及舊門後∕將要涉入的場景(被潛藏的事件),或是你我他多方的角力,或是〈待我如同形上學〉,以宮籟為陰性空間,性愛與月事的反覆換喻。崔舜華詩歌中那些細緻的動力學變化彷彿就是韓波所說的:「我就是他者。」
另一方面讀者可以發現崔舜華的詩歌中,食物與服裝在詩句中不斷替代。這些對經驗生活的敘事猶若Paul
Ricoeur《胡塞爾與歷史的意義》中所說:「原初的自我是生活,它的第一個成就是前科學的感知」,在對感知的分析中,一個新的被給予方式被開掘出來:動感意識。「動感意識」的發現,往往不在身心二元格局內。一方面女性身體受到工業化後驅使的性感形象作為一種時尚或自我表達;另一方面,如前述的行述性,服裝的諸多描寫一方面給予崔舜華的詩裡面不同女性角色,另一面有意識地接受或拒絕女性社會形象來產生作品內部對於情感狀態的判斷。在許多詩中,舜華透過服裝,有時擴大為窗簾、床鋪布紋漸次房間成為身體的延伸。我們要注意的是在許多當代詩人的句構與意象構成,與早期超現實主義單純仰賴身心論述的前行不同的是在後工業社會出現之後我們的身體感,如同Marshall
McLuhan曾經主張,任何科技的發明都是我們身體的延伸或自我切斷,而隨著新的延伸的出現,我們身體的其他器官和延伸必須重新調整新的比例。而服裝在崔舜華的詩歌便是扮演這樣的角色:
供你華靡異想
當我伸出手,當我
並不伸出手
銀黑蔻丹或楓緞洋服
金色的希臘走下伸展台對我
伸出巴黎般的手肘
我的肩膀緊挨著你的
棉料填充的厚外套,右手臂
髮梢悄悄分歧,留下荒誕路徑
針織披肩善作閱讀
溫暖柔軟,默記在心
服裝成為舜華詩歌的一種外部記憶,或甚至自我意識的一部分,這也是為什麼我常閱讀其詩歌可以感受到那種多方視角精細情感互動的動力學(Dynamics)。而食物的意象,比如紅酒燉肉、玫瑰粥、裸麥湯器……更直指先前提到的materia,比如有些詩句:
才有上好的營養素
罌粟紅,橄欖綠,榴槤橘
嬰孩般無所遁形的藍
我良久沒有張嘴
動用卵石滾落的音節
我將出生標註在冬天
在人人慣性夢遊的年代
打鼾時吃粥
碰到牆,轉彎洗水果
飲食作為一種生活的療傷,恰好與舜華在詩中呈現的勸世話語作為呼應補助的部分,如同:「就過生活如同∕被排演了千萬次的蒼老的舞台後∕那唯一一次的差錯∕買廉價的玩偶∕說違心的笑論∕渡久旱的河流。」也誠若「我蝸居床沿∕披裹原始草糧般的衣料」的譬喻草糧與衣料乃是互為表裡食物與服裝對身體的內外描述,表現與滋養。
崔舜華在詩中的意象向來即是彩度鮮豔,並且許多看似壯闊的場景從身體推向世界,這種身心靈的擴大。如〈魔鬼藏在細節裡〉「世界的邊緣∕座落著巨大的廣場∕中央的噴泉壓抑地吞吐∕花蕊般冶豔的湧瀑∕遠處的戰爭向虛空呼喊:∕動盪,動盪,動盪」或是將巨大焦慮收納於一個群體如〈待我如同形上學〉「在西曬前跋涉床榻的小冒險:∕寵物蜥鬣、偽裝術、玻璃花器∕輕量揶揄與法式瑜伽內衣∕殷求你待我如同形上學∕待我如世間第一個晚春∕烘焙我腹內永恆乾燥的胚胎期」或是〈旅程〉「但世界對你而言∕從不旋轉,或傾斜∕眾人皆需依你的睡痕行走∕趕路,或不趕?∕紐約的房客如是說∕金髮碧眼的John∕使你錯謬地想起中國∕鸚鵡色澤的磁殼城市。」這亦是在崔舜華的詩學之中,從宮籟、肉身到衣著服裝動力學(Dynamics)的變形與擴大。
對我來說,我們這個世代之中,崔舜華用女性主義的讚詞來說,是名引用的女人,將整個世界與人生納為她修辭的、她反抗、她包容的詩歌。在整個被隱蔽的七年級世代所幸舜華仍然持續地在寫著,戀人如同全世界都無法避諱的一行意象性字列,而身為一名長期閱讀她作品的讀者,我也會記得每個在腰間吻過潦草的字,感謝詩人為戀人而完滿的這些詩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