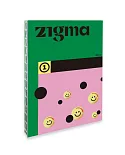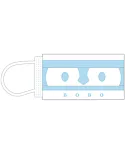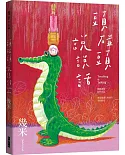後記
家,是最熟悉的味道
離家
小時候我很皮,不好帶,這麼多個孫兒中,只有我曾被關進老家漆黑的廁所裡,哭著面壁思過。阿珠聽說只要找個生過三個男孩子的阿姨認我做乾女兒,便能壓得住我,於是就翻起通訊錄,就為了幫我找個乾媽。
哪知國中更變本加厲,吃了熊心豹子膽,離家出走。最後是阿公拎著我回家,壓著我的頭要我在眾大人面前道歉。
但,「離家,出走」,在這個家隱約變成被促使著要去完成的成年禮。父親二十多歲時曾開著二手車,與母親及叔叔走遍美國近四十個州,姑姑也不遑多讓,存了筆盤纏,背著行囊玩了歐洲一圈,偶爾為了節省旅費而夜宿火車站。
十九歲那一年,因為開始服藥控制類風濕性關節炎,和我在一起的男孩子嚇跑了,另找了個新女友。阿珠忿忿不平,可氣死了。那段期間我的全身關節也拗得很,脾氣一來常讓我痛得晚上難以好眠,有時疼得邊哭邊拳打枕頭生悶氣,哭累了,也就睡著了。
到後來我常對自己說:「哭啥啊!就算哭散了整身骨頭,明早起床還是要面對現實,妳以為哭了就沒病啦?」痛,在夜裡說了好幾回,到最後化為身體裡的一部份,不知不覺地,我學會接受,我知道上帝不會給予跨越不了的考驗。
有天陪著阿公和阿珠窩在暖爐前看連續劇,裡面的女人不知道為了騙財的壞蛋哭了多少回,台灣鄉土劇總是長壽,千篇一律的灑狗血劇情,但常逗得我們直大笑。廣告時我隨口說怕以後骨頭壞光了,走不動,想趁寒假去東南亞玩一遭,阿公也很泰然地說:「查某人,想出外闖闖要趁早。結婚成家、開始工作後,想出去就沒這麼簡單了阿。」從小,父母親省吃儉用,帶著我和弟妹到過許多地方,但一個人走,倒是件新鮮事。
阿珠冷不防問我醫生甘嘸准許我出國,我才突然想到:完蛋,得帶著一堆藥行動!接下來的日子,我印下來回機票,將申請資料填妥,也順利拿到一個月的藥劑*。而這個動作,到爾後幾年,變得熟悉卻又總是充滿驚喜。
記得第一次離開的前一晚,父親還笑著問我:「妳真的要去嗎?」
我知道他正試圖以輕鬆的神情好壓抑內心的緊張與不捨。
「嗯,機票都買了。」
「我補貼這些機票錢,留在台灣吧,女孩子隻身去東南亞玩這麼久太危險。」
「阿公都說沒問題了(還偷塞了點零用錢給我),我想是真的。放心,每天報平安。」
以前我常嚷著說想做這個,想嘗試那個,父親認為我的定性不夠,常放冷箭說:「等做到後再跟我說。」父親從不要我有個很酷的人生,但期許我用力活著。
當生命的另一個階段很直白地告訴我得靠著藥物持續活動力時,我開始變得不太喜歡「說夢想」。夢想之於我是真的遙不可及的事,像是可以和喬治克隆尼一起看極光啊,跳一下就可以穿越時空到想去的地方啊,或是冰箱裡永遠都擺滿著 Ben&Jerry’s
每種口味的冰淇淋。當人生給予的束縛愈多,選擇相對越少,我常告訴自己,其實妳只剩下真心喜歡、想要的,可以確認自身安全,而且能執行的,和不太能做的,就這麼簡單,兩個選項。所以當時沒有太多顧忌,就這樣放手一搏前進了。
朋友曾在明信片上寫道她很喜歡「Terminal」(航廈)這個主題,迎往送來,又能連結到世界各個角落,彷彿有永遠寫不完的故事。我盼求自己的心靈也是座隱形的 terminal,當想起過去的時日,不論是感動的,荒唐的,都能讓自己會心一笑。
*截至目前為止,我共申請過五次出國的藥劑,短的一個月至最長期兩個月。但前兩年開始,因雙手關節已有明顯變形扭曲,除了服藥外,每週也開始施打兩次恩博針劑,此後尚未有任何出國經驗。RA病友或是身體較不方便行動者可以藉此為參考,但還是以專業醫生的建議為準則。
回家
「今天抵達○○,一切安好。好想吃炒高麗菜、滷豬腳、牛肉麵,雞排也想!」在外頭時,我常寄給父親這樣的簡訊,幾乎每天都在列菜單。走得再怎麼遠,想家的滋味還是最深刻。
父親不曾到機場接我,但每次回家的晚餐都澎湃得足以燃燒我的胃,父親鮮少陪我前往醫院,但他不忘為我添購極好的床墊與電暖器以紓解骨頭帶來的不適。這就是我的父親,穩重少話,與我的個性大相逕庭,但我很愛他。
Christopher Reeve(飾演電影《超人》的男主角)在一次馬術比賽中意外落馬,脊椎嚴重受傷而造成癱瘓。在他1998年出版的自傳《Still Me》中曾說:「當第一部《超人》初上映時,我接受過許多訪問,記者們最常問我:『你對英雄的定義是什麼?(What is a
hero?)』那時的我總說不顧後果、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人便是英雄。但你知道嗎?若你現在再問我相同的問題,我的答案肯定完全不同。我覺得真正的英雄是那種儘管面臨了席捲而來的障礙,但仍能找到自我力量並有堅毅容忍精神的人們。而那些支持著這些英雄的家人與朋友,也是真正的英雄。」
我的家人之於我,也是如此。我一直深感幸福,因為我從來都不是一個人活著,一個人努力著。
作者序
食畫,食說
我偶爾半試探性的問身邊的親密友人:「欸,如果我很早就會死掉了…」通常講到這裡,還沒完話時,他們的回答不是「呸,亂講!」「我不喜歡你這樣說!」「肖為!」(台語:瘋話),不然就是用很堅定的眼神看著我說:「才不會!妳會活很久的!」
有一次,我把相同的問題丟給一位特教班的學生,他很可愛地告訴我:「怎麼會死掉?我會去救你啊!」而學生童趣的回答,就這樣一直放在我的心底。
也許是長期服藥及壓力的緣故,有一段時間身體健康狀況愈下,醫生便要我過段時日回來做腸胃鏡檢查。護士再三吩咐檢查前一週只能吃低渣飲食,前一天只能喝清腸劑,這指令聽完,根本已經奪了我半條命。
父親擅燒菜,從醫院回來的這一晚,家常菜的香氣一如往常,就像壁紙,貼滿整間屋子。廚房瓦斯爐的左側是鍋燉肥肉,我卻得默默為自己開火,煮碗白粥。為了讓自己有空想的五花肉能吃,我開起燒肉的鍋蓋,啟動狗兒般的靈敏鼻子,在一旁吃起清粥,覺得能讓自己好過一點。
隔幾天,日本友人來信,信內說盡義大利的巷弄美食,這不打緊,同時在 Facebook 上還貼了令人垂涎的實體照片,看得我整個人哭笑不得,直窩進沙發抱枕內哀號:「是要逼死誰啊~!」也不知怎麼回事,大叫後我竟想起學生說過的那句話:「怎麼會死掉?我會去救你啊!」
其實我也可以救自己啊。
於是便到房間拿起尚未用完的素描本,借了弟弟不再使用的調色盤與畫筆,看著螢幕上的照片,為自己點餐,想吃什麼,就畫什麼,假裝這些玩意都進了我的肚子裡,即使這一天我只喝了清腸劑。
在很多有趣的事情上,我是個三分鐘熱度的人。或許是嗜食與天馬行空的個性,Gourmet’s food imagination project(此系列畫作最初的名字)倒讓我執意許久,一畫就停不下來,最後零零總總結集了將近一百幅。有句玩笑話說:There is no love sincerer than the love of
food.(沒有任何的愛比對食物的愛還要忠誠。)我想,我便是這句話的最佳代言人吧。
這兩、三年累積的圖畫,除了食物異想外,也包括旅途上、生活中遇見的大小事,與那些在我生命裡溫暖綻放的他與她。有個男孩子在離去時曾經對我說:「Beautiful memories, packed in the box, kept for sometime in the future. Thank you,
Anita.」我不是一個一直都很勇敢的女生,但他在我人生最低潮時,不顧我每天得吞下一把藥,或是有時雙手得穿戴上固定器,卻毫無猶疑地,笑著接受了我,並帶給我許多鼓舞與無比自信,即便我們已分開旅行,各自遠颺,但他口中的,或是我心上的 beautiful memories,從沒離開過。
我常憂心也許有一天不再能畫畫,不再方便行動,不再有足夠的力氣拿起單眼相機,但我很欣幸現在的自己能重拾筆來,勾勒出過去每個值得紀念的片段。也許這些故事不是最酷的,最扣人心弦的,但其中的微小感動,希望你們也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