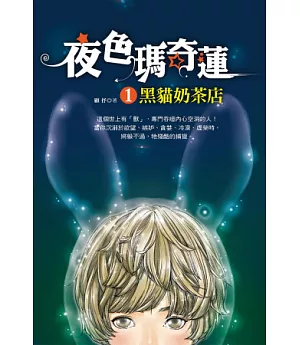導讀
Chapter 1:編號1018的鑰匙
我叫毛豆。
對,這不像是一個女生的名字,甚至不像是一個人的名字,作為名字,它有點滑稽、有點荒唐,我也不喜歡這個名字,但它已經陪伴了我十五年,這世上比我的名字滑稽荒唐,而又存在數年之久的事物實在多如繁星。
現在是二月的早晨,我坐在街角公園的長凳上,凍得有點哆嗦。我的左手在衣袋裡摸索了一會兒,摸到一支菸和一個塑膠打火機,我「啪嗒」「啪嗒」地按動打火機,菸卻沒有點燃。我不會抽菸,也不想抽,我用拇指和食指拿住它——是劣質的假「南京」,爸爸從來沒抽過什麼好菸,這支菸就是他臨走前剩下的,只吸了三分之一不到。
然後,他就接了那個電話,再也沒有回來。
過了一會兒,我重新把手放進口袋。現在天又亮了一些,街上的行人多了起來,我像看水族館裡的熱帶魚一樣看著他們經過,早起的上班族,步速很快,大概是要去趕地鐵,在台階處一個踉蹌。睡眼惺忪的中年婦女,打著呵欠,不顧儀態地穿著碎花棉睡衣出來遛狗,狗則遇見電線桿就抬起後腿。精神矍鑠的老人背著劍,白綢子的練功褲下面露出黑色布鞋,像是剛剛劫富濟貧。哦,當然還有學生,像猴子一樣縮在肥大的校服裡面,弓著腰把車騎得飛快,簡直像是要離地而起,因為怕遲到被訓導主任逮到吧……
不過,這像車輪一樣勻速轉動的一切又和我有什麼關係呢。
今天,我是不能去上學了,自然也不用擔心遲到。
向老師求助?我並不是那種討人喜愛的學生,更何況,並不是什麼事情老師都能幫上忙的。我從小就不喜歡求人,遇到什麼都自己解決,小學時候在學校的建築工地上跌倒,鋼筋刺破了膝蓋,也是自己一路走回家擦了藥水了事。我們家人都這樣。
其實所謂「我們家人」,也只是我和爸爸兩個人而已。
我的記憶中沒有媽媽,一點印象也沒有,不僅如此,家裡根本就沒有媽媽的照片,說起媽媽,就像是茫茫宇宙中的外星生物似的,知道有這麼回事,不過誰也不能肯定真的見過。
我的右手也插在口袋裡摸索,像是在大海裡打撈沉船,不過連一個一塊的硬幣也沒有,只觸到一個硬硬的金屬狀東西,邊緣的鋸齒像是會咬住手指。
鑰匙。
我抽出右手,在手心裡掂了掂——
這,就是無故失蹤的爸爸留下的唯一線索了。
鑰匙上有凸起的印,瑪奇蓮,一○一八。
接下來,我必須去瑪奇蓮,打開號碼為一○一八的儲物箱。
瑪奇蓮是一個連鎖超市的牌子,在我住的城市就像蝨子一樣多,既有大型的倉儲式瑪奇蓮,也有像雜貨鋪一樣大小的二十四小時瑪奇蓮,一切都乾淨、衛生、環環相扣,我們這個不大不小的城市也透過瑪奇蓮,變成了全球化鏈條上的一環。不過,再也吃不到好吃的魚肉串了,兩毛五分錢一串的魚肉串,一種過時的食品。回憶中的東西總是帶著夢幻的滋味,特別是再也吃不到以後。
我和爸爸居住的區域,大概有十個瑪奇蓮,一個倉儲,九個二十四小時,就像一個太陽系,一顆恆星,八顆行星,也許還有更多。因為爸爸手頭不寬裕,其實我們住的地方,在整個城裡也算是很差的,周圍盡是些矮小的平房,從樓上朝下望去,如同高山環抱中的一塊灰色盆地。
我們雖說住在樓房裡,其實並不像新建的房子那樣配有社區,樓外並沒有貼磚,牆體的水泥感覺沒糊好,皺巴巴的,像是沒穿衣服的老人。樓道裡左一張、右一張貼滿了下水道疏通和治療牛皮癬的油印廣告,還有小孩用粉筆畫的大烏龜,連我用毛筆蘸了水寫的「沒有」兩個字,都沒有人去把它擦掉,至今還留在上面。樓梯扶手上則積滿了灰塵,像是餅上的屑子,一碰就如雪片似的往下掉,以前我喜歡坐在上面滑下去,爸爸說我是這個樓的公用抹布。
儘管如此,與本區風格大相徑庭的瑪奇蓮在這個區一個接著一個悄悄開放的時候,大家竟沒有絲毫排斥地接受了。於是我們繼續住在破爛不堪的房子裡,與井井有條的瑪奇蓮和平共處,這沒什麼稀奇,有的偏遠地區連路都沒鋪好,一樣可以網上購物,如今的時代就是這個樣子。
哦,對了,我爸爸是個快遞員,走街串巷的。
我從公園長凳上站了起來,一夜沒睡覺,身體有些酸痛,好在我年輕,伸展一下就沒事了。跟學校請假的事回頭再說,隨便撒個謊就得了,就說生病了,反正我經常撒謊。被老師識破也無所謂,不過竟然一次也沒被戳穿。
實際上,沒人管我怎麼樣。
我大概用了十分鐘不到,就走到了離家最近的那個二十四小時瑪奇蓮,也是最寒酸的一個,連大一點的冰櫃都沒有,也買不到狗用沐浴精,附近人家養活自己都困難,決不會給狗買什麼沐浴精。不出所料,這裡壓根沒有儲物櫃,物品都直接交給店員保管。沒有什麼一○一八,碰!槍斃。
接下來的一個瑪奇蓮稍遠,距離此地約一站地。因為我沒有錢,只得走著去。沿途都是工地,乏味至極,走到的時候覺得好像用嘴做過推土機。儲物櫃是有,不過一共九個,標以○一至○九。收銀台旁「撲突」「撲突」煮著茶葉蛋和粽子,擺在超市門口出售的是大肉包,我舔了舔嘴唇,聽見自己肚子裡像是有一隻鴿子,發出令人難堪的「咕」地一聲。
我迅速離開,前往下一站、下下一站和下下下一站,本區在地圖上小得像芝麻一樣,實際走起來又是另一回事。幸好穿著球鞋,不過腳底仍是火辣辣地疼。這幾個瑪奇蓮有一個致命的相似處,就是都沒有一○一八,不過除此之外,它們也差不多,排列整齊的貨架、肉和蔬菜欄,連收銀台上插著的棒棒糖都一模一樣。
走到第六個瑪奇蓮的時候,我坐下來喘了口氣。
要不要去倉儲呢?
答案是不,爸爸總說在那個倉儲裡面會迷路,暈頭轉向的。
我猶豫了一下,還是去了學校附近那個,現在正是上課時間,大家應該不至於沒事跑出來。
步行到那裡,整個人都快虛脫了。這個瑪奇蓮,我倒是很熟悉,不過完全不記得有沒有一○一八,我想一般人都不會無聊到去記儲物櫃的號碼吧。
這個時候人流量很小,超市裡安靜得可以聽見冰櫃的嗡嗡聲。到了中午,學生們就會過來買一種大杯子裝的冰沙,甚至冬天也照買不誤。我是不喝那個的,但有時也會陪小荷過來買——我的朋友不多,周小荷算一個,她和我小學、初中都是同班。
這個瑪奇蓮的儲物櫃稍微多一點,有那麼十幾個,藍色的編號印在白色的密碼箱上,相當醒目。最上面一個是一○○○,最下面一個是一○一六。
一○一六,接近了。
我的頭腦快速地計算著:也許離這兒最近的那個瑪奇蓮裡,就有一○一八。
就在我準備離開時,超市裡進來了一個頭髮灰白的男人,身材高大,穿著藏青色粗線毛衣,裡面探出同色系格子襯衫的領子,嘴角掛著一絲揶揄似的近乎凝固了的笑容。
「還挺考究。」我心想,「老傢伙。」
對我這種年齡的人來說,二十歲以上的都是老人。不要怪我這麼想,十幾歲的小孩,誰也無法想像,自己也有一天會超過二十歲。
但我不由自主地看著那個男人,他有一種吸引別人目光的氣質,不是誰都有這種氣質,怎麼說呢,類似一種隨著他的步伐和動作,方向和能量都不斷變化的磁場。也可能是我在胡說。
他徑直走向貨架頂端,在那裡蹲下。
我則假裝對一包「烘烤魷魚絲」很感興趣,慢慢向裡面移動。
只見那裡有一排藍色櫃子,上面有白色的編號,與外面的儲物櫃恰恰相反。那個男人將一把鑰匙插入密碼箱,取出一個包裹似的東西,然後站起身,從兩排貨架之間離開瑪奇蓮,什麼也沒買。
「啊。」我恍然大悟,備用儲物櫃,也許是因為這個瑪奇蓮在學校邊上,顧客相對較多吧。
男人打開的是一○一七,旁邊就是我找了一個早上的一○一八。
瑪奇蓮的儲物櫃上都插著鑰匙,存進東西--拿出鑰匙--購物--取出東西--放回鑰匙,就是這麼簡單的流程。
不過,偶爾也會有人把鑰匙帶走,偶爾。
我也蹲下身,像獵人瞄準一隻山雞似的,把鑰匙對準一○一八的鑰匙孔,插入,只聽清脆的「哢嗒」一聲,一○一八密碼箱的門彈開了,帶著微微的愉悅之感。
我把手伸進密碼箱,如同一個人走進深不可測的洞穴,渾身的皮膚都繃緊了,不在於洞穴裡面本身有些什麼,而是被那種欲知而又未知的感覺燒灼。
一個肥厚柔軟的東西,以及一個觸感粗糙的紙袋。
把一個M號玩具熊和一個牛皮紙袋拽出密碼箱時,我忽然有點喘不過氣來。這算是什麼呢,生日禮物嗎?我早過了喜歡玩具熊的年齡了。
我捏了捏那隻胖鼓鼓的熊,它是棕色的,多毛,有兩隻豆子一樣的眼睛,一瞬間我的腦子裡湧現出無數個名字,但最後還是決定叫它「傢伙」,我最先想到的那個名字。
我打開那個檔袋,又迅速地合上,看了一眼周圍,店裡只有少許幾個顧客,有的在研究優酪乳的保存期,有的在擺弄巧克力的贈品,收銀小姐則趴在櫃檯上,呵欠連天,沒有人注意到我。
這份禮物是錢,我不敢在這裡數,不過我想也許有兩三千塊。我對錢沒有什麼概念,不過,手上有了兩三千塊,對這個世界的看法還是會略有改變。
好,嘲笑我吧,現在誰身上不帶個千八百塊出門呢,一雙有牌子的球鞋也要這個數目,不過我真的沒有見過這麼多錢,爸爸不像其他父母,按月給孩子零用錢,我家有一個抽屜,裡面放著一些硬幣,想要自己去拿,不過裡面永遠不會超過兩百塊。
這個牛皮紙袋讓我興奮莫名,「傢伙」也不賴,不過這紙袋簡直太好了。
我合上一○一八的門,拎著「傢伙」,抱著紙袋,從貨架另一側溜出瑪奇蓮,我可不想引起其他人的盤問,「小孩,你手裡是什麼?」「這些錢哪裡來的?」這些鈔票上又沒印著我的名字,儘管現在,它們確確實實屬於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