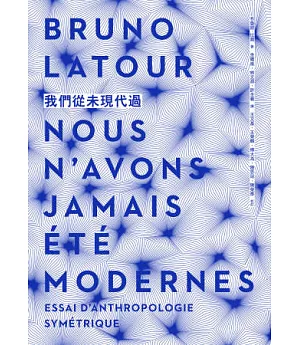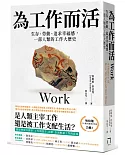中文版序
《我們從未現代過》的三個意義
比較《我們從未現代過》與孔恩(Thomas Kuhn)在1962年出版的鉅作《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我們不禁會感到在這三十年之間,科技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曾走過何等長遠而又引人入勝的旅程。就如同孔恩在全書第一行中所指出的,他寫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的目的, 就在於「對我們所深信不疑的科學形象,造成一個決定性的變化」。雖然該書曾引發深遠而又廣泛的影響,甚至可能是二十世紀人文科學界屈指可數的長銷書,但是全書的焦點仍然侷限於挑戰傳統的科學形象(image of
science)。相較之下,《我們從未現代過》一書的企圖心卻遠遠超過對科學的關懷,該書的切入點是科學,但它的目標卻是全面檢討現代性(modernity)這個核心問題。透過晚近科技研究對於科學的突破性理解,這個領域內最具原創性的學者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藉此重新審視現代性論述中一系列的大分裂(Great Divide),像是自然 vs. 文化、主體 vs.
客體、事實vs. 價值、現代的我們 vs. 傳統的他者,從而得到「我們從未現代過」(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這個聳人聽聞,但又全然不同於後現代主義的重要結論。由於全書的企圖就在於揭示出科技與宗教、文化、藝術、政治之間有著現代性論述中無從想見的密切關連,因此本書並不是科技研究的入門書,相反地,它是一個對於領域外眾多好學深思的朋友們的邀請:邀請大家一起來探索彼此的關懷間千絲萬縷的連繫,共同來省思為何至今我們仍對這些關連視而不見;更重要的是,共同來揣想一個能看到它們的新視野,將可幫助我們創造一個什麼樣的新的世界。
《我們從未現代過》是一個既曖昧而又令人疑惑的書名,它當然不可能意味著現代世界從來不曾存在過,或是宣稱無數學者先前關於現代性的細緻討論都是虛幻不實的。為了初步瞭解這個書名的意義,我們必須先要注意到拉圖極有創意地使用「憲法」這個比喻來理解現代性,因此他稱之為現代性的憲章(Modern
Constitution)。簡單地說,許多國家的憲法中明文規定司法與行政的分立,這個制度性的規定在許多時候有著一定的效力,它一方面侷限了法官與政治人物間公開的、制度性的互動,另一方面,又將他們間綿密的往來推擠到台面下,隔離於公眾意識之外,因而該國人民會覺得自己的確身處於這樣一個雙權分立的現代社會之中。由拉圖的角度看來,許多現代性的大分裂都可以類比為這種法律規定的分立,它使我們不斷地看到科技獨立於社會文化之外的事例,卻將兩者間的交引纏繞排除到公眾的視野之外。當然,正是在這兩者的類比之下,我們反而會感到從不曾明文規定的「現代性的憲章」的力量,其實遠比各國的憲法要來得有效而深刻,因為無數的人們與媒體報導都會指出法官與政治人物的宴飲勾結,但是很少人能夠想像科學事實如何能夠與文化價值密切相關。
基於憲章的這個比喻,《我們從未現代過》至少有三個意義。
第一、雖然在許多時候,我們的行動模式確實拳拳服膺於這個規範性的憲章,但科技實作中卻總是也同時充滿著許多這個憲章所不容許的、因而視而不見的活動,人們不斷地把這些理論上應該斷然分隔的不同領域結合在一起(拉圖所謂「轉譯」〔translation〕、「中介」〔mediation〕、「網路」〔network〕),創造出混種物(hybrid)之後,又再將它們純化分離(purification),而還原回到截然分立的兩軸(例如自然vs.
社會),於是由結果看起來,我們彷彿一直存活在這種二元分立的現代世界之中。科技研究這個領域最大的貢獻,就在於考掘出這些憲章所不容許的活動;更重要的是,科技研究不是爆料或爬糞,它並不把這些憲章所不容的活動當成醜聞或是病理的現象。相反地,科技研究指出,正是因為有著這些為憲章所不容許的(是以視而不見的)活動的支撐,現代性憲章才能夠有效地運作並規範我們的生活,並帶來人們所稱頌的一切的現代化的成就與進步。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實作與憲章間有著這樣的深刻的不一致,但由拉圖的角度看來,直到不久之前為止,這兩者之間的關係都還稱得上是一種運作良好的、具有功能性的關係。為了突出現代世界自十七世紀興起以來,我們的行為根本沒有全然符合現代性憲章的規範,而且永遠不可能符合(因為那些行為不符合規範,卻有重要功能),拉圖才斷然指出「我們從未現代過」。這當是本書書名第一個意義。
不過,「我們從未現代過」並不只是對於過去歷史的新視野與新領悟,它更涉及對於當下時代的判斷與未來歷史的展望。由拉圖的角度看來,由於越來越多不為現代性憲章所容許的混種物紛紛湧上檯面、甚至成為公共爭議的焦點,曾經一度可以運作的制度勢必面對嚴苛的挑戰,而走到需要徹底改弦易轍的歷史關頭。有趣的是,拉圖並不據此宣布一個新的大分裂或是「後現代」,相反地,他的主張是,只要我們能認識到原本「現代性」的斷裂就不是全然真實的,從而去共同、公開地面對那些在現代性憲章中泯滅不見的混種物與交引纏繞的實作(entangling
practice),我們就可以處理當前新局的挑戰。本書書名的第二個意義就在於由現在開始,我們不可能、也不應當再繼續信守現代性憲章的規範;簡單地說,「我們將不再繼續現代下去」,是以它同時是一個對當下時代變遷的診斷以及因應的方略。
請容我在此提供一個有些簡化的例子,以使讀者有一點具體的感覺。在關於基因改造食物(genetic modified organisms, GMO)的辯論中,有一種很常見的辯論方式就是聚焦於「基因改造」這個技術與改造而生的混種物,辯論它們究竟是屬於自然還是不自然的現象與過程。主張GMO屬於自然的人會說, 自然界中本來就有混種的現象,
而主張不自然的人士則會強調自然界的混種過程所花的時間非常漫長, 因而對相關物種與環境的衝擊都極為有限,相較之下,「基因改造食物」所涉及的人為、瞬間完成的混種仍是不自然的。這個辯論中,雙方都企圖訴諸「自然的道德權威」(moral authority of
nature),彷彿只要是自然的,我們就一定可以、且應當接受,而不需要過於擔心「基因改造食物」這個新混種對社會或環境的可能衝擊,所以辯論的關鍵點在於「基因改造食物」究竟是屬於「自然」還是「人為、社會」。我想這個辯論方式,應當十分接近於拉圖所謂的現代論的立場,辯論重點在於決定混種物屬於「現代性大分裂」的兩個陣營中的哪一個。
恰成對比的,另一種討論的方式,是把「基因改造食物」當成一種由「科技∕自然」與「社會∕人為」共同支持出來的混種物,我們不會斤斤計較於它是否真屬於「自然」,反而會仔細檢視它的哪一個技術性的特徵,會產生什麼樣的社會效應,對此,我們希望見到什麼樣的規範、甚至改造?一個具體的好例子就是由英國STS學者Brian
Wynne等人參與的調查,他們企圖找出人民對GMO感到憂慮的真正原因,透過深度訪談,他們發現人民願意接受合理的風險,但承受這個風險必須有助於社會公義。生技公司宣稱GMO可以解決第三世界的飢荒,但同時卻在GMO內植入使種子自動失效的裝置。由於農民必須每年重新向生技公司購買種子,GMO將使全球農業更進一步地被少數跨國公司掌控,其社會效應絕不是減少飢荒。在訪談中,許多民眾表示,如果生技公司取消這個裝置,他們便比較願意為減少飢荒而承擔GMO的未知風險。Brian
Wynne等人的訪談闡明了原本隱晦不彰的社會價值,迫使科技與企業界面對本身關於社會的錯誤假設,從而轉化GMO爭議的主軸,更可能從而改變這個混種物的具體物質特性與社會效應。
最後,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拉圖把變遷的起點訂在1989年,這不止是因為柏林圍牆於當年倒塌,更不止是因為六四天安門事件,而是因為在當年史無前例地出現了以全球環境狀況為主題的會議。相較於1993年拉圖以新聞報紙中對於臭氧層的破洞的科學爭議揭開全書的扉頁,等到高爾2007年以《不願面對的真相》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時,我們不得不承認拉圖的確在十多年前就指出了科技研究者所應當凝神關注的全球性新興現象。
第三個意義:「我們」,從未現代過?
《我們從未現代過》第三個意義在於,如果連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一書的英文(乃至其他歐洲語文)讀者也從未真正現代過,連他們也從未壟斷關於自然的真理,那麼所謂現代文明與前現代原始文化間無法溝通的大分裂當然便難以維繫了。雙方很可能沒有現代性論者所斷言地那麼截然的不同,彼此要平等對待、相互欣賞與學習是可能的,而且並不需要付出採取文化相對主義(cultural
relativism)的慘重代價。但是,當您在書店中看到書名《我們從未現代過》,特別是它來自法國巴黎的作者時,不知道您會不會心生疑惑:拉圖所謂的「我們」是指誰呢?究竟包不包括正在翻閱本書中譯本的華文讀者呢?
這個看起來頗為天真的問題,其實很合理而且值得深究。歷史上有太多以「我們」為名的文獻,事實上都是高度排他性的。以美國獨立宣言為例,宣言前言開宗明義就說「我們以為這些真理是不證自明的:凡人生而平等,秉造物者之賜,擁有多種不可讓渡的權利,包含生命權、自由權、與追尋幸福之權」。聽起來「我們」談及所有的人,這兩字也理應包含所有的人類,但是大家都知道,就連負責起草宣言的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一生中都擁有超過600名的奴隸,這些奴隸何嘗擁有生命權?當年美國人七月四日齊聲誦讀「我們」如何如何之際,真正不證自明的是,有許多環繞身邊的人都被排除在「我們」之外,而是不證自明的「他者」。
我們這些中譯本的讀者,究竟是不是作者拉圖心中的「我們」呢?這涉及本書書名的第三個可能意義,也是一個需要小心探索的問題,隨著答案的不同,我們也將會以十分不同的方式來理解與使用這本書中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
在過去兩百年之中,正是本書主題的「科學」,劃下了區分「現代西方」與「傳統東方」的大分裂。1793年英國首次派遣大使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率領使節團來到大清國(那時「中國」一詞還沒有被用來翻譯China),希望與清朝建交通商。充滿自信的乾隆皇帝毫無興趣地回應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早已預見即將面對這樣一個自我感覺良好的大清國,馬戛爾尼使節團在出發前特別準備了一個巨大的熱氣球,他們相信「只要能讓熱氣球漂浮在北京城的上空,全中國就會知道西方的優越性」。可惜由於和珅的阻止,馬戛爾尼無法在北京施放熱氣球,是以乾隆朝的中國人錯過了一個當場領略到「他們」是何等優越的機會,也因此東亞的人們則在多年之後,才以更痛苦也更加羞辱的方式,瞭解到彼此是何等的不同。
就如馬戛爾尼所早已預見的,東西方不同的關鍵,就在於科技。他們西方人因擁有科技而跨越歷史的分水嶺,成為現代人;而我們為了追求現代與科技,幾乎必須揚棄我們所曾經擁有而感到自豪的一切,包括宗教、文化、傳統、習俗。我們不妨回想一下,東亞現代史上有多少先行者就是以揚棄傳統並擁抱現代科技而知名的,想想福澤諭吉(1835-1901)在自傳中對漢醫的不齒,小學課本中孫中山扭斷泥偶的手臂而破除迷信,後來曾任台大校長的五四運動領袖傅斯年曾說他寧死也不請教中醫,甚至當年台灣人對日本殖民的最大的肯定也來自現代衛生,學者因而名為「殖民現代性」。
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漫長追趕,經過幾個世代的仁人志士以發展科技作為畢生志業之後,就在我們終於覺得幾乎要追上他們的科技發展時,拉圖居然跳出來說─「他們」從來沒有現代過,這不是很像一個近乎惡質的玩笑嗎?
正好相反,這使中譯本讀者多了一個理由、並多了一種方式來閱讀這本極有挑戰性的書。一方面,基於科技在我們生活中無所不在的影響力,我們是不折不扣的現代人,為此我們極有理由關心前述兩個意義下的「我們從未現代過」。
我們也在自己生活周遭目擊到許多拉圖書中所描述的新興現象,從而感到訝異、興奮、疑慮、不安,因而可以由閱讀本書中深化自己對這些現象的理解、綢繆我們的對策。另一方面,不可否認地,就在不久之前,我們曾在一個世紀以上的時間中被西方人視為不科學的、無法理解的他者,我們之中的進步分子也曾為此不斷地以「迷信」、「落伍」來撻伐自己的同胞,直至今日我們之中仍還有許多人採用未經科學檢證的風水、收驚、傳統醫療與民俗療法,是以我們更有理由要從被排除在外的「他者」的角度來閱讀《我們從未現代過》這本書。身為中醫現代史的研究者,我可以向讀者保證,這也會是一個最有啟發性而愉悅的閱讀角度。
(本文曾發表於《科技、醫療與社會》卷十(2010),頁221-36)
雷祥麟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暨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