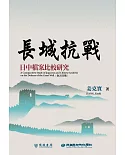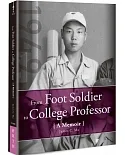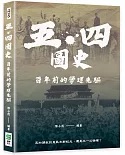序
不確定的遺產
在辛亥革命百年之後,人們不禁會問,其留下的恆久遺產是什麼。然而這個問題卻頗費躊躇。辛亥革命通常被我們視為一次政治革命,而不是社會革命。儘管辛亥革命給中國的政治體系帶來了根本性的變革——消滅了封建帝制並建立了一個共和政府——它卻沒能給社會關係帶來同樣的變革。與1789年法國大革命,1917年俄國革命以及1949年中國革命這些「大革命」們不同的是,辛亥革命對階級結構以及產權制度的影響微乎其微。
此外,如果以後見之明來看上一世紀,辛亥革命的政治影響也相當有限。辛亥革命之後出現的新共和政權被證明是既軟弱又短暫,很快落入軍閥混戰,隨後又先後被民族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創建的列寧主義黨派所取代。還處在搖籃期的民主的希望便被今天這個眾所周知的世界上最強大的專制國家的演變所吞噬。
難道這就是歷史的結局嗎?在政治學家史謙德(David Strand)的新書《一個未完成的共和國》中,他提出中國的辛亥革命並不是失敗,只是尚未完成。 根據史謙德所言,辛亥革命給中國留下了曠日持久的共和主義政治文化,它以鼓舞人心的演講,喧鬧的集會以及粗獷的示威為特點,使人民在政治上能以平等的地位與領導者對話。
史謙德指出,這種政治文化所留下的持久影響可以從1949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每十年就重複爆發一次的公眾爭論中得到驗證。儘管史謙德承認民族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各自黨派和政權的先後建立開啟了中國專制政權的命運,但他也指出共和力量大有希望使中國民主化,而這只是時間的問題,就像發生在其他曾經的列寧主義政權的那樣,從臺灣到東歐再到前蘇聯。
2012年臺灣地區的總統選舉見證了臺灣自辛亥革命以來時斷時續進行著的民主政治歷程的成熟,它強有力地證明了中國政治文化與民主之見並非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但臺灣地區富有啟示性的經驗並非預示著共和國也會有相同的發展。誠然,中國(和臺灣地區一樣)一直將辛亥革命的領袖孫中山尊稱為現代中華民族之父。同時中國也時不時地以民主的名義發起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從毛澤東時期的“新民主主義”到後毛澤東時代的村莊,小區以及人大選舉。
更進一步,由當代各類積極行動者發起的所謂“權益保護運動”,涉及空氣質量、食品安全、廉價住房和其他涉及普通民眾關心的問題,表明了普通市民還沒有喪失向政治領導人訴說真相的欲望。然而從一些方面來看,相比短暫的共和政權過渡期以及其後來在臺灣的發展,中國大陸目前的政治現象更能讓人想起辛亥革命本該推翻的長期存在的帝國政權。
史謙德描繪的辛亥革命,具有好爭辯的政治文化,持槍的女權主義者強行進入參議院所在地,用扇子直接扇了民族主義者領袖宋教仁的耳光。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今天的示威者——就和帝制中國時期的一樣——他們僅僅是責備基層官員破壞了高層的指令。儘管當代中國的示威活動響亮而激烈,它們卻很少直接挑戰中央政府的領導及其政策。示威者顯示出了我在其他書中描述的 “規則意識”( rules
consciousness),這樣他們實際上是通過接受中央政府的說法並表現出對領導者的尊敬來確定政府的正統性。 現代的示威者忠誠地呼籲政府的政策法規,甚至不惜對中央政權俯首稱臣(如1989年人民大會堂的學生請願以及此後幾十年下崗工人不停在政府辦公室前的所作所為),當代抗議者的行為進一步強化而不是削弱中央政府的統治權。
史謙德認為“暢所欲言、正直與有警惕心的公眾的遺產”是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果, 這種傳統發展到一定程度會鞏固而不會抵制中央政府的權威,這點可能可以通過審視早至帝制政權時期的更為古老的政治文化中得以體會。
但是無論我們將當代人民的積極主義追溯到何時,顯而易見的是,在中國,國家和社會的關係是不斷變化且無法預測的。在某種特殊的環境之下(如蔣經國統治之下的臺灣),廣泛存在於社會的不穩定性有益於民主轉型,但在其他環境之下(如今天的中國大陸)氾濫的示威可能反而會導致更加強大的專制統治。
儘管現在評估辛亥革命的遺產顯然還為時過早,毫無疑問的是它開啟了一個動盪的世紀,這個世紀充滿著對足以取代歷史悠久的帝制的現代政治體系的不斷渴求。辛亥革命的一個影響是確定了帝王制不再是一種適合中國的國體形式。另一個影響就是鼓勵更多的公眾有意識的去瞭解和參與政治討論。
但是仍然懸而未決的,是國家與社會之間就哪種政體從長遠看來更適合中國的共識問題。中國共產黨一直積極努力地去避免20多年前降臨在大多數其他共產主義國家身上的厄運。從過去的革命中汲取部分經驗,創新性地將強制性手段和應對性手法相結合,展現出了不同尋常的靈活性和適應性。
今天,這些努力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但是深處的不穩定性困擾著深思熟慮的中國政府官員,也同樣困擾著普通民眾——只要預測一下他們現行政治體系的未來就可以知道,辛亥革命實際上遠未完成。
裴宜理
周言 邱婕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