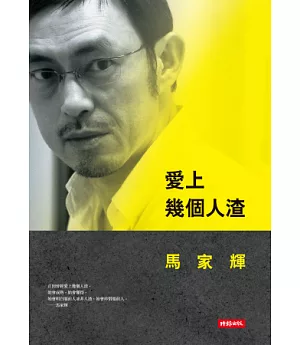推薦序
灣仔酒館裡的人渣回憶∕小說家駱以軍
我記得二○○六年香港書展期間,有一個晚上,家輝大哥帶我去灣仔的一間酒吧。同桌還有莫言、黎紫書、胡淑雯。如果以「酒館」──如卡爾維諾的《命運交織的酒館》,以二十二張「大阿爾卡那」和五十六張「小阿爾卡那」的塔羅牌陣,水平、垂直、不規則輪廓、搓洗、排列組合,形成一套建構故事的機制,中世紀或文藝復興或我們置身的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所有「形成小說」的話語──以「酒館」作為一座城市「不斷累聚向下望的身世」,我們眼前的這個酒館的景觀,似乎正是所謂的「香港」。
各種老外(英國的、美國的、印度的、北歐的或南歐的,各種膚色和髮色的),大部分穿著優雅的襯衫、衣香鬢影的女人們,他們拿著酒杯,用英文交談著,像群鳥憩聚在一座森林不同的陰影裡,啁啁啾啾。沒有台北的PUB裡你總覺得是老外男人摟著穿著緊身短裙長髮台灣正妹那種「性的殖民地不對稱張力」。但家輝大哥似乎在眼前這間「灣仔酒吧」之上,用回憶說故事,再複視藻井地疊現出另一個時空的「香港」:他回憶他少年時光鬼混的灣仔,美國水兵、香港妓女們,燠熱潮溼的南方、女孩們浮花浪蕊、男孩們偷拐搶騙,在這燒灼著繁華和屈辱的燈泡櫥當前穿梭的少年眼中,則是一座「傷害啟蒙的遊樂園」。
這或許也正是馬家輝式的「香港」,面對北京的小說家、台灣的小說家,馬華的小說家,所欲描述的「妖怪的自我」:「人渣」們如混雜淌流的記憶資料,早已在「我」祕密的身世結構中了。
所以我在讀日本小說家宮本輝的《道頓崛川》,那個深情回望,暗影錯縱的、戰後的、敗壞的大阪,民間黑市卻又如廢墟裡的螻蟻們充滿生機忙碌的,和美軍勾結盜賣軍用輪胎、黑道、想成為撞球世界冠軍的浮浪少年、毀了好幾個女人一生的酒館歐吉桑、華麗的脫衣舞孃、毀掉的毒蟲酒鬼賭棍、互砍讓對方殘廢的幫派小混混……像一條髒污、被倒棄了化學毒廢物,卻浮著一層豔麗七彩油斑的悲傷的河流。我總認為,能寫出這樣藏污納垢卻如唐卡之繁複迴旋的小說,濃縮隱喻了一座城市「海上花」之夢的,是像家輝大哥這樣的眼睛。
他知道江湖裡那些男女歡情薄、謊言裡的虛無和眷戀;知道經濟關係、權力交涉、爾虞我詐背後的人情義理;在這絞肉機般無情的資本主義峽谷聳立而起,那死生無常、冷酷異境後面,一些老文人老報人老生意人們的尊嚴和不為人知的溫暖事蹟。
後來有一次到香港,其中一個夜晚,家輝大哥又拉我到旺角的小酒館,我們互相噴菸吐霧,他不像平日那個媒體明星的自覺,臉在黯影中無比嚮往與虔敬,跟我說他打算寫一部自己身世之謎的流浪家族史小說(其實我想那或也是「香港」的某種隱喻)。
我聽得入迷,後來他又拉我陪他去附近的「麻雀館」假裝賭客「觀察場景」。但可惜的是我們走到那一整排店家全是「麻雀館」的暗影同時迷麗之街時,一間一間店家正拉下鐵門打烊,那些穿著背心短褲叨著菸、或戴著厚鏡片、表情模糊、說不出的憊懶厭棄的牌客們,挨擠、零落地走出。家輝大哥嗒然若失,說他想從這「麻雀館」充滿雜亂聲響、人臉雜遝的場景寫起。我驚呼那正是我喜歡的捷克小說家赫拉巴爾的故事幻術起點啊!他有一個詞:「底層的珍珠」。一座城市的文明、身世、記憶,就是從這樣藏污納垢、壓扁擠塌的垃圾場廢紙塊,妖妖裊裊長出來的啊。
我說沒關係,你下次可以自己再來啊。但家輝大哥沮喪地說,不行,他走進去,隨便就被人認出來。(他的臉透過電視,在香港走到哪都會被人認出)。
這種「灣仔∕香港」的嬉弄,「在之外」,像邊境或細胞膜、不同城市酒店旋轉門穿梭的「業餘間諜」、流動的微形攝影機、過客……,他形成了一種奇幻的自我戲劇:一座一座城市如鏡廊、萬花筒、默片……,那有一種香港仔特有的「阿飛氣氛」,世故的、冷的、嘴角帶著譏誚笑意,無法真正入戲進入他人夢境中當真的身世自憐和排外爭吵,所以他也講民國滄桑,也議論北京與香港人的「指人為狗」事件,或是微博、語言的巴別塔,薄熙來事件,講重慶的吃、北京的出租車……但那一切似乎都是「在旅途中」的轉場。都是電影般的浮花浪蕊。劇終了,觀眾席燈亮起,他抹抹臉上的冷淚,站起身,提著皮箱,鑽進的士,或穿過機場海關,便又是「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那樣的蕭瑟孤寂。
人物品藻時,你發現他愛挑漂亮的人講(不論木心、汪精衛、梁朝偉、吳彥祖);筆下人各自命運詭譎、顛沛飄零,身分或身世在歷史激流的折灣暫緩處,但他似乎皆從其美麗臉孔啟動其感慨。而閑筆城市(或寫香港,或寫「我」這個香港人在別的不同城市移動),光影轉換處,你發現他極愛聊那些市井雜談「俗氣味」的細節作為落點:譬如重慶火鍋、□骨的感嘆、香港的菲傭、北京的爺、風水……,龍蛇雜處,相濡以「沫」(挨擠、擦撞之各色人種、各階層人的體熱汗臭與唾沫),這種挨擠感,層疊雜遝,張愛玲在〈桂花蒸阿小悲秋〉裡喜歡的街車聲,油哈味,襖褲疾行在窄弄的糜蒸空氣裡的散文性格,書名曰《愛上幾個人渣》,其實或必須是一香港灣仔出身的,貪戀繁華骨子裡卻虛幻之眼,泅泳過城市最底部污髒水溝卻打撈浮世繪最豔麗之油彩的「阿飛靈魂」,才得以調度如此靈活跳躍,蒙太奇,閃回,剪接幻覺,穿透……,一種既舊又新、亦莊亦諧、知識分子之高蹈姿態渾進市井雜語,將不同時間鏡面之城市縫接,觀看之視窗。
整本書最動人處,當屬輯三「哀傷的粉絲」這一章:諸如〈選擇相信,或不信〉、〈放心,媽,我會給你燒一副紙麻將〉、〈選擇快樂的女子〉、〈哀傷的粉絲〉……篇篇皆沉靜深邃,像中年傷秋在一人生的時點,淘洗記憶河流裡那幾顆被磨圓刨光,如今剩下懷念或哀矜的小卵石。
但緊接著到了輯四「愛上幾個人渣」,那像是薩克斯風手驟轉進亂世浮生的花腔顫音之炫技:從「志明與春嬌」,到「盛女愛作戰」,到「張國榮為什麼叫作『哥哥』?」,到瑪麗蓮夢露……,我有時覺得,馬家輝大哥是田納西.威廉斯那個年代,或費茲傑羅《大亨小傳》那個世界裡的人物。看遍燈紅酒綠、禽島般的漂亮人兒在跑馬燈換片的新時代奢華想像中,匆促草率地登場下場。他冷眼旁觀,卻從不犬儒,他看到那浮華男女一些愚蠢行徑時,也會笑罵一聲:「人渣!」但你發現他是軟心腸的,甚至寶愛著這些虛幻搭景裡庸碌趁熱鬧活得起勁的人們。他本該有香港知識分子的冷和酷,但他有時卻近乎浪漫地同情且理解這些「香港∕灣仔」風格的「漂亮」(未必是美)。因為他自己也是漂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