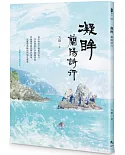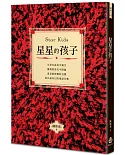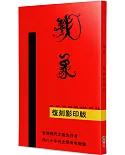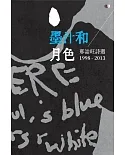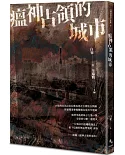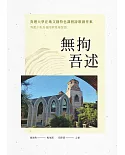太平洋濱的刺蝟---代序
記不得第幾次參加在花蓮市松園舉行的詩歌節了,十月依然燠熱的室內,不知哪裡冒出來的那麼多聽眾---他們平常都在哪裡﹖讀詩嗎﹖為什麼台灣詩集一般難賣一刷﹖也許都並不衝著我來的罷,只能這樣解釋。
從位於南京街的家走到松園不需廿分鐘,途經那已經拆空了的「溝仔尾」(舊夜市及風化區) ,「市中心」精華路段的中正、中山和中華路,過美崙溪走上美崙坡便是了---這一路由「非詩」步行進入「詩」,過程依然使我困惑。
相較於「非詩」的版圖,松園那小小幾間房間,像大海中央的孤島。島上一群「詩人」奮力向四方虛空吶喊,連迴聲都聽不到。
「你是回來松園開會嗎?」媽在我出門前這樣問,似乎瞭解我正要去參加一場醫學會議。
遠遠地松園那獨棟老舊的兩層建築傳出了麥克風擴大的人聲和音樂,海風徐來,松林亭亭, 卅年前在林中戶外寫生課的景象依舊歷歷在目, 只是少了一些原始和神秘。
總是有人捧著書來要簽名, 一本接一本---不禁起疑:我的詩集有這麼好賣? 還是轉手這些經作者簽字的書可以上網拍得好價錢﹖
一位婦人也湊過來要簽名, 一面解釋(大概見我一臉困惑於她似乎不是平常會讀詩的那種人):我女兒讀慈濟,老師帶她們全班來,我也陪著來。
「謝謝你來…。」我堆起職業性的笑容(一面懷疑詩人如何能是一種「職業」),一面說:「大姊…。」
她一聽,立刻臉色一變,氣沖雲霄:「什麼大姊,我還比你小兩歲!」
當我上臺讀著歌誦愛與青春的詩時,台下有著這樣介意我比她大兩歲還膽敢尊稱她「大姊」的「讀者」,心中又是尷尬,又有說不出的難過。
很難解釋這難過從何而來,只直覺詩人與詩與讀者中間的那條看不見的連繫的線,不應該是落在這樣一個喧鬧,擁擠而揉離的場合。
千年之外的屈原,李白,千里之遙的波特來爾,莎翁,之於我們,都絲毫不曾影響這條線的堅實緊密。
而在這濕熱擁擠的會場,我卻覺得我和詩,和詩另一頭的讀者,相隔無比遙遠。
詩唸完了,台下響起掌聲,為什麼,我覺得我唸的這首詩一點也不好,我唸得也不好,為什麼就沒有人坦率誠實地說:我不喜歡這首詩,你唸的不好。
聽見這樣的掌聲,我眼角微濡,心中泣血。
詩人需要的敬意不是這樣的。我在吶喊。
如果你在讀著我的詩的時候嘗經心頭不由自主地一緊一震,曾經眉頭微蹙或嘴角飄過一絲心領神會的微笑或用眼尾餘光瞥見了我們共同窺見了的那光年之外一顆神秘的星光,既使今生只是陌路,我都能在車馬喧囂中聽見千里之遙千年之外你如潮汐般的呼吸。
那樣地貼近。
如果不曾,請你隨手放下我的詩,繼續你的人生行路,其他的閱讀。
而在松園,一切是那麼的疏離而遙遠。
詩在拍手,致敬,高歌,「面對面」之間,遺落了更多詩的初衷與本懷。
柏拉圖從他的理想國裡趕走了詩人,正為的就是詩人「複製了拙劣的想像型式」, 而「遠離了真實」。
在詩裡,我要的是靈魂裡深埋的真相,而不是此刻週遭如潮水般湧來廉價的掌聲。
如果你們要聽見我,就請你們讀我的詩,好好地,安靜地,專注地,深情地,老老實實地。
不要想到詩人。
如果你們想要對詩人好,就請只對他的詩好,就夠了。
我閤上手中的手冊,再一次後悔來到這詩歌節。
而過後不久我又要搭著火車北上由「詩」進入「非詩」的國度。
在我工作的醫院裡,有許多人亳不掩飾地鄙視著我白袍之外的繆斯身份。不務正業,誨淫誨盜。由松園返回臺北,這一路同樣使我困惑。昨日為我鼓掌的人知道今日的我的難堪處境嗎?
梁實秋說的,住在隔壁的詩人不過是個笑話。我真的真的真的願意就只是個笑話, 因為,居住在白色巨塔裡的詩人都應該是螻蟻屎溺之流罷。
「聽說你在詩歌節第一天的晚餐上都不跟人說話…。」有位年輕詩人在詩歌節後沒兩天這樣跟我八卦:「有人看見你一個人坐一張桌子,都不理人…。 」
我驀然想起那個晚上我端著餐盤踏進餐廳的情景。每個人都極力做出良善,隨和且怡然舒泰的模樣,努力社交著。小小的餐室,長長的刺蝟的刺;隱隱的低氣壓。
而我是同志,情色詩人,和我一起用餐恐怕會得愛滋病吧? !
每個人都有禮貌地立刻找到了共桌吃飯的人。
我端著餐盤像個隱形人坐在自己的位子上。
刺蝟們在詩歌節裡暫時收短了身上的刺,相互取暖。但並不包括我在內。
我只好是那隻刺最長的刺蝟,在我的理想國裡,驅逐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