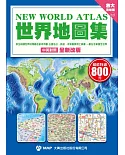推薦序1
反著活,倒著走
許多中國人的父母過度強調孩子的早熟早慧,孩子從小到大因此活得規規矩矩,少年老成,三十多歲扛起背包旅行才第一次感覺年輕,五十多歲功成名就後才開始泡夜店,就像好萊塢電影《班傑明的奇幻旅程》裡描述那個出生時是老頭,臨終前終於變成嬰孩的男主角那樣,生命是反著活的。西方人眼裡看來滑稽甚至有點恐怖,但大多數這一代的中國人都能理解。
也有一種人,老是在上班族一大早爭先恐後上班的時候,才跟別人反方向搭著地鐵回家睡覺,我們無法理解這種人的生活方式,這樣的人如果不是壞人,正好留長髮,又有辦法維生,就一律管叫「藝術家」。這樣性格的人,會選擇跟從歐洲出發一路往亞洲前進的旅行者背道而馳,從北京的後海喝杯啤酒後就搭便車出發去德國,
想必也沒有人覺得太訝異,反正就是喜歡把路倒過來走的那種人,要是能像黃明正那樣倒立著過日子、看世界的話,恐怕也會這麼幹。
有意思的是,這種特立獨行的人,不分種族國籍排成一列擺在一起,看起來無論穿著打扮、神采、態度都很像,不信的話去隨便一家標榜地下音樂的酒館混一個晚上。
因為這個時代,就連不一樣,都不一樣得很相似。
《出走,搭車去柏林──在路上的頹廢壯遊,給自己的成人禮。》的作者,是來自北京的獨立紀錄片導演劉暢,跟他的哥兒們谷岳,
一個這輩子只在十多年前正式上過一個月班的朋友,兩個藝術家,一個沒什麼存款卻有氣喘,另一個活到三十多歲沒出國自助旅行也沒住過青年旅館,卻憑著對於世界的想像,跟一本過期好幾年的旅行指南書,一路從北京搭車去柏林,亂七八糟、顛顛倒倒,以為這一路會看清世界,結果看得最清的是自己。
他們這趟旅行的過程,雖然跟許多背包客、驢友的路線不同,但是得到的結論,老實說跟世界上古今中外任何一個背起背包出國三個月的年輕人,都差不多。
以為這是一輩子一次的壯遊,但到達目的地以後,才發現真正的旅行才要開始,這點也不怎麼稀奇,父子檔自編自導自演,描述老來喪子的醫師父親,背起亡兒的背包代替兒子完成庇里牛斯山朝聖之旅《The Way》,就是這麼演的,挺主流的,所以這兩人接著不久又籌劃起從阿拉斯加到阿根廷的旅行,也是意料中事。
本書整個故事真正特別的,在於故事的主角,是兩個中國的中年男人。
中國這一代都會男人的世界觀,跟世界是有距離的,基於種種內外在因素,在亞洲比起韓國、日本、港台的男女,海外壯遊或自我放逐的經驗是少的,所以看到這兩個無論是自我期許或是社會評價都很高的北京文化人,能夠放下身段,走進地圖上沒有多少著墨的機場與機場之間的虛線,用搭車的方式,用誠實的態度和開放的心胸填滿知識的空白,走上個人派的朝聖之路,用慢遊的方式來表達對世界的敬意,真誠的欣賞中亞的吉爾吉斯與土耳其鄉間無法第一眼看到的美好,虛心體驗勤勉的韓國人在世界盡頭的競爭力,並且回頭反思這一代中國人(主要是漢人)對陌生人的冷漠與不信任,以及中國有車的中產階級對於明明是舉手之勞,所表現出來的卻是近乎可恥的功利與吝嗇,這些外頭人人都知道的事情,一旦來自外人就會被當成耳邊風的批評,如今出於菁英分子的親身經歷,或許就能形成一股內省的力量。
譬如,在這趟旅行的回憶中,劉暢說到在吉爾吉斯出乎意外的美好生活經驗,讓他重新思考現代人最在意的「幸福」這檔事兒。
他說:「簡單並快樂,就是幸福感,就好像生活盡在掌控中,哪怕天公不做美,下雪了,遇到什麼災害了,他們也能應付。如果風調雨順,他們可能會多養點兒羊,再多養點兒馬,他們的生活小富即安,有自己固定的房子,在山上有放牧點,有自己的車,子女也在大城市裡工作,小兒子在身邊服侍,人與人之間關係簡單,那種和睦感滿足感特別讓人羡慕。」
這種描述,跟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裡面描繪的世外桃源其實是極度類似的。
當然,指著開著名車,戴著名錶,住在豪宅裡的山西煤老闆富二代的鼻子說:「你眼前所擁有的一切所帶來的快樂,還不如吉爾吉斯的一窮二白的一介牧民。」是愚蠢的,但是對介於富二代跟窮牧人光譜的兩個極端之間,占據這一代中國人絕大比例的中產階級來說,卻是一個極好的提醒,提醒我們中年男人也可以去旅行,提醒我們可以路反著走,偶爾生命可以倒著活,就算沒有豔遇的旅程也可以很不錯。
國際NGO工作者 褚士瑩
推薦序2
不是「旅行」,而是「流浪」
我一直想「流浪」!
我說的不是「旅行」,而是「流浪」。在我的定義中,流浪不該有行程,甚至不該有明確的路線,簡單來說,流浪就該讓命運決定把你帶到哪兒去。《出走,搭車去柏林──在路上的頹廢壯遊,給自己的成人禮。》就是這樣的「流浪」故事。
作者劉暢和伙伴谷岳的搭車計畫──從北京一路搭便車到柏林。搭便車充滿不確定性,搭上誰的車,走哪一條路線,遇見什麼人、什麼事,都由命運決定。我看到這兒,就熱血了起來,完全是我心中夢幻的「流浪」。才看完前言,我的心跳已經加速,已經迫不及待跟著他的文字回到搭車上路的那一天。
「谷岳是搭車計畫的始作俑者,我陪著在路上不斷傻樂。」劉暢的這段文字,我特愛「傻樂」這個詞。這段交給命運決定的流浪旅程,就像人生一樣,遇到什麼都該用這傻樂的心情去面對。他們用傻樂與每個接觸過的人交心,也因為這樣,旅程中所經歷的片段,說起來似乎都有那麼點相同的青年旅館種種、與當地人共舞……等,有了劉暢與谷岳參與其中,就變得不同。
除了「流浪」這回事,更打動我的是作者劉暢的心境轉折。畢竟我們同是三十歲,這個青春所剩無幾,夢想被時間與現實擠壓的年紀。工作了幾年,人生已經不再新鮮,充滿了「不得不」的感嘆,不敢想自己哪一天可以達成別人的期待,而自我的期待已經消失很久了。三十歲就是這麼一個讓人想嘆氣,卻仍有點不甘心的年紀。我才紮紮實實的掙扎了一回,看到劉暢筆下的感嘆,更有種同是天涯人的心情。值得開心的是,我們同樣的掙扎了,也同樣透過流浪找回了自己年輕的靈魂。
他在旅行中點點滴滴地突破自我,極度內向的他學著谷岳至少也成為三星半的搭車人。從第一次比出搭車國際標準姿勢,第一天就想放棄回城裡吃涮羊肉,到最後旅程結束時「怎麼就這樣結束了?」的失落心情,這三個月的旅程確實改變了他,也改變了許多看過紀錄片的年輕人,更改變了即將在半個月後踏上流浪旅程的我。
看到旅程的終點即將到達,我也跟著有點感傷了!這精彩的旅程就要畫下句點了。「搭上最後一輛車,駛進終點時,我在想,無論多麼難的事,如果你當一個旁觀者,就覺得肯定很難,但如果身體力行,多麼難的事情都會慢慢過去。」我在心中默念了兩遍劉暢最後寫下的心情。
所有流浪過的人都知道,流浪從不會真正結束。「這只是一個歇腳的時刻。」劉暢說。流浪過程中得到的養分會在心中滋養出另一段流浪,每個句點都是下一個章節的開始。看到最後我發現這本書不只是個流浪的故事,而是個三十歲失去夢想的紀錄片導演找回自己熱情靈魂的故事。
我有幸在流浪啟程之前看完本書。劉暢與谷岳因著《在路上》這本書而上路,我的流浪旅程也必定因《出走,搭車去柏林》這本書而會有不同的化學變化。至於搭車流浪會出現在我旅程的哪一個章節?就交給命運決定吧!這才叫流浪嘛!
旅遊作家 唐宏安
推薦序3
因為無法預期,讓回憶更美好
「一趟旅程,永遠是無法預期的;但也就因為無法預期,更能誘發出回憶的美好!」這是我每次結束旅程之後,浮現在腦海中的一段話。
我也曾經在過往的旅遊中,花一個月搭便車旅行。雖然聽起來感覺很厲害,但我卻覺得這絕對是旅遊行為中最具備挑戰性的事。因為在過程中,真的會發生太多想得到和想不到的情況,往往事發突然,完全無法控制。
像書中〈遇上了搭車的競爭對手〉該篇提到,本來以為是會越來越順的旅程,怎知會半路殺出程咬金,出現了搭便車同好,重點又是一位女性,兩個大男人搭便車的優勢頓時消失了。也就因為如此,會衍生出一個搭便車的不成文公式,那就是「單身辣妹最容易搭上車,三人以上(尤指男性)困難度是難上加難」,藉由這句話,也讓我回想到當初那如苦行僧的旅程。
再者,這樣的旅遊行徑是最挑戰中國人傳統觀念的。作者在書中也提到,在中國願意搭載他們倆的司機真是太少了,但到了歐洲,舉起手來搭車,感覺上似乎是簡單多了。這讓我想到我們從小到大的教育,總是將「陌生人」三個字冠上惡名昭彰的罪名,避之猶恐不及。
而事實上真是如此嗎?相信藉由本書可以了解到很多情況並不是如此。因為在他們的旅行過程中,曾遇到小女孩主動幫忙帶路、也遇到富二代不但讓他們搭便車,還幫忙代訂四星級飯店,重點是連住宿費都付了等等,種種經歷聽起來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卻在他們的旅程中上演。而我也曾遇過相同的情形,剎那間真的會讓人覺得疑惑,為何在我們熟悉的國度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如此疏遠呢?彼此之間都有戒心,不願意去幫助陌生人,深怕會招來麻煩。
我曾經在旅程中,遇到一位十八歲的外國女孩在荒郊野外讓我上車。我當時的造型和土匪沒兩樣,而她竟然敢讓我上車,各位試想,在這種情形中,到底誰比較危險呢?
說實話,換做是以前的我,我是不可能搭載陌生人的,但現在的想法卻全然不同,也是因為一句話感動了我。當年我在搭便車的過程中,曾經有一位搭載我的司機對我說:「保護來我國家的旅行者的安全,是我的責任。」這種窩心的感覺,就和本書兩位作者的感受一樣,令人難以忘懷。
「我喜歡冒險,但絕不是冒生命危險。」我覺得這一句話就足以形容搭便車旅行的感受。其實做搭便車的旅行,並不是要證明自己有多行,只是要藉由這樣子的方式,凸顯出「自助旅行」可以是多元化、不受拘束的生活方式。好比作者在書中寫道,「如果有機會和別人交換各自的生活,那麼,我會選擇和誰交換?」不如藉由旅行的機會,把上述的疑問句,直接化為肯定句。
強烈推薦此書!最後我套用書中的一段話。「人生不再新鮮,多少對未知的探求也泯滅在這許許多多的『不得不』裡。」如此無奈的文字,不就反映出現代人的心聲嗎?各位親愛的朋友,與其如此,不如短暫拋開那無謂的「不得不」,規畫一趟屬於自己的旅行吧!
自助旅遊達人 陳岳賢
前言
因《在路上》而開始的冒險旅程
如果你在百度上搜尋「搭車去柏林」,你可能會得到幾十萬條資訊:二○○九年,兩個北京小伙子──谷岳、劉暢用一個夏天,以舉手搭便車的方式途經十幾個國家,一萬六千公里的旅程到達德國柏林,看望一個女孩。這個幸福的女孩叫伊卡,是谷岳相戀三年的女友,這種極富浪漫色彩的苦行見證了普通人愛情裡的閃光點。那麼,兩個旅行者中的另一個人,劉暢,總是會遇到朋友們各種各樣的疑問,你,又是為什麼而去的呢?我想,寫這本書也許可以表達出我含混不清的旅行目的,以及為了逃離我們庸庸碌碌的人生而作的一切努力。
一開始,我認為一切都跟一本書有關。那就是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在路上》。書中兩個年輕人不斷瘋狂地穿行美洲:搭車、自駕、不能抑制地無目的地旅行。「這種離經叛道的行為儘管幾乎不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它卻具有相當的迷人之處。」
二十世紀五○年代,《在路上》出版後,《紐約時報》刊登的書評這樣寫道:「在極度的時尚使人們的注意力變得支離破碎,敏感性變得遲鈍薄弱的時代,如果說一件真正的藝術品的面世具有任何重大意義的話,該書的出版就是一個歷史性事件。」
《在路上》讓無數的年輕人拿起簡單的行囊上路,開始了一代又一代人沒有目的地的旅途。他們害怕鏡子中的自我,最終丟失在物質洪流裡,或僅僅是表演著為尋找自我所做的逃離。去哪裡並不重要,關鍵在於做出反抗現實的姿態來,這些年輕人表演、鞠躬,之後就往後一躍,跳進舞臺的側幕裡,五十多年來重複上演著這樣一幕幕鬧劇。這一文化轟轟烈烈繁衍至今天,從文學、從音樂、從電影,成為主流消費文化之外的另一體系。說到這裡,我們為什麼選擇搭車旅行已經表示得很清楚:我和谷岳很快就會離「年輕」這一辭彙越來越遠,我們長年如同螞蟻一般的努力奮鬥在時代洪流面前,漸漸變得微不足道,物質的家園早已褪色,精神的家園形單影隻,搭車旅行,在路上,更像一場遲來的成人禮。
作為一名微不足道的導演,在搭車旅行之前,我曾設想過拍一部公路電影,一男一女,兩段截然不同的旅程,目的地相同卻永遠沒有相遇。男主角路過生命的孤獨與割捨,女主角路過生命的迷惘與歡愉。寫作劇本是漫長艱辛的過程,我發現,公路片只能在公路上完成。在漫長的煎熬和等待中,好友谷岳的邀請彷彿是從天而降的禮物。三個多月的旅程,我們接觸到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在他們的車裡、家裡,遭遇不同人的人生:在新疆廣袤的沙漠,慷慨地搭每一位路人同行的石油卡車司機;在吉爾吉斯酒後遭遇牧民熱騰騰的馬油大餐;烏茲別克沙漠船隻墓地的守墓老人;裡海邊獨臂豪飲的俄羅斯水手;土耳其豪放熱誠的富二代;伊斯坦堡雄渾壯觀的歐亞兩岸;羅馬尼亞堅強的孤兒院志願者;匈牙利布達佩斯青年旅館的韓國老闆;布拉格的CROSS重金屬俱樂部;東柏林的藝術家貧民窟……親自體驗並拍攝一部公路紀錄片,是我這些年來最大的夢想。我相信公路電影的製作者們都經歷著這樣在路上的日子,思想的巡遊也必然伴隨著身體的遊歷。
《在路上》這本書從二○○○年一直陪伴我到現在,四次閱讀都沒有翻到最終章,命中注定它要留給這次旅程。在搭車旅途的某輛大卡車上,我在顛簸的駕駛室的臥鋪上讀完了最後一頁。車窗外是何時何地的風景,都已不再重要。
《在路上》的結尾這樣寫道:
我知道在愛荷華州,在人們允許孩子們哭泣的地方,孩子們在大聲地哭泣著。今夜,星星就要出來,你可知道那大熊星座就是上帝?今夜金星一定低垂,在祝福大地的黑夜完全降臨之前,把它熠熠的光輝灑落在草原上,藏起河流,裹住山峰,隱沒掉最後一片海灘,然而完全沒有人知道,自己除了可悲地趨向衰老外,還將有何遭遇。
這本小書是我個人的小小旅行隨想,有些旅程段落詳細,有些只是一筆帶過。這趟旅程我和谷岳約定好一人寫一本書,同樣的旅行不同的視角,不同的生命體驗與收穫。我偏執於一個普通北京人的視角,偶然的機緣巧合,展開搭車去十餘個國家的夢想之旅,我沒有超於常人的意志品質,也沒有職業旅行家的豐富經驗,更沒有超凡脫俗的個人魅力。我只是因為想要追求一些自己以為需要的東西而與朋友踏上旅途。旅途終結的時候,每個人的內心都因為這段路而得到了某種圓滿,於是那個原來執著的目標也許就不再重要。
劉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