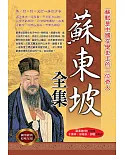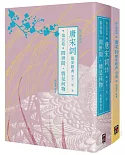推薦序
風華絕代的魏晉南北朝文學
東吳大學中文系教授 林宜陵
本書寫魏晉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阮咸等名士縱情的生活,努力追求生命的本質快樂與精神上的自由,「在田園竹林間肆意酣暢」、「在狂嘯與痛哭中,繼續另類的生活姿態」。寫南朝竟陵之友,把文壇照耀得絢爛奪目。他們是毅然投身於混沌的朝堂。卻因為單純與傲氣,最終換來官場凋零夢。高大的宮牆豢養著畸形的欲望,繁華褪色後盡是惆悵。
魏代的正始(魏齊王芳)詩歌,《文心雕龍明詩》「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
晉代詩風分為太康詩歌與永嘉詩歌:
太康(晉武帝)詩歌(西元二八○至二八九)成員有張載、張協、張亢、陸機、陸雲、潘岳、潘尼、左思;鍾嶸《詩品》稱:「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
永嘉(晉懷帝)時期(西元三○七至三一三)有孫綽、許詢、桓溫、庾亮諸公。鍾嶸《詩品》稱:「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溫)、庾(亮)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直至劉琨、郭璞與陶淵明才另創一番天地。
南朝詩歌更由沈約《四聲譜》創「四聲八病」之說成為古詩的變體,促使律體的逐漸形成,成為日後詞的先聲,小詩的興起也促進唐絕句的形成,形式主義的與貴族宮體與山水文學的都在此時興起。
有南朝宋的元嘉(宋文帝)詩風(西元四二四至四五三),《文心雕龍.明詩》說此期:「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以山水詩為主,代表人物為謝靈運、鮑照、顏延之三大家。
齊的永明(齊武帝)體沈約等所發現的詩歌音律,和晉宋以來詩歌中對偶形式相互結合,就形成「永明體」的新體詩,是「古體」過渡到「近體」的重要階段代表詩人有沈約與謝朓梁陳時期的宮體詩,代表詩人有蕭衍(梁武帝)、蕭統(昭明太子)蕭綱(梁簡文帝)、蕭繹(梁元帝)。
同時期的北朝有北人仿南、南人入北詩歌相互激蕩。產生北人仿南:魏胡太后〈陽春白雪〉:「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闥,楊花飄蕩落南家。含情出戶腳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來雙燕子,願銜楊花入巢裡。」南人入北:王褒與庾信,庾信有〈重別周尚書〉「陽關萬里道,不見一人歸。唯有河邊雁,秋來南向飛」。
這個文壇與文人俱是多樣精彩的時代,本書作者以更貼進現代的思想與語言,舉實例詮釋作品讓讀者更容易感受文學極盛時代的風采,是一部極適合閱讀與體會文學與文化的作品。
作者自序
亂世奏清曲,憂思獨傷心
醉酒林間,他們像久居山中一般。寧願遺世獨立,也不願進入俗塵。萬里山河竟無容身之所,身心俱疲不如出世獨居。
帶著閃爍的怨念,夜夜笙歌的他們在瓊漿中老去,昔日的浮華早已煙雲散盡,而今的歲月卻是殘陋不堪。
依然奏起《廣陵散》,依稀盛年時雅緻的曲調。只是,風雅中多了幾許淒涼。風雅是當他們年老,與自己的回憶相遇時最大的諷刺。
當所有往事和塵埃都落定在寬大的衣袍之後,虛構的烏托邦頓時崩殂。
苦雨中,是腐朽的理想幻化出的螢火蟲,微弱的光,一閃即滅。—題記
漢末的戰亂,三國的紛爭,八王之亂,五胡亂華,南北朝代更迭不止。在那三百多年的大分裂裡,幾乎沒有片刻的安寧。這是一個真正的亂世。在文化旅途上尋尋覓覓的余秋雨,停駐在漢亡後屢次易主的喋血朝闕前,發出深深嘆息。
戰禍使很多人喪生,也使許多能夠發出聲息言論的人不斷去思考死亡與罪惡的含義,越發體悟到生命的悲涼。「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曹操的《蒿里行》裡,滿目的白骨與空寂;「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朽株。」
陶淵明的《歸田園居》,盡是悲天憫人的沈吟。不得不說,這個時代文人的內心格外敏感脆弱,無時無刻不在感受命運多舛和人生無常。不過,也恰恰因為如此,激發了他們把真心全部投入到文學創作上,造就了一個奇葩輩出、文豪遍地的奇怪世界。
沒有漢代氣勢狂狷,也沒有紅袖美酒充斥的唐朝開放,更沒有清麗婉約的宋代文明,魏晉南北朝只有混亂可言,不到處慷慨放歌,也不仰天大笑,更不拈花微蹙愛嗔痴。獨獨選擇一面悲傷獨酌,一面灑脫隨性,在兩廂截然不同情緒的角力下,痛並快樂著。
於是有的人放達悲憫、有的人沈迷聲色,有的人放開紅塵遁世遊仙。世事無常,盡管醉生夢死、歸隱仙藥,偶爾與老莊隔世下棋,周旋於天地之道。這些生活的內容,不知不覺間成為了文人口中不斷吟詠的主題,在醉夢間痴痴嬉笑,傾吐心聲,追尋無妄的未來。也許唯有這麼做,他們才能獲得一絲的解脫。
若說魏風仍存有豪邁激昂的意味,那麼未來的數百年間剩下的幾乎就是玄道。玄學成為時代的主題,在這個時期,多數士人的心變成了一桿沒有秤砣的秤,不斷承載著他們臆想出來的逍遙涯海,無法計算重量。然而即便虛幻,他們仍給後人留下了最唯美的背影。
現代美學家宗白華先生曾言:「晉人風神瀟灑,不滯於物。他們以虛靈的胸襟、玄學的意味體會自然,乃表裡澄澈、一片空明,建立了最高的晶瑩的美的意境。」其實何止晉人如此,三百年分裂時期,久經離患和失志的文人們內心無一不具有空靈的美感。雖然他們痴迷於玄學,以至於險有誤國誤天下之狀,可是他們把心靈自由之美和山川自然之美,放大到了渾然遨遊天地間的地步。
另外一些文人、士人則因為門閥制度和觀念,在亂世中停滯不前,因為門閥制度阻塞了寒士的官宦之路,才高八斗者難免心生怨懟,憤憤而不平。還有一些人則是成了時代的犧牲品,於哭笑不得間,或自願或無奈的捨棄了塵世,留下無數餘恨的筆墨。
在文人們的悲歡天堂的另一面,樂府、民歌的世俗情趣,為這段過於清幽孤高的時空平添了幾分柔媚、幾分激情。在聆聽南人欲語還休的幽咽同時,偶聞得北方豪邁爽朗的放歌,精神陡然一震。原來那時的人們是抑鬱,卻也可以開懷的。
無論怎樣,笑過、哭過,甜過、苦過,或放浪形骸之外,或俯仰悲傷於內,五味雜陳的生活滋味被那些亂世裡不斷閃過的佳人盡數品在口中,藏於心中,落到筆下。人生得此,盡顯超然於歷史的風流之姿,不枉凡塵走一遭。
一個如此特別的時代,上演的戲碼百轉千迴,即便隨著時光的演進完全幻滅,依然能給後人留下無數不能忘懷的記憶。雖然諸多的真相在時間的推移下隱匿,但清澈的文字不會隨著血肉的風化而消亡,後世的看客若想重返那段光怪陸離的歲月,大可翻開當時人們留下的涓涓字跡,從文字中讀出那個年代不能說的秘密與趣事。如同經歷一場曠日持久的狂歡,投入之後再抽身,讓身體歸復平靜,內心卻悸動不已。
不要寄望太深,也不要失望愈厲,這本就是個旖旎迷亂的時代,愛它便愛得五體投地,恨它大可以恨得不屑言語。在這裡,有人醒,有人醉,有人怨,有人痴,他們並不在乎別人怎麼想,欣然笑納紅塵的洗禮。如果觀客真心喜歡,即便那字裡行間的墨者魂靈不能打破時空的界限飛越滄桑,仍能勾起同喜同悲者的共鳴。
知音,不求繁如星辰,唯願寥寥幾顆,與他們在天際間攜袂肆意行走,逆流逐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