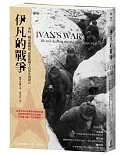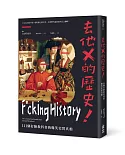尋找李長聲的真身 湯禎兆
不敢自詡為李長聲的忠實讀者,但先生著作一上手,條件反射地捧讀下去是免不了的自然反應。《日和見閒話》內的文章,也因此之故算是一讀再讀的了,可是這次卻看出點班雅明來。
那當然不敢虛應是為了湊時髦而胡扯,何況「浪遊人」(flaneur)一詞已至幾近一見即俗的荼蘼盡處,硬套在先生文稿上,不啻佛頂撓糞。是的,要找四處遊蕩的閒逛者原型,回首萬曆請張岱坐鎮便成,何必遠赴德意志沾光。何況先生絕對沒有蘇珊.桑塔格一針見血道破班雅明的土星性格──憂鬱非本性,出入濟凡心,那到底李長聲還算是哪碼子的「浪遊人」?
是甚麼觸發我對李長聲產生「浪遊人」的聯想?對,一切都拜永井荷風所賜。日本近年的荷風熱,固然託東京散步的古老湊時髦所致,然而李長聲對永井荷風的鍾情,卻是從來貫徹貨真價實情透紙背。永井揭櫫的散策風情,在市內蹓躂作細緻觀察,而且又依戀文明城市,自屬「浪遊人」的典型人板──「浪遊人」鍾情世俗物事,選擇大隱隱於市,在街頭巷尾中穿梭徜徉,一個人獨自信步而行,既入世又出塵。何謂永井荷風漫遊的還統牽古今,在胡同中嗅出鄉愁,文學化乃至神話化本也理所當然,然而那不正屬「浪遊人」所具備的一雙陰陽眼,在流行物事中看出腐朽屍意,於老去幻景窺出泉湧活力。猶有甚者,是當中的乾坤挪移術,當李長聲侃侃而談永井荷風如何苦練法蘭西外家套路,回瞻啟迪參悟江戶本門心經,由是借東京作為力場,創立永井一脈的散策門派──你真的可以視而不見作掩耳盜鈴狀,把作者借力打力的創作告白履歷書就此過目即忘?作者由長春遊走至千葉,今天為人以知日學者傳誦捧讀,然而筆下從沒有背離筆記風情,幾至打造成李氏獨門別具一格的知日文學大道來。
不過,李長聲倒沒有把永井荷風捧上殿堂奉為偶像,如果對文革風有一鱗半爪的承傳,那大抵絕不在於後記中敬謝不敏的痞子風,而屬切忌神諭級的靈光普照。我猜想他與三島由紀夫最投契的一次,或許乃在於對永井荷風的魅力評議:「用最優雅的文章寫最低級的事情,用最都市化的文章寫最粗鄙的事情。」雅俗交融的物我不二境界,我輩小卒,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但李長聲的一句「呵呵」,卻道盡知己忘情一矢中的滋味。正因知己相忘江湖,集中才有酒醉及對談等篇章的精闢體會。
由衷而言,李長聲最最「浪遊人」的真身,仍非以上的輪廓線條。正如蘇珊.桑塔格對班雅明最敏銳精闢的觀察,也非在憂鬱性格的觀照,而是對他作為微物收藏家的深刻體會。她固然指出班雅明的收藏家的身份,也不諱言他為物所累,但微物同時正好也成為了無功利沉思及狂想的對象。由大米到栗子,從馬刺到豆腐,自梅乾往青苔,甚或俯猴覽天狗,要認識並總群勢,文辭盡情的精要,範文早己一一臚列。當中的關鍵精韻,時髦趨時可謂之微物政治,學究用語為文本細讀,最像人話的尋常語,大抵都算是觀察入微吧。
我認為一系列村上春樹密碼文章,最適合作示範舉隅。〈井〉與〈貓〉之選題下筆,自有上陣定勢之氣道,恰若後方擂鼓,武將喊場作正面痛擊的淋漓快意。然觀其兵備,一招一式全皆名門路數,實事求是於村上國境中進行探井及尋貓的冒險,最後一言一語之所得,全無捷徑適俗之點滴,恪守執正馭奇的功架。個人最偏好的還有〈情人旅館的字畫〉,可謂盡得一唱三詠風流。啟首點明旅館中掛上相田光男的字的畫框,大家一臉惘然靜待老師解畫之際,準備打算再上一課看小說學日本文化,豈料交代相田光男背景之後,作者筆鋒一轉,將先前的懸疑佈局無情戳破,原來相田不過一芥草茅,讀者面面相覷啞口無言。說時遲那時快,作者直陳對相田光男不入流的書法無甚好感後,登時便委婉地點明與村上同流的知己會意──把他的字掛在情人旅館中,一切原來早有評價。於是連我等凡夫,瞬即明白他鄉遇上Richard
Clayderman或Kenny G,體悟到高手比試沒有多餘一招半式的愉悅趣味。
我得承認對李長聲的微物「浪遊人」真身由衷佩服,尤其在刻下萬物萬目幾近皆可統整為文化研究的出版風潮下,建基於文本細讀後的體會思考,迴避了任何大論述的空泛框架,更加與時尚的先理論後配對之務新筆法背道而馳。每次捧閱李長聲的文集後,我總想周星馳若要寫作,大抵也應把金句對白改為:書,應該是這樣寫的。
寫作理應沒有甚麼時尚不時尚,甚或出版地域差異的隔閡吧──都甚麼年代了,如有甚麼分別,一切都不過屬好看與不好看之別,僅此而已,別無其他。
後記
出書寫後記,是要對讀者有一個交待,也不免替自己做一些辯解。
先交待「日和見」。──在電腦上打出兩行字,座椅猛地搖晃起來。僑居二十餘年,對地震習以為常,繼續往下寫,卻愈搖愈烈,而且有一種扭動的感覺。吊燈擺盪,書從架上劈哩啪啦掉下來,這可是頭一遭。幾年前發生豆腐渣設計事件,所居樓房也特意檢查了防震程度,應該抗得住,但這麼強烈的地震接二連三,不由地心驚。時間是二○一一年三月十一日,太陽已偏西。
看電視才知道震災之嚴重。引發的海嘯把船舶涌上岸,飛機浮起來,房屋浩浩蕩蕩地漂移,遇到障礙便碎為齏粉,足見那海水沖盪的力量,停車場上的汽車猶如被大手劃拉的滿桌麻將牌。走下八層樓,查看住居周圍:地面噴泥沙,信號燈不亮,道路寸斷;寸斷是日本說法,他們常說中國人愛誇張,白髮三千丈,但寸斷也未免言過其實,充其量丈斷。這一大片地方是從東京灣裡填出來的,據說下面被震成液態。上水道損壞,斷水,海上自衛隊用艦船送水,這是我第一次跟日本兵零距離接觸。去商店買水桶,售罄,看來很多人家像我一樣未防備。又去買手電筒,只剩下一種最貴的,這種時候買不買,價錢仍然是一個考量。上樓下樓打了十天水,深感生命在於運動。最鬧心的卻是人為的,福島核電站發生事故,束手無策的模樣令人惶惶不可終日。人們往西逃,外國人蜂擁離開日本,據統計,三月十二日至四月八日之間出走五十三萬人。走了廚師,走了跑堂的,好些中華料理店歇業,只剩下老闆為房租叫苦不迭。
日子過得膽戰,膽戰的日子也得過,過著過著事情就開始過去,不遠處的迪士尼樂園重新響起了歡樂,我也接著交待「日和見」。
這個日本詞的本義是看天,看天氣好壞。日本人重視天氣,見面少不了今天天氣哈哈哈。有這類套話很便利寒暄,避免了相視一笑或者被問及行蹤的尷尬。人類如今也只能預測用各種手段看得見的天氣,像這次東日本大地震,說是「想定外」。地震、海嘯是造化要修改自己的作品罷,基本結構沒有變,天照樣暖,花照樣開。東京都副知事說:不妨賞花,不妨喝酒,自慎過頭就冷卻消費,但也要想想東京的火葬場正燒著從災區運來的屍體。這位副知事是作家,而知事石原慎太郎作為文學家更著名,他說海嘯是天譴,好好滌蕩一下日本人橫流的私慾。
那麼,辯解點甚麼呢?
以前某先生讀了我的作文,說我「頗有經過文革的人士所慣有的行文的『痞子味』」。這個批評是對的。說話作文有腔調,人所難免,也許即所謂文體。日本電視上有一位戰地攝影家走紅,不是因攝影,而是他說話慢條斯理的腔調,聽多了就變成裝腔作勢,引起了反感。村上春樹說過,重讀自己寫的東西好像聞自己脫下來的臭襪子,我重讀確實聞到了一股痞子味。我不唱卡拉OK,文革年代也不跟著唱語錄歌,簡直像元祖「宅男」,地道逍遙派。之所以逍遙,有一點天生,有點學魏晉人物,也曾為自己屬於不革命而忐忑。「日和見」引申為觀望,有等待時機以求一逞的意思,我對於橫掃甚麼的,作壁上觀。彷彿閱盡了人類從上至下的全部醜態,有了點虛無,凡事都覺得無聊,疑神疑鬼。畢竟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烙印了這一代的集體記憶與共同語言,說出來有一種認同,一種會心。把歷史放在諧謔中記憶,可減輕心靈的負擔,若無其事地前行。或如文化評論家桑原武夫所言,中國和法國有這樣的觀點,即在某種意義上,語言比內容優先,語言的修練形成價值。其實同代人並不是我的讀者,真不該下意識地跟他們說話,滿紙痞子味。有人把一首古詩貼上網:夜深衣薄露華凝,屢欲催眠恐未應,恰有天風解人意,窗前吹滅讀書燈。年輕朋友笑道:洗巴洗巴睡吧。這該是現今痞子味。讀年輕一代能增加活力,讀年老一代能圓滑世故,讀同代人的東西呢,很可能同聲相求,臭味相投,一起發牢騷,一道走下坡路。
時見國內稱我為學者,這是編輯亂扣大帽子,以壯版面也。我夠不上學者,不過對日本文化有一些觀感罷了。譬如有人說,對日本文化的入門認識,文學從谷崎潤一郎的《陰翳禮讚》開始,電影從《猷山節考》,攝影從荒木經惟,然而我沒看過這個電影,也不喜歡荒木其作,且討厭其人。由於福島核電站事故,電力不足,東京一下子昏暗,我也沒看出陰翳之美。我行文有一個毛病,那就是通篇好話,得便總提醒一下,事情還有另一面,況且寫的是人們常說具有二重性的日本,也只能點到為止,卻常被讀成譏諷。「日和見」加「主義」意味機會主義,作者若不單為文學,不把自己當上帝,而是與讀者同在,娛樂讀者,似需要點機會主義。書暢其銷,如某某日本人所言,文化就跟在屁股後來了。
年輕多夢想,正好寫小說;人老了,若返璞歸真,那就寫隨筆為好。我雖然寫隨筆,卻尚未歸真,這一番交待和辯解無非要推銷自己,想賣這本書。
東日本大震災死難者七七之日 合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