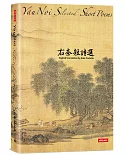推薦序
攝影家寫的詩
詩歌是人類最初的感動。無論任何文明,詩在文字文明形成前即已發軔,文字文明底定後,詩歌通常也是最早的記錄。
但詩在文字文明的秩序穩定後,卻很快就被整編進了「皇室-貴族-官僚-文士」為主軸的文字文明核心架構下,它在詩的形式要件如對仗音節、韻律輕重、用字遣辭等方面會趨於工整嚴肅,這是文學秩序的儀式要件。由於它已納入「皇室-貴族-官僚-文士」的文化架構下,詩的關心範圍也開始往國族神話、宗教信仰、大型傳奇寓言、英雄史詩、倫理事務、田園自然之美和愛情之美等方面集中,這些題材範圍差不多也是各類文明古典時代的共同特性,後來它也成了詩的文士知識分子傳統。
到了二十世紀,由於文化學的興起,人們對文化及文學秩序的形成,始有比較客觀的評價。而在此之前,則多半會在肯定文學秩序的守舊觀念下,視新生的文學類型,如十七世紀出現,十八世紀大盛的小說,以及較簡明的詩作等為較差的作品。
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著名文化學者羅文薩爾(Leo Lowenthal)在所著的《文學、通俗文化與社會》中指出,從十六世紀末開始,古代的封建社會進入尾聲,開始邁向變化快速的現代社會,各種通俗的文化形式,如新的劇院、新的寫作形式也都紛然出現,而最先對這種現象做出定位的乃是法國的蒙田(Michel de Hontaigne, 1533-1592)和巴斯噶(Blaise pascal,
1623-1662)。蒙田認為古典的文學與文化,乃是在陶冶人的心靈,而通俗文化則是一種缺乏正面功能,只是用來消遣和用來逃避生命壓力的東西,它只能算是一種「中間的地獄邊緣地帶」(Limbo in-between)。巴斯噶乃是具有神秘主義特色的神學家,他認為人在孤獨時乃是與上帝對話的時刻,但多數人都恐懼孤獨,因此才有通俗低劣的通俗文化之出現,而後通俗文化向德國擴延,哥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即視通俗作品為「容易製作的亂七八糟大雜膾」,只會造成「半調子的外行人」(Dilettantism)。而在十九世紀的英國,正統的文學更強,而當時的通俗文學亦盛。1724年,倫敦即有七十九種雜誌。,1757年。已增至一百五十種到二百種之間,而出版的書籍創作則幾年間增加了四倍,當時的主流詩人作家如華滋華斯(R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文學教父薩繆爾.約翰生(Samuel Johnson, 1709-1784)、大詩人及評論家阿諾德(Hatthew Arnold,
1822-1888)等對這現象都做了很負面的評價。華滋華斯認為通俗作品沒有價值,只會麻痺人的感性;約翰生則認為當時作家滿街走,所寫的都是垃圾;阿諾德則認為好的文學可以激發人的想像力和創造力,通俗文學則是沒有價值的低劣文學。
由羅文薩爾的文學考據已可看出,從十七到十九世紀,由於正統主流文學所造成的秩序極為強大,它已成了文士知識分子的傳統,不同的文學形式已難有出頭機會,只有到了二十世紀中葉以後,特別是後現代主義興起,「高文學」和「低文學」的藩籬被打破,創新求變的機會遂告大增。
就以英美詩壇為例,過去的詩有極強的「知識分子自我主義」(intellectual Egoism),詩要怎麼寫,用甚麼腔調來寫都有定規,而這種定規現在早已被打破。最近,臺北出版了當代最佳美國短篇小說作者雷蒙.卡佛(Raymond Carrer,
1938-1988)的小說集。雷蒙.卡佛即曾明言,他的小說都是在寫工作糊口的中低下人群的生命感受,他們的生命質感與知識分子不同,他的小說遂能成一家之言。雷蒙.卡佛除了是短篇小說作者外,同時也是個寫詩人。他的詩用字平易,老媼能解,在此我姑且引一首常被許多詩選集收錄進去的〈幸福〉,該詩曰:
天候太早,仍舊漆黑一片
我一杯咖啡坐窗前
通常這麼早的時候
我都思緒泉湧
我見到一個男孩和他的朋友
走在路上
挨戶送著報紙
他們戴著帽子,穿著毛衣
一個孩子肩上背著袋子
他們非常快樂的樣子
這兩個孩子沒有交談
我認為如果他們能夠,他們一定互挽著手臂
這是很早的清晨
他們一起在做著工作
他們繼續、慢慢的
天色露出亮光
雖然月亮仍蒼白的高掛在水面上
在剎那之間這是多美的畫面
死亡、野心,甚至愛
都尚未走進來
這是幸福,它來到
無法預期,走在前面
大清早的這一幕講著這個道理。
雷蒙.卡佛的這首詩,講兩個一大早結伴送報的少年,這可能有點辛苦,但卻健康愉快,他們這種年紀乃是「死亡、野心、愛」都尚未出現的時候,快樂最單純無負擔,這就是幸福。這首卑之無甚高論的詩,它所講的幸福,一定讓許多人頗有感觸,它不是多好的詩,但卻會讓人產生某種感覺和溫暖,可說是首相當不錯的作品,它和許多知識分子性格的作品真的很不一樣。
近年來,由於世人對文化的認知改變,對文學的秩序已更加開放,知識分子性格較強的古典作品固然不錯,但下里巴人能讓人感動的作品也不必然就差。稍早前,舊金山州立大學詩學中心,詩人作家蒂潘尼(John Timpane)及瓦茲(Maureen Watts)等合編了一本《外行詩入門》(Poetry for
Dummies),該書觀點較新,即反映了新時代對詩的看法。書中即指出,過去人們對詩有十種迷思,應予破除;這十種迷思是:
(一)詩只是給知識分子或學術界看的:事實上詩不只寫給知識分子看,詩是寫給每個尋求感動的人看的。
(二)詩很艱澀難讀:事實是有些詩的確難讀難懂,一定要透過專家指引,才可能讀懂,但絕大多數詩作都很宜人親近,人們對詩不要有先入為主的偏見。
(三)寫詩無益於改善生計,你不可能靠寫詩賺到錢:事實是寫詩雖然難以發大財,但寫詩拿到五位數美元版稅,得到五位數文學獎金及其他獎項的仍然極多。
(四)詩是當下的感動,古老的詩現在已無意義:這種說法當然是錯的,詩的意境無分今古,他們在書裡就以中國在西元三五○年至五○○年所寫的〈子夜歌〉為例,證明縱使古代的詩,到了二十一世紀的現在仍極動人。
(五)詩是軟性感性的類型:這也是錯誤的迷思,事實上是詩既能抒情,也可說理、敘事,詩的範圍包括了人類心靈活動的全部。
(六)詩的韻律感業已過時:這也是種誤會,縱使現在人寫的詩,其韻律和古代不同,但韻律變化也更多。因此寫詩讀詩,更要保持對文字的想像,俾擴大自己的韻律感。
(七)詩是個人的,讀詩沒有正確的答案:這種說法當然不對,詩當然各人體會不同。但在交流的界面上,人們仍要尋找最好的共感公分母,如此始能確保詩的交流性。
(八)詩是個人孤獨的行為:實際的說法應該是在寫詩的瞬間,它可能是個人孤獨的行為,但詩絕非個人的獨白,更像是詩人與時代、詩人與別人的共同創作,擴大自己與時代的對話,多去體會別人的感受,乃是詩共同性的關鍵。
(九)詩乃是書面的:許多人認為詩是一種書面語的表達和閱讀,但這種說法只對了一部分,詩同時也是聲音韻律的交流,它才是詩的精神本質。
(十)任何你想寫的就是詩:這種說法雖然似乎有理,但卻未免將詩看得太簡單。任何事務皆可入詩,但都必須錘練,提高視野,尋找妥當的表達方式。不要把詩看得太高,但也不要把詩看得太低,這才是詩。
在前面,我以偌大的篇幅簡述了詩的內在標準的變遷,這時候就要回過頭來看大陸著名攝影家,但也是業餘詩人劉海星的詩作了。
劉海星的攝影與詩作都未經科班的訓練,表現在攝影上的,反而能夠獨樹一幟,在鏡頭下掌握住了中國山川河岳等自然景色的開闊之美,名之為「大美」,那是一種原生性的壯闊、滄桑,與歲月歷史搏鬥的痕跡。如果要將它的鏡頭語言轉化為感性語言,那是要透過鏡頭折射出攝影者心靈深處對國土的深刻摯愛。
而對劉海星的詩,初看之時我頗覺訝異,在某種程度上,甚至還有些排斥,因為像他那樣以外顯的方式來表達感性的寫作方法,在詩這個寫作領域,以這種筆法來寫詩的,已經不彈此調許久矣。現在人寫詩強調「隔」與「含蓄」,唯「隔」與「含蓄」,始能「深沉」。當寫詩人的「我」,在敘述中扮演了太強勢的主角,即難免限制了寫詩人的省思空間。鏡頭語言和詩的語言乃是不同的語言系統,劉海星的詩作,有太多詩的語言乃是轉譯自鏡頭語言的痕跡。這乃是開始時或有排斥感的主因。
但在讀過他的詩集後,我另外也體會到,近年來中國大陸的詩創作,或許受到西洋風氣東漸的影響,詩的知識分子氣味已太過沉重,加以大陸各種懷疑主義當道,對家國自主性的思維早已淡了,劉海星的攝影作品之所以能引起極大回響,即反映了對土地之愛的微妙集體情愫,他的詩追隨著這個步伐繼續發展,未嘗不是重建集體新認同的重要一步。當往這個方向去理解,我初時的排斥感也就變得不再那麼強烈了。
在這本詩集裡,最吻合作者本意的,乃是〈我是一條進化的比較成功的狗〉:
我會像他一樣寫詩
因為我比他痛苦或者幸福
這些都不重要
只是我的舌頭更長
需要伸出長長的舌頭
散發體內的暑熱
是的,你現在才知道我是一條狗
一條進化的比較成功的狗
只要有風就會流淚
只要抬眼
就會對著痛苦和快樂狂吠
四處閒逛
尋找自己和別人的感情
伸出長長的舌頭
散發心中的暑熱
我只是一條進化的比較成功的狗
在這首詩裡,作者以詩自喻,他寫詩乃是在尋找自己和別人的感情。他在詩裡模擬鏡頭語言談對家國之愛、親情之愛,也談記憶,談困惑或質疑。詩句的縫隙間都洋溢著對生命的禮讚。由於這是劉海星對詩初次上手,他在語言、意象的掌握上總是略嫌不足。我還是要用本文前段所說的,不把詩看得太嚴重,但也不要把詩看得太容易,這乃是詩的真正法門,並以此與作者互勉!
南方朔
2011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