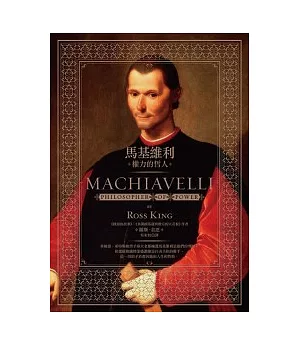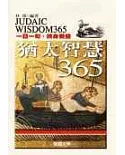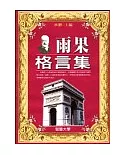結語
《戰爭的藝術》是馬基維利唯一一部在生前出版的作品。《君王論》雖然以手稿的形式流通,但卻是到了馬基維利去世之後四年多才告出版。一五三一年夏天,教皇克萊門七世准許安東尼奧.布拉多──這是十六世紀羅馬最大的出版社──出版《君王論》、《佛羅倫斯史》和《李維羅馬史疏義》。布拉多版在一五三二年一月初問世,此時克萊門已批准佛羅倫斯的印刷工坊吉雍提自行印製;佛羅倫斯版在一五三二年五月付梓。之前只有少數人能讀到的作品,如今廣為流傳。
馬基維利生前,《君王論》已讓他小有惡名。「因為《君王論》的緣故,每個人都恨他。」馬基維利去世前後,有人如此評道。「好人認為他有罪,惡人認為他比自己更邪惡、更有能力,所以人人都恨他。」1這話顯然過於誇大:人多半知道馬基維利寫劇本,是個惹人爭議的政府官員,但未必知道他寫治國之術。不過,馬基維利死後幾十年間,仇恨確實開始滋長。《君王論》出版二十五年後,教皇保祿四世將之放在「禁書目錄」情節最為重大的一類,到了十六世紀末,馬基維利的名字在某些地區已經成了近乎邪惡的化身,以及虛偽和無神論的代名詞。伊麗莎白一世時期的劇作家如馬洛和莎士比亞,用他的名字創造出一個惡魔般的惡棍。馬洛的《馬耳他的猶太人》於一五九一年推出,開場白就是一個名叫「馬基維利」的角色講話,他說他想要呈現一個名叫巴拉巴斯的猶太人的悲劇,他因為遵循馬基維利的教誨而致富。觀眾接著看到精神有問題的巴拉巴斯,他充滿野心、貪婪、奸詐和大開殺戒,最後死在一鍋沸油中。
由於《君王論》要到一六四○年才會翻成英文,所以馬洛和莎士比亞似乎是從派特瑞克在一五七七年所翻譯的《反馬基維利》吸收到馬基維利的惡魔形象。這本書是由法國的新教徒簡提葉所寫的。簡提葉注意到,馬基維利的《君王論》是題獻給法國皇太后凱瑟琳.德.梅迪奇的父親,於是簡提葉就把一五七二年八月「聖巴托洛繆節大屠殺」的帳算到馬基維利的頭上,當時有數千名法國新教徒被天主教暴民殺害。聖巴托洛繆節大屠殺並不是第一筆算在他頭上的帳,也不是最後一筆。早在一五三九年,一位英國的樞機主教玻爾就譴責馬基維利是「人類之敵」,認為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就是他秘密研讀馬基維利的結果。後來又有人說《君王論》被譯為土耳其語,造成蘇丹殘害手足之烈,更甚以往。
無論凱瑟琳.德.梅迪奇、亨利八世或土耳其蘇丹是否真的從《君王論》得到靈感,馬基維利是受「聯想入罪」之害最深的作家。羅倫佐.迪.皮耶羅.德.梅迪奇可能在一五一六年拒絕過這部作品,但此後很少有獨裁者或暴君會忽略《君王論》的教誨。克倫威爾擁有一份手抄本;拿破崙在打滑鐵盧戰役的時候,隨身帶著一本《君王論》,時常翻閱;希特勒也承認,床頭會放一本《君王論》。也難怪季辛吉在一九七二年接受《新共和》專訪時,急於否認馬基維利的學說對他的影響。其他人就沒那麼避諱了。黑手黨大老甘比諾和約翰.高帝都自稱是馬基維利的門徒,已故的共和黨顧問阿特沃特—此人在一九八○年代以手段卑下而惡名昭彰──誇稱他看了《君王論》二十三遍。當已故的美國饒舌歌手吐派克.夏庫爾想找一個可怕的新稱謂,結果自稱為「馬克維利」(Makaveli),以紀念他在一九九五年坐牢十一個月期間,曾研讀過馬基維利的作品。
在一般人的想像中,馬基維利的名字已經成了背叛和謊言的代名詞。牛津英語詞典對machiavellian一字的定義是「不擇手段的陰謀家」。心理學家甚至用這個詞來描述傲慢、不誠實、憤世嫉俗、操控的人格。2但並不是人人都同意這些貶抑之詞足以表現馬基維利的思想。早在一六四○年代,法國作家路易.馬宏就寫了《為馬基維利辯護》,聲稱《君王論》的作者其實是一位受到誤解的基督教道德家。普雷佐利尼在一九五四年寫了一本書,故意取名為《反基督馬基維利》,認為宗教和政治的偏見,加上全然的無知,使得馬基維利成為歷史上最受誤解的思想家;從麥可.懷特的副書名「被誤解的人」來看,過了半世紀之後,情形並沒有改變。
事實上,馬基維利一直享有盛名,但不只有欺騙、愛操控的惡棍形象而已。一五八五年,此時馬洛和莎士比亞還未大放異彩,義大利法學家簡提利──他後來成為牛津大學皇家民法教授──稱讚馬基維利是個謹慎而有智慧的人,捍衛民主,唾棄專制。對於狄德羅和盧梭(兩人都相信《君王論》乃是諷刺之作),3馬基維利倡導共和與自由,而克羅齊和列奧.施特勞斯則將他奉為政治新「科學」的創建者。在「復興運動」期間,馬基維利被譽為愛國人士,倡議義大利之統一,最近還有歷史學者和政治學家,如馬丁利、佛格林,和維羅利持這個觀點(但是推論更加複雜)。其他的政治學家則將之標舉為現代西方思想的奠基人物之一,他的遺緒不是暴力和背叛,而是古典共和主義、政治自由和公民道德,對後世影響深遠,也及於美國的制憲先賢。
4馬基維利當然是一位複雜的思想家,他的著作就證明了廣為流傳的看法並不真確:馬基維利講究的是用邪惡計謀達到征服之目的。然而,他的複雜度引發了許多令人迷惑的詮釋。一九七一年,以撒.柏林在《紐約時報》寫了一篇書評,概述二十多種對《君王論》的解讀,各個南轅北轍,從羅素說它是「黑道手冊」,到一個布爾什維克黨人稱讚這部作品以辯證的方式掌握權力的本質,使之成為馬克思和列寧的先驅。「還有哪位作者,」柏林問道,「能讓讀者對他有如此不同的解讀,其論調差異如此之深之廣?」在一九七一年之後還繼續有人提出新解,其中包括充滿陰謀色彩的女性主義解讀,把這部作品看成「家庭劇」,急於讓像是法律和政治等男性建制與黑暗動盪的命運女神捉對廝殺。
5因此,馬基維利並沒有全然被妖魔化或是遭到不公平的誤解,被當成一個鼓吹邪惡的人──至少眼力較高的讀者不致如此。反之,他已被不同政治立場的擁護者徵召,急於把他的旗幟覆蓋在自己的目標上。啟蒙思想家如狄德羅、盧梭,顯然把馬基維利看成政治自由的發言人;十九世紀的義大利愛國志士認為他大力擁護義大利的統一;布爾什維克黨人稱頌他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先驅;二十世紀後半葉的學院女性主義者在他的著作中看到男性的權力受女性所威脅──種種詮釋都說明了,馬基維利的思想可以任由各種截然對立的意識型態所揉捏。這些挪用的歧異與複雜證明了馬基維利著作的歧異與複雜。
這些詮釋的歧異也證明了馬基維利的矛盾之處甚多。他的著作矛盾充斥,就算是最精明的政治學家也仍在費勁調和。馬基維利真是一個專制統治的理論家?還是一個支持共和的愛國志士,讚揚自由和得民心的政府?《君王論》中的許多言論與《李維羅馬史疏義》扞格不入,這是無可否認的──他的作品充滿許多內在矛盾。
有些模棱兩可之處的關鍵可能出在馬基維利這個人的性格上頭。馬基維利具有多重身分──外交官、劇作家、詩人、歷史學家、政治理論家、農夫、軍事工程師、公民軍隊長,這讓他變得更像一個真正的文藝復興人,一如他的朋友達文西那般。達文西一面譴責戰爭的「野蠻瘋狂」,一面又設計精巧而致命的武器,馬基維利也是如此,處處可見矛盾與前後不一。他是一個觀念新穎的思想家,為政治學鋪了路,但也輕易相信占星和算命。他愛好自由,但又相信我們的行動受到必然律的限制。他為文獻策,告訴領導者該如何統治,但又認為他們勢必會按著自己如脫韁野馬的本性而行事。他為共和體制辯護,但又願意為摧毀佛羅倫斯共和、壓制自由的家族效力。他盛讚虛飾(甚至寫了詩來稱頌欺騙),但他的個性卻是無法奉承或欺騙他人。
也許他最矛盾的地方在於,他比任何十六世紀的人都了解如何取得、保持政治權力──然而,他的權力在一五一二年遭到剝奪,花了很多年在政治邊緣,做出一連串笨拙、徒勞的嘗試以恢復地位。這個人宣揚了可以擊打命運使之屈服的想法,但他又是一個命運女神展現其惡意的可悲例子。
在馬基維利的生命與著作中,常可見到與命運女神的戰鬥。「我的厄運如何讓我悲傷啊,」克雷昂卓在《克麗齊雅》中如此哀嘆,「打從出了娘胎至今,我似乎從沒得到我想要的。」這句話或許也可充作馬基維利的墓誌銘。不過,他的墓碑上另有題詞。一五二七年六月二十二日,馬基維利葬在佛羅倫斯的聖十字教堂,緊鄰他父親的墓地。過了幾個世紀之後的一七八七年,史賓納奇在南側廊通道造了宏偉的新墓,離米開朗基羅、伽利略、布魯尼的墳墓僅有幾步之遙。大理石的紀念碑上雕有狄普洛瑪西的像,下刻銘文:TANTO
NOMINI NULLUM PAR ELOGIUM,意為「沒有一首哀歌可與這個名字相當」。畢竟命運還算待馬基維利不薄,至少在他死後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