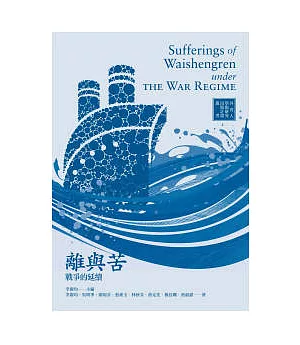序言 《離與苦》主編序:沒有人知道龔伯伯去了哪裡?/李廣均
身影
小時候,龔伯伯是家中常客。每到週末假日,龔伯伯總會和幾位爸爸的老鄉一起來家裡吃飯,然後留下來打牌,在香菸和濃茶的陪伴下不知度過多少夜晚。龔伯伯喜歡和小孩子玩,他身軀壯碩像棵大樹,我和弟弟總會調皮地騎在他脖子上,希望他能把我們高高舉起,玩一下開飛機的遊戲,過年時也總能從他手上領到一個大紅包。
上了大學,寒暑假回家也一定會碰上這群「伯伯和爺爺」,但不知從何時開始,有些人不見了。媽媽不經意地說誰死了、誰回大陸去了。「那龔伯伯呢?」我好奇地問。媽媽楞了一下說:「你爸爸打電話找他好久都找不到,老說有人要害他,也不和大家來往,好像變成神經病了。」我聽完有些難過,雖然後來一直沒機會再看到他,心中卻常想起小時候爬在他身上嘻鬧的畫面。幾年後,媒體曾數次出現獨居榮民死亡多日才被發現的報導,我總是心頭一顫,心想那會是龔伯伯嗎?
「獨居榮民死亡多日」的新聞常以一種怵目驚心又令人不忍的方式報導。鄰居們總在難忍惡臭的情形下發現老人已經死亡多日,抵達現場的警方與記者甚至驚訝地發現,老人飼養的流浪狗已將屍體啃食大半。可是仔細閱讀下來,媒體的相關報導最後只是讓讀者對流浪狗留下「忘恩負義」的印象,對於如何了解獨居榮民、龔伯伯或其他和龔伯伯有同樣人生遭遇者的生命故事,則顯得貧乏又冷漠。
我常想,獨居老人和流浪狗其實有某種相似的遭遇和位置,都是被社會遺忘或遺棄的一群,彼此常以一種靜默卻溫暖的方式,將這個社會無法提供的照顧和陪伴提供給對方,包括最後的屍身。老人如果地下有知,會用「忘恩負義」的字眼來責備小狗?還是會同意讓小狗啃食他的殘軀,作為感激狗兒陪伴老人度過無依晚年的回報呢?
龔伯伯怎麼會變成神經病?是怎樣的歷史巨變和人生際遇讓他從人群中消失?老人為何獨居,又是什麼樣的政令限制和社會現實讓老人「選擇」與流浪狗為伴?他們如何「自謀生活」?如何在沒有支領退休金(只有三個月薪俸)、沒有輔導安置下,走入一個語言不通、人生地不熟的台灣社會?其中有個叫李師科的人,一九五九年因病申請退役,二十三年後的四月十四日犯下台灣第一起蒙面持槍銀行搶案,二十三天後被捕,十九天後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槍決身亡。
他們大多無法理解,當以為戰爭結束而選擇離開軍隊,另一場更為艱困的人生戰役才正要開始。令人感嘆的是,他們沒有足夠的語言能力訴說自己的人生經驗,也不見得能理解為何自己會有這樣的離苦遭遇,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他們多數必須獨自承擔戰亂年代中人群流散的「離與苦」。本書選錄七篇文章,每位作者試圖從不同的角度來回答上述這些問題,幫助我們以一個進出歷史、超越政治的觀點來了解「外省人」的流亡經驗。
失落的話語
吳明季剛進入田野時,每天面對的是一群死氣沉沉的老伯伯。他們對許多事情都不感興趣,話不多、表達能力也不好,很難清楚完整地表達自身感受,訪談回答時總是伴隨大量的沉默。年輕的吳明季對榮民老伯打發時間的生活方式覺得難以忍受,直覺是種幾近死亡的沉悶,但沉默和流亡有何關連?「死寂」又如何展現控訴的力量?
吳明季發現,有些單身榮民在家中客廳掛著自己的遺照,每天和遺照生活在一起,而她就坐在客廳對著遺照與本人一起聊天;也有些榮民伯伯在生前就將自己的墳墓造好,她就看過這樣的墓碑「○○省○○縣○○○榮民之墓,民國○年○月○日生,民國○年○月自己建」。如果遺照和墳墓象徵死亡,那每天面對自己的遺照與搭建自己的墓碑又意味著什麼?表達能力原本就不好的榮民伯伯對此無話可說。因此,吳明季試圖從「流亡」來理解老兵的沉默。
流亡是什麼?榮民伯伯又因流亡又失落了什麼?我們對此不甚了解,尤其國內對於流亡的研究相對有限,以至於能述說流亡情境的話語並不多,即便是流亡者本身(如老兵),也缺乏適當用語來表述心情與處境。此外,在受到各種相關論述(如忠黨愛國)的影響下,榮民伯伯常將許多不同層次的事混為一談,更加無法適切表達他們的真實感受。但是沉默不能隱瞞失落的處境,反而逕自化成田野中榮民伯伯們那種幾近死亡的沉悶。
吳明季認為,長期以來台灣社會對於老兵賦予太多報效黨國的道德意義,幾乎所有討論都必須依附在「忠黨愛國」的論述之下,老兵自身的流亡處境反而晦暗不明。當整個社會對老兵的認識都已淪為某種既定論述,連老兵也不知如何表達自己的處境與感受時,除了沉默又能如何?作者形容,她在田野中接觸到的沉默和死寂就像巨大的黑洞,在此情形下,任何言說都變得毫無可能,我們既無從認識榮民伯伯的流亡經驗,外省人的失落處境也無法被了解。
此外,吳明季更進一步指出老兵失落話語的三重處境:第一重失落話語是老兵處在「與瘋子、白痴、腐敗垃圾為伍」的象徵性位置;第二重失落話語是老兵所遭遇的流亡經歷;第三重失落話語則是位居台灣社會偏遠鄉下的老人處境。這些失落話語又同時顯示兩層意義,第一層顯示出這些失落處境的本身,第二層則是我們的社會無從認識這些失落,而整個社會也沒有成熟進步的話語論述來再現老兵,因此讓其他論述話語(如功在黨國)充斥並掩飾了老兵的失落處境。
吳明季長期在田野中感受死寂與沉默、語言與現實、現實與記憶之間的繁複關係,並嘗試在諸般繁複交錯中,捕捉一則又一則的創傷故事。她的田野研究讓我們得以明白,原來「沉默和死寂」也有訴說故事的力量,作者是在田野工作進行一年後的某天下午頓悟,在流淚痛哭中體會「最重要的是它沒說的部分」。
流離與回「家」
不管是否曾經返鄉探親,許多榮民伯伯都必須面對人事已非的改變,也必須接受身邊沒有親人陪伴的事實。在如此時空與心境下,許多榮民伯伯選擇搬入榮民之家就養,這似乎是個合理的選擇,或也足以彰顯政府照顧榮民的德政,然而廖如芬則根據她的觀察對此提出不同意見。
廖如芬第一次進入榮民之家,看見許多榮民或坐在一旁發呆不語,或是一個人靜靜聽著收音機打發時間,此番景象和她原先的想像落差很大。尚未進入榮家前,廖如芬以為軍中同袍的患難情誼,必定能在他們之間建立深厚情感基礎,可是此預設在她踏入榮家大門後徹底崩解。榮家內的每位榮民伯伯彷彿一座座孤立的星球,在各自的軌道上轉動,彼此幾乎沒什麼交集,她對這種景況驚詫不已,進而企圖探問這種人際疏離產生的原因。究竟是榮民伯伯生性古怪、不好相處?還是和榮家內部的生活型態、管理方式有關?
廖如芬質疑,「不好相處」的說法只會讓我們忽略「榮民之家」本身的制度設計與管理問題。她進一步指出,榮民之家在空間安排與行政管理上的諸多作法,不僅帶給榮民心理戒備與不安全感,甚至還引發許多榮民伯伯之間的猜忌、紛爭乃至流血衝突。例如,一般安養堂的床位設計是一間間彼此相隔卻沒有房門。這種空間安排缺乏私人隱密性,也沒有隔音設備,因此帶來人際之間的疏離與猜忌。
到底什麼是「家」?大家或許都同意,產生「家」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私人生活領域的形成,也就是一個可以與外界區隔的私密空間。可是榮民之家的空間設計沒有考慮居民之間的安全距離與隱密性,因而產生許多人際互動上的緊張與摩擦。榮民之家這種缺乏私人隱密性的空間安排,讓「家」的味道蕩然無存,也讓榮民之「家」產生不少反諷意味。
榮民伯伯們或因為單身來台沒有親人,或因為擔心生病無人照料,只好選擇住進榮民之家。原本寄望搬進能找到一絲「家」的感覺,無奈卻連「家」的形式與感受都不能體會。一位住進榮家不久的台籍榮民就說:「這邊的榮民都是這麼想的,他們說我們在這裡並不是都很光榮!我們在這邊就是吃飯、拉屎、睡覺,最後沒辦法吃的時候,就是耗著。這邊是待命,他講的待命要死掉的!」
雖然我們為老榮民蓋了安養居所,提供無障礙空間的設計與護理服務,內部的空間設計與行政管理卻忽略居民的自我投入、情感歸屬與人際互動,反而讓榮民之「家」成為一個極大的諷刺。榮民伯伯們一生經歷不只一次離家的痛苦,遺憾的是住進榮家仍然無法找回家的感覺,榮民之「家」的管理方式和生活經驗,反而更加凸顯榮民伯伯無「家」可歸的流離人生。
老有所終?
除了選擇住進榮民之家,也有些老兵選擇進住私人安養院所。他們在私人安養中心的生活品質又是如何?戰爭和軍旅生涯對於他們的影響,會因為戰爭結束而停止嗎?張素玉試圖透過深入訪談,了解榮民伯伯的安養情況,探討戰爭和軍旅生涯對他們晚年生活的影響:包括生活品質、人際關係、身心健康等。
身為訪談對象之一的明伯伯,他的晚年生活經常在感傷與懊悔中度過。明伯伯當初因為嫂嫂不願出錢整修祖先墓地而氣憤難平,在前往市集賣東西籌錢時,不巧碰上軍隊抓他充兵,他當時三十二歲。雖然老婆曾勸明伯伯過兩天再出門,無奈他一時氣憤聽不進去。明伯伯回憶在鄉公所前見妻兒最後一面的情景,當時兒子才兩歲,連叫爸爸的發音都不準。四十餘年來,明伯伯至今一直沒有妻兒的音訊,如今即使悔不當初,也只能孤單地在安養院中渡過餘生。戰爭對他的影響未曾停歇。
另一位郝伯伯也是在無情戰亂中莫名奇妙被迫從軍,徹底改變他後半輩子的生活。郝伯伯當時年僅十六歲,在家中被幾個軍人不分青紅皂白強虜入伍。郝伯伯說不只他,他的許多朋友也是這樣被捉走。由於出身低微,又沒機會讀書,使郝伯伯個性羞赧自卑,覺得自己處處不如人,平常也害怕與人接觸。擔心自己沒讀過書會說錯話得罪別人。他常說自己是個沒錢沒親人的老士官,人家則是有錢有家有孩子,甚至連重孫也有了。對於郝伯伯這種自卑的自我評價與低落的心理認知,作者指出,我們只有從近代戰亂歷史與個人流亡經驗中才能得到解答。
如同明伯伯和郝伯伯,許多當初被軍隊「抓伕」、「抓兵」來台的榮民伯伯,五十餘年來,這段經歷深深影響他們的婚姻與家庭生活、職業選擇、經濟狀況、社會關係、身體健康及心理調適,使他們在晚年長期處於一種低落自怨的心理狀態,不斷遊走在氣憤、無奈、痛心、懊悔的情緒中。對他們而言,雖然戰爭結束數十年了,但戰爭帶來的傷害和影響卻從未停止,持續而深刻地影響晚年生活。
張素玉認為,榮民伯伯當初從軍多非自願。「抓伕」、「抓兵」將他們抽離原本熟悉的人際關係與謀生脈絡,軍旅生涯又沒提供足夠的職業訓練,離開軍隊後的出路更是有限而辛苦,至多只能從事低技術性的勞動工作。張素玉呼籲不應將榮民視為既得利益者,因為他們並未擁有較好的生活品質,也沒有比其他弱勢群體享有更多福利。在國家對他們有所虧欠的情況下,政府有必要提供妥善適當的福利措施照顧榮民,社會也應試著重新認識他們的一生──他們非但不是既得利益者,反而是動盪時代下的犧牲品和無情戰爭下的受害者。
家與枷
如果沒有結婚的榮民伯伯可以選擇住進榮民之家或安養院,那結婚的榮民伯伯或許可以寄望婚姻與家庭生活,但在禁婚政策、部隊移防、語言不通、學歷不高、收入微薄、省籍情結的政治環境與社會條件下結婚後,他們過的又是怎樣的家庭生活呢?林秋芬的研究提醒我們注意一個重要的現象:住在榮民醫院或安養院的病患不一定是榮民自己,而是他們罹患精神疾病的配偶。林秋芬對於老榮民與罹病配偶間婚姻與家庭生活的研究,也呼應了吳明季對老兵婚姻的觀察與分析。
對許多榮民伯伯而言,到榮民醫院探視配偶是一條每年必走之路,但走上這條路到底是夫妻情深的驅使?還是道德責任的承擔?林秋芬指出,每年固定往來榮民醫院探視妻子的老榮民不在少數,他們多是民國三十八年前後隨政府來台的老兵,目前散居全台各地。比起其他精神病患的照顧者,老榮民的經濟資源與社會網絡相對有限,自身承擔的心理壓力也更為沉重。老榮民或為了傳宗接代,或為了彌補戰亂年代中對家庭生活的懷想,明知自己在婚姻市場中處於不利位置(如以吳明季的觀察是:「簍底的爛橘子由我們撿起來」),仍然辛苦維繫一個結婚成家的夢想。
林秋芬指出,一九八○年代以前,政府只是把精神醫療視為一個以救助、收容為主的照顧工作,而非醫療業務。因此,早期精神醫療是以收容為主,其他與治療有關的病床、復建資源,則相對明顯不足。在這種情形下,精神病患的原生家庭往往必須自力救濟,有些家屬因而寄望可以藉由婚姻安排為患者沖喜治病,也藉此找到一個可以長期照顧患者的對象;至於老榮民對於結婚成家的期待多是為了傳宗接代,也希望自己年老時可以有人照顧,由此觀之,老榮民與精神疾病患者的婚姻雖是各取所需,卻也是一種弱勢者與弱勢者的結合,注定婚後生活的波折與辛苦。
配偶病情發作後,老榮民的婚姻與家庭生活也跟著出現重大轉變。榮民伯伯一方面要擔心太太是否會走失,也要擔心太太發作後出現的暴力行為,特別是對自己和家人(尤其是小孩)的傷害。老榮民一方面要工作上班,另一方面又要忙著將發病的太太送進醫院治療,還要分身照顧嗷嗷待哺的幼兒,一根蠟燭多頭燒的奔波在工作、醫院與家庭之間,默默犧牲了自身的職業發展與生涯規劃。此外,在傳統文化對精神疾病的誤解與汙名化影響下,老榮民對於太太生病一事多半不願提起,只能把所有痛苦放在心裡,造成他的另一種心理負擔。
五十幾年前,老榮民隨政府遷台,被迫和原生家庭分開;一九八○年代末期政府開放探親,他們返鄉探親,眼見一切人事已非,只好又離開老家回到台灣。如今太太病發住院,讓自己再度遭逢與家人分離的命運,老榮民心中有一般人無法理解的痛苦,他們的一生可說是長期處於一種不完整的家庭經驗。
當披覆土地、家族的屋頂被掀開之際
除了榮民之家和安養院,黃克先試圖從宗教的角度切入,提出另一種了解外省人「離與苦」的觀察角度。據統計,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九年之間,台灣的基督徒人數陡然增加了八倍,天主教人數則成長二十倍;相較之下,外省人口的基督徒比例(百分之十)又明顯高於閩南人口的基督徒比例(百分之一.五)。該如何理解台灣社會中為何會有大量「外省人」進入了基督教會,他們為何改信基督教,此一「改宗」現象對了解外省人的「離與苦」又有何特殊意義?
黃克先認為,要有效解釋外省人與基督教的「選擇性親近」,必須先回答:外省人第一代如何疏離傳統信仰?不同於一般化約成心理因素的看法,作者指出,除了流落異鄉、心理孤寂的解釋,還必須從一個更高的知識觀點和歷史深度來解釋外省人的「改宗」現象,也就是從中國遭遇現代性的歷史背景,理解第一代外省人與基督教之間的親近關係。
作者提醒,「改宗」看似個人決定,實際上牽涉了特殊的社會條件和歷史背景。從改宗現象可以看到「流亡」與戰爭對人的影響,也得以重新認識「外省人」。黃克先的研究讓我們有機會從階級差異的角度來認識「高階外省人」的流亡經驗。對「高階外省人」而言,原生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以教會學校為基礎的養成教育,都和現代中國資產階級的興起關係密切。掌握此觀點才能看清,許多「外省人」的離家之路不只是個人的犧牲,還是國家規訓的教化結果。由此觀之,外省人宗教信仰的改變,不只涉及對心靈慰藉的追求,更是許多複雜社會變遷的歷史結果,其中包括中國的現代性經驗、資產階級的興起、國民黨政權的社會基礎等。
如作者所言,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外省人」「跟著國民政府」來到台灣的過程與原因,究竟是出於志願還是被迫?是個人認同與國家意識形態緊密縫合下的自主選擇?還是現代國家官僚體制規訓下的工作調動,或是被國家暴力脅迫來台?如果不能釐清這些問題,不僅無法清楚描繪「外省人」的群體圖像,台灣社會對於「外省人」的認識與討論,也會繼續受限於國族政治和認同政治的思考模式。黃克先的「改宗」研究,引領我們看到「外省人」的異質性,也提醒著我們「國族政治∕認同政治」的局限性。
是過氣貴族還是孤臣遺民?
面對戰爭與政治,「外省人」如何承受與面對?有人以沉默抗議流亡,有人則選擇以鄉愁療傷。楊佳嫻關心的是:若生命中最重要的「地方」成了無法返回之地,流離的人們該如何撫慰這份返回的想望?而這份想望又如何化為書寫動力,取代維繫於固定疆域的地方感?作者提醒,外省人中除了老兵、眷村子弟、帶有鄉音的小學老師,還有一群社經地位較高的移民──「高階外省人」。楊佳嫻透過觀察白先勇、李渝筆下的文學世界與人物(主要包括大學教授與軍政要員及其眷屬),理解他們的鄉愁、家國創傷與文化傳遞。
有論者認為,外省移民因敗亂來到台灣,精神上背負許多重擔,內心充滿對家國的懷念與愁緒,外省作家的創作因此常伴隨難以解開的家國纏結,作品也因負載沉重的鄉愁而在回憶與失落間徘徊,透露出一份「孤臣孽子」的悽憤,可稱為「孤臣文學」。以白先勇為例,其文學世界總帶著時代的哀愁,這份哀愁的源頭正是那個受傷的「中國」。此一文化鄉愁指涉的「不是一個具體的『家』,一個房子、一個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這些地方,所有關於中國的記憶的總合,很難解釋的。可是我真想得厲害」。此一鄉愁依繫的「關於中國的記憶的總合」可以超越個體或具體地理,涵蓋許多時空累積下的想像居所。白先勇透過書寫來召喚這個「記憶總合」,在小說中體現為文化的物質化(如古董擺設、字畫、線裝古籍)或集體記憶。
可是外省族群就要為這樣的悲情所凝固嗎?楊佳嫻指出,既然「故國」、「原鄉」已不可返,只好將家國之思寄託於文化層面,以文化傳統的賡續,在精神上保有一方心土,將原本維繫實體地點的地方感,轉嫁於文字、藝術、宗教儀式、家族記憶等,這些轉換看似抽象,實則更能不受地域阻隔、牽絆。對於「高階外省人」而言,鄉愁不只化為種種文化記憶,也是可資傳遞的精神遺產。換言之,文化認同取代了疆域認同,創作者轉而從精神方面去撫慰那不可彌補的家國距離。
除了表現對時間(青春)和空間(家鄉)的鄉愁,「高階外省人」還有文化鄉愁,而且比起前兩者更有彌補的機會。作者指出,不論是白先勇或李渝都暗示,上一代的遺憾可以由下一代來縫補:如果不能帶著下一代去認識故國家鄉的實際面貌,那麼就從文化層面去認識。因此,小說人物或是教導子孫吟詠詩句,或是傳藏閱讀魯迅,「中國」透過文學文化形式在下一代紮根發芽,這份文化傳遞不只是古董詩詞,更是有別於「傳統中國」的「新文學傳統」。
同樣「流落」在台北,白先勇筆下的「高階外省人」充滿了悲涼情懷,緬懷過往,是頹廢、瘋狂的;相對的,李渝筆下的「高階外省人」卻是在潦落半生後仍不放棄傳遞文化,深具建設性。白先勇的小說人物看見的是失敗、未竟的一面;李渝的小說人物看到的則是對中國下一代珍貴、堅實的期望。和白先勇《台北人》的傷感、瘋狂或死亡不同,李渝不著眼於人物的失意面,而是透過下一代的眼光記錄「台北人」,作為現代中國人的延伸,也藉此傳遞那不滅的文化意志。
台灣文學中的老兵形象
透過文學作品分析整理外省人的離苦經歷,曾淑惠嘗試研究當代台灣文學中有關老兵的幾種書寫主題,包括思鄉懷舊、殊異生命型態、袍澤情深、性欲畸態、婚姻殘缺與生涯際遇等。
老兵早年經歷戰亂流離,來台後則掙扎於異鄉生活的辛酸,思鄉懷舊因而成為老兵生命情感中的鮮明標記,也是許多文學作品探討的主題。老兵身處陌生的台灣,家人、故鄉的記憶是最熟悉的,因此,不論是有人將此情感投射於「雞群」,或將鄉愁化成「地理」並試圖嵌入第二代的腦海,都只有引來厭惡與訕笑。透過描寫世代間的矛盾與衝突,作家更能凸顯老兵懷鄉情感的複雜與沉重。
其次,描寫老兵們殊異生命型態也是創作主題之一:誰會以布滿地雷的海邊為家?又有誰會長年住在被演習炮火轟擊過的荒禿山崗?這些埋伏危險的蒼涼景點卻正是老兵的「家」常風景。也有人試圖再現老兵的「刺青」,視其為一種政治忠誠的宣示,諷刺黨國思想已進入生命的「骨髓」,成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有下士班長帶著整班士兵死守海防班哨,為了一塊從未去過的土地,換得四十年來「左大腿空洞的疼」。
老兵長期生活於軍隊,在槍林彈雨中與同袍培養了難以抹滅的革命情感,面對漂流異鄉的辛苦,文本描寫彼此照顧的袍澤之情往往更勝血緣關係,相濡以沫的情深義重也讓老兵有了生命溫暖。老兵之間一路扶持的同鄉情誼總有相互安慰的作用,不論是金錢使用或情感慰藉都不分彼此,這種情同手足的袍澤情深也成為許多老兵文學的創作主題。
在年齡差距、經濟因素與社會地位的影響下,一般台灣女子很少願意嫁給外省低階退伍士官兵。這種情形下,老兵若想結婚成家,只能與台灣社會中處於「邊緣地位」的婦女接觸,如殘疾、貧苦、離婚、寡居、養女、娼妓等。這類婚姻與家庭可說是戰後台灣在特殊歷史社會條件下,邊緣弱勢者(老兵與邊緣地位的婦女)之間的一種特殊組合。許多老兵文學藉由討論老兵的情感際遇、性欲抒解與婚姻狀況,呈現老兵離鄉無依的孤苦生活。不論是性欲藥物還是紅包場歌星,都可能是老兵生活的一部分。
多數老兵位階偏低,加上教育程度不夠,不論是接受輔導就業或轉業,多半只能從事以勞力為主的非技術性工作,也有許多士官兵以自行就業的方式謀生,最常見的就是經營小本生意(賣饅頭、賣早餐)。四十多年來,他們「在工地挑砂石」、「在凌晨時分出門掃街道」、「在路上寒著臉開計程車」,也在夜市「兜售玉蘭花或包子饅頭」,也有人「在花蓮海邊撿拾黑白亮的石頭,將國土一袋一袋賤賣給早年浴血對抗的日本人」。
曾淑惠認為,在逐漸開放的一九八○年代,老兵文學展現豐富的書寫景觀,作家秉持悲憫真摯的關懷,肯定老兵的生命力並向其致敬。創作筆調上,創作者或冷眼敘寫,或嬉笑嘲諷,或悲切激憤,都闡釋了特殊時空中的老兵特質及其複雜轉折的生命境況。也有作家用「蒼蠅、螻蟻」比喻老兵的邊緣位置,進而批判社會的粗糙對待與缺乏理解。老兵文學呈現社會邊緣族群的弱勢心理,也呈現社會底層的問題,這是激憤的抗議,也是對老兵的同情與不平之鳴!
小結:一個溫柔的窗口
尊嚴是現代自由民主政治的核心價值。對於民主政治的推動而言,尊嚴的追求和維護需要不斷努力和爭取,但也可能因追求尊嚴的努力失敗或遭受拒絕而受到傷害,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將此過程和努力稱為「肯認政治」。一個人要如何獲得尊嚴呢?泰勒進一步指出,一個人或一個群體要獲得尊嚴,必須先傾聽自己內心最真實的聲音,如此才能找到真實的自我。除此之外,追求尊嚴還要獲得重要他人的承認,如果不能獲得他人的承認或是被誤認,也會是一種嚴重的傷害和壓迫。
泰勒對於尊嚴和「肯認政治」的看法有助於了解台灣社會的族群關係,特別是對「外省人」。一九八○年代以來,台灣社會經歷本土化和民主化的洗禮,省籍、族群、認同等問題也逐一浮上檯面。一方面,在兩岸關係改變下,絕大多數「外省人」在返鄉探親後決定回到台灣定居;另一方面,「外省人」則成為本土化和族群政治的祭品,夾擠在「台灣人」和「中國人」兩種身分間進退兩難。一九九○年代以來,「外省人」顯得焦慮而憤怒,他們的貢獻沒被看見,內心真實的聲音沒被聽見,更談不上尊嚴的追求和肯定。
追求尊嚴和肯定不是件容易的事。對外省人來說,一個重要的工作是如何找到真實的自我,這其中涉及如何實踐意識解放、如何建立外省人的主體性、如何與政治和政黨區分切割、如何確認自己的群體身分和歷史觀點等。本書的出版就是基於上述的努力與成果,希望讓台灣社會有機會認識外省人,也讓外省人有機會知道自己的故事,進而被台灣社會了解和承認。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選出的文章作者有個共同特色,他們絕大多數來自「本省」家庭,是戰後出生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他們對於「外省人」生命故事的挖掘和努力,似乎顛覆了我們對於「省籍情結」的刻板印象,也為未來台灣社會的族群和解提供了一絲希望。我們有理由相信,「省籍對立」不必然會複製到下一代身上,族群差異終將成為台灣社會的多元資產,而非負債。
多年來,我總覺得台灣社會不了解「外省人」,也一直無法整理出一種合理的方式來接納理解他們。令人難過的是,許多「外省人」也無從理解自己的困難和處境,此一事實更加深了他們的弱勢位置和離苦心境,不論是選擇沉默以對或離群獨居,似乎都只是他們流亡處境的一種延伸。在編寫本書的過程中,我好幾次掉下眼淚,不知是為了龔伯伯、獨居的榮民伯伯,還是為了我生命中曾經熟悉卻又寂然消失的許多身影。我遺憾沒來得及探望他們,如今只能寄望此書的編寫與出版能彌補心中憾意於萬一,也希望提供台灣社會一個溫柔的窗口,來了解他們的「離與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