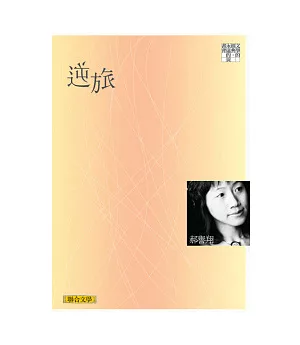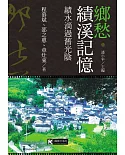經典版序
純真年代 郝譽翔
一九九一年夏天,我陪父親回山東老家,青島酷熱高溫,逼近四十度。
那一趟炎夏之旅,便是這本《逆旅》的由來。
但雖然說是我「陪」父親,其實不是,他自己一人獨來獨往慣了,根本不需要人陪,而是我自告奮勇要跟。那時,距離一九八七年解嚴開放探親,也才不過四年而已,蒙在大陸上的神秘面紗尚未褪去,兩岸之間的隔閡與隔絕,實非今日所能想像。當我知道父親要回老家,便一直嚷著要跟,那真的如同書中所寫,是抱著參加暑期戰鬥營的好奇心態返鄉。然而回去了,才曉得原來不是這麼一回事。原初的追尋新奇刺激,到後來,卻變成了說不出的驚詫、愕然和悵惘,在歷經了這趟啟蒙之旅後,我這才知道,歷史太大,而個人太小,開始敬畏於生命的厚度與重量。
當然,我也得要感謝我的父親。我跟著他,果然成了多餘的累贅,在開放之初,他已回過老家一趟,而這一次,他早就另有圖謀,我後來才恍然大悟。於是回老家住沒兩天,父親便藉口說要辦事,便上青島去了,只留下我獨自面對一屋子陌生的親戚,而他們說的山東土話,我幾乎一個字都聽不懂。
他這一走就是十多天,音訊全無。我們老家在平度縣官庄鄉南坦坡村,從村子裡得要騎上半個小時的腳踏車,才能到官庄鄉,然後坐公車到平度縣城,再轉搭長途客運到青島,清晨天還沒有亮就出門,直到傍晚才能抵達目的地。就在這樣一個偏遠到彷彿與世隔絕的農村,小小的,只有幾十戶,我獨自住了近乎整個夏天。所以,我至今始終都還不能忘懷那一片遼闊的黃土地、高粱青紗帳、筆直的白楊樹,以及老家親戚們的臉孔。我忘不了我的姑姑,她年輕時是村中數一數二的大美人,後來生了八個孩子,還身披英雄母親的綵帶,接受共產黨表揚。我也忘不了我的姑丈,他的皺紋深深鐫刻在額頭上,活像是從張藝謀《紅高粱》裡走出來的人物。還有我的表姊和表哥們,以及我的小表妹小英,那時的她還不到二十歲,從未出過農村,後來卻陪我遊遍了整個山東,成為村子裡閱歷最豐富的人。據說,在後來的好幾年中,她都還有滿肚子的旅遊故事可對村子裡的人講。她真正成了班雅明所謂的「說故事的人」。
然而我們結伴旅行時,我表妹卻不總是愉快的,她經常埋怨怎麼不管走到哪裡,都是在看廟?上餐館吃飯,也不如回家坐在板凳上,吃發黃的饃饃再配一碟韭菜來得自在。她的生命在老家的黃土地上長了根。透過她,我也彷彿看到了命運的另一種可能,假如在一九四九那年,我的父親沒有離開山東,那麼,我可能就是她了──在鄉下長大,熬過幾次饑荒,小學沒能讀完就輟學,平日的工作是種田,後來村子附近設了工廠,就偶爾跑去打打零工,但也是有一搭、沒一搭的,因為那工廠始終處在一種岌岌可危的狀態;而在白日閒暇時,或許也會幻想起一段美麗的愛情,但心中卻很清楚,最後的結局就是嫁給隔壁村年齡相近的男孩,必定也是種田的──在一望無際的高粱環抱之下,一個年輕女孩的選擇不會太多。
命運來到這裡,便有了分岔的可能。如果如果,久而久之,我居然也覺得自己就是她了,每天吃饃饃,睡在炕上,我還特別喜愛老家饃饃帶著一股酸勁的滋味。然而唯一和她們不一樣的,足以清楚標誌我的外來身分的,竟是洗澡這一回事。農村沒有廁所,也沒有浴室,表哥表嫂把自己的房間讓給我睡,當我第一次提出洗澡的要求時,他們面面相覷,支吾了老半天。
「這個嘛,洗澡……」表嫂呢喃著。
看她疑惑的表情,似乎是一件距離生活非常遙遠的事。表哥表嫂跑到屋外,兩人嘰嘰咕咕商量好久,才終於拿著一個臉盆和紅色的熱水瓶,放在房間的泥土地上。我把房門關好,把熱水倒進盆裡,一縷白色的熱氣裊裊升起,飄散入黑夜,而房中只有天花板垂下來一盞小小的黃色燈泡,光線黯淡,我連手中拿的是沐浴乳、還是洗髮精都搞不清楚,就著那一點少得可憐的水,我不僅洗了澡,還一併洗了頭髮。
我每天都要洗頭洗澡,成了村子裡的新聞。後來,我才知道,那水竟是從支部書記家買來的,一瓶一毛錢。全村只有支部書記家才有專門燒水的鍋爐,想要熱水,就得上那兒去買。但村民買水是為了泡茶,只有我是為了要洗澡,這讓支部書記的女兒很驚訝。她的年紀和我一般大,每當到了晚上七、八點,眼看著,又該是我洗澡的時間到了,她就會跑到我家門前,問我:「今天洗澡不?」然後她便興沖沖地跑回家,幫我打水過來,等我洗完澡,走出房門,她還等在院子裡,就是想看我會不會換了一個模樣?
老家的村子很小,雞犬相聞,是一個沒有隱私的地方。我的衣服和姑姑、表妹、表嫂的全晾在一塊兒,曬在院子裡的一條細繩上。我的明顯和她們的不一樣。村裡的女人經常聚在我的內衣褲底下,一邊研究撫摸,一邊讚歎起來說:「台灣的果然是又漂亮,質料又好。」
後來,姑姑告訴我,附近的工廠設有洗澡間,每星期三傍晚開放一次。姑姑太老了,不想洗,要表妹帶我去,村子裡其他女孩知道了,也嚷著要跟,一群人便組成了自行車隊,從村子浩浩蕩蕩出發,騎到工廠至少也要花半個小時以上。我們騎過黃昏的田埂,兩旁都是一望無際的綠色田地,涼風嘩啦啦的掀起裙子,就像一朵朵盛開的花。工廠門口聚著一些人在抽菸,看到我們就笑,說:「那個台灣人又來洗澡了。」
那是一間開放式的大澡堂,沒有燈,在黃昏幽暗的光線中,女孩們摸索著脫下衣服,赤條條站在一排蓮蓬頭的水柱下。我們這才發覺,原來不管是台灣、或是大陸,是農民、還是支部書記的女兒,其實長得也沒有什麼兩樣。大家都發出了吃吃的笑,那笑聲混合著水聲,引起驚人的嗡嗡迴響。等洗完了澡,我們一群人又整裝待發,騎車穿過工廠的大門,穿過紅色的落日和長長的田埂,等回到村子時,雙腳早已沾滿了路上揚起的沙,好像剛才全都白洗了一場。
如今回想起來,這些畫面都還歷歷在目,但屈指算算,距離我上次回大陸山東老家,也已經悠悠二十年過去了哪,我再也不曾回去。父親逝世之後,我更是從此斷了與老家的聯繫,然而,在這一段期間中,卻也正是大陸農村面臨翻天覆地改變的時刻。聽說,沿海農村的人全都跑光了,跑到城市裡去打工。所以每當我行走在上海、或是北京時,看到蹲踞在紅磚道兩旁的民工,我都不禁想起老家的表哥和表嫂們,他們現在到底是在哪裡呢?是否也正徘徊在一座陌生城市的街頭?
但在二十年前,據我所知,離鄉打工的念頭卻從來沒有來到他們的腦海中。我回去那一年,村子裡正逢乾旱,農民又買到假農藥,一年種地的辛苦全都付諸於流水。我原本以為,我會如同詩歌中所描寫的,在老家看到一派悠然閒適的田園之樂,但沒有,一點也沒有,天災和人禍是農民的宿命,現實面的殘酷簡直令人不忍逼視,尤其是在資訊封閉的鄉下。對於我的表哥和表嫂而言,除了眼前這一塊乾枯的田地,和小小的村子之外,他們最遠的腳步就是到平度縣城,肚子餓了,便買兩根油條,站在路邊啃完就是,除此之外,他們哪裡也去不了。青島,遙遠得就像是外國一樣,他們連想都不敢去想。
我回老家的一個多月中,村子裡就發生三次喝農藥自殺的事件。一對夫妻為了五十塊人民幣,大吵一架,結果妻子喝了農藥,命是救回來了,但醫藥費卻花了一千多塊。「真傻。」姑姑嘖嘖地說。但除了發傻之外,對於困窘的現實,村民們也拿不出其他的辦法。
田地既無可指望,他們只好到村子附近的工廠去打工。如今回想起來,那很可能就是大陸老百姓由農轉工的濫觴。支部書記的女兒在工廠當秘書,我和表妹去找她玩耍,看她端端正正地坐在一張桌子前面,有模有樣,但其實什麼事情都沒有。那間工廠空空蕩蕩的,看不見什麼工人,而下午時分的太陽,斜斜照進廠房,油然生出一股死寂和蕭條。
「工廠賠錢,發不出薪水。」支部書記的女兒一邊修指甲,一邊嘆氣,埋怨說上級主管發了個命令,要每個員工捐獻兩百塊,好幫助工廠度過難關。
我聽了很稀奇,居然有這種事?沒薪水可領還要倒貼錢,那幹麼來上班?但後來,我才發覺這一點也不稀奇。村子裡的男人白天種地,到了晚上八點,他們就會提著一盞盞燈籠,挨家挨戶去敲門,召喚著大家到另一家更遠些的工廠去上夜班。他們同樣是半年沒有拿到工資了,但卻還是照常上工,因為只要去,就有一絲領到錢的希望。
每天晚上,當咚咚咚的敲門聲一響,我就看見表哥窸窸窣窣穿上襯衫,跟著其他的男人出門,一長串的燈籠,便逐漸消失在黑夜籠罩的大地上。等到第二天早上,表哥回來時,一雙眼睛都是紅的,補眠一下,他又得趕緊爬起床種田。我搖搖頭說,這樣實在太辛苦了,還不如離開農村,去城裡打工吧。我還很認真的幫表妹想生計,建議她去青島的路邊擺個攤子,賣涼水。他們聽了,卻淨是一臉無奈的笑,說他們沒有城市的戶籍,根本就去不了,所以我說的,盡是一些不切實際的餿主意。
但如今他們卻真的全跑到城市去了。
城市果然有那麼好嗎?我這才知道自己當年有多麼的天真,以為城市就是一個流著奶與蜜的天堂。於是再回過頭來看這本《逆旅》,悵惘之餘,還有更多的感慨與眷戀,我彷彿又看到了二十歲出頭的自己,背著小小的行囊,遊走在那片大地之上,卻渾然不知自己正站在一個時間的轉捩點上,而那不但是我個人生命旅程的轉捩點,更是一個大歷史的轉捩點──從此以後,中國的農村,便無可抵擋地被捲入商業化與現代化的浪潮,於是那樣純真的年代的我,以及大陸,都儼然不再存在了,只能於此書的文字中去尋找。
經典版評述
君父的城邦衰頹之後:重讀郝譽翔的《逆旅》 清華大學台文所副教授 陳建忠
一、衰頹的君父城邦:《逆旅》解題
上個世紀末,緊接著第一部小說集《洗》,郝譽翔又完成了《逆旅》。但時光的列車匆匆,倏忽已過十個年頭。今天再來看這本作品集,對共同經歷過戒嚴、解嚴、政黨輪替與再輪替等歷史階段的讀者來說,《逆旅》當中所涉及的外省族群流亡敘事,確實沾染著彼時那種台灣社會記憶全面突圍下,某種黃昏族群的落寞色彩。君父的城邦已衰頹,而他的女兒猶必須辛勤的補綴身世之網。彷彿有人是歷史的勝利者,有人則是失敗者,而郝譽翔便是那追索父系身世,自況為「政治不正確」的作者。
不過,跨過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台灣社會似乎也如同換了一個人間。當此際,新世代作家倍出且不以歷史興亡為己任不說,新世代的讀者又將如何來領受一個色調斑駁的流亡故事呢?或者,其實一個好的作品,原本就具有多種詮釋的可能,不完全理解流亡的悲苦,何妨從其他的角度來閱讀《逆旅》?
於是就像《逆旅》的書名所昭告的:「逆旅」,除了指涉書中那個絕不擁有輝煌偉業的父親,欲尋找一處安頓之地而難得;身而為人,誰又能完全掌握自己的運命,知道自己情感或精神的理想投宿地究竟何在?再換個角度看,「逆旅」,也不妨解為逆記憶之流而溯源的旅程,郝譽翔因回憶家族史而寫就《逆旅》,而讀者何嘗不能在參差對照裡,重新開啟幽微隱蔽的記憶之洞,印證自我成長與家人、時代間同樣糾葛難明的關連,從而再次思想起「成人不自在」這樣類似的話語,然後再帶著某種程度已被自∕字療的創傷,繼續下一段旅程。
以下,藉著重讀《逆旅》,期待這冊作家個人的代表之作,能夠引發更多迴響。這樣,我們在各自的生命旅程上,必然不會再感到過於孤單罷。
二、女兒的審父與戀父之書
雖說,《逆旅》最讓人印象深刻的題材,乃是自稱籍貫山東的郝譽翔所描述的外省族群身世。但,我認為最能跨越時空,而依然能被新世代讀者先理解的,卻可能是有關作品中親情、家庭與成長經驗的描述。單親家庭的女兒,如何看待一個擁有流亡身世與眾多情人們的父親?自傳性的體例,已先帶給讀者某種窺視的快意。
甚且,身為六年級生,九○年代文壇具代表性的新世代作家(當然,現在已升格為熟女作家),郝譽翔及其同輩的作者,如張蕙菁、成英姝、駱以軍等,明顯受到西方翻譯文學的強烈影響(即便郝譽翔是中文系博士),乍看之下對很多事物都有鮮明的個人意見,敢寫而能寫,語言風格極其突出,但實際上面對歷史與現實問題的態度則不免於憊懶或狐疑。有人說這是「內向世代」的特點,但,毋寧說,更像是「懷疑世代」,往往流連於熱情與空想之間。在這方面,郝譽翔在《逆旅》中,藉描寫女兒與女性對父親、父權充滿「諷喻性」、「抵抗性」的情節,固然表達了她的某種反叛意志,骨子裡卻又透露出若有所失、無可如何的悵惘。
〈搖籃曲〉一文,便探問著:「父親究竟到哪裡去了?」,「父親從來不屬於我們,可是也不屬於別人,他是天生的浪遊者」。一方面調侃父親的「博愛」,一方面卻又期待父愛。終爾,會在某個片刻,把「遛鳥」的變態男誤認為父親,也是因為過於思念父親所致:「於是我刻意要去錯認父親的了,甚至帶著自虐的快意去渲染我的想像力,否則我無法理解他的生命到底與我有何干係……」然而,對這樣具有浪人性格的父親,女兒反而要為唱起搖籃曲(顛倒了唱者與聽者的秩序),藉由文字來為其描摹形象、安魂鎮魄,這就可以看出兼具反諷與悵惘的心情:
請來吧,請來到我的文字中安歇,不要再流浪了,請來到我的臂彎中尋覓憩息的地方,請安心的闔上眼睡吧。
諸如這樣既調侃又似乎理解的描寫,透露著作者複雜的親情態度。〈青春電梯〉裡,對父親奔波兩岸尋找愛的行徑,文中寫到:「從一個將近七十歲老人的口中聽到『愛』這個字眼,真令我詫異」。而向女兒借錢要去中國娶新娘的父親,便恍如「趕著去購買他的愛情,一張通往青春生命的入場券」。
〈晚禱〉裡,則寫著:「我聞到鮮血的味道,從父親的牙齦噴濺開,他說我還不想死呀請救救我,黑色的肉蟲在鼻孔裡爬行,變黃的襯衫扭出一個潮濕的冬季,膝關節貼著大陸買來的膏藥,手裡過著過期的機票,在不甘心的鼠蹊當中卻挺躍出一具年輕的女體」。這哪裡有安息模樣,卻又是另一種形式的親情需要、祝禱。
更勁爆的文字,當然要屬〈情人們〉當中一段關於女兒墮胎情節的描寫。作者描寫手術檯上,父親舔舐陰部的畫面,詭異而近乎荒謬(台灣版「索多碼一百二十日」?),卻又似乎反向地逼問著,當女兒墮胎時,身為醫者的父親是否又在另一個情人懷裡?或正在幫某個女孩墮胎?
我從手術檯上爬起來,撫摸著父親的頭髮,他的頭髮如同嬰孩一般柔軟而金黃。碧綠色的血從我的陰道口流出來,他伸長舌頭舔著,柔軟的舌來回拂拭過我的陰唇。
既審父,又戀父,書中便如此充滿著兩種情感碰撞出來的文字火花。
三、尋找身世與命運解答之書
當然,閱讀《逆旅》絕不可能忽略外省第二代作家寫家族史,這樣的閱讀視角。不過,我們或許可以再加留意,這同時也是一部女性視角的家族史,一部涉及父親流亡與白色恐怖經驗的家族史,一部為被遺忘的山東流亡學校之「澎湖冤案」留下史證的家族史。顯然,某種程度的審父與戀父的情緒依舊蔓延至此,郝譽翔亦悲憫父親及其同時代人的流亡之苦、受難之慘,但也不免要對這樣的身世投之以某種不安、費解的眼光。
值得一提的是,同樣在二○○○年,駱以軍的《月球姓氏》也是一本以家族中父系、母系、妻系的家族故事做為題材的長篇小說,這當然也是一個以「外省第二代」敘事者出發的文本,但目的不是用來「建構」歷史,反而是透過一再質疑小說中的族史敘述而達到「解構」歷史的效果。郝譽翔的處理同樣讓我們見識到,在台灣成長的二世,其實對族群命運仍懷有著複雜難解的情緒,這當然也和台灣特殊的社會氛圍有關,不惟特定族群使然。
開篇的〈取名〉、〈誕生,一九六九〉,這些文字,大抵說明了「郝譽翔」如何自己取名與不合時宜的誕生史,就中已透露出她藉由對自己命運定調,來理解成長中的一切非比尋常。
到了〈冬之旅〉系列小說,才算是對父親身世與流亡經驗的正面描寫,可說是比較具有敘史企圖的作品。像當中「回首」一則所講的:「當許多年過去以後,郝福禎最喜歡對人提起的,還是一九四八到四九,從青島流亡上海、杭州、湖南、廣州直到澎湖、台灣的那一年,一路由北入南,彷彿噴射煙火的嘉年華慶典……」雖則,文學作品總是對父親身世夾雜史實與想像的「創作」;但,何嘗不是如〈搖籃曲〉裡所試圖表達的,讓父親在文字中安歇,永在。這樣,可以稍稍彌補那一段跟父親並存的大歷史,也似乎緩解了浪子父親所帶來傷害感:
一九四九到底是怎樣的一年?他是否來自青島?而他到底怎麼到達台灣的?果然有張敏之校長這個人嗎?他的回憶竟在述說的過程中不斷的自我解構,虛設,朦朧搖擺於話語之中。
《逆旅》處理身世問題,但,除了父系過往,郝譽翔自己也同樣面對尋求生命答案的問題。為何我是父親的女兒?為何那片黃土地與我有關?因而,另一部分相關的描寫,當可注意到書中關於浪遊兩岸、行旅中國的部份。這些旅程,讓書裡的父親、女兒,徹底顯露他們探求生命解答的過程裡,大惑不解或終於放下的心路歷程。
如同〈島與島〉寫到第一次進入山東的感受:「這片貧乏的黃土地除此之外竟完全無法引起你的任何想像,於是你開始感覺到好餓好餓,彷彿呼吸時都氧氣不足……。」這似乎不再是鍾理和的原鄉夢,而是外省第二代的探親之旅,終於必須踏上那塊土地,尋求情感上的彌補或了斷。
在原書初版的「後記」裡,郝譽翔為這本書的「本事」提供了說明,試圖再次印證父親是山東流亡學生與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史實。而她之所以書寫,乃是不願意這段歷史被遺忘:
他們不但被畢生信仰的政權所放逐,又被台灣這塊島嶼所放逐,然後在本土論述越來越強勢的今天,歷史就預備這樣子悄悄地把他們遺忘了。
對此,我倒想起政黨再次輪替後,重新要修改中學課程綱要的大人先生們,當他們提高文言文比例、修改歷史教科書內容的同時,倒是可以去看看,他們又是否在意這些白色恐怖史?固非本土論述特別強勢使然。郝譽翔十年前寫作《逆旅》時,大概不會料想到台灣社會對於歷史記憶,也是這樣一種另類的「逆旅」,每個統治者都要去找回鞏固統治正當性的歷史,於是都在刻意的逆寫歷史、捏塑歷史。
我們該有更多像《逆旅》那樣充滿激情的家族史,但那並不是為了重建君父的城邦,或營壘,而是多族群、多性∕別、多階級的各種民間歷史敘事,甚至是個人的敘事。這將讓我們體認到,身為一個台灣人,真正必須謙卑面對歷史,但也必須包容多樣的歷史。
四、以待來茲:構築一座女性的城邦
我一直不想去界定這部作品的體裁,是小說集?或是小說加散文集?但依書寫的形態言,這些作品應寫於很不同的脈絡下,風格各異,恐非作者刻意結構的一部作品。然而,就如同把這部作品視為自傳、半自傳或全然虛構,這都並非最要緊的問題,重要的是,郝譽翔藉由書寫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時代、世代,也看到個人如何面對親人與成長這件事。
因此,我覺得尚有一個《逆旅》中的閱讀關鍵,無法不提。
父親,當然是書裡的主角,女兒命運的發動者。但母親呢?我認為,書裡對母親的描寫還稍嫌不足;甚且,還未必有足夠的同情。〈情人們〉這篇文章,用女兒與母親的對話,來討論父親的情人們,格外詼諧有趣:「我常懷疑母親可能不是一個女人,她是上帝的惡作劇,在女人的身體裡面錯置男人的靈魂。」而父親愛的可是女人啊!
不過,我當然也好奇,就像剛好也在二○○○年出版《漫遊者》,另一位書寫外省父系史的朱天心,她的筆下鮮少看到台籍母系史的描摹。女性的城邦何在?又是何模樣?郝譽翔的台籍母親,將會被她如何描述?是書裡,那個聯合自己母親(外婆),一起故意講台語排擠外省父親那樣的人嗎?據聞郝譽翔剛剛擁有台灣女兒,未來她若續寫台灣母親,誠然值得期待。
二○一○.十.十三寫於紅毛(新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