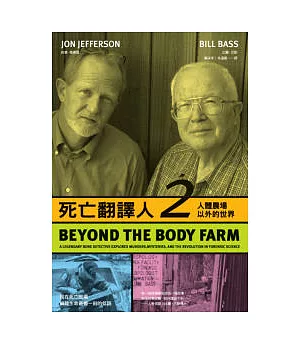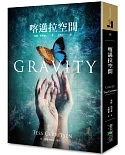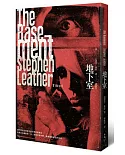前言:法醫科學半世紀的演進與革命
五十一年前一個四月早晨,我在堪薩斯大學骨頭實驗室,正彎腰看一盤骨頭,我的人類學教授查爾斯.斯諾(Charlie Snow)走進來, 問我願不願意陪他去處理一宗人身鑑定案。就在那一刻,斯諾博士改變了我的人生方向,我的事業生涯也從此轉轍。
當時一位律師問斯諾博士,能否從火燒過的遺骸判定死者身分;遺骸在列克星敦城外一輛卡車上發現,燒焦的駕駛室中同時還找到司機的屍體。這輛卡車被越過公路中線的全國連鎖超市A&P的貨車撞上,猛烈撞擊造成兩輛車上三人喪生,卡車司機和乘客(據信是他的同居人)雙雙身亡。斯諾博士告訴律師,當然能,只要能找到司機同居人的牙科病歷,他一定能辨別燒過的遺骸到底是不是她。這可不是毫無根據的吹牛,身為美國陸軍中央鑑識實驗室主任,斯諾博士於二次大戰期間和戰後許多年裡,一直在鑑定腐敗的、破碎的及燒成灰的美國士兵遺體。
他是一專門學問的先驅,這門學科數十年後被稱為「法醫人類學」(forensic
anthropology):利用傳統上著重古老人骨研究的體質人類學知識和技術,協助破解刑事案件,尤其用來辨認凶殺案無名被害人的身分,並判斷他們遇害的經過。即使不能指認被害人姓名──我就有一架子無法指認姓名的骸骨──法醫人類學家仍能幫忙提供警方種種細節,包括被害人的種族、性別、身高、使用左手或右手的習慣(理所當然,慣用右手的人右臂肌肉附著點往往比較粗大),以及遇害方式:被害人是被刺殺、槍擊、勒死、棍棒打死或以其他方式奪命?從留在骨頭上的痕跡都可看出端倪。
斯諾博士邀我陪他去處理這宗改變我一生的鑑識案,原因是我有車,而他沒有,雖然我寧可相信車子不是主要因素,而是他看中我在骨頭辨識上逐漸展露的才華。不管怎麼說,我開車載我們兩人前往埋葬那位死亡乘客的鄉村教堂墓園。裝遺骸的棺材浸滿水,黏答答的,發出惡臭,與我前一天在實驗室研究的那個象牙色光澤的骨頭天差地別。事實上,當棺蓋掀開時,入目景象和氣味太過刺激,我當場吐了出來。
那是五十一年前的往事,此後我處理過數百宗鑑識案。我很高興告訴大家,從那次嘔吐到現在,我不曾在鑑識過程中再吐過。我也很高興告訴大家,在這段歲月裡,法醫科學──用來破解刑案的人類學、昆蟲學、齒科學(牙科)、遺傳學和其他協助逮捕兇手並證明其犯罪的科學──已經突飛猛進,當我在肯塔基州的泥濘墓地,站在斯諾博士身邊彎腰嘔吐時,根本想像不到會有如此的進展。
我並非暗示一九五○年代的法醫科學或法醫科學家是原始或落後的。在肯塔基州受教於斯諾博士之後,我進入賓州大學,投身國際知名的「骨頭偵探」威爾頓.克魯格曼博士(Dr. Wilton
Krogman)門下,攻讀博士學位。沒有人稱克魯格曼為法醫人類學家,這個名稱當時尚未被創造出來,不過我這輩子,無論在認識克魯格曼之前或之後,從未見過任何人比他更擅長在人骨上找線索,更會聆聽死者悄悄訴說祕密,透露他們生前是什麼人,以及如何遇害。克魯格曼專長的特殊領域是兒童骨骼生長與發育,尤其是他們的牙齒。基於這個理由,不管什麼時候,都有數十位齒科學專家在他門下學習。我在賓大那幾年,實際上是他教的唯一一個法醫人類學學生,雖然我沒有接受牙醫或齒科學的正規訓練,但我吸收了有關人類牙齒的豐富知識,尤其學到如何由牙齒辨別凶殺案被害人的年齡和身分。
我在事業生涯中學到的最重要課題之一是,伸張正義要靠團隊努力。任何凶殺案破案過程中,團隊成員可能包括制服警察、便衣刑警、犯罪現場和實驗室技術員、指紋專家、法醫(或可稱為「內科法醫師」)、槍械和彈道鑑定專家、毒物學家、法醫牙科醫師及DNA專家。
不過,從更寬廣的角度來看,法醫團隊工作不只跨越不同科學專業,也含括數十年的研究和創新。我站在克魯格曼博士高大的肩膀上;而克魯格曼自己又站在湯瑪斯.溫格特.陶德(Thomas Wingate
Todd)的肩膀上,後者是克利夫蘭凱斯西儲大學的傳奇解剖學家,這位科學家最先注意到恥骨會隨年齡增長而穩定持續變化,從恥骨變化可以推斷無名骸骨的歲數。其他早年應用考古學和人類學技術提供現代凶殺案偵查線索的巨人,包括史密森學會的體質人類學家艾歷斯.赫爾德利奇卡(Ale? Hrdli?ka)和達爾.史都華(T. Dale
Stewart)。一九三○年代至一九六○年代之間,聯邦調查局先後向赫爾德利奇卡和史都華請益的案件多達數百件,該局剛好坐落在距史密森學會一箭之地。兩人在協助聯邦調查局辦案過程中,像克魯格曼一樣,幫忙界定了法醫人類學的工具、技術和能力。
一九七二年,美國法醫學會體質人類學組召開首次會議;五年後,我們一小撮人創立了美國法醫人類學家協會。在我的事業生涯中,有一度,協會認證的法醫人類學家大約三分之二是我訓練出來的;現在這個比例比以前低,因為我已經退休,而其他教師接棒繼續培養博士。不過,如果仔細看法醫人類學家的「族譜」,我的名字底下掛著令人欣慰的粗大枝椏,並再分支成許多受敬重的名字,這些科學家分布在不同機構,如史密森學會、中央鑑識實驗室、聯邦調查局、喬治亞州調查局、肯塔基州法醫署,以及為數眾多的大學,其中包括(當然!)田納西大學,該校擁有世界數一數二的法醫人類學課程。
田納西大學法醫人類學課程的重點,至少是它最有名的部分,當屬人類學研究場,而它更為人知(有些年輕同事聽了就皺眉的)的名稱是人體農場。經常有人問我如何及為何創設人體農場。我但願我能回答說,因為我那個出色的學術腦袋突然靈光一閃,迸出完全成熟的構想,但真相是,人體農場和許多科學進程一樣,一次跨出一、兩步。從一九六○年到一九七一年,我在勞倫斯的堪薩斯大學教授人類學,在那十一年當中,我有時替堪薩斯執法人員鑑定骨骼殘骸,幫忙對象從地方警局到堪薩斯州調查局(KBI);最後我和哈洛.奈依(Harold
Nye)
成為朋友。奈依在杜魯門.卡波第的經典小說《冷血》描述的真實刑案裡,扮演緝拿殺人兇手的關鍵角色,他後來升任堪薩斯州調查局局長。
一九七一年我搬到諾克斯維爾,接掌田納西大學人類學系。我上任時,對我略有耳聞的田納西州法醫問我,願不願意擔任該州的法醫人類學家,協助執法機構辨認屍體。我答應了,當時我並未料到田納西州的凶殺案被害人與堪薩斯州的凶殺案被害人截然不同。
在堪薩斯州,警方請我幫忙鑑定某人身分時,通常帶來一盒乾燥的骨頭;堪薩斯州地廣人稀,天氣比較乾燥,偶爾骨頭上會附著殘存的一點點木乃伊化的組織,但多半時候我鑑定的案子只剩下骨骼遺骸。反之,田納西州面積只有堪薩斯州一半大,人口卻是它的兩倍,雨量則是好幾倍,被害人屍體往往比較新鮮、比較臭,也比較多蟲,多得數不清,爬滿了蛆──綠頭蒼蠅的幼蟲。當田納西警員或地區檢察官問我這些屍體已經放了多久時,我沒有扎實可靠的科學根據作答。所以,我決定補救自己知識之不足。
田納西大學醫學中心後方有一片幾畝大的荒廢地,林木雜生,中間一塊焦黑空地,醫院在此焚燒垃圾多年。一九八○年間,我在這片荒地鋪起一塊面積十六平方呎的水泥地,四周用鐵絲網圍起來,上面蓋了鐵絲網「屋頂」。我計畫在掠食性動物進不去(除非牠小得能夠鑽過鐵絲網孔)的圍欄裡面擺置人類屍體,供我的研究生和我密切觀察,記錄在長期死後間隔(extended postmortem
interval)期間人體腐敗的順序和時間。
一九八一年五月,我們收到第一具供研究用的捐贈遺體。為了不讓捐贈者身分曝光,我制定一套編號系統,研究報告上只提人體號碼,不寫姓名。第一具人體在一九八一年取得,因此編號是1-81;不久2-81、3-81和4-81接踵而來。一九八二年,編號順序由1-82開始,然後是2-82,以此類推。(法醫案件編號系統與捐贈遺體編號系統類似,只是年份寫在前面,故一九八一年我們處理的第一件法醫案件編號是81-1。)
起初遺體捐贈來得緩慢,因此我們非常依賴州內各地法醫提供無人認領的屍體。最初幾年,編號甚至超不出個位數;不過,現在很多人知道我們的研究,願意給予支持,因此每年的編號已經邁入三位數──遠超過一百具屍體,而捐贈遺體超出無名屍的差幅愈來愈大。公眾之所以對我們的研究日益好奇,一個早期和影響深遠的因素是派翠西亞.康薇爾的小說《人體農場》,這本書於一九九四年秋天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
事實上「人體農場」的綽號並非康薇爾所創(就我們了解,這個不知算不算榮耀的命名功勞屬於一位名叫伊凡.傅特瑞爾的聯邦調查局指紋專家),但她確實打響了我們的知名度。自從她的書讓我們聲名大噪以來,這些年人體農場已被拍成許多電視紀錄片,登在報紙和雜誌文章上,也被廣播電台報導過,過去兩年還成為一系列暢銷犯罪小說「巴斯犯罪鑑識小說系列」的主題,那是約拿.傑佛遜和我用筆名「傑佛遜.巴斯」合著的。小說情節和許多角色純屬虛構,但科學部分有憑有據,基於二十幾年來人類學研究場的豐富實驗。隨著人體農場的名聲愈來愈響亮,它的規模也愈來愈大;此刻它包含二、三英畝林地,用高大的木籬笆圍起來。但近年捐贈遺體大幅增加,這塊地根本不夠大。幸好田納西大學已表示願意擴大研究場,再增加十一英畝地。不過,如果業務繼續以當前速度增長的話,幾年內新增的面積又會不敷使用。這些日子,人們真的是死要進入人體農場……
不出意外地,一九八○年代初期當我們展開研究計畫時,實驗目的只是想回答一些最基本的問題:手臂多久才會脫落?顱骨什麼時候開始外露?在什麼時間點人體會腐敗至只剩枯骨?不必多高竿的科學家也知道,腐敗過程在夏天比冬天快得多。然而過不了多久,研究計畫就變得更高深複雜了,我們發展出死後腐敗時間表和數學公式,一旦取得屍體發現前數日或數週的氣溫紀錄,就可以據此估計死者已經死亡多久,而且出奇準確。我們從實驗得知,關鍵在於「日均溫累積值」(accumulated-degree-days),簡稱積溫值(ADD),也就是每天平均氣溫的總和。例如,一具屍體在最炎熱的夏天放進人體農場,每天氣溫平均熱到華氏八十度,經過十天,這具屍體的日均溫累積值將是八百度,早已邁入化成骨骼的階段。在酷寒的冬天,連續十天每天溫度都是冷得刺骨的華氏三十度,屍體的日均溫累積值只有三百度,幾乎才剛開始因內部腐敗產生氣體而膨脹。利用積溫值標出分解進程最妙的地方是,資料可以用在世界任何地方:不管哪裡的屍體,在大約一千二百五十到一千三百積溫值之間,都會分解得只剩光禿禿的骨頭,或骨頭上覆蓋著木乃伊化的乾縮組織。
此外還有昆蟲研究。那是我們最早期的研究計畫之一,一九八一年間由我的研究所學生比爾.羅德里格茲(Bill
Rodriguez)負責,記錄眾多到屍體來進食的昆蟲種類:來了哪種昆蟲,何時出現,停留多久。比爾高踞屍體旁邊,一坐就是幾個鐘頭,還要忙著驅趕企圖在他鼻孔和嘴巴下蛋的蒼蠅,他替一門新的專業領域奠定了基礎,這個領域迅速成為法醫昆蟲學。如今,部分由於比爾在人體農場開疆闢土的昆蟲研究,世界各地的犯罪現場技術員都知道要蒐集凶殺案被害人身上的昆蟲標本,交給昆蟲學家研判這些蟲子已在屍身進食多久。自從比爾首開先河的昆蟲研究以來,已有無數昆蟲學家來過人體農場,因為這裡是舉世獨一無二的研究設施,任何時候都擺著數十具人類屍體,處於不同的腐化階段,有新近死亡的,有完全骨骼化的,還有介於兩者之間的各種情形,供觀察研究之用,對昆蟲和對科學家一樣來者不拒。
昆蟲學家不是唯一依賴人體農場提供獨特研究機會的科學家。我以前的研究生之一,目前是橡樹嶺國家實驗室研究員的阿帕德.瓦斯博士(Dr. Arpad
Vass),花了過去幾年時間採樣屍體腐化釋放出的氣體,並進行化學分析。截至目前為止,阿帕德已經辨認出四百五十多種不同的氣體成分;由於確切知道這些化學物質是什麼,阿帕德研發出一款「機械鼻」,他可以用程式操控這個儀器去嗅出祕密藏屍地點,就像搜索犬可以訓練來找屍體一樣。阿帕德也利用「死後法醫化學」──姑且以此彆扭的名詞稱之──來判斷死後間隔時間:經由分析死亡的化學作用及腐爛產生的化學物質,並研究屍體腐爛過程中各種化學物質的比例變化(就像昆蟲學家研究昆蟲來來去去的換班行列),阿帕德能夠找出化學作用與時間的關聯,像看時鐘一般,由腐物讀出屍體已死亡多少個鐘頭或多少天或多少週。他也著手研究屍體為什麼會釋放能量場(energy
field);他的假設是,分解的化學反應實際上將屍體變成一個巨大的生化電池;如果這個假設證明為真,則意味代言「勁量」電池的活力兔即使已經死翹翹,可能還保有一些電壓。
關於田納西大學的法醫課程,大多數人不了解的是,當一具屍體在人體農場完全變成骨骼之日,才是它的所謂科學生命開始之時。事實上當世人填表同意捐贈遺體給人體農場──現在已有超過一千人填了表──他們同意捐贈的其實是骸骨;肌肉只是包裝骸骨送來,可被生物分解的材料。在內伊蘭球場下方上鎖的房間裡,一層層迅速擴充的架子上,田納西大學建立了當今規模最大的知名骸骨收藏(亦即已知身分、年齡、性別、身高和種族的骸骨),不僅在美國最大,可能在全世界也是首屈一指。
到了二○○七年中,所謂的威廉.巴斯捐贈藏品包括近七百個標本,而且平均每三天再增加一具骸骨。這些標本是訓練人類學家和法醫科學家的可觀資源(除了本系學生外,透過全國法醫學會,人類學系每年還協助訓練數百名犯罪現場與刑事犯罪實驗室技術員)。這些骨骼也是提供資料給法醫人類學資料庫(Forensic Anthropology Data
Bank)的金礦,該資料庫儲存了世界各地人種的詳細骨骼尺寸,使得法醫科學家碰到無名骸骨時,更易判斷骨頭所屬的種族和族群,知道是歐洲人、美國原住民、非裔美國人、沙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人、太平洋島民、澳洲原住民、中國人,或資料庫包含的數十種任何其他族群。
捐贈骸骨也構成鑑識判別函數分析程式(ForDisc)的骨幹,此一功能強大的電腦程式是我的同事,也是我過去的學生李查.簡茲博士(Dr. Richard
Jantz)在田納西大學開發的,只要根據幾個簡單的骨骼測量尺寸,就可以判斷無名骸骨的性別、身高和種族。(ForDisc在第九章〈聆聽蟲子〉詳述的案件中扮演關鍵角色。)二○○六年到二○○七年間,每具捐贈收藏的骸骨都做了斷層掃描。我期盼在未來幾年,這些掃描資料能用在各式各樣有趣的研究與應用法醫科學上,例如聯邦調查局實驗中的顏面重建軟體ReFace(詳情見第十四章〈李歐瑪.派特森案之二〉)。
法醫科學近幾十年最戲劇化也最具革命性的進展之一是DNA鑑定問世。雖然DNA鑑定不是魔杖──如李歐瑪.派特森案痛苦地顯示──但它仍是石破天驚的突破。DNA研究不再限於遺傳學範疇;人類學領域目前興起一門新學科,叫做「分子人類學」(molecular anthropology)。田納西大學人類學系師資陣容現在加入一位才華洋溢的年輕分子人類學家葛瑞茜耶拉.卡芭納博士(Dr.
Graciela Cabana),毫無疑問,經由在人體農場的研究,她一定會找到迷人的途徑拓展她的專長領域。
有一項研究人體農場大概永遠不會去做,那就是寫書對人體健康的影響,至少是我的身體健康。二○○二年,我開始寫回憶錄《死亡翻譯人》(Death’s
Acre)之初,有天我的心臟停止跳動,幾乎死亡。而後,就在這本書快完成之際,我的心臟科醫生通知我,二○○二年與死神擦身而過之後植入的心律調節器即將壽終正寢,必須馬上更換。我於週三早晨進入手術房,當天中午就回家了。第二天,我感覺很好,好到可以帶愛犬小崔去做每天下午的例行散步,開刀後甫過二週,我已能開車去納許維爾,對一群醫療專業人員發表兩小時演講。表面上我已正式退休多年,事實上有些星期我仍然工作四、五十個小時,不過是出於自願,而非為了生計。偶爾忙到後來我會希望自己更常推辭工作,但多數時候我欣然接受,因為我愛演講,也喜歡接受有趣的法醫案件諮詢。例如,過不久,我應該會去協助一組法醫科學家開棺檢驗赫赫有名的魔術師哈利.胡迪尼(Harry
Houdini)的屍骸,他死於一九二六年萬聖節,據說死於盲腸破裂,但八十年來謠言不斷,有說他曾接到死亡威脅,也有說他被下毒,疑雲重重,像魔術師變的戲法一樣,遮蔽了真相。
胡迪尼可以說是世界最偉大的脫逃藝術家,但到頭來,他還是逃不過死神的魔掌。我們無一人逃得過,但在科技和醫療的魔法下,有些人能夠大大延長在人生舞台的表演年限。我很幸運,心臟科學像法醫科學一樣,在我成年後突飛猛進。
然而,人類心臟一如人類心智,依舊神祕莫測,有時還悲慘地帶有缺陷,如永遠戒不掉的嗜殺傾向,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注意。能夠幫忙解決其中一些凶殺案,同時──多虧研究生和教職員在人體農場的多年鑽研──提供科學工具協助其他法醫科學家破案,是我的天職,也是我的殊榮。我從未想過藉人體農場闖出什麼名號,我只是比其他人先跨出科學研究的一步,期能解答凶殺案調查過程或課堂討論中引發的問題。但這些研究步伐逐漸引導我和我的同仁及學生步上奇妙的旅程。
接下來的章節裡,你將讀到我們在人體農場學得的一切如何協助我們辨認死者,釐清他們的遭遇,在許多案件中(可惜不是所有案件)將兇手繩之以法。但真正的突破,如我在維吉尼亞理工學院的槍擊慘案之後領悟的,仍然難以企及。當我們不只學會破解更多凶殺案,而且學會防止更多凶殺案時,真正的突破才會到來。
直到那一天來臨,我們在深鎖大門和木頭圍籬後面不怎麼象牙塔的研究,將繼續提供調查人員更多和更好的工具,破解真實世界──人體農場以外的世界──發生的犯罪案件。
比爾.巴斯博士 諾克斯維爾,田納西州 二○○七年六月
推薦序一
半世紀法醫鑑識科學進步的見證人
實務經驗豐富的知名法醫人類學家比爾.巴斯博士,從五十多年前投入法醫鑑識工作以來,熱情始終不減,即便已經退休,仍不時四處奔波親赴案件現場,提供鑑識人員意見,或是演講著述把法醫人類學的重要性、豐富性傳遞給社會大眾。而從回憶錄《死亡翻譯人》以來一直與巴斯博士合作的約拿.傑佛遜先生,顯然也被博士的熱情感染,陸續參與在鑑識案件的現場裡。本書是他們二位再度合作,將法醫人類學半世紀以來的發展、演變、進步,以平易活潑的文字完整呈現在讀者面前。
我與巴斯博士相識從與他是工作、專業上的往來,到建立起深厚的友誼,至今也有三、四十年了。他豐沛的生命力不但展現在工作成就上,也吸引號召許多年輕學子加入法醫人類學的行列,甚至他推動成立的「人體農場」——田納西大學人體實驗場,更是啟發了小說戲劇,引起一片大眾文化熱潮。
從上一個世紀以來,法醫鑑識科學的發展達到了前所未見的高度,許多學科、技術、人才的陸續加入,啟發並拓展了原有的概念與觀點,而愈來愈多樣的、高價的設備也運用在其中,成為許多犯罪案件破案的指引。然而在本書中,巴斯博士提醒了我們「伸張正義要靠團隊努力」、「團隊工作不只跨越不同科學專業,也涵括數十年的研究和創新」,這一番見解實在是站上高處,心懷謙卑的風範。
在書中提及的十三個案例(十六個章節,但有兩個案例占了不只一章的篇幅),有些未必是刑案,但是不論是否攸關司法正義,巴斯博士都秉持追求真理、真相的心態,提供協助,為警方、家屬與相關人(例如書中第七章的保險公司)做出詳盡仔細的回答,這份用心與敬業顯露出巴斯博士在專業技術之外的專業心態,也是可以作為法醫鑑識工作人員的榜樣。
作為巴斯博士的好友與同為鑑識科學人士的一員,我樂見本書的中文版出版,深盼此書不僅為有心參與從事司法工作、加入鑑識科學行列的讀者,帶來許多啟發,更期盼因著這樣對鑑識工作充滿幽默風趣、深刻感性的描寫而能引起更多迴響,讓社會大眾對於鑑識工作有更豐富、完整的認識與肯定。
──李昌鈺
西元二○一○年九月廿日於美國
李昌鈺
國際刑事鑑識專家、美國紐海芬大學首席教授、康乃狄克州警政廳榮譽廳長暨警政刑事科學中心主任、國家現場鑑識培訓中心主任
推薦序二
轉錄遺體故事的法醫檔案簿
每具遺體都有一個故事,它只存在於法醫的檔案簿裡。
當遺體默默訴說自己的故事時,是用何種語言將事實揭露?作為死亡翻譯者的法醫如何探究死亡前一刻、一瞬間所發生的事?如何重返犯罪現場,讓大家知道躺在那?、不會說謊的傢伙是誰 ,以何種方式步入死亡,死亡原因到底是什麼。
從骨骼到牙齒
一百多年前,人類學家將人區分為三大人種──高加索種(具代表性的是歐洲白人)、尼格羅種(非洲黑人)、蒙古種(亞洲人)。撇開種族歧視的議題不談,種族不僅是一種文化、社會架構、更是一種生物特徵。不同種族的骨骼,尤其是顱骨,具有明顯的差異。這在號稱民族大熔爐的美國頗有意義。骨骼除了區分人種,對於性別、年齡的判定幫助亦很大,可將失蹤人口的搜尋限縮到比較小的範圍。骨骼創傷則記錄了凶器的種類或性狀,遭受攻擊的方式,死亡的原因。也捕捉到加害者的蛛絲馬跡,甚至顯示出生前的活動。
牙齒是另一個有力工具。沒有任何兩個人的牙齒狀況能一模一樣。身分鑑定主要依賴法醫牙科學(forensic
dentistry),因為牙齒是全身最堅硬、最不會腐壞的部分,容易保存;且牙齒的型態、大小、方向、排列等人人各異。齒列異常情形(包括缺牙、齲齒、殘根)、補綴狀況(假牙、補牙、其他治療)也都有各人獨特之處。即使兩個無牙的人,齒槽骨的型態亦絕對不同。同卵雙生的兩人DNA一模一樣,就只能靠牙齒來區別。另外具標誌意義的上顎正中門牙,切面若呈內凹的鏟子狀,屬於亞裔的機率很高。鏟型門牙是蒙古種的特有體徵。
在大規模災難中,牙齒鑑定常常能有效且最迅速的確認罹難者身分。
DNA鑑定
近幾十年來最革命性的變化就是DNA鑑定。這種技術能精確描繪任何人的基因圖,用以和任何關鍵證據作比對。一點點微物跡證都可能取得DNA ─ 如骨骼、牙齒、皮屑、毛髮、血液、唾液、精液……可說DNA無所不在。
雖然DNA鑑定並非毫無缺點──費時較久且價格較貴、樣本易受汙染,但無疑的,DNA仍是近代鑑識科學強而有力的工具。
人體農場
面對死後腐壞程度不同的遺體,若無充分的證據,實在很難推定死亡時間。三十多年前巴斯博士利用任教的田納西州立大學廢地,擺置遺體,長期觀察並記錄遺體的分解變化。經數十年研究,發展出日均溫累積值(簡稱積溫值,ADD),即每日氣溫平均的總合和分解狀況的關聯。更棒的是,這資料可用於世界各地,放諸四海而皆準。巴斯博士的昆蟲研究記錄了形形色色到人體「進食」的昆蟲──何時來、何種昆蟲、產下的卵孵化至何階段,作為時間參考。還有專家經由分析遺體的化學作用的各種產物,找出化學物質與時間的變化關係。
人骨偵探軟體ForDisc
田納西州立大學著名的「法醫人類學資料庫」儲存世界各地人種的骨骼詳細資料,並研發出鑑識判別函數分析程式(簡稱ForDisc),只要測量無名屍頦骨的大小,鍵入電腦,就能判斷該人的種族、性別、身高。愈來愈快的,無名屍找到自己的名字。
巴斯博士藉由本書的十三樁案例,把法醫人類學的樣貌具體而完整地展現在讀者面前。如同著名影集「CSI犯罪調查」一般,教育大眾對犯罪現場小心維護,謹慎尋找蛛絲馬跡,保存證據的重要性。也喚起人們的熱情,吸引許多年輕人投入鑑識科學的研究領域。不論科學怎麼進步,人,永遠是最重要的;沒有人才的投入,我們依舊享受不到科學的甜美果實。
托爾斯泰的短篇小說「上帝知道一切的等待吧」敘述一個商人含冤入獄,流放到西伯利亞,最終死於獄中。雖然他知道兇手是誰,卻無法指認,無數次,只能仰頭問:「上帝,?在哪裡?」。今天,我們能夠呼喊:「法醫,你(妳)在哪裡?」,期待減少人世間的無可奈何。
謹向默默捍衛無數悲慘罹難者的法醫致上最大敬意。
──石台平
西元二○一○年九月六日於台中
(楊婷鈞同學、黃惠娟醫師記述)
石台平
前刑事局法醫室主任,現為戴德法醫事務所負責人,曾參與多起重大刑事案件鑑識以及大型災難人身鑑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