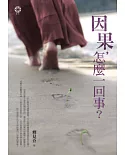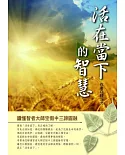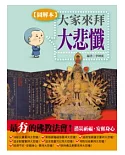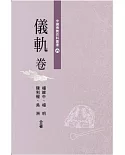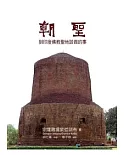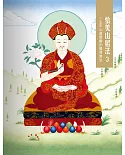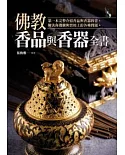作者序
我寫物語的話
……記得那是在一九四六年的春天,我無意中用物語的口氣寫過一篇〈鈔票的話〉刊登在鎮江《新江蘇報》的副刊上,大概因為文學的意義是在表情達意,而這樣寫法,更能夠生動的把情意表達出來,因此,我起初雖沒有受誰的啟示,但我覺得這樣寫法沒有錯。
這裡所收集的二十篇「物語」,都曾在雜誌上發表過的,發表過了本來不一定急急的出什麼集子,但是,說來真非常令人感動:當我「物語」還只寫到第十四篇的時候,喜事天上來,我最敬仰的慈航老人托人帶了一筆款子給我,記得老人信上這樣向我說:「你的『物語』還要繼續寫嗎?我先送給你一些錢把它趕快出版吧!」
像我這樣兩袖清風的一個青年僧,在這樣的年頭,從來就不敢打什麼出書的妄想,然而這位老人家的慈悲,他能關心到這些微末的地方,叫我又怎麼能辜負這位老人的一片好意呢?所以我在出版了《普門品講話》之後,還能有這本小書和讀者見面。……
我回憶起當初開始寫第一篇物語,是我正給一位老和尚叫我替他看守山林的時候,出家人不能離開了生活中食住的需要,在這種流浪逃亡的日子中,我不得不向生活低頭,為了一宿三餐,我就開始廉價的出售青春與勞力。
我那時,每天山上山下,出沒在森林中,像一個獵者,時時注意山中的動靜。獵者的對象是獐貓鹿兔,我的責任則是注意偷伐樹木的歹人。這些工作,在佛教中除了換取一句虛而不實的讚譽「發心」之外,沒有別的報酬。這樣,日復一日,我開始為不停留的時光與逝去的年華感到恐慌!那一個青年的生命裡不充滿了光熱?那一個青年對未來沒有美麗的希望?我想到我不能讓寶貴的青春與生命無謂的虛度,我該在人生的旅途上留下一點痕跡,因此,我就在那只能容身一人的草棚中,覆在亂草堆旁寫成第一篇物語──大鐘。
我在寫「物語」的期中,當然收到過不少令人興奮的鼓勵,但也聽到過善意的批評。當我寫到物語之八〈香爐〉的時候,內中有所謂十大願文,因此,反對的聲浪,就從那些我所斥為頑固偽裝的人群裡向我打來。
他們說:學佛的人不該咒詛人死,甚至有人說物語都是寫的佛教中的內幕,不應該給教外的人知道。我對於「學佛的人不應該咒詛人死」這句話,在某一方面當然我是不否認這句話是對的,好像那些修阿羅漢果的人,即使有人用刀來殺他,他除了引頸就戮以外,決不願還手。但如果以整個眾生幸福為對象的大乘菩薩,他也許親自拿起刀來去殺死幾個魔鬼,讓大眾和靜安寧的生活下去,這本不可用一面的眼光來相看的。而且,「物語」的體裁不是那些板起面孔來說教的八股文章,也可以說它是文藝的創作。文藝的意義是反映現實,對善的加以歌頌、播揚;對惡的施以指摘、咒詛。
一個對文學有愛好的人,先天注定他是一個必然的獨立人物,他必須用他獨立的頭腦來思考,他必需用他獨立的眼睛來觀察,他必須用他獨立的心靈來感應!不然的話,他不是鸚鵡,就是一架留聲機!文學不是那一個人要說的話,而是大家要說的話。我們即使說:站在宗教的立場,擺出道學的態度,還是說些和善的話好;但佛教中,除了那些麻木不仁的教徒以外,凡是一個關心佛教,對佛教具有抱負和熱忱的人,那一個沒有這種心理?文藝的價值就是敢於刻劃大眾想要說的話,而不是阻礙佛教的新生。還希望佛教長老不要多心才好。我雖造了口業,咒詛人死,將來即使我如何不幸,只要佛教真能中興,我也是甘願遭受這個果報的。
同樣的話,在別人能有不同的看法,當我又聽到說有一位法師在開大座講經的時候,把這十大願特別提出來講解說明,並致讚揚,說這是充份的洋溢了愛教的熱情,我知道這佛教中真正的大德長者,畢竟還是多的。……
其次,有人說「物語」的內容是佛教的內幕,不應該公諸於外人,這些話也很令我大惑不解。佛教又不是政治,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內幕,真正的佛教,唯恐別人不知道,知道倒也好辦了。在我寫「物語」的初願,只想把什麼是佛教,什麼不是佛教分辨清楚。因為正與邪、好與壞、是與非,現在佛教再也不能不把它算清楚了。
我在寫「物語」的期中,很多人以為我和他故意為難,化緣的人以為我寫〈緣簿的話〉是對付他的,做經懺的師父也以為我很多話是和他們為難。關於這一點,我不能不說這些人太過敏了。
在「物語」中,我不會把那一個人的話,那一個人的事,寫進我的文章裡來;不過,在我的文章中,所敘的一些事、一些話,的確是有人這樣做和這樣說啊!
化緣為大眾做福利事業不是不好,而是化緣完全為個人的福樂打算,總嫌太自私了;做經懺也不是不能做,而是不依法做實在有失佛教的面子。佛教到了今天,這些問題應該到了攤牌的階段。佛教的事業,大家借著佛教的招牌,當作自己謀取生活的道路,「寄佛偷生」,「販賣如來」,說來是夠傷心的!
我寫「物語」的本懷,就是希望我們佛教徒革除這些陋習,不過,我知道這是我太大的奢望了。不過,據我所知,確有不少人看了「物語」而認識了很多的是與非。看了「物語」而認識佛教、同情佛教,甚至信仰了佛教。
現在「物語」定名為《無聲息的歌唱》出版了,略說一點因緣如上。佛教裡常見到的東西本來不止這二十個名目,等到將來有時間,還想再補寫十篇或二十篇。我要想把整個的佛教,用很少的文字,替它留下一個縮影,這樣是否得當,還希望讀者給我指教!
星雲 一九五三年六月台北
編者序
一甲子善美的因緣
《無聲息的歌唱》是星雲大師一甲子前曾印行過的小冊子,把佛教裡二十種常見的法物器具,用散文的體裁和各物自語的口氣寫出,寓褒貶,別善惡,於微言中見大義,於法語中見本懷,為佛教利益人間的精神留下一個縮影。
這本小冊子是大師二十三歲在法雲寺看守山林時,在山上「小小」的草寮裡,伏在冰冷的地上,一字一句寫下的。最初陸續在雜誌上發表,當時還沒有全部寫完時,慈航法師便託人帶來一筆錢,催促著大師要趕快出版。出版後很受歡迎,曾經有一位王鄭法蓮老太太,憑著一股信佛虔心,拿了大師所撰寫的《無聲息的歌唱》沿門兜售,竟然賣出了兩千本,可說是台灣佛教最早的現代文學作品。
《無聲息的歌唱》是一本有別於其他佛教的書籍,以「擬人化」的體裁反映現實,而不是板起面孔來說教。在台灣當時佛道不分,缺乏佛教正信的四○年代,大師一心只想把什麼是佛教,什麼不是佛教分辨清楚,希望更多人認識佛教,並逐步改革舊有佛教的陋習,讓佛教走上年輕化、現代化、人間化、國際化,許多熱情青年因讀了這本書而生發信心,信仰佛教,甚而出家,一起加入弘法的行列。
經過半世紀以來的歷史歲月洗禮之後,香海文化為了能接引舊雨新知,且在現今動盪的社會裡,讓更多人親炙佛法,了解佛理,在重新出版時,特別為每一種法器拍攝照片,或特寫,或人文情境照,期待這本文圖並茂、富含文學之美的佛教法器工具書,幫助大眾體解無言的法器,卻能透出無量的佛法意涵,體會自然界中觸目所及,一切皆是無聲的法義禪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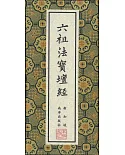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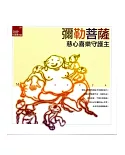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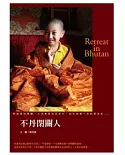
![普濟幽冥 瑜伽焰口施食8U15[新版]](https://www.books.com.tw/image/getImage?i=https%3A%2F%2Fwww.books.com.tw%2Fimg%2F001%2F056%2F63%2F0010566322.jpg&width=125&height=155)